网友评论()2016.05.10 第266期 作者:萧轶
导语:“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近日,贾平凹就新作《极花》接受北青报采访时,说出的这段话被断章取义地传播,引起了轩然大波。有女权主义者回应称:“如果被拐来做媳妇的女人是贾平凹的女儿,他还会这么说吗?”评论人萧轶认为,在这个女权主义强势崛起的大陆上,表面叙述妇女被拐卖而实际呼吁关注农村的《极花》,很容易因为哀婉农村而落下嫌疑,也注定着贾平凹要被绑架上时代的审判席。
回顾我们时代的城乡叙事,就是一部与狼共舞的城市化进行曲。一直宣称乡土文学并未退场、质疑着城市化的正义性的贾平凹,无论是《秦腔》借助“反现代”的现代性所建构的乡村文化的伦理认同,还是最近《极花》里串联起城乡的伤痛救赎,似乎都必然在这个“城市信仰”的时代遭遇城乡叙事的围剿与谩骂。令人遗憾的是,女权主义者们只看到了女性的命运,而不去批判造成千万此种命运的无形之手。

城乡结构的历史谱系
马克斯·韦伯曾对东西方城市进行过对比,在他看来,以欧洲城市为代表的西方城市是商贸发展和自治传统的历史产物,以中国城市为代表的东方城市,是作为帝国中央行政管理分支机构而存在的,其首要意义在于城市的政治性。自大秦帝国一统天下,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度形成了“首都—郡城—县城”的城市行政等级体系,尽管唐宋存在过商贸市镇,但政治行政功能依旧是城市地理发展的首要基础;即使在开放的民国,诸如婺源在江西与安徽之间的规来划去依旧体现着地理空间的政治性;此后,国共两党为增强对乡村社会的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逐步摧毁了乡村社会结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梁漱溟、费孝通为代表的“乡土派”与以吴景超为代表的“都市派”之间的争论,正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城乡问题的思考节点,由此产生了“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之间的现代叙事。
1949年到1954年,则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大区制。“大饥荒”摧毁了大区制,但中央重组了六大中央局重新调配区域,这就让诸如北上广沈渝等地因不同的政治需求,而形成了工业中心、经济中心和交通中心等非均衡发展。改革开放后的地方革新,则向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学习,构建了以城市为主体的地方治理结构。在现代化道路上,最初出现的是国家决策的“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后又添加了由知识界面对世界潮流而提出的“政治现代化”,一时称为“五个现代化”。
在全球化的裹挟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下,被重新构建的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现代化,不仅使得“政治现代化”成为语言死亡事件,还让本就名存实亡的“农村现代化”变成了“城镇化”。进入21世纪的门槛后,建设口号再度更改为“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村城市化”,最终定型为我们时代的城市化,将农民赶进城。户口迁移后就再也无法回归农村户口,是我们时代城市化精神内核的最佳体现。这也导致了城乡关系由城乡互哺到城乡融合,最终走向了城乡二元化。而我们所要谈论的城乡叙事变迁,背后就是“乡土中国”开始从城乡一体转向了城乡脱离,城民与乡民之间逐步固化成新的阶级对立:主与奴的阶级对立逐步迈向了城与乡的阶级对立。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叙事逐步形成了“城市信仰”的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赐予了国家强力推进城市化的永恒正义。乡土文学的叙事方式和对乡村生活的评议判断,在构建城市化的正义性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甚至如同背靠利维坦高歌城市化的进行曲。

延安文艺座谈会
乡土文学的历史谱系
从乡土文学的奠基者鲁迅到乡土文学的理论家周作人,再加上民国时期的京派小说、革命恋爱乡土文学、茅盾为主的剖析派和七月派乡土文学,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充满着政治意义的话语表达,为了宣传某种政治理念而写作出了大量的乡土文学。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解放区”乡土文学更具政治性,从而建构了1949年后文学创作的话语体系。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则跨越了两个时代,赵树理更是成为新中国乡土文学的奠基人,而停留在审美维度的孙犁派在接下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下不得不自我投降,黯然退出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政治意识形态指示,让乡土文学变成了国家歌唱的“星光大道”;直到文革结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忆苦思甜,形成了“乡土伤痕小说”群体;改革开放后,伤痕小说分化为评析往昔岁月的知青小说体和追问现实的乡土反思体,从而发端了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和悲剧生活的农村叙事综合为一体的寻根文学;随着市场经济的勇猛大潮,乡土文学被冲击地体无完肤,逐步进入了新世纪的无序状态或曰多元格局,政治先锋似的乡土文学终于走向了式微的坡坎。乡土文学的式微之路,映照着乡土文明的逐渐崩溃,新的时代议题被抬出来了,新的书写内容也随之而来。
尽管新世纪文学被其他流派所取代,但乡土文学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步异化为城乡叙事的新型题材,既有乡土的气息,也有城市的灯光。在“城乡一体”走向“城乡脱离”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社会不再是市民与农民的二元结构,而是演变成市民、农民和进城农民的“三元结构”。在1984年,被催逼进城的农民终于被赐予了新的社会身份:他们摆脱了农民的身份,也没摆脱农民的身份,尴尬地被冠以“农民工”的名号,一种携带歧视意义的半军事化身份。正是新型城市结构的出现,让乡土文学寻找到了回光返照的书写内容。由于“农民工”的生存现实,让他们既不能回到乡村去,也无法留在城市里,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新型城乡叙事文学。在文学想象中,“城市脱离”的社会现状获取了城乡叙事的存在方式。

城市信仰的正义建构
新世纪的城乡叙事,主要有三大阵营:以返乡笔记为主体的乡愁大军,以训教规训为主体的教化绅士,以及建言献策为主体的三农专家。由于国家抛弃了农业现代化道路,进而抛弃城镇化口号,千年以来的农耕文明被连根拔起,农民被催逼着背井离乡,从传统观念到乡土实体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根本性摧毁。这三大阵营在“含泪劝告”的审美疲劳和信心打击下,逐步构成了城市化进行曲的合唱团。现代工业文明搅乱了城乡的分野界限,作家们反刃劈向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左手描述着乡村的现实,右手书写着乡村的疮痍。“乡愁”这个充满诗意的哲学词汇,在无形之中承担了城市化现代性危机的焦虑转移,从文化想象上塑造国家政策的认同功能。农民的身份从“乡下人”到“农民工”的转换过程中,沈从文构建的“乡下人”神话叙事被现实击碎,新时代的“农民工”也被城乡叙事所诟病,甚至权力还利用《打工》等类型杂志收编了“农民作家”的话语精神和表达方式。
在对城乡叙事文学创作的评议判断上,评论家们也因发展主义的“城市信仰”和国家旋律的意识形态所催眠,构建了超越左右、弱强的现实分野,达成了“世界大同”般的社会共识。从科学角度上,城市被理解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从社会符号上,城市文化意味着先进美好;从社会角度上,城市化运动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进步形态……最终,“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诗性口号成为了黑格尔意义上的“绝对精神”和“永恒正义”。新世纪城乡叙事三大主力,从不同程度上将城市文明渗透到乡村社会,城市的价值体系逐步取代乡土观念,既定观念的城市思维成为时代的主流。现代化历史观的叙事结构,将社会进程阐释为从传统到现代、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落后到先进、封闭到开放的城市化进程,城乡叙事三大主力军与国家信念汇合成“城市中国”的新时代信仰。在这个观念异化过程中,城市化被简单地理解为经济进步与人口迁徙,抛弃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方式,更抛弃了“进城的乡下人”向城市居民过渡中他们必须经历的“城市意识”:如何从被排斥到被接纳的深层经验,更抛弃了致使农村现状的始作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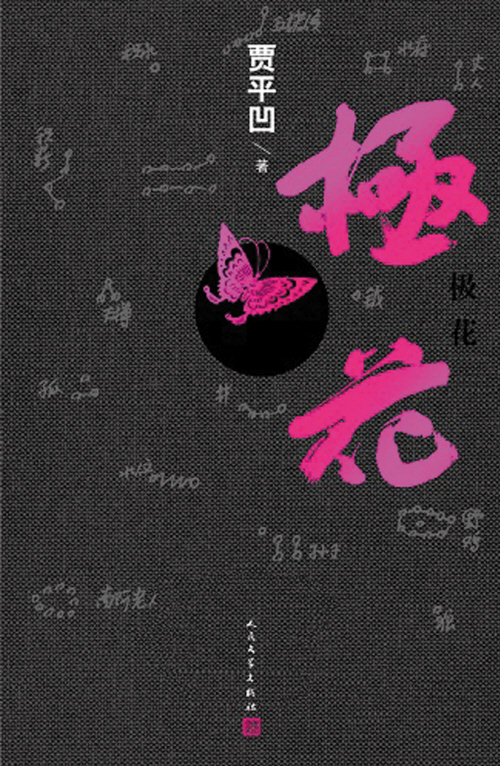
贾平凹“必须”坐在审判席上
然而,我们发现,无论是浪漫肉麻的乡愁叙事,还是训诫教化的规训态度,抑或热忱劝告乡村追求现代化生活的建言献策,话语战争的农村对象化,时刻都是城市书写的畸形投射和工业朋克的娇嗔作态: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病入膏肓等陈词滥调,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对乡村的书写之中。这种言辞的背后,正是话语权所有者自以为是的理性思维让自己陷入了当代语言生产机制,成为社会既成观念的背书者。在谈论乡村时,往往是在乡村人缺席的状态下。这种不对等的话语杀伐,给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在成功逃离后返乡的乡愁大军们或养尊处优的城市教化绅士们的大合唱下,因为真正乡村人的话语缺席,让他们越发自负地信任自己对强加给乡村的既定观念背书行为。
而这种城乡脱离而催生的对立思维,并非萌芽于新世纪,从古代的“进城”、“上街”到1949年后的“上山下乡”等词汇上,再到80年代“新时期”文学以褒扬城市化和拒斥乡土的改革情感,随着城乡脱离的进程而越发显得对立。古代城乡并不明显,下乡改造则直接宣布了农村的低劣,虽然八九十年代文学也逼问现实、触摸人性和困惑挣扎,但最终在与国家信念的握手言和下,将城乡书写变得对立起来。而书写者往往是城市人,对于乡下人的内心困境无从认知,导致了书写的扁平化叙事。
同质化的扬城抑乡叙事体系导致了城乡二元叙事的文学创作与乡村问题的评议判断,文学被祛魅成平庸的书写,教化则包裹在文明的理念之下。然而,他们忘记了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既要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也有思想方面的现代化;既有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也有个体层面的现代化,以及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人性,而这恰恰是发展车轮最容易碾压的。
所以,一直宣称乡土文学并未退场的贾平凹,无论是《秦腔》借助“反现代”的现代性所建构的乡村文化的伦理认同,还是最近《极花》里串联起城乡的伤痛救赎,延续着对农村破败的哀婉,质疑着城市化的正义,都必然在这个“城市信仰”的时代遭遇城乡叙事的围剿与谩骂。内容与否都无关紧要,深沉悲悯的情怀在这个时代会显得廉价而政治不正确,何况他还在苦难叙事上不断对着乡村抒情呢?
再者,表面叙述妇女被拐卖而实际呼吁关注农村的《极花》,很容易因为哀婉农村而落下嫌疑,在女权主义强势崛起的大陆,也注定着他要被架上时代的审判席。令人遗憾的是,女权主义者们只看到了女性的命运,而不去批判造成千万此种命运的无形之手。如果认同了女权批判的正义感,那么和曾经差点被安装进我们电脑中的绿坝有何区别呢?
萧轶,不自由撰稿人,不靠谱书评人。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萧轶:青年撰稿人

凤凰文化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文化资讯
往期《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