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2016.04.23 第258期 作者:思郁
导语: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每年的这一天,各种书单、各路读书活动都会蜂拥而至,好像我们都等待着这24小时来让阅读重新回归生活。但事实上这些东西与读书毫无关系,不过也是一种媒体产品罢了。书评人思郁把这一年一度的阅读狂欢视为精神还魂时刻,这样的读书日只能让人明白,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真正的阅读越来越远。我们都在向“屏读者”过渡,并在其中自我异化。电子媒介取消了深度和意义,提供着短时的、表面的、视觉化的、新奇的、媚俗的信息,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娱乐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媒介的超级意识形态,读书连最基本的娱乐价值都无法提供了,那些承载严肃阅读内容的书籍,注定会一步步隐退到私人领域,甚至退守到博物馆和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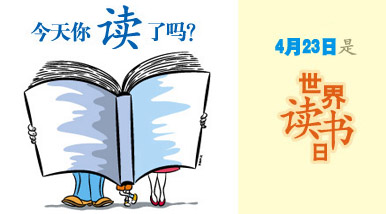
未来我们大概这样阅读:早晨醒来,把手腕上屏幕的闹钟关掉,顺便查看下今天的天气和新闻。去浴室洗漱的空隙,墙上的屏幕播报着今天的新闻消息。穿衣服的时候,衣橱上的屏幕提醒我们今天适合的搭配。吃早餐的时候,平铺在桌面上的显示器显示出我们感兴趣的信息。开车的时候,车上的屏幕会把新闻朗读出来,或者选择我们感兴趣的故事。到了办公室,房间里所有的墙面和桌面都是屏幕,根据我的需要已经做好了继续工作的准备。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我想散散步,手腕或者眼镜上的屏幕会规划好路线,并随时监控心率、卡路里消耗情况等数据。晚餐时,餐桌上的屏幕播放适合消化和家庭氛围的音乐。晚饭后,可以选用各种屏幕的电影或者游戏进行娱乐消遣。睡觉前,我用床头或者天花板的屏幕阅读一本书,直到伴随着放松的音乐安然入睡。
这是凯文·凯利在《必然》中描述的一幅未来画面,他把这种未来的阅读方式总结为:屏读(Screening)。换句话说,我们随时都在阅读,但是这种阅读的载体已经发生了变化,纸质书已经不存在,我们阅读各式各样的电子屏幕。阅读行为虽然存在,但是这种阅读更多是指向了泛阅读,停留在一种阅读的姿态上,就像用眼睛扫一下屏幕,手指轻轻划过页面,就可迅速浏览标题,因为信息太多,只能通过标题选择部分阅读。阅读的意义在这种快速翻页中已经丧失殆尽了,这只不过我们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一种技能而已,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习惯性地信息获取,甚至只是填充时间的一种状态。我们在这种阅读习惯中,丧失了记忆的能力,丧失了训练自己的大脑快速运作的能力,因为有电子媒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记忆。更重要的一点,这幅阅读画面中,我们看不到人与人的交流,甚至看不到人面对屏幕时情感的变化,阅读那种惊心动魄的体验和感受已经不复存在。
借用恩斯特·卡西尔的话说:“随着人们象征性活动的进展,物质现实似乎在成比例地缩小。人们没有直面周遭的事物,而是在不断地和自己对话。他们把自己完全包裹在语言形式、艺术形象、神话象征或宗教仪式之中,以至于不借助人工媒介,他们就无法看见或了解任何东西。”没有了工具,没有了手机和网络,现在的我们基本寸步难行,这就是重度依赖媒介产生的自我异化。
凯利并未危言耸听,我们都在向“屏读者”过渡。现如今的手机阅读就是最初级的屏读者,想想我们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就知道这种屏读有多大的吸引力。我并不是一个技术的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沉醉在旧日迷梦或者刻意显示出脱俗格调而非要固守和哀悼纸质书的刻奇主义者。实在是阅读媒介的变化并不单单意味着我们只是改变了阅读的工具。我无法像翁贝托·艾柯那样乐观--书籍如同轮子,一经造出,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改善,你不可能将一个轮子做得更像轮子,阅读工具的变化并不可能改变我们的阅读审美、阅读习惯和渴求知识的能力。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提到一种“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与拓展,比如汽车只是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电子书同样也能看作储存更多,携带和阅读更方便的纸质书。但是这种乐观的论调亟待修正,因为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含着超越自身的意义:我们发明了钟表,重新定义了时间,久而久之,我们就以为时间就是钟表上的数字,而忘记了真正的时间是四季轮回、生老病死;我们发明了书写文字,把口头语言固定在了纸面上,开始有了自己的历史和记忆,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斯罗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象,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这项伟大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历史。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提供了一幅历史上的阅读图景。简单来说,人类的历史,在一系列电子媒介发明以前,基本生活在印刷术统治时期。尤其是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与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法国大革命与启蒙思想之间的关系,已经有数不清的专著出版,思想以及这种思想背后的印刷术代表的就是这种媒介对公众话语的塑造和改变。
但是自从电报、摄影、电视、网络和手机等电子媒介发明之后,印刷术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衰微了。在印刷术统治时代,我们所能接受的每一条信息和行动都是对等的,目的是为了采取行动,所以大多数人都觉得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人们了解到的信息都具有行动价值。但在我们现在的信息世界里,人们失去了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好像关乎每个人,但又好像与每个人都没有关系。我们第一次得到了不能回答我们任何问题的信息,而且对于这些信息,我们也不必做出任何回答。想想我们对于中东问题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对于叙利亚难民问题能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只是接受信息,不停地刷新信息、转发信息,然后其他更新的信息蜂拥而至,吸引我们的关注力。
至于阅读,呈现在电子屏幕上的阅读,已经无法具备纸质书所固有的深度和意义。我们要知道,电子媒介就是为信息而生,它的存在,自动取消了深度和意义。这是个扁平的世界,里面填充的所有文字都是讯息的一种,文学也自动编码成了信息的形式进行流通和传播。而信息只具备短时的、表面的、视觉化的、新奇的、媚俗的特点。君不见,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点击量最高的文字一定是配图多,文字少,简单明了,不用思考,最好用轻松活泼的语言,再加上夺人眼球的三俗标题。这样的文字如果称得上文学,便是对文学本身的消解。
我有个朋友小说家刘汀,他有天就说,判定微信朋友圈传播的文字是不是一篇好文章,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印在纸上,或者印刷成书,到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种支离破碎的语言,已经惨不忍读。媒介不但能改变内容,同样也会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我们能够集中的注意力越来越短,几分钟都会翻看一下手机,刷新一下新闻;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思考,渴望看到段子、笑话和图片解说--看图片只需要辨认,看文字还需要理解,而理解意味着逻辑严密的思考,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句子意义的过程。换句话说,图片比文字更能让人轻松易懂,让人放松娱乐。这种“不想思考”的惰性思维改变对严肃的文学阅读而言,是致命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铺天盖地的各种书单、书选、书榜,虽然打着“读书”的名号,但其实也早与读书毫无关系。它们只是一种信息的简单罗列和公共传播,既取消了阅读本来的沉静体验和深入品鉴,也忽略了阅读的个体差异与私人判断。它们用去思考化的概括式总结与排列替代了阅读的复杂性和本应建立在思考基础上的筛选,于读书人无用,于不读书人多余。它们不过也是一种媒体产品罢了。
我们大概是钟爱纸质书的最后一代人。其实说是一代人已经很勉强了,这一代中已经分化为极小的读书圈子,大体上以媒体为核心,以出版业基础,以写作为兴趣和职业的,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遥相呼应的互文关系。但是在这个封闭性和排他性很强圈子之外,读书无用论的声音此起彼伏。
读书无用这种说法自然是真的,除非你能将读书转换成一种商业价值,变成一种有形的商品,比如写一本畅销书;再或者书籍的内容呼应着潜在的实用功能,成为某种价值的指导,比如各种养生、创业、理财、励志、厚黑题材的泛滥。但是读书无用这种庸常的论调之中隐藏着一个更深层含义,指的是读书连最基本的娱乐价值都无法提供了,阅读书籍的产生的神圣和愉悦也丧失了。
“文学除了娱乐大众之外,几乎无所不能。”这句话恰恰点明了文学逐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娱乐当然不是文学阅读的主要属性,文学的愉悦来自文字的美感和意义的深邃,这样的愉悦只有那些能够静下心来,沉浸在阅读中的读者才能体会到。用桑塔格的话说,一篇值得阅读的小说是对心灵的一种教诲,它能扩大我们对人类的可能性、人类的本性及世上所发生之事的理解力,它也是内向自省意识的创造者。但是这个时代,要文学具备娱乐性,就等于舍弃掉文学的本性,变换各种面目讨好读者。
娱乐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媒介的超级意识形态,谁能占领娱乐的高地,就能俘获大量的读者。而那些承载严肃阅读内容的书籍,注定会一步步隐退到私人领域,甚至退守到博物馆和纪念馆,就像一年一度举行的“世界读书日”,成为人们偶尔的“精神还魂”时刻。我们要注意的是,精神还魂是瞬间的抽离,是仪式性的逃避,是虚假的热情,是自我陶醉式的精神饲养。这样的读书日,只能让人明白,我们的日常生活距离真正的阅读越来越远。阅读变成了一种无意义能指的在场,意义所指的缺席。它仅存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阅读这种行为有多么的不合时宜,书籍距离被收藏进博物馆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思郁,八零后,不自由写作者。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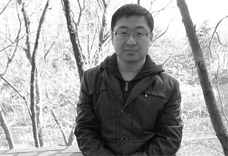
思郁,八零后,不自由写作者。

凤凰文化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文化资讯
往期《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