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2015.10.10 第208期 作者:云也退
导语:时隔半个多世纪,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垂青了“非虚构写作者”,2015年的诺奖花落白俄罗斯女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上一本获得诺奖的非虚构作品还是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阿列克谢耶维奇就出生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她的生命轨迹与冷战重合,而阿富汗战争又恰好在她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刻开打……感知过大灾大厄,付诸笔端便成了道德职责之应有。没有一种受苦是正当的,无论怎样,阿列克谢耶维奇咬牙坚持的东西是对的。评论人云也退推测,将来的人们仍然会将她的获奖定性为一个政治性的选择,这无疑会削弱作品的说服力。人们记住了事实,就会忘了她,记住了她是“反苏”的,就不会高看其“文学之美”,虽然她的作品单靠“纪实”就能撼动人心。除了记录,尴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别无选择。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1986年,我决定不再写战争了。我完成《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连一个流鼻血的孩子都不忍看一眼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抵挡痛苦一阵子;而我,我已筋疲力尽了。”
可你是谁?你是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你生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生命轨迹与冷战重合,你知道苏联入侵卫星国是怎么一回事,而阿富汗战争又恰好在你心智完全成熟的时刻开打……感知过big event——通常也是huge disaster的人,伊姆雷·凯尔泰兹,普里莫·莱维,艾利·威塞尔,他们能不写集中营么?小库尔特·冯内古特能不写德累斯顿大轰炸么?克里斯塔·沃尔夫能不写两德的离合么?还有,1980年10月底的一天,当澳大利亚人托马斯·基尼利在贝弗利山区闲逛,在一家包店里偶遇一对大屠杀幸存者,听完他们的叙述,立刻着手撰写一本名叫《辛德勒名单》的书。书写大灾大厄,乃道德职责之应有。
诺贝尔文学奖又扩招了,不仅首次招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国籍的获奖者,而且连体裁也放宽了: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我们所谓的“非虚构写作者”,本职是记者,以记录真实,不作任何虚构自诫。她的作品也是文学么?《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切尔诺贝利之声》、《锌皮娃娃兵》,看书名就不像小说。但诺奖却给了她。
据说获悉时,年过六旬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喜形于色,同她行文的深沉悲凉相对照,太不矜持,但联系到她最近几年说过的话,这反应又殊可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个不苟玩笑的人,她没有办法用今天人们常用的玩世不恭来舒缓自己的紧张。她心怀太多的恨与憾,把敌我界分得太明确:发动战争的人,钳制众口的人,检查书报的人,统治者和他们满地乱跑的、“奉命行事”的鹰犬爪牙,都是敌人,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她的朋友,他们很可怜,很悲惨,更可怜的是,就算是被剥夺到了一无所有,还甘愿被敌人拿来当枪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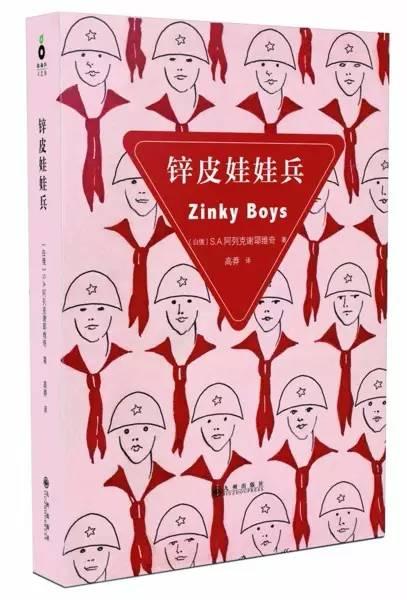
《锌皮娃娃兵》
1986年——她在《锌皮娃娃兵》一书中说——她本想不写了,因为之前访谈了太多苦难的事情,精神几乎崩溃。但两个事情改变了她的想法。
其一,一次她去乡下的一个村庄看一位女友,发现其母站在门口哭泣。过去一问,她邻居的儿子伊万不久前才“为国捐躯”,现在儿子安德烈从阿富汗发回了信,“妈妈,太棒了!我是个伞兵……”她读着读着就哭了。
其二,城里,一个车站的候车室,一名军官坐着,带着一个半空的提箱。他身边坐了一个瘦瘦的男孩,用一个小叉子在一棵橡皮树的泥土里挖着。两个乡下女人坐在他们身边,打招呼:“你们是谁?”军官说,他送一个小兵回家:“他疯了。”“疯了?”“疯了,从喀布尔回来,他一路上手里拿着什么就挖,铲子,叉子,小棍,自来水笔。”男孩抬头看了一眼,阿列克谢耶维奇注意到,他两个瞳孔已经放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球。
“而那时,人们依然在谈、在写什么国际主义义务,什么民族利益,我们的南部边境之类。检查机关监督所有战争报道,确保里面不能提及我们的死命(意为我们的必死性)。人们只能从一些零碎的传言里听到消息,某某某瞥见了乡村小茅屋里堆着的尸体,或是看见了军方预制的白花花的锌皮棺材。”不写战争,怎么可能?“我明明正身处一场战争期间。”
那就写吧。她用了三年时间访问各种与战争有关的人,每个人的诉说就是一幅画像。它们不是文献,而是画面,组成了一段人类感受的历史,而不是关于战争本身的历史。——这个区分很重要,极为重要:如果是文献,那就是历史范畴,顶多处于非虚构的灰色地带,如果是画面,那就可以跻身“文学”,至少是被诺贝尔文学奖扩大化了的“文学”。
《锌皮娃娃兵》出版,并在西方有了名气时,苏联人还很少知道它。俄罗斯这个国家有她的悖论:她是世界上人均阅读习惯最好的国家之一,至今不次于东南边的宿敌日本,街头读书的人多,人们聊天也总是谈到最近读的书,图书馆馆藏丰富,人流络绎,老式的卡片式书目存放柜散发出令人神往的气息;但是,政权似乎总能相当成功地查禁一些有危险的书籍,大幅度削弱它们潜在的影响。
锌皮棺材厝回了没有生命的人。还有气息的,则带着各种各样的伤,看人看事早已不抱热情和希望,浑身紧张,眼光呆滞,心头恚恨不知往哪里倾诉。回到家乡后所受的待遇警醒了他们,自己被骗了,被国家给骗了。和战友的袍泽之谊是他们唯一的所获,除了这些人,再无别人能让他们打开心扉,畅诉苦愁。
除了访谈,还是访谈。与著名的“纪实小说”如诺曼·梅勒的《黑夜大军》相比,阿列克谢耶维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单靠“纪实”——记录受访者的话——就能撼动人心。看一个士兵的自述:
“回到家,我们看到什么?我问一个朋友要五块钱,他不肯,因为他老婆不让。这叫什么朋友?我很快就知道我们要得太多了……在这儿,生活就是一个大泥潭,所有人都只关心他自己的豪宅、汽车,在哪儿能买到一点熏香肠……要不是我们的人多,我们有十万人呐,他们就把我们挡门外啦……在那边我们都恨死了敌人。但是这里我得找个人来恨,非得这样我才能重新交到朋友。但是,恨谁呢?”
人性被扭成了麻花,稳定情绪的机制早就倾覆。阿列克谢耶维奇观看战争最直截可见的各个方面,《锌皮娃娃兵》里有痛苦,有丧失,还有欲望,有饥饿,有嫉妒和渴望。可怜的苏联士兵,逃得一条性命回来的,半边大脑储存着来自发达国家的吉光片羽:意大利的太阳镜,日本的电子产品,美国的罐头;另半边大脑则填满了屈辱。新兵在营房里的日子,和在野地里一样充满噩梦,早入伍一两年的老兵以折磨他们取乐。一个新兵被活埋到了脖子,老兵掏出生殖器,对着他的脑袋撒尿,发出一阵阵狂浪的笑声。这位新兵到早晨才被放出来,一怒之下,亲手杀死了两个凌虐自己的人。其他人就没那么强的复仇欲了,一位新兵说:他那一个班里,其他十人都是老兵,逼他每天服侍,打扫,洗濯,从小溪里取水,一晚上只能睡不到三小时,动辄挨打。
“有一次外出给老兵找水,踩上了一个地雷,万幸的是,那只是个信号雷,一枚信号弹蹿起,整个一片都被点亮了。我被轰倒在地上,赶紧匍匐着继续找水,去给老兵们刷牙……他们才不会在乎我遇到了什么事,他们只会打我,打我,打我。”
显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述会成为各种“共产政权黑皮书”的必引资料来源。这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会削弱作品的说服力。如果你熟悉如安东尼·比弗在《攻克柏林》中描写的苏联士兵,你读到阿列克谢耶维奇时也会多个心眼。服兵役的女人——阿列克谢耶维奇说——起初得到一个美好的许诺:当好后勤,就是报效国家。但后来噩梦便开始了:兵爷岂能对她们毫无想法?一个女人告诉阿列克谢耶维奇:一个酷暑,厕所里的苍蝇多得可以把人拎起来,她服侍在一个军官身边,整整两个月,她没有睡过一晚好觉。在危机时刻,她一度以刀相搏,才从豺狼一样的“自己人”手里保住了身子。
陌生而熟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对啊,西方人不是总爱说苏联士兵强奸女人的事吗?如果人们读时都这样的想法,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过了十几二十年还有多少人要看,就可以打个问号。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一个作家“不朽”的保证。她以一己之力,披露了被官方隐瞒的大量事实,由此创作的作品,作为作家的她,其存在感是较弱的。人们记住了事实,就会忘了她,记住了她是“反苏”的,就不会高看其写作;而有朝一日档案公开,战争与核泄漏的真相进入常识领域,谁还会为了“文学之美”,去读这个白俄罗斯女记者的书?
有人把她归入“纪实性虚构”一类,但她自称,她创立的是一个名唤“人类声音”的体裁——浓重的书生气扑面而来;哪一本文学史,都不会为“人类声音”单开一个栏目的。而且,“人类声音”可涵括的书,又岂仅限于受害者访谈呢?一些纯文学出身的大家写下的纪实性作品,如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或是富有文学意味的非虚构,如艾利·威塞尔的《夜》,也是“人类声音”;美国普利策奖得主斯塔兹·特克尔也有深受好评的二战老兵访问记面世;甚至当年“六日战争”后,阿摩司·奥兹轰动一时的士兵访谈录《第七天》,也不应视而不见。
在体裁上,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尴尬的,所以,我觉得人们将来仍然会以定性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的方式来定性她:一个政治性的选择。因为她写了苏联,写了这个国家的战争、灾难和丑闻,而得到了这顶桂冠。她很高兴,因为她一直遗憾于无力撼动丑恶的政治势力,得奖,起码说明人心站在她一边。

《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未来如何评价她,现在不便揣测了。正如本文开头那几句引语,我还是佩服她,坚持做一件自伤性的工作。如果读她的书读到绝望,那是因为她本人深味过绝望。在《战争的非女性面孔》一书中,有个人物在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交谈时哭了,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收到那人寄来的一个包裹,其中有她在军队里服役的一些档案。那女人附了一句话:“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让你懂得我们有多难。但是,我们不会把自己的事写成书。”
一般人都不会把自己的创伤写成书,拿去卖版税的。取走别人的故事,代为叙述,代为表达,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做,必须忐忑不安(可以联想下那个“嫁给大山的女人”风波)。但她继续下去,因为人祸仍在继续,也因为作为知识分子,她除了写书之外没有更好的介入途径。
战争是绝对男权的事物,因而女性往往成为推翻战争之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声道。在《锌皮娃娃兵》里,一个最令人痛心的故事,是一位母亲收到了来自阿富汗的锌皮棺材,里面装着她儿子的遗体。棺材被移进她狭小的房间时,母亲迸发出一阵哭号:“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他是个木匠,有半年时间都在给将军们修别墅!从没有人教给他怎么开抢,怎么扔手榴弹!他上战场后一个月就死了!”
然而后来,她和很多曾被采访过的女人一样,出面控告阿列克谢耶维奇。她说:“我不需要你写的事实,我需要的是一个英雄儿子。”
她被收买了,但是,玩味她的心理,你未必不会苦涩地点头。这位母亲既已失去了全部,她又何妨与当局配合,绞杀民间独立的声音,只要她当真不在乎同杀害儿子的刽子手合作?在民智未开的地方,拿亲人的尸体讹财的事情并不少见;又或许,她的的确确从阿列克谢耶维奇描写的死亡故事中感受到了二次伤害,而这种书写却关系着作家器重的职业操守……
但没有一种受苦是正当的。无论怎样,这位新获奖的女记者咬牙坚持的东西是对的。白俄罗斯在苏联诸加盟共和国里是保留老苏联元素最多的一个,这其中最险恶的一点,也许阿列克谢耶维奇并未危言耸听:人民从幼年起就被囚禁,其心智从未得到彻底的发展。因而她说,她爱这个伤害了自己的女人,因为她囿于认知局促,无法区分不同层次的事。《旧约·约拿书》的末尾,上帝告诉约拿,他宽恕尼尼微的人,是因为这座大城“其中无法分辨左右手的约有十二万多人”。很多人行不可理喻之事,说难以置信之话,是因为他们只会这么做,这么说。
有媒体称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俄国张纯如”,还是很有道理的:她的书有许多缺点,例如情感丰富的女作家所共有的问题——掌控不好情绪。但一想到张纯如,就不好意思苛求一个主动涉足黑暗,去饮用它有毒的奶水的女记者。想想张纯如,我们得承认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不崩溃是比放弃和自杀更艰难的抉择。由于那个著名的鸡蛋石头论,许多脆弱的石头被误伤了,但阿列克谢耶维奇面对的是一块披拂着前苏遗风的真正的顽石,不管怎样,我都站在她的一边。
云也退,专栏作家,在《第一财经日报》等多处开设个人专栏,经营个人公众号yunyetuitui,谈文学、文化、健身、旅行、相声。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凤凰文化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文化资讯
往期《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