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2015.3.5 第131期 作者:思郁
导语:春节期间,一篇上海大学博士生的回乡札记走红,进而也引来了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乡村从未成为过提供稳定感、满足感的物质依靠,更不曾有过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又到元宵节,可能很多离乡工作的人无法与家人欢度了,但关于乡愁和故园的情感与思考却永远不会停止。评论人思郁认为,乡村生活的现实和变化的时代步伐让农民更愿意背井离乡进入城市,然而城市无法真正融入,家乡亦是面目全非,从离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注定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异乡人。乡愁是一种致命的浪漫,是知识分子的强颜欢笑,田园牧歌生活背后的黑暗与辛酸在这种怀旧中被隐藏掉了。

美国人何伟(PeterHessler)在《甲骨文》开篇写到:“从北京到安阳--从现在的首都到被视为是古中国文明摇篮的城市--搭火车要花上六个小时。我坐在床边,有时不免觉得单调麻木。窗外的风景如壁纸一样地重复: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一个农民、一片田、一条路、一个村庄。这份重复的感觉并不新奇。”
这样重复的风景在早年读书的时候处处可见。这样的风景这些年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农民几乎看不到了,一片片的田地上很突兀地出现了正在建造的高楼,村庄越来越稀少,越来越空无。事实上,我的家乡就像那位上海大学博士的返乡笔记中说的情况,除了南北地理上的差异,人情与世俗并无二致,大部分年轻人都进了城,一年在外,村中留守的都是老人和孩子,纯正的庄稼人越来越少。
城市和乡村都不是家乡
没有人再种庄稼:一方面是地划分的越来越少,我印象中,在十年前,村里每个人还能分到将近三亩地,现如今已经不足一亩;另外,种地的收成越来越低,一年下来,刨去农药、化肥、灌溉等成本费用,所收获的粮食除去全家食用,其余可售卖变成人民币的少得可怜。对农民来说,吃饱饭已经不是问题,手中没有钱花才是大问题。为了挣钱,只有脱离土地的束缚,进城也罢,转行也罢,只要有途径可以挣钱,他们都会尝试。
没有人再留恋一亩三分地,老婆热炕头的简单生活。父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人甘心留守在乡村,伺候那一片庄稼地。更不要说那些年轻气盛的青年人,外面的大千世界太精彩,诱惑无处不在,处处都充满了可能性,而留下来只会慢慢枯萎。新近播出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高中毕业前夕,田晓霞请他在国营饭馆吃饭,顺便告诫他说即使回到农村,也千万不能忘记读书:“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抱柴禾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
这不是对乡村生活的抹黑,是活生生的现实,多少年亦如是,仿佛亘古未变。我们不可能都有足够的自信,像诺奖诗人切斯沃夫·米沃什一样说一生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那正是因为他去过了很多地方,反而没有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而那些终生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他们对生活的认知无法超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巴掌大的天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只有一种慢慢萎缩、枯萎、衰老的生活状态,而后者至少提供了无数生活的可能性。
进城打工是农村年轻人普遍选择的方式,对于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人,他们更愿意在附近的县城做点小买卖。这里最为吊诡的部分在于,对于那些进城的打工者来说,他们清楚城市并非他们的家乡,当他们远离了家乡进入新鲜的城市时,他们更加清楚是城市中的异类。虽然一年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只是暂留之地,是挣够钱都转身离开的所在。他们当然想留在城市生活,而且有很多人都成功了,但是他们的记忆仍然生活在乡村里,完全的城市人至少需要两三代人才能完成这个蜕变。而对于打工者来说,城市是一个大写的他者,无论是人情世故,文化差异,城市政策,工作环境等等都让他们更加明白,他们不是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所以,当他们攒够了足够的钱,就会义无反顾地回去,回到家乡去。
城市不是他们的家,但家乡亦是面目全非。这种心理上的扭曲十分微妙,一方面是他们见到了城市的模样,城市文明的记忆覆盖了原本童年乡村的记忆,所以家乡亦非原来的家乡。他们需要重新建构一个适合自己生存的新家,从城市回来的打工者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乡村附近的县城买房--尽管距离乡村不过四五公里,但在心理上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城里人。而另外一部分从城市回来的打工者,用自己半生舍命打工的积蓄,娶妻生子,重新在乡村定居下来--他们会重新修建自己破旧的房子,哪怕一年到头,这个院子的房子都无人居住。对这一部分农民来说,家就意味着每年春节回来住半个月的房子。只有在一年到头的春节,返乡的大潮才让空无的街道充满了人群--正如另一方的城市,突然变成了一座空城。
液态的变化世界
几乎无人留恋乡村生活,这就是现如今农村的现状。变化无时无刻不再发生,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在于,这种变化仿佛是突如其来的,就好像原本亘古未变的古老生活方式,突然被一种强大的驱动力给打破了,一下子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流动了起来。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散了。你只有变化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一旦你停下来,你就会被时代抛弃。这种被时代裹挟着身不由己的变化,城市的上班族能感觉到,乡村生活的农民同样深有体会,他们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全都是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落差。他们的恐惧更加根深蒂固,因为土地无所依靠,这就意味着夺去了他们手中最后的救命稻草,只有绝处逢生,毅然出走,寻找新的生存方式,才能跟得上这种变化。
可以借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术语,把这种变化的世界称之为“液态的变化世界”,顾名思义,液态的生活即是流动的生活,这是一种生活在永不确定的环境中,缺乏稳定性的生活状态。这种生活处处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焦虑与恐惧,我们害怕措手不及,害怕跟不上潮流,害怕被别人抛在后面,害怕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是无数的恐惧,这是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最为精准的体验。流动的生活暗示了一种观念:表层即是意义的全部。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追寻生活之下蕴含了的什么。借用鲍曼的话说: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包括我们追随的时尚与我们关注的对象:“我们有梦想也有恐惧,我们有渴望也有厌倦,我们既充满希望,但又坐卧不安。我们赖以谋生以及为之谋划未来的周遭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在这个液态的现代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转瞬即逝,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
变化是我们这个社会中唯一可以确定的东西,城市在变,乡村也在变。我们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和生活,不过是有的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有的人失败了。这个时代是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时代,农妇的女儿可以努力上进,由工厂流水线女工扶摇直上进入董事会,打工仔可以成立上市公司,煤矿工人的儿子可以影响时代的进程。正是这些成功的故事激励着一批批农民的儿子进入城市,他们也有自己的野心,不甘心在乡村默默无为,度过一生。但是伴随着这种野心的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变化之后就再也回不去了。我们都变成了自己家乡的异乡人,一个匆匆的过客,一个借助春节的短暂性触摸维持不变的假象的现代人。城市化进程把进城的打工者同化为城里人的同时,也将乡村同质化自己的影像。在我的家乡,即将进行的几个举措就是在未来几年把乡村聚集在一起,统一搬迁进城,然后将剩余的土地大规模承包种植。这种农村强行城镇化的趋势很是明显,我们那个村子的很多土地已经被承包,而且没有人惋惜失去自己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现在不积极寻找其他生存方式,迟早会被城镇化模式强行驱逐。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积极求变。如果这种变化是无法阻挡和避免的,为什么我们还要惋惜这种变化呢?
对乡村的怀旧是知识分子的强颜欢笑
乡愁是一种致命的浪漫,田园牧歌生活的背后是多少的黑暗与辛酸,怀旧多少是知识分子的强颜欢笑,所以我始终对刘亮程和韩少功书写的乡村系列散文充满了怀疑。哈佛的俄裔女学者斯维特兰娜·博伊姆给“怀旧”一词下的定义是“对于某个不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过的家园的向往”。在远方想家并不是怀旧,但是如果你返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却再也找不回到家的感觉,那才是真正的怀旧。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怀旧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冲动,精神的漂移,记忆的沉迷,幻象的觉醒。儿时的一首歌总能打动人心,不是因为它的动听,只是因为那首歌牵动了儿时的美好记忆。我们所怀想的只是一种记忆的幻象,梦想的家园。返乡的冲动一次次冲击着内心的栅栏,一旦等你按耐不住返乡的冲动,把一种记忆中的梦游拉回清醒的现实,付诸行动的话,失望的情绪会击溃你脆弱精神的防线,你迟早会发现记忆中的家园早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换句话说,当那些人哀悼着乡村正在丧失自己传统的时候,别忘了他们是在城市窗明几净的房子里奋笔疾书。
早在我们离开了乡村之后,都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异乡人。无论是我们这些靠读书进入城市的人,还是那些很早就进入城市的普通打工者。我们之间面对乡村的经验并无二致,乡村被异化为了他者的目光,回家是自我欺骗的幻觉。我们是城市的边缘人,家乡的异乡人,精神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我们与那些打工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会讲述、修订、抒发自己的经验,而他们才是沉默的行动者。他们的行为比我们更重要,因为正是他们携带着关于城市的经验和记忆回到乡村后,改变了乡村的面貌。而我们只是吟唱着乡村的挽歌,在城市中继续生活、怀想,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回不去的家乡。
思郁,八零后,不自由写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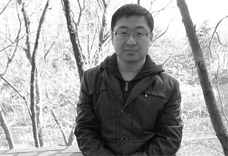
思郁,八零后,不自由写作者。

凤凰文化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文化资讯
往期《洞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