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我们是否依然有必要谈论哲学?哲学是否又分大人物哲学和小人物哲学。如果说,小人物哲学最能到达真实的历史,那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人物哲学的国家,孜孜不倦思考小人物哲学的家伙又会“收获”什么样的尴尬和笑话?

据说,年轻的列宁在读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时恐惧不已。《第六病室》描述了一种可以致死的“精神传染病”,医生安德烈仅仅因为受到与病人伊凡谈话的吸引,就也被当成了病人关了起来,最终死亡。安德烈和伊凡在最后一次谈话中说:
“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我亲爱的,”他喃喃地说,身子发抖,擦掉冷汗。“我的精神支持不住了。”
“那您就谈谈哲学嘛,”伊凡·德米特里奇讥诮地说。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对了,对了。……有一会您说俄国没有哲学,可是人人都谈哲学,连小人物也谈。然而要知道,小人物谈哲学对谁也没有害处啊,”安德烈·叶菲梅奇说,那声调仿佛就要哭出来,引起别人的怜悯似的。“可是,我亲爱的,您为什么发出这种幸灾乐祸的笑声呢?如果小人物不满意,怎么能不谈哲学呢?一个有头脑的、受过教育的、有自尊心的、爱好自由的、具有神的相貌的人,却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到这个肮脏而愚蠢的小城里来做医师,一辈子跟拔火罐、水蛭、芥子膏打交道!欺骗,狭隘,庸俗!啊,我的上帝!”
“您在说蠢话了。要是不愿意做医师,那就去做大臣好了。”
好一幅“哲学治疗”的图景!同时却是“小人物谈哲学”的窘境。对于小人物来说,哲学治疗的企图无疑失败了。列宁的恐惧是否与此有关?只有等到他创立了列宁主义,列宁才能摆脱这种恐惧。列宁主义,那可是大人物的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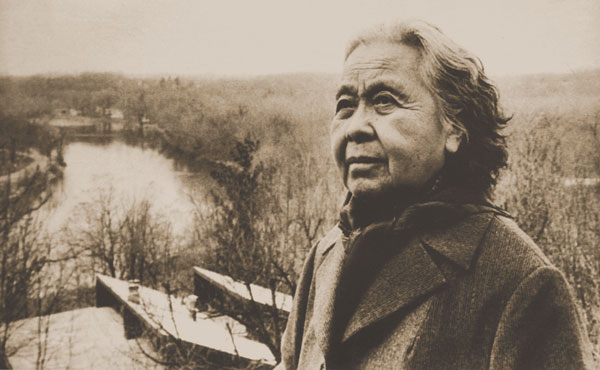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丁玲在延安整风发动之际发表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改为《在医院中》)——他的这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引爆文艺整风的原因之一——其实也受到了契诃夫《第六病室》的影响,女医生陆萍同样是在第六号病房里遇见了没有双脚的病人。但丁玲的用意却和契诃夫迥异。陆萍在上海的一个产科学校毕业,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想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然而却在恶劣的医院环境下——只有一个注射针,对病人毫无“人道主义的同情”——四处碰壁,在热情投入工作时煤气中毒几至丧命,后来被一个到苏联去过的失去双脚的病人说服:
“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毛泽东的延安讲话有一部分即针对丁玲而发。丁玲在面对蜂拥而来的批评时说:“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她已试图放弃“小人物谈哲学”而皈依“大人物”的哲学,皈依毛泽东思想。
黑格尔说:“在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在希腊,只有一些人是自由的。 而在日耳曼各国家,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在另一个地方,他说得更为清楚:“东方观念的光荣在于‘一个人’(the One Individual),一切皆隶属于这位客观的存在,以致任何其他个人皆无单独的存在,并且在他的主体的自由里照不见他自己。……一方面是持久、稳定,——可称为仅属于空间的国家(与属于‘时间’者有分别)——乃非历史的历史(unhistorical history);例如中国”。这一个人当然是大人物,是皇帝。
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的说法,联系《第六病室》和《在医院中》,可以说,那些小人物的哲学恰恰就是自由。无自由,即无历史,也即,无哲学,即无历史。(当然,这恰好也让我们中了黑格尔逻辑的圈套。哲学的诡计?不!)
哲学就是自由,其实并不难理解。哲学就是自由,这也是“哲学家的哲学”留给我们的启示,其典范就是“苏格拉底之死”。还有比哲学/自由更值得以死去争取的吗?苏格拉底的罪名是,他的哲学“毒害”了雅典的青年。哲学毕竟不利于他们服务于城邦。
是不是因为要为苏格拉底复仇,柏拉图才设想出了哲学王?这样,“哲学家的哲学”就变成了“大人物的哲学”,而它原本只是“小人物的哲学。”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大人物的哲学,这样的时代有多么可怕,我们都领教过了;所有人都在谈论一个大人物的哲学,那也有可能催生无数小人物的哲学,我们只有在避之不及的时候才愿意和它亲近,虽然那无比凄凉,无比哀婉。那么,既然我们不是哲学家,有没有可能在大人物的哲学和小人物的哲学之外,找到属于一个人——一个人,而非皇帝——的正常的哲学,或曰一个正常人的哲学?
一个国家的人们普遍信仰唯物主义,最终却收获了贫穷,这可能构成了一个哲学笑话。但当他们摆脱了贫穷,却没有成为精致美妙的唯心主义者,却又构成了哲学的尴尬。
其实,哲学并无大小之分。所谓“大人物的哲学”和“小人物的哲学”,产生于哲学在政治挤压下的变形。哲学,是复数的;在虚构的意义上它们甚至是平等的。一个例子就是古罗马皇帝马克斯·奥勒留,他是一个皇帝,但他更明白自己是一个人。他力争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作为人,他选择了大多数人会选择的斯多噶主义:“灵魂乃天赐,圣洁不动情。”
不同领域的人都可以产生哲学,但哲学,还应该是那些在各自领域达到顶峰的人彼此交流的结果。诗人作家最容易选择斯多噶主义。奥勒留的哲学可以和诗人作家分享,取消了“大人物的哲学”和“小人物的哲学”的差异。
一个人选择浪漫主义,他的生活就充满了危险的偶然性;一个人选择存在主义,他的生活就充满了荒谬;一个人选择颂扬上帝的形而上学,他的生活就充满了庄严和神圣。
也许你会反过来说,一个人的生活样态决定了他选择的哲学。但我更愿意相信:最终是一个人选择的哲学,决定了他的生活的气质——或品质——和存在的基调。
王东东,1983年生于河南杞县。诗人,文化批评家。《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获2014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台湾第四届人文社科思源奖文学类首奖,并将由台湾政治大学出版。有诗集《空椅子》、《云》面世。写作之余,也从事翻译。
版权声明:《洞见》为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作者独家授权,转载请注明出处,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王东东,1983年生于河南杞县。诗人,文化批评家。《1940年代的诗歌与民主》获2014年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台湾第四届人文社科思源奖文学类首奖。有诗集《空椅子》、《云》面世。写作之余,也从事翻译。

凤凰文化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文化资讯
往期《洞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