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2016.04.01 第257期 作者:叶克飞
导语:2016年3月31日,2002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去世,享年86岁。作为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凯尔泰斯进过纳粹的集中营。二战胜利后,冷战格局里的匈牙利又经历了极权时期和各种动荡。这一切经历本来是一个作家难得宝贵的素材,然而凯尔泰斯却并不喜欢在文学创作中加入大时代的元素。作为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当然可以洞悉自己的不幸,作为一个时刻都能发现幸福、在强权前安于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可以洞悉自己的悲观,只是他选择始终冷静。在他看来,“对永恒事物的体验与表达,对那段表象的短暂体验起着决定性作用。将要逝去的东西要比永恒真实的东西更为深刻。”他在小说中以旁观者心态静观自己的命运,在日记中苦苦追索人生的终极意义。只不过他的困惑、彷徨和伤感,也许无人能够理解。

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的作品中,除了奥斯维辛四部曲之外,我最喜欢的是《船夫日记》。
这真的是一部日记,从1961年到1991年,三十年间的日记零星散布,并无主题。“船夫”是一个象征,意味着凯尔泰斯·伊姆雷的时空之旅。他并不是第一位以船夫自况的作家,福楼拜在《三故事》中让朱利安历经颠沛流离后,停在一条大河边做起了摆渡人,黑塞则在《悉达多》里让悉达多历经世事沧桑,最终也在一条大河边驻足,开始船夫生活。
1983年,凯尔泰斯·伊姆雷写道:“自我纪实是一种船夫的苦役。我像坚持划桨似的执著于此,饱尝磨难,艰辛向前。船行的方向是否正确?也许这正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弗兰克o克莫德说:‘我们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小说家。’”
与其他作品别无二致的是情绪,睿智如他,历经苦难仍内心平和,并以旁观者的心态静观自己的命运。但与小说不同,他在日记中苦苦追索人生的终极意义,甚至不惜为之进行偏执狂般的思考。他大量引用歌德、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加缪和伯恩哈德等人的观点,并与这些先哲对话。曾经在生死边缘徘徊过的他,对生死问题早已看得透彻,所以他说:“对我来说,最适当的自杀——看起来--就是生活。”那些家国之痛,也仅仅化作一句毫无归属感的“我的国家,就是流亡”。
尽管曾置身于德国人的残酷压制下,但凯尔泰斯·伊姆雷始终与同时代的匈牙利知识分子一样,受德国文化影响极大。在这本书里,与之对话的先哲们多来自德语区。如1980年6月2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书里散发着霉味儿--这是一部完成了的著作和一个实现了的人生在宇宙中唯一可以改变传统的印记:书的味道。‘1789年8月28日中午,我随着正午十二点的钟声降生到这个世界,在法兰克福的美茵河畔。当时的星相非常幸运……’”
此时的他正在魏玛,流连于歌德故居--当年,他曾被关押于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把这一幕移植到了自己的奥斯维辛四部曲中,在《惨败》里,老人在陋室中沉思,然后从书架上取下这本歌德的《诗与真》。命运就是这般吊诡,德国文化滋养着一代匈牙利乃至中欧的知识分子,可德国政治却一度是这个地区里最不安全的因素,并最终导致人们的万劫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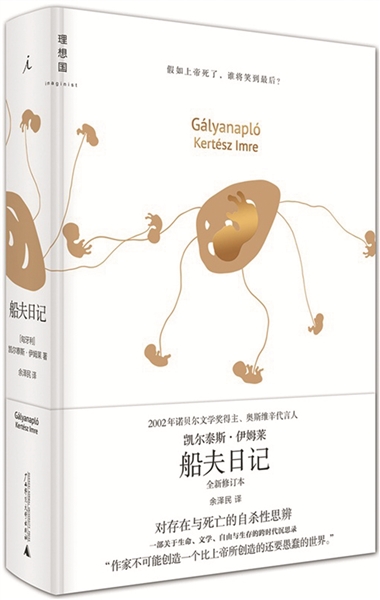
像这种将日记与文学创作相连的情况,在《船夫日记》里随处可以找到。或者说,读完《船夫日记》,就能了解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创作脉络和思想历程,也能了解大时代的变迁,包括人类的堕落沉沦和自我救赎,也包括个体面对强权的默默抗争。
也有一些大时代的元素因为时间原因,并未在《船夫日记》中呈现,但若你熟悉历史,仍能在凯尔泰斯·伊姆雷的小说里找到痕迹——尽管他并不太喜欢这样做。
比如小说《英国旗》,它讲述的是主人公从集中营出来后,却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灰暗日子。从1961年开始记录的《船夫日记》自然没有这段故事的呈现,可小说里的一个细节却让我动容,它在大段回忆与独白中难得记录了一段现实,那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的一幕,在纷乱人群中,有人从驶过汽车的车窗伸出手臂,挥舞着一面英国旗。在布达佩斯旅行时,我屡屡想到这一幕,同时想到被判处死刑,直到多年后才被平反的纳吉。
我很难想象,那时的凯尔泰斯·伊姆雷心境如何。他当然深深清楚,集中营仍在延续,德国纳粹走了,匈牙利却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中营。我也知道,他选择了冷静旁观,一如他在奥斯维辛时那样。但他有没有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又有没有一个自我审视的过程?如果有,这个过程对《船夫日记》的创作又有没有影响?
我想这一切都是存在的,作为一个集中营的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可以洞悉自己的不幸,作为一个时刻都能发现幸福、在强权前安于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可以洞悉自己的悲观。只是,他始终冷静。
《船夫日记》有着一个异常冷静、并在我眼里堪称伟大的开头。他这样写道——
“1961年。我开始写小说一年了。
我必须抛弃一切。
我踩着松软的落叶在公园里漫步。深层的草还是绿色的,上面覆盖着黄色的败叶,其他那些挂在周围橡树上的枯叶,就像无数只沮丧的手低垂着。我感觉到:如果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奇迹将会发生。”
也许,奇迹就是凯尔泰斯·伊姆雷作为曾经的受害者,却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冷静观察与思考一切纷繁吧?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他来说似乎不具有特殊意义,正如他不喜欢在小说里掺加大时代的元素那样。
即使是在东欧剧变前夕,他仍然没有将社会变革当成日记中的主体。在他看来,“对永恒事物的体验与表达,对那段表象的短暂体验起着决定性作用。将要逝去的东西要比永恒真实的东西更为深刻。”
这种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探寻,是无数人曾经的努力方向,我不能说凯尔泰斯·伊姆雷窥其全豹,但起码经历帮助了他。只是人生有一个悖论:你思考越多,疑惑也就越多,懂得越多,就会更加认为自己无知。在散文集《另一个人》里,他描述着这种彷徨心态:“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其实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而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他已做得足够好。他了解人生,了解善恶,了解人性与极权,也了解人类所有美好的或忧伤的情感。正如他在《另一个人》中记录自己的情感时那样:“她走了,并且带走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她带走了那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创作从开始到完成;她还带走了一段岁月,在这段岁月里,我们是如此相爱地生活在一个并不幸福的婚姻里。我们的爱,就像一个满面笑容、张着胳膊奔跑的聋哑孩子,慢慢地,他的嘴角弯成了哭的模样,因为没人能理解他,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奔跑的目标。”
多么伤感,但并非无人能够理解。
叶克飞,专栏作家。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叶克飞,专栏作家。

凤凰文化 官方微信
微信扫描二维码
每天获取文化资讯
往期《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