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在《故乡》中开始的时候说,“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远离了我。”如果比照现实中老屋的死去,这种描述有了另外的寓意:在步入现代社会之中,古老事物来不及转身,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在进入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当更多的人成为房奴,更多的地方变成城中村时,一些承载着文化内涵的老房子,已经在拆字令下倒塌。
作为已逝岁月仅存的证词,它们代表过去发言,描述着对生活的另外设想:适意、安闲、没有紧张感,有的,只是某种恰如其分的享受。随处所见的废墟掩盖了昨日的生活现场。那些失之交臂的老房子,人们只能透过那些旧日的门窗向时间深处窥视,但也许看到的只有灰尘,不知疲倦地,在光束中舞蹈。

住在老民居中,便意味着要和自然亲密接触,要承受一家人住在一起的家长里短。中国人所追求的四世同堂,也只能在老宅院中才能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正逐渐发生着变化。富起来的农民们高兴地拆掉百年老屋,盖起丑陋的水泥楼,把传了几代几十代的老家具扔掉,用上复合板家具。而人们在拆掉老屋后,转眼在别的地方以文化的名义,修建了各式各样的假古董。过去关于家的和合理论,在高大的格子楼中已经瓦解。 [详细]
许多住惯老宅的人,对老院子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老院能够自由地喂养动物。和这些现代化的防御措施相比,老屋破旧的木质门窗,似乎什么都挡不住。看着被淹没在新式建筑中的老民居,不禁想问:在社会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今天,老民居和它背后的传统生活方式还能走多远?更多的老宅人家则在无奈中丢掉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西羊市127号米家大院内,曾住着庞大的米氏家族。现在,老房子只剩下一座厅房,被夹在新房之间,显得陈旧、衰老。[详细]
何镜堂说,在旧城改造中,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两个问题:一是我们拆掉了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美建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历史建筑消失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旧城是一个城市的“根”,如果简单拆除掉,一个城市很可能就失去了它的“根”。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没有给后人留下多少足以成为经典的当代建筑。如果离开传统、断绝血脉,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而离开创新,就会使我们陷入保守和复古。努力创作有地域特色和中国文化精髓的现代建筑,是当代建筑师的历史责任。 [详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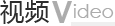
请先确认是否安装了 最新Flash 播放器
请点击安装按钮


房屋与生活以一种极其脆弱的方式粘接着,这显然违反了房屋的本意,也与生活的设想无关,但不知什么原因,事情就弄成了这样。总之,生活已经同房子一起变得破烂不堪,无法挽救,像经历了一场相互戕害的婚姻。
这里将不再是浪漫、童话和奇遇出没的场所,那些呼啸而来的钢筋水泥将把它们彻底埋没。[详细]
走在村子中间,随处可见坍塌的海草房。村里的年轻人大都搬到了城市,原有的旧海草房也弃之不用了,没人建海草房了,盖海草房特有的苫房技艺,也面临着失传。随着海草房原材料呢和懂这门技术的匠人越来越少啊,很多海草房就像我身后的房子一样,逐渐的衰败了。[详细]
南京老城南的躯体正暴露在大锤与推土机之下,拆迁工人们的钢铁机械对准了那些七架梁的木构大宅。死去的雕花门窗散落在倒塌的断壁与碎砖间,粗壮的梁木四处横陈,立向天空的几根残柱像巨型生物的残骸。[详细]
月湖西区历史文化街区总占地面积为46.8公顷,分为重点保护区、传统风貌协调区两个保护层次。其中,共有各类传统民居院落145座,其中文保单位院落29座,历史建筑院落116座。 [详细]
随着一些“苏式”建筑内部设施陈旧老化,新的更为现代化的大厦和住宅楼在旧楼的地基上相继崛起。那些承载了多少住户记忆的老房子,渐渐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变成一堆堆残砖碎瓦,伴着人们的叹息消于无形。[详细]

学城市规划出身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演讲中指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城市不仅是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一个人工的环境,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和容器,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受聘为中央电视台设计新大楼的荷兰裔建筑师的库哈斯感叹说:“罗西说城市不能没有历史,如今却有大批人热衷于没有历史的生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坦陈,自己非常担心新农村建设搞不好,“如果搞不好将是一场好心的灾难。”[详细]
“中国传统文化令人迷惑。对于一个经常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有时会给人以垂死的印象,有时又会让人感觉到他的活力。现在是什么使得中国与自身脱离?只要到北京的任何一条街道走走,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中国人每个星期都在对城市过去的遗迹、对所有让人感觉是这个国家活遗产的东西进行着改造。能够逃过改造的只有那些官方公布的受到保护的古迹。此外还有大规模的社会破坏。” [详细]
一座古城毁了就是毁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现在的北京和别的亚洲大城市还有什么区别,不过是现代化博物馆中的一个新标本而已。与其说是用文字“修复”,不如说是“哀悼”。北京,其实是一个缓慢的毁灭过程,只不过远没有到后来这二十年的疯狂程度。或者可以说,我是即将消失的北京的最后见证人之一。一个1990年代出生的孩子,大概认为北京就是现在这样,天经地义,一个古城只是谣传而已。前几年也去过我的祖籍湖州和绍兴,以及上海、苏州,我相信这种毁灭是全国性的。我认为,不仅我这样的异乡人在自己故乡迷失了,所有不聋不傻的中国人全都在自己故乡迷失了。 [详细]

《三峡好人》的导演将剧中人物的命运放在三峡工程这个大背景中展开,以船、水和老屋(正在拆迁和等待拆迁的)等作为整个电影叙事展开的空间背景和意象,既敏锐地抓住了三峡的地域特征,又准确地捕捉住了正在步入现代性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使之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深刻的象征意蕴。如果说,漂泊不定的渡船表征我们所处的这个动态不定的时代,那么流动的水与正在拆迁中的老屋更强化了这一现代性特征。水淹没一切,也涤尽一切,无论是房子,街道,还是人与人的关系。[详细]
“旧城不是包袱,不是破烂,不是改造对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阮仪三说,它是民族文化传统,是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孕育生息城市的土壤。对于欧洲而言,只有“城市更新”,没有“旧城改造”一说。旧城改造的大动干戈,让城市脱胎换骨,而历史文化韵味却荡然无存。阮仪三很感慨,在欧洲的许多城市,还能找到15世纪的建筑,甚至一整条街。而在我们这里,明代的房屋都已经很稀有了。[详细]

曾经最安土重迁的中国人,可却面临找不到自己的根的窘境。“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样的回忆多数人怕是有过吧,只是现在却连最初的凭吊的场所都没有了,面对不断刷新高度的摩天大楼,终究只能是“多可喜,亦多可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