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0-09 19:16:43 凤凰文化 宗城
导语:2017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网络被鹿晗的一条“恋爱公告”刷爆,微博服务器甚至一度瘫痪。这不是鹿晗第一次震动微博了,2014年他的一条微博评论就创下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每当小鲜肉霸屏,总会有人哀叹“娱乐至死”,更不用说面对这些粉丝自发生成的狂欢。然而,评论人宗城认为即便在被知识分子推崇的年代里,娱乐也依然是大众最关心的东西,如今娱乐的力量只是被发展的媒介放大了,并不意味着娱乐到此“致死”。宗教般的粉丝帝国也不是件新鲜事,这种狂热的群体氛围历史上随处可见。从集体中解放的年轻个体,面对消费社会的来临,容易产生无能和焦虑的感觉,他们必须以消费行为获取身份认同,他们渴望重建一个集体来缓解孤独,于是粉丝团应运而生。身处其中的粉丝看似获得了主体感与自信,其实仍未逃出权力持有者和资源集中者合力设下的牢笼。他们看上去足够快乐、远离痛苦,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所爱的人,但这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消费逻辑与宗教幻觉统治的乌托邦。

“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鹿晗的一条动态,几秒种后,微博瘫痪了。
为什么仅仅一条“拍拖公示”,就足够让庞大的微博瞬间瘫痪?想到近几年,那些足够让微博震撼的事件,也无非是娱乐明星拍拖、分手、撕X、出轨、离婚,如薛之谦与李雨桐、马蓉与王宝强、白百合与陈羽凡、文章与姚笛,事关隐私,包含男女关系。过去,当卓伟这位的“爆料头子”在时,人们以为是卓伟们大肆炒作,才让娱乐明星的隐私铺天盖地,但卓伟沉寂后,娱乐八卦热闹如常。关心娱乐八卦,跟风流行句式,流量推手只是辅助,是公众自发成全了“鹿晗”的盛宴。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吗?
“娱乐至死”是公众最容易想到的原因,自从尼尔·波兹曼的书传到中国,我们这个时代就容易被归纳为“娱乐至死的时代”,尽管“娱乐至死”与“娱乐致死”存在微妙不同,公众的发散理解也稍微偏离了波兹曼的本意,但“娱乐至死”的论调,乍看之下确有道理。“老人”们常常哀叹年轻人不再关心思想,怒斥娱乐笼罩时代。作为对照,他们往往会将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期作为对比。
大众关心娱乐甚于思想,这一点我认同,准确来说,是大众关心个体情感、个体冲突甚于宏大命题、深度讨论。但是否意味着就在当下时代“娱乐至死”?或许未必。即便在被知识分子推崇的年代里,娱乐也依然是大众最关心的东西。五四新文化时期,现在我们都说它思潮激荡、青春澎湃,但那时候销量最好的读物,其实是八卦刊物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鸳鸯蝴蝶派主要写什么?男女情爱。又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听起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但且不说当时流行的港台娱乐潮,即便是那些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按明星偶像的路子包装的——如今是“鹿晗,我愿为你献身”,那时是“顾城,我愿为你而死”。
媒介的发展放大了娱乐的力量。互联网还没诞生时,官方趣味、贵族趣味统治一切,大众的趣味在明面上是被压制的。大家可以在街巷里弄谈论八卦隐私,而官僚与贵族在自己把持的文化机构发表符合自己品味的作品,彼此相隔遥远。但互联网兴起后,“禁锢”被稀释了,大众也终于找到了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大众趣味被瞬间展现出来,而标榜高雅趣味的他者无能为力。今天,娱乐如同脱缰野马,即便是“限娱令”,也不可能全然勒住。

就连许知远与马东对谈这样的文化事件,最后也被娱乐、窥私同化。许马事件,舆论一边倒的“夸马贬许”,批评许知远的采访技巧,赞赏马东的娴熟回应。但到了第二天,维护许知远的声音多了起来,一些议者借此引申出对“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大众与精英”等话题的探讨。可是,随着时间的流动,这些延伸话题却很快冷却了,而依然火热的,只是对许知远个人“解释权”的争夺,挺许派和倒许派互相对峙,许知远这一个体成为大众窥探的对象。于是,这场本可能演变为“知识分子在今天如何作为”的大讨论,收缩成了一场八卦个人的娱乐盛宴。实际上,这是一场“信息的镇压”,娱乐化、猎奇性的信息再次压缩深度议题的讨论空间。
另一个例子是今天的影视剧宣传。尴尬的现状是,知识分子创作的作品,很难通过严肃正经的宣传方式得到推广。2006年的《大明王朝1566》,人人说好,可一直叫好不叫座,看它的人局限在文化圈子。后来《大明王朝1566》逐渐有了影响力,不是靠文化人的卖力吆喝,而是官方表态和市民群体介入,恰恰在这个时候,《大明王朝1566》也被CP粉盯上了,海瑞与王用汲的交往被解读出满满的“基情”。
比起深度议题,娱乐看起来更轻松,成为谈资的门槛也更低。在互联网与饭局中,什么更容易成为谈资,什么就更容易传播开来,尼采或者加缪显然不如鹿晗和关晓彤方便扯淡。
娱乐话题在安全性上也比深度议题更有优势,这个大家都懂得。
宗教般的粉丝帝国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鲍曼就预言了消费主导型社会的来临。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体必须以消费行为来获取身份认同,否则自由化个体会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陷入“无能和焦虑这样的感觉”。这时的都市男女亟需一个精神慰藉缓解孤独感,甚至渴望重建一个集体——哪怕这个集体充满虚幻。
集体需要一个用来统和或者接受供奉的符号,于是一个个以偶像为中心如同宗教般的粉丝帝国便拔地而起。在外人看来,这些一会儿锁场、一会儿订制飞机、一会儿拉帮结派,甚至为了偶像要生要死的人们不可理喻。但在他们内部看来,他们保持理性、秩序井然,而偶像的点点滴滴已然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维护偶像,就是在维护他们的生活。
鹿晗与王俊凯是这个偶像生产过程的两个典型。2015年,一篇题为《鹿晗的粉丝帝国:疯狂外表下,她们是严守制度的信徒》的文章,详细描绘了这个粉丝群体的运作机制和内部景象。他们借助社交网络,在线上集结为一个又一个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若干核心成员,也都有各自的分工,他们会将团体与鹿晗的形象作为自己的事业去经营:关于鹿晗的东西要抢购;关于鹿晗的恶性新闻要去澄清;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鹿晗,他们可以倒逼媒体与大众关注;为了维持偶像的形象,他们在行动中严于律己。类似的情况也展现于王俊凯的粉丝团身上:为了给王俊凯过生日,粉丝们可以包下LED屏幕、报纸、机场地铁广告屏,动用直升机应援,甚至把生日祝福送到了纽约时代广场、上海迪士尼、北京水立方、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机场等世界多个地标所在之处,整个过程秩序井然,策划能力不亚于任何专业宣传机构。

一位王俊凯的粉丝代表曾说:“粉丝做的所有事情出发点都是出于对小凯的爱,其实我们也并没有特别强大,可能因为带着爱,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会报以万分谨慎和认真的态度,会不断地学习、总结提高自己应对复杂的舆论环境的能力,大众看到的每一次宣传背后也许是粉丝字斟句酌的考量。没有什么必须所为和不作为,我们做事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对小凯更好,他需要的时候粉丝就站出来作为,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安安静静地陪伴支持。”
爱、陪伴、谨慎、学习、让偶像更好,这是鹿晗、王俊凯乃至其他青春偶像的粉丝们常提的词汇。它们像一面镜子,照出这些藏在偶像身后的人的需求。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宗教帝国的行事逻辑里,帮助偶像更好,自己会快乐会满足,自己人生的意义也就有了。于是,他们心甘情愿为偶像服务,哪怕遭受外界嘲笑。
这个帝国不独少年,上班族、中年妇女也藏身其中。少女将他们视如爱人,大妈则把他们看作自家孩子。
一种虚幻的意义感在帝国中绚烂。由于偶像是最高的意义指向,且帝国内部构成了一个个紧密的群体,而外部则是被塑造出的“敌人”——那些冒犯偶像的人。于是,在粉丝们高度理性的行为中存在极度狂热的热情,这种热情有时是温和的,有时却充满“被迫害感”,仿佛敌人就要迎上前来,帝国内的人们应紧密团结、奋勇御敌。
这种氛围并不新鲜,在五四、在1968,乃至更遥远的时代,我们也都曾经历,粉丝们不过是将其明晃晃地再度呈现。在这个过程中,“群体的反省”仍然是彻底缺位的。
在反讽与自嘲的时代,现实中的人们被秩序里的权威压制,宠溺青春偶像则可以彰显自己的力量,获得主体感。虚幻的热情中,随着巨大能量的释放,权威的威信好像被一步步瓦解,而平民的自信得以一步步提升。
可他们真的获得主体地位了吗?权威真的被消解了吗?剥开狂热的外衣,帝国的子民们行为如此雷同,仅仅化作一个个为偶像可以做一切事情的棋子,他们自身的独立意识其实被狂热消解了。所以,他们往往不敢或不愿意指出偶像的错误、这个团体的隐忧,也丝毫不会为了诸如锁场这般行为有所反思。
当自嘲、戏谑、宠溺偶像甚至自我轻贱将严肃的判断力彻底吞没,粉丝对痛苦与剥削的抵抗和感知能力也将一步步退化,最终的结果是看起来成为精神的主人、潮流的主导,其实仍不过是活在最高权力持有者和资源集中者合力设下的牢笼里的顺民。他们看上去足够快乐、远离痛苦,他们有自己的事业、有所爱的人,但这不过是一个又一个消费逻辑与宗教幻觉统治的乌托邦。
宗城,90后撰稿人。
责编:徐鹏远 PN071

不闹革命的文化批评
凤凰网文化出品

时代文化观察者
微信扫一扫

2017-10-06 12:58:500

2017-10-05 21:32:260
2017-09-24 22:12:540

2017-09-22 11:08:470

2017-09-08 02:26:240

2018-07-11 14:080

2017-07-26 17:160

2017-06-27 18:510

2017-05-24 12:290

2017-03-16 12:230
2016-07-28 16:250

2016-06-23 12:380

2016-05-10 11:530

2015-12-14 16:310

2015-11-26 15:150
2018-10-27 19:520
2018-10-27 19:510
2018-10-27 19:450
2018-10-11 10:460
2018-08-21 10:200
2018-10-11 10:220
2018-08-31 11:040
2018-08-31 10:400
2018-08-21 10:390
2018-08-21 10:330
2018-10-27 18:330

2018-08-31 17:370
2018-08-31 10:530
2018-08-21 10:160

2018-08-11 12: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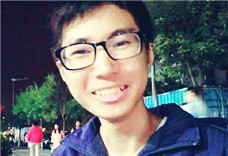
宗城,90后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