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1-17 18:38:24 凤凰文化 宗城
编者按:小众的诗歌难得成为热点,事情缘起老诗人食指对余秀华的批评。在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他认为余秀华作为从农村出来的诗人,从来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对小康生活的向往,不考虑人类的命运、祖国的未来,只向往喝喝咖啡、打打炮,评论界不应该把她捧红。余秀华则发布博客文章《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进行回应。
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背后,其实涵盖了两代诗人身份观的格格不入。不同的时代背景熔炼出不同时代诗人的底色。食指那一代人诗人写诗,表面上是诗人,心底里装着士大夫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类诗人看中诗歌的社会属性,风格往往高屋建瓴、纵横捭阖。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从“为社会写诗”转变为“为自我写诗”,他们更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刻意淡化集体的痕迹,甚至自觉与贵族式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欢迎庶民的入场。
当代文坛对非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很感兴趣,对乡村苦难、十年动荡、女性身体也很感兴趣。对于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诗人,他们今天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学热的余温,是他们背后那个经典的影子。而现在能够走红的诗人几乎都有“底层”或“农民”“工人”烙印。
如今,诗人仍被尊重,却已经从神坛跌落,甚至,诗人成为被同情、怜悯的符号,因为他们越来越被主流话语形容为“一群贫穷落寞而不被理解的人”。无论诗歌圈子里讨论怎么激烈,流派如何繁杂,诗歌也不再热门了。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论,最后很可能是自说自话,而当喧嚣过后,若有一天庶民时代走向黄昏,诗歌又会通往何方?

余秀华
食指那一代诗人,装着士大夫的情怀
若单纯从话语术的角度批评食指的用词,申斥他“过时”的诗歌理念和明显的阶级分化意识,诚然有道理,却会让讨论陷入浅薄,沦为“政治正确”的狂欢。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今天,食指的诗歌观念被视作“不合时宜”,而余秀华则赢得了中立者的集体同情?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背后,涵盖了两代诗人身份观的格格不入。
食指是朦胧诗的开创者,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代表作是《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是他1968年的作品,六十年代是他文思泉涌的时期,十年动荡断了一茬,但到了1978年,他又写出著名诗歌《疯狗》,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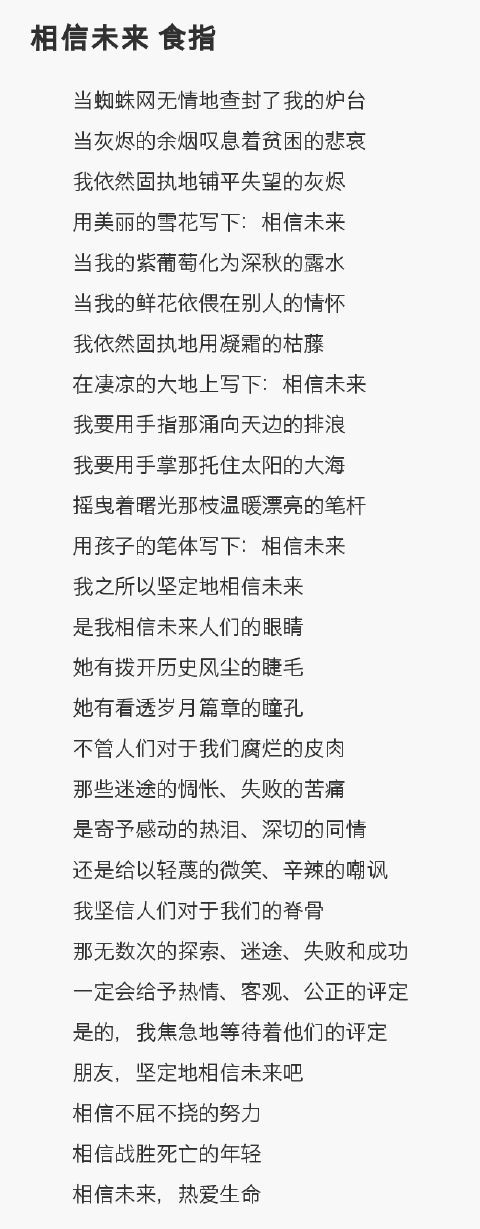
食指《相信未来》
余秀华与食指隔了三十年,她2009年正式写诗,2014年在《诗刊》发表作品,并配发了她的创作谈《摇摇晃晃的人间》,也是在那段时间,她开始走红,一些无良媒体给她冠以“脑瘫诗人”的外号,引得大众集体同情,但与此同时,她的诗歌天赋也被文坛和出版界关注,广西师大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后来又有同名纪录片。到如今,余秀华已经是一个在诗界有一席之地的诗人,甚至可以说——她是当代绝少的流行诗人。
不同的时代背景熔炼出不同时代诗人的底色。食指那一代人诗人写诗,表面上是诗人,心底里装着士大夫的情怀。他们和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这类诗人看中诗歌的社会属性,风格往往高屋建瓴、纵横捭阖。
而余秀华更聚焦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她的诗歌是个人的抒情、个人的感官体验,她认为“诗歌是一个很小我的事情”。由此生发出一点点哲学思辨,如“有时候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又如那句传播甚广的“告诉你稗子那提心吊胆的春”。
食指在批评中强调写诗要对历史负责,强调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未来,这是士大夫诗人典型的思维路径,用文言文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创作服务于这种观念,《相信未来》就是典型例子,一句“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地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将个人情感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将诗人的形象浓缩为“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战斗的人,这么多年,食指还是那个食指,时代却已不是他熟悉的时代。

食指
在他的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诗人聚焦于个人的矛盾,但这种“凝视个人”的努力最后仍会屈服于集体,被宏大的词汇所吞没。郭小川的《望星空》即如此。这首本为庆祝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的诗歌,花了诗人半年的功夫,乍看之下是一首典型的政治抒情诗,出现了“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座美妙的人民会堂”这样的诗句,但它又体现了高度个人的一面,甚至因此在五十年代末被抨击为“虚无主义”、“小资格调”,迷茫、惆怅是《望星空》不可忽略的情绪组成。
光是“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这三行诗,诗人就两次提到“惆怅”。可是,到了第四章,郭小川又回归宏大,回归对民族和人类的礼赞,高喊“人生虽是暂短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
他们在为社会写诗,为“人民”写诗,但在此,“人民”是一个高度虚化的符号,而士大夫的形象才是清晰的,食指这一代人把白话诗的社会属性发挥到极致。
现在走红的诗人带有“底层”或“农民”的烙印
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从“为社会写诗”转变为“为自我写诗”,他们更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刻意淡化集体的痕迹,甚至自觉与贵族式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欢迎庶民的入场。
有趣的是,食指的青春期同样身处庶民时代,但他们那一代诗人,无论是他,还是郭小川、贺敬之,甚至是作词的阎肃先生,他们都有礼赞平民的勇气,但他们的姿态都是自上而下的,而余秀华,她处在一个新式庶民时代——由网络构建的大众部落里,她很少呼吁关怀平民,但她写诗的视角是与平民对等的。

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所以,当食指倡导白话诗应回归“大众性”与“民族性”,看热闹的大众反而倾斜于余秀华这边,这一方面是由于余秀华近年来的高热度,另一方面跟大众对这两位诗人的“符号认知”也有关系。
在大众眼里,“为天地立心”的食指是一位老诗人、一位权威诗人,他已经进入经典,同时这也意味着他成为“过去时”,实际上,当食指患病后,他就已经一步步淡出大众视野,更有人感慨他成为“被祖国埋葬的诗人”。
而截然相反,余秀华被塑造为“进行时”,从底层诗人、农民诗人一步步走入公众视野,尽管她竭力撕下这些标签,一些评论者也建议将其归于“人”或“女人”的身份看待,而非农民、底层,但坦率而言,的确是后者构成了大众对余秀华的第一步认知。
这不是个例。如今,能够走红的诗人几乎都有“底层”或“农民”“工人”烙印。不只是余秀华,还比如打工诗人许立志、皮村文学小组的诗人群像等,虽然他们都强调自身主体性,反抗标签,但某种程度上,工厂、村镇的在地经验是他们的诗歌的鲜明特色,也是他们区别于学院诗人的地方。
当代文坛对非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很感兴趣,对乡村苦难、十年动荡、女性身体也很感兴趣。例如:二十一世纪走过来,“底层文学”总是时不时冒出来,吴义勤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就说过:“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范畴也是层出不穷......我们也看到了在‘底层文学热’背后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了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和遮蔽.....”但是,苦难并不等于艺术,基于苦难的“政治正确”也绝不该蒙蔽艺术的标准。
当然,我们还能看到北岛、西川、欧阳江河、于坚、韩东等人的身影,前不久,北岛在豆瓣开课还引起一批粉丝的热议,但这些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诗人,他们今天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学热的余温,是他们背后那个经典的影子。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新作,像欧阳江河,他仍然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但这已经不是一个依靠诗作出名的时代了,这个时代走红靠的是人设、是高度浓缩的符号气质。

北岛
诗歌从士大夫时代走向庶民时代
从食指到余秀华,国内诗歌从士大夫时代走向了庶民时代。这并非一蹴而就,而经历了三十年的流变。新中国成立后民众识字率的大幅提升为此埋下伏笔,不懂字,何以谈诗?在广大群众普遍是文盲的年代,诗歌乃至文学的话语权被牢牢控制在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手中,回望唐宋元明清,莫不如此。
但当大部分人普遍识字,文化传播的媒介亦迅速改变,文化精英的掌控权也随之松动。食指那一代人写诗,他们是写给当时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看,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她们的作品不只发在权威刊物,也发在网上,网民才是评议的主力军。
这在前互联网时代就露出端倪,八十年代,权威的地位就已经松动了,所以文学革命是一浪接一浪,青年人力气足,大有一副掀翻老子自个儿当家做主的气派。到了九十年代,“诗人之死”,文学热退潮。诗人很难再成为意见领袖,顾城、海子式的文学偶像成为历史。

海子
与此同时,诗歌开始“下移”,首先有“第三代诗人”,拿来西方的后现代流行词汇,刮起一股反英雄、反崇高的浪潮,继而又有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对着干,大有华山论剑的态势,甚至还有“下半身写作”,强调写作中的“身体性”,这一派的代表诗人沈浩波曾说:“‘下半身’一方面是指身体感,但更多的是指‘形而下’的‘下’,是很严肃的诗歌写作态度。”总而言之,早在九十年代,白话诗的走向就已经背弃了食指的理想,而余秀华是“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的继承者。
但无论诗歌圈子里讨论怎么激烈,流派如何繁杂,诗歌也不再热门了。千禧年后,诗人甚至被污名化。以“梨花体”、“乌青体”为代表,白话诗成为公众怀疑甚至嘲笑的对象。而像余秀华这样的诗人,即便有机会曝光在公众眼中,依靠的与其说是那些优秀的作品,不如说是媒体出于关怀而出现的集体动员与那些被文化工业制造的标签。
其实,诗歌一直以来都是小众的运动,即便在热烈浪漫的八十年代,写诗也更多是知识人的专利,专门的诗歌评议圈子并不广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以诗歌为引子生发出的社会话题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由此能让我们管窥社会价值判断的变化。

顾城
在八十年代,人们敬仰诗人,诗人之死如同偶像之死,那时候,诗人被供奉在一个神圣的位置。但如今,诗人仍被尊重,却已经从神坛跌落,甚至,诗人成为被同情、怜悯的符号,因为他们越来越被主流话语形容为“一群贫穷落寞而不被理解的人”。
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论,最后很可能是自说自话,而当喧嚣过后,若有一天庶民时代走向黄昏,诗歌又会通往何方?是走向AI时代,还是重回人类精英的怀抱?而身处庶民时代的诗人,又是否能写出永恒的诗篇?
这不是今人能解答的问题,而是交付时间的思索,下一个十年过后,当我们再回首这个时代和它的诗歌,答案也许就能浮出水面。
宗城,90后撰稿人
责编:游海洪 PN135

不闹革命的文化批评
凤凰网文化出品

时代文化观察者
微信扫一扫
2018-01-14 16:14:570

2017-11-29 09:26:560

2017-11-27 20:36:450
2017-11-24 18:20:550

2017-11-15 18:20:170

2018-07-11 14:080

2017-07-26 17:160

2017-06-27 18:510

2017-05-24 12:290

2017-03-16 12:230
2016-07-28 16:250

2016-06-23 12:380

2016-05-10 11:530

2015-12-14 16:310

2015-11-26 15:150
2018-10-27 19:520
2018-10-27 19:510
2018-10-27 19:450
2018-10-11 10:460
2018-08-21 10:200
2018-10-11 10:220
2018-08-31 11:040
2018-08-31 10:400
2018-08-21 10:390
2018-08-21 10:330
2018-10-27 18:330

2018-08-31 17:370
2018-08-31 10:530
2018-08-21 10:160

2018-08-11 12: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