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7-11 14:08:36 凤凰网文化 魏冰心

余秀华,图片来源: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
采访、撰文|魏冰心
余秀华最初被大家看到时,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红色符合大家对她的炽烈、滚烫的印象,后来出版的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封面上,在茂密田野里张开手臂的女人,也穿着红衣。
这件红色羽绒服,是因为三年多之前要来北京,余秀华的妈妈特意带她到镇上买的,没几家卖衣服的店,选来选去不是黑的就是灰的,于是就挑了个嫩点儿的,红色的,也“亮眼一点”。果不其然,这件红色羽绒服迅速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它几乎出现在了当时跟余秀华有关的所有报道里,经意地不经意地,它像一个鲜艳的暗示,暗示她的来途与去路。
“我刚出来的时候还是非常土气的,现在好一点了。”余秀华和我并排坐在会议室长长的桌子前,穿一件花色斜襟旗袍,改良过的宽松款式,补充道。
一些鸡蛋
2014年12月17日,余秀华第一次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参加《诗刊》为她策划的一场五人诗歌朗诵会。凤凰网读书频道也是这场朗诵会的主办方之一,我记得那是个工作日,午饭时主编说他要去人民大学参加一位“脑瘫女诗人”的朗诵会。有个同事问了句什么是“脑瘫”,但很快这个话题就终结了,我们转而聊了些别的,接着我和同事回办公室,主编背着书包去地铁站。
即便是对余秀华怀有十二分善意的《诗刊》,在最初的宣传里,也使用了“脑瘫”这个标签。这个时代太不缺新闻了,如果没有身残志坚的底层人设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耸动标题,余秀华可能依然在博客上寂寞地写着诗,没有印着她名字的书,没有以她为主角的获奖纪录片。
《诗刊》编辑刘年在一篇后记里提起,来北京参加朗诵会的时候,余秀华提了一些鸡蛋。这是我在关于余秀华的故事里听到的,最朴素感人的细节。站在妈妈身边,提着鸡蛋的余秀华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迎来什么,那一刻,只想对发表自己诗歌的编辑表示感谢。
几年过去,余秀华更多时候被描述成一个反叛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我见面时,她自己先打趣,“杨老师说了,今天不许对记者胡说八道,不许说‘他妈的’,不许说‘放屁’。”
她嘴里的杨老师,是她的编辑杨晓燕。余秀华的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记录,从确定选题到下印厂,仅用了9天。这本书的责编是时任图书品牌“理想国”大众馆主编的杨晓燕,后来杨晓燕离职去了另家出版机构,余秀华有了新书,也还是交给她来做。

余秀华
生活上,杨晓燕是余秀华的好朋友,“杨老师”、“余老师”这样互相称呼。杨晓燕说:“之前有家媒体主动来采访余老师,看到我给余老师补袜子,就把这个细节写进去。余老师的身体状况在那儿,她自己补不了袜子,这样做其实很正常。那篇稿子的导向我觉得有点问题……”杨晓燕希望媒体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余秀华的作品上,而不是一味强调其他的。
余秀华本人倒是不回避任何问题,随着她为更多人所知晓,各种争议接踵而至。余秀华走起路来会因为平衡问题倾斜身体,遇到批评和质疑,她反而挺直了身子,正面迎击。
“不管你写得比我好,还是不比我好,你都没有资格批评我。你对一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读她的诗歌,你哪来的权力来批评?你没有。”说到今年年初跟老一辈诗人食指的风波,余秀华还是一脸的不忿。
“屡屡回击是为了保护自己吗?”我问她。
“不是,最好的保护是不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引来更多声音。但我的性格做不到不说话。”说这话时余秀华摘了眼镜,眼前的世界模模糊糊。
海子的诗有语病

《无端欢喜》,余秀华著
余秀华这次来北京,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无端欢喜》。有点“佛系”的名字,封面上印一颗开了花的仙人掌,如果不是余秀华所写,恐怕要被当作鸡汤文了。很奇妙,余秀华有种消解词语的能力,“永恒”、“馈赠”、“礼赞”,这些其他作家觉得土掉渣的标题,她都大大方方用了,用得自然并且厚重。
人们想问的各种问题,她率先一一在书里写好了。
关于爱情,是:“我不知道该去埋怨谁,最后还是恨我自己,恨我的丑陋和残疾,这样的循环让我在尘世里悲哀行走:一个个俗不可耐的男人都无法喜欢我,真是失败。”
关于离婚,她明确写着:“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什么梦想,也对生活没有指望。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那就是离婚。这几年的幸运和荣光,最好的事情就是离婚。”
关于身体:“我感觉有一点沮丧:我如此引以为傲的旺盛的性欲其实和很多人是一样的。”
文章写于2015年-2017年,大致是成名三年以来的生活记录。这期间,离婚,母亲去世,她把这些变故与变化带来的心理感受写下,看起来毫无保留。
一次她从北京坐飞机到武汉,身上背着两个包,心情不好,走得格外艰难,摔了一跤。她写:“我想幸亏我妈妈没有跟着我,她如果看见了,该如何心疼?而她,再也不会跟着我了,许多日子,我在人群里没有看到过一个跟她相像的人,她就这样离开了我,离开得如此彻底,如此决绝。” 读来让人落泪。这篇文章后来取名《不知最冷是何情》,其中讲到父亲在母亲过世后不久,找了个情人。
可一旦你拿着书里的东西再去问她,她却不愿意认真对待了。我举出书里的一个观点,她说:“我那是瞎写的,早就忘了。”我有点惊讶,旋即又有点明白,她是以对待文学的态度在对待自己的作品,而我们大多数人,总想把那当作她的生活。
《我养的小狗,名叫小巫》是余秀华比较出名的一首诗。最早在人民大学的教室里,她站在讲台上全身颤抖着朗读的,也是这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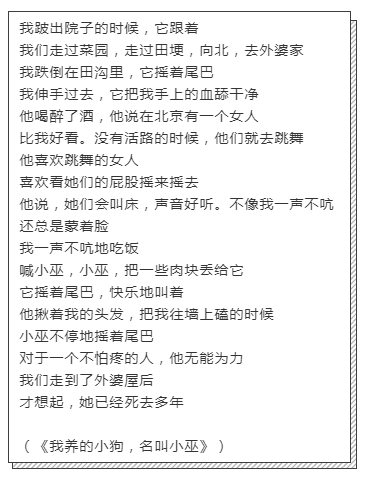
因为这首诗,人们纷纷以为她常年承受家暴。前夫是农民,在工地上干体力活,没什么文化,而余秀华身体有恙,掂起再轻巧的笔手都会抖,一强一弱,加上铁证如山一样的诗句,没错了,于是标题里带有“余秀华”和“家暴”的文章网络上一抓一大把。
其实余秀华自己从没这么说过,有记者就“家暴”发问,余秀华回答说:“他敢打我?”口吻虽然泼辣,却也是对这个可能会给前夫带来恶名的问题的化解。她很想跟前夫离婚,不惜花掉辛辛苦苦赚来的稿费,但没有投文学之机把天秤拉向自己这一边。
好奇余秀华写作上的师承,我开口问她读过哪些书。
以前因为穷,不敢瞎花钱,书看得很少,现在有了一些钱,看得也不多,她说:“像他们有人说一年看几百本书,我心想,我一年看几本就不错了。”一定要说出个名字的话,是海子。但余秀华马上又说:“后来我看出了他诗歌的很多毛病,又不喜欢了。”
海子的诗有什么毛病?
“有病句你都看不出来吗?”她反问。
不加微信

余秀华
余秀华跟我聊起家常。
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已经在武汉找到了工作;妈妈去世了,余秀华跟爸爸继续生活在横店——不是那个每年接待几百个剧组的影视基地横店,而是位于湖北钟祥市石牌镇的横店村——现在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他们住进新房子,家里的地被征收,爸爸也不用种地,而是在家附近上班,一天8个小时,在别人的葡萄园里锄草打农药。爸爸很勤快,除了上班还在鱼塘里养鱼,家里的空地上种着菜。一日三餐,爸爸做给她吃。
不像最早出名时候那样天天被记者围堵,但仍时常有不认识的人来看她,前几天还有个从瑞典过来的老太太,70多岁了,带着一个翻译。这些人不请自来,到村里一问,就知道哪个是余秀华家。也不干别的,就聊聊天,“聊聊天就走了。”
余秀华学会了在淘宝上买衣服,不喜欢穿裤装,喜欢连衣裙,花的、纯色的、低领的、吊带的,通通经过快递小哥之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运来。
至于写作,她坦言今年一直过得比较萎靡,起床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耗着,身体不太好,精神也困倦,东西写得少。
不大看她文章的爸爸老是担心她,她不结婚,等自己也离开了,她要怎么办,谁来照顾她?
“我还有儿子呢!幸亏我生了个儿子。”余秀华觉得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眼下可不想再结婚。
采访过程中余秀华的电话响了,她毫不犹豫地接听,还开了免提。通完话她介绍说这是《诗刊》长得很帅的一位编辑,还问我认不认识。
做采访之前,记者通常会准备一两个暖场问题,以便跟采访者建立愉快的聊天气氛。这次采访,场是余秀华暖的。刚坐下,余秀华就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白!不看了,太白了。”说着就把眼镜摘下,搁在桌子上。她冲着我微笑,眼皮双得很好看。
一场访谈加一顿午餐,我知道了她用手机小小的屏幕看完了大部头的《悲惨世界》,知道了她第二天晚上的饭局有几个人过来,甚至知道了她用的化妆品牌子叫“朵拉朵尚”……自信已经跟眼前的采访对象非常亲近,临别时我大胆提出:“加个微信吧?”
她拒绝了。
其实,采访时我还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觉得有人真正地了解你,走进过你的内心吗?
她说:“我不想让别人理解我,这个事儿太可怕了。”

余秀华
对话余秀华:小时候担心原子弹会不会把我炸了
“故事可以虚构,情感虚构不了”
凤凰网文化:新书叫《无端欢喜》,这是你平时的一个状态吗?没有什么理由就高兴。
余秀华:其实我平时的状态是无端泪流。(笑)我觉得无论是无端欢喜还是无端悲伤,都是源于对生命的热爱。欢喜好像更好一点,不要那么惨兮兮的。
凤凰网文化:你现在还住在横店,对吧?
余秀华:对。
凤凰网文化:平常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几点起床?
余秀华:我今年过得很萎靡,起床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度过。我今年身体就不太好,精神很困倦,身体很困倦,除了诗歌,写别的东西很少。
凤凰网文化:新书里没有今年写的文章吧?
余秀华:这是今年才出的,是前几年陆陆续续写的。
凤凰网文化:我看你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自传体小说……
余秀华:小说是前年写的。
凤凰网文化:那发得比较晚。
余秀华:我觉得自己写不好,也没拿出来给人看。有一天和《收获》的编辑碰上了,我说能不能把我的诗歌放在《收获》上边,人家说《收获》只发小说不发诗歌,我就说我也写过小说,但是写得很差,不能给别人看,他说不要紧,给我看看呗,反正我是没指望能发。结果我的名气把他的头给冲昏了,他拿给主编看,主编非常喜欢,就发了,都是被我的幸运给冲昏了头了。
凤凰网文化:你说写得不好,怎么个不好法?
余秀华:按照我们中国传统小说的标准来看,它不好。它没有多少设计感,很多东西就直接写出来,没有太多的虚构,如果再让我写,我可能会写一部虚构的东西。
凤凰网文化:“文体跨界”正好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当年余秋雨出版《借我一生》时抛出了“记忆文学”的说法,结果遭受了不少质疑,大家觉得记忆与文学之间存在着虚构和非虚构的基本写作伦理鸿沟,你怎么看?
余秀华: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小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诗歌到底是什么东西?诗歌你可以把它归为语言的艺术,那么小说呢?小说是不是语言的艺术?虚构就是一种情绪,一种感想,故事可以虚构,情感虚构不了,可以这样讲。
凤凰网文化:这本散文集里你提到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说你不太喜欢不明朗的、把握不了的事情,对吧?
余秀华:我是特别不喜欢那种稍微复杂一点的人际关系,遇到我就头疼得要命,恨不得逃跑,什么朋友、女性之间的事情,非常反感。我是一个特别直接和简单的人,我觉得应该想干嘛就干嘛,直截了当。
凤凰网文化:那你有时候表现出的桀骜不驯,“关你屁事”这种,是对你掌握不了的事情的一个应对吗?
余秀华:我不知道这样好不好,但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一个人,他可能在这个人世间获得了名利,获得了一些社会地位,但这些未必能够满足他自己的快感。当然有时候可以满足,但是不长久,很短暂。更多的时候自己是孤独的个体,作为一个人你如果处处被别人所牵制的话我觉得很失败,很不值得。
所以非常喜欢那些桀骜不驯的人,只要他不去危害社会,不去危害别人就可以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不一定做得到,我很想做到,我现在有很多纠结的时候,比如说我晚上会为一件事纠结的睡不着,白天你们来采访我,我又恢复成这个(一切没事的)样子。
凤凰网文化:遇到别人的批评就反击,有没有想过这样会显得不好?可能在别人看来是听不进批评?
余秀华:要是我爸,我就忍着。但是像别人,和我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我就想,不管你批评的是对是错,你都没有资格批评我。不管你写得比我好,还是不比我好,你没有资格对我指手划脚。我生气,我想说是谁给你的批评权力?你对一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读她的诗歌,你哪来的权力来批评?你没有。
凤凰网文化:回击是一种自我保护吗?
余秀华:回击别人不是保护,是对自我的一种伤害,最好的保护是不说话,你一说话可能会引来更多的声音。但是我做不到,性格做不到这点。
凤凰网文化:在回应一个事情之前会跟朋友商量吗?
余秀华:我跟很多朋友商量,有的朋友就说,别理他,你要装淑女,我说淑女也不是装出来的,我就没打算装成淑女,我就装个泼妇。
凤凰网文化:说到泼妇这个词,我昨天正好看到你的文章里写,你说你本身就是个农妇,农民的劣根性,你是有的。
余秀华:这个我很不爱听。
凤凰网文化:你自己写的。
余秀华:是我写的,我说农民的劣根性是指过去受教育的程度低,互相吵架的时候骂出的那些难听话,我估计你都没听过。农村在骂战的时候真的肮脏,人的狭隘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凤凰网文化:那你觉得现实生活中有人真的能够特别理解你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走进你的灵魂这种?
余秀华: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求别人能理解我。一个人他可能在一件事上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换另一件事他又不理解了,不可能完全理解的。我也不想让别人理解我,这个事太可怕了。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理解?
余秀华:不知道,我觉得没什么好处,理解我有什么好?
凤凰网文化:很多痛苦的源头不就是觉得别人不理解你,所以很孤独吗?
余秀华:和理解没有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不喜欢,你不喜欢这种关系你才会痛苦,并不是别人理不理解你。人很浅薄的,你一个浅薄的人去理解另外一个浅薄的人有啥意思?毫无意义。
凤凰网文化:你以前说自己是有一个封闭的自我世界的,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吗?
余秀华:一个人永远是封闭的,就算你现在看起来会参加很多活动,会接受一些采访,但其实内心和这些事情没什么关系,有自己独特的一个体系,很少能有人进来。我不知道我这个年纪是不是心性特别脆弱的时候,需要一个自己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也许年纪大了之后,会害怕孤独,这又不一定了。

余秀华在《朗读者》的舞台上跟董卿互动
“我生活在一个好年代”
凤凰网文化:之前你说因为你的手写起字来很费劲,所以才选择诗这种形式,因为诗是所有文体里字数最少的。
余秀华:对。
凤凰网文化:现在也写散文和小说,还挺长的,是因为用电脑方便多了?
余秀华:是啊,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好年代,年纪大的他遇不上这些东西,我好歹遇上了,挺好。
凤凰网文化:这个年代各方面更加便利,也能让更多人看到你的诗了。
余秀华:那个我才不管,他们应该感谢我。诗歌这么多年都是一种很文艺的状态,所以它需要找一个变态的人来刺激一下。所以找我来刺激一下。
凤凰网文化:很多人喜欢你的诗歌。
余秀华:我管他们喜欢我什么呢!好多人出于一种好奇吧,他们会觉得一个农妇,还是个脑瘫,他们有时候就把脑瘫和脑残联系在一起,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人为什么会写诗呢,他们想看看是啥样子的。这个我不在意。我现在还想解释一个问题,脑瘫不是脑残。
凤凰网文化:的确,很多人是对“余秀华”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也就是你作为诗人的“个人史”)感兴趣。那么现在我知道作家张悦然正在办一个“匿名写作”的比赛,彻底把作者的名字隐去,你想过要匿名一把吗?这样别人就不会关注你的身份了。
余秀华:我还是可以让别人一下子就看出来是我的。我觉得一个人写作的时候一定要形成自己的风格,让别人可以从人群里把你认出来,就像一个标志一样。
凤凰网文化:所以并不愿意把你的诗跟你的身份剥离开?
余秀华:哪个诗人会让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诗歌剥离呢?我的诗歌到现在并不高于多少人,这是肯定的,并不比别人高明很多。
当然了,也不差,属于中级水平,你把名字剥离出去,有的时候会认出来这个是余秀华写的,有的时候认不出来。因为我写诗的风格不仅一种,而且现在我也在不停地尝试变化。
凤凰网文化:现在的诗里面爱情诗居多。
余秀华:诗就是这样成的,比如对这个人动了心我写下来了,还没有过几天,完了,完了的过程我没有写,那是一个很烦心的过程。
凤凰网文化:你的作品与情感密切相关,但情感是很不稳定的,会不会担心有天感情被透支了,就没的可写呢?
余秀华:我觉得情诗可以写,别的东西也可以写。说不定我遇上哪个人又一下就喜欢他了,又写很多情诗。你不觉得很多作者都是这样吗?他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写了很多诗,因为这个人是他的灵感,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两个就怎么样了。
凤凰网文化:那肯定。你说你想尝试写别的类型的诗,是什么样的?
余秀华:诗歌还是要写生活,季节、动物、植物,这样的东西。但是我想,所有的诗歌都应该归结为情诗。为什么呢?因为有感情才可以写诗,没有感情写不了。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在写作上,你靠的是天分还是后期的学习?
余秀华:我不知道天分是什么,我后期的学习也不多,就稀里糊涂的。像他们有的人说,一年能看几百本书,我心想,我一年看几本就觉得很好了。
凤凰网文化:以前看的书都是从哪里来的?
余秀华:我以前看书很少,真的是没钱,不敢瞎花钱,基本上不买书,不买衣服,就那样过日子。
凤凰网文化:都没怎么看别人的就自己写了?
余秀华:没看,我基本上在写诗的时候没读过诗。
凤凰网文化:那就是天分了。
余秀华:没办法。
凤凰网文化:很多人写作的时候,倒不是说模仿,但他肯定会受某个人影响比较深,所以在你这里不存在这样一个人?
余秀华:当时看海子的诗,但看得不是很懂,觉得海子还行吧。但到后来我看出了他诗歌的很多毛病,又不喜欢了。
凤凰网文化:什么毛病呢?
余秀华:他的想象力没有问题,表达的方式没有问题,但是语言本身有问题。
凤凰网文化:语言本身有什么问题?
余秀华:有病句你没看出来吗?
凤凰网文化:写诗本来不就要创造语言?
余秀华:错。写诗恰好是要把话说清楚,并不是产生病句。为什么会觉得是病句?因为他说的道理你听不懂,你会觉得拗口。很多小诗人会觉得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就把自己语言写得陌生化,追求词语的陌生化,他会觉得是好诗。其实不是这样的,现造词语还是有多种问题的,这样的都不是好诗。要的是意象的陌生化,不是病句。很多时候我们无意地拔高了一个人,当然你如果现在去批评海子,他们会把你骂死。
凤凰网文化: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
余秀华:我觉得这样说很傻,有一次我骂汪国真,被我的粉丝骂了。
凤凰网文化:汪国真有很多粉丝。
余秀华:对,而且他的粉丝同时还是我的粉丝。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想过你的粉丝都是什么样的人?
余秀华:我的粉丝女性居多,女性三分之一,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都有一部分,然后学生再一部分。
凤凰网文化:你的身体状况让你写诗的时候多了一些内容,可以这样讲吧?
余秀华:感悟要深一点,感悟的角度会不一样一些,但是它也许更接近本质,也许变得离本质更远。
凤凰网文化:身体状态对写作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影响?语言风格,精神结构……
余秀华:肯定有,每个人的体质的不一样,都会产生影响,这是肯定的。因为你的身体和情绪和选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先天残疾,在选择之前它就培育了你的性格,敏感的性格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凤凰网文化:除了敏感,还有别的吗?
余秀华:还有焦虑。小时候一方面是迷信,有人说你这个身体的残疾是你前世做了坏事了,这辈子受惩罚。
凤凰网文化:谁跟你讲的这种话?
余秀华:我爸爸找那些信神的人,他们都这样讲。另一方面,那时候不是刚刚发明了原子弹,1964年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就成天听他们讲原子弹一发出来就可以把全世界毁灭,我担心会不会把我炸了。到了上学,就开始焦虑成绩不好。
凤凰网文化:你当时成绩不好吗?
余秀华:就是焦虑,生怕自己成绩不好,对自己要求有点高,怕自己成绩下降了。还有就是,那时候也会对未来产生期待,说未来我这个身体怎么办?总之就是一直很焦虑。到了结婚以后,更焦虑了,有很多事焦虑得很。

余秀华
成名带来最大的收获是金钱
凤凰网文化:假如让你选,身体没问题,但也可能没出名,你更想要哪一种?
余秀华:如果没有身体问题,我现在应该和你们差不多,是一个很好的很有能力的工作者,这个不可否认。但是如果文化基因在我的身体里的话,我一样会写诗,我觉得一个人的爱好是天生的,不管你做什么工作。我是个农民,我写诗,但如果我身体好,我自己开了个公司,我还是会写诗。写诗是我的自然流露。
凤凰网文化:出名这件事,你觉得给你带来的最好的部分是什么?是钱吗?
余秀华:那肯定钱是最重要的,你说一个人有名声没有钱他要名声干嘛?对吧?
凤凰网文化:你现在算是比较有钱的吗?
余秀华:不算,比他们差远了。
凤凰网文化:比谁们?
余秀华:我准备给儿子买个房子,但首付还有问题。
凤凰网文化:房子想买在哪里?
余秀华:在武汉。等我儿子稳定下来再说,我儿子也不急,我也不急,我也不想他结婚,结了婚很麻烦的。
凤凰网文化:他肯定是不会回农村了吧?
余秀华:现在没有农村了。你看那些读过书的哪有回农村的?如果回去了只能我养他。新农村建设,把我们家的地全部征了,等于我们家现在其实是没有地的。
凤凰网文化:爸爸也不干农活了?
余秀华:我爸爸现在打工了。别人有个葡萄园,他在这个葡萄园里干锄草打药这些事。
凤凰网文化:你文章里写,现在不太见得到前夫了对吧?
余秀华:对。我也不想见他。
凤凰网文化:他一直在外地打工,所以虽然在同个村子也见不到?
余秀华:他说他今年搞了点钱回去种树。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知道的?你俩还有联系?
余秀华:他跟我爸联系。在离婚之前他就不和我联系了,他都跟我爸联系。他这个人吧,不自信,什么事都依赖我爸。
凤凰网文化:在之前的一个采访里,范俭说你前夫即使打工也不思进取,在工地上打工也分上等活儿、下等活儿。
余秀华:他就会搬砖,技术活一样都不会。
凤凰网文化:看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想,他其实搬砖也很累,对吧?
余秀华:是啊。
凤凰网文化:我们其实很难要求一个人一定要有上进心,他难道不想轻松一点吗?在要求上进心这件事上,是不是有点苛刻了?
余秀华:当时我爸还没学过砌墙,但我爸自己都会,因为我爸太能干了。结婚以后他(前夫)什么都不会,我爸就教他,教他好多也教不会。他不是记性这方面的问题,他是学不进去,也不用心学,真是搞不懂。
没有进取心,他脾气还大,这就很麻烦。仔细一想,你从人的性格来分析他,是成立的。比如他没有进取心表现出来是自卑,但他又觉得我是个人,你为什么不尊重我,又会有自尊,自尊和自卑会放在同一个事情上,这样脾气就很大。其实我也是,别人骂我,我肯定还人家,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其实说起来,我和他的性格是一样的。
凤凰网文化:在之前的一个采访里,范俭(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导演,编者注)提到你为一个喜欢的男人很伤心。
余秀华:当时喜欢的是谁?
凤凰网文化:我不知道啊,没说名字。
余秀华:那我早就忘记了,喜欢一个人不会超过三天。
凤凰网文化:那这能是真喜欢吗?
余秀华: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想,我这辈子就喜欢他了,无论他以后对我怎么样我都喜欢他。结果过不了多久就觉得,这个傻X。
凤凰网文化:成名以后,你会更接近爱情吗?或者说爱情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吗?
余秀华:没有,我这么多年没接近过爱情,只是偶尔会产生一些冲动或者情感。如果谁现在说想和我结婚,我会撤腿就跑,害怕婚姻。我觉得自己特别矛盾,我特别渴望爱情,但是我又特别恐惧婚姻。
责编:游海洪 PN135

我们时代的心灵史
凤凰网文化出品

时代文化观察者
微信扫一扫

2017-07-26 17:16:310

2017-06-27 18:51:300

2017-05-24 12:29:030

2017-03-16 12:23:220

2017-02-09 15:05:480
2018-12-20 12:500
2018-12-19 10:180

2018-12-17 12:570
2018-11-16 12:210
2018-11-03 12:590
2016-07-28 16:250

2016-06-23 12:380

2016-05-10 11:530

2015-12-14 16:310

2015-11-26 15:150
2018-10-27 19:520
2018-10-27 19:510
2018-10-27 19:450
2018-10-11 10:460
2018-08-21 10:200
2018-10-11 10:220
2018-08-31 11:040
2018-08-31 10:400
2018-08-21 10:390
2018-08-21 10:330
2018-10-27 18:330

2018-08-31 17:370
2018-08-31 10:530
2018-08-21 10:160

2018-08-11 12: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