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9-08 10:25 凤凰文化 宗城
导语:二十一年前的今天,恰逢中秋佳节的前一日,美国加利福利亚,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七十五岁的张爱玲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溘然长逝。早年在《天才梦》里宣扬“出名要趁早”的她,晚年不接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不停地变换住所,如隐居者一般寄居于洛城大大小小的公寓中。《红玫瑰与白玫瑰》中那句“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冥冥之中竟成了对张爱玲自己人生的注脚。
张爱玲复杂的身世背景和传奇的人生经历,连同她那些体裁多样的作品,一并构成了蔚为大观的“张学”,回响经久不息。在评论人宗城看来,那些强加在张爱玲身上,甚嚣尘上的政治符号,经由时间的淘洗终将化为沉渣。理解张爱玲最好的方式,应当是贴近她本真的作家属性,探究她文本中独有的“癖好”,体察张爱玲式的悲哀——那种冷眼张看自己笔下被欲望主使,被命运播弄的痴男怨女,机关算尽,却逃脱不了低到尘埃里的那份世态炎凉。

张爱玲
谈及民国作家,绕不开张爱玲,但认真谈张爱玲,又并不容易。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作家,在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张爱玲关注的依然是男女情爱、家庭琐事。有关硝烟,她不过微开窗缝,于《封锁》处平静透露,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几笔勾勒。就像前南电影《谁在那儿歌唱》,明明是法西斯阴影下的故事,爆炸声却只在最后响起。以至于革命文学流行的年代,批评家说她格局小,小资习气浓厚。张爱玲是个复杂的作家,也因其复杂性,日后常摇身一变,成为不同论见者挥舞的棒子。女性写作的拥趸赞其为民国的先行者;阶级斗争的拥护家则斥其立场狭隘;热衷春花秋月的看客,又将她的恋爱史翻来覆去炒冷饭。
我们不如暂弃成见。既然张爱玲是位作家,且让我们回归其文本,在阅读中思考张爱玲的写作特点,分析她的写作习惯。毕竟,时代变迁,诸多根植于意识形态的争论终将化为沉渣,能留下来的,还是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作为张爱玲的读者,我自问对其研究未及透彻,只是对其文本,例如小说和杂文集,有过基于兴趣的探讨。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明显具有区别性的特点,流淌于她的作品中。对于这些特点,张爱玲也曾在文章中承认,这是她写作的癖好,并非无心之举。或许,正是这些癖好,如积木般组合成张爱玲作品之于时代的别样建筑,使这位上海女性,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一朵奇葩。
心里的蜘蛛模仿人类张灯结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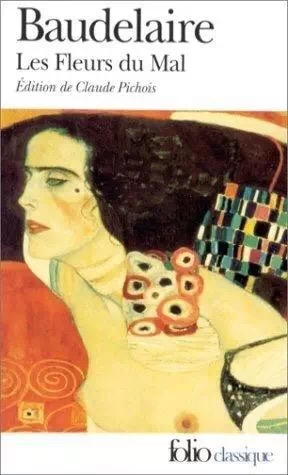
《恶之花》法文版封面
不知读者可曾注意,在运用意象时,张爱玲对蜘蛛网十分心仪,这源于她对波德莱尔的模仿。读过《恶之花》的张爱玲,记住了“一群哑然奇丑的蜘蛛,悄悄在我们的脑袋结网”这样形象的诗句。
一九三六年的《秋雨》,她这么写:“雨,像银灰色黏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地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
一九四三年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她说:“许许多多冷酷的思想像新织的蜘蛛网一般的飘黏在他的脸上,他摇摇头,竭力把那网子摆脱了。”
张爱玲喜欢蜘蛛网那种漂浮、粘稠,难以挣脱的感觉,她认为用其形容一些透明甚至无形的东西会很贴切。
不过,“蜘蛛网”只是张爱玲不明显的一个小癖好,比起接下来的几个,未免小巫见大巫。
斑斓的色彩如音符般起舞
高中时期,我曾借阅一位同学的张爱玲杂文集,看了一天,匆匆归还,书名已然忘了,但就是从那时起,我注意到张爱玲对色彩的敏感。读张爱玲的作品,颇觉富有肌理,她的文字透着光泽,一如她钟情那一件件旗袍。没有色彩的张爱玲,是无味的张爱玲。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疏疏几把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中学快毕业时,张爱玲的作品便隐隐有色彩缤纷的萌芽。这里截取的一段,是她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牛》的段落。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就很注重景物描写中的色彩勾勒。
再以同期的《秋雨》为例。这篇张爱玲十六岁写下的短文,虽然青涩,却也和《牛》一般,透露一个少女对色彩的痴迷。我曾在笔记本抄录了这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
“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料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
短短一段,五处色调,四种颜色,文字中俨然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图景。
张爱玲对色彩的敏感,她本人公开承认过,就在三年后那篇惊艳的《天才梦》:
“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如“珠灰”,“黄昏”,“婉妙”,“splendour”(辉煌,壮丽),“melancholy”(忧郁),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色彩癖发作的典型文本,在这篇小说中,张爱玲在描写人物的着装、环境的特点,甚至人的一举一动乃至思想活动时,都不厌其烦地抹上色彩。

电影《倾城之恋》剧照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有多么执迷于色彩?且看几处便明了: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蓝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
这是第二章的第五段上半截,我们数数,这半截就有了九处描写关乎色彩,要知道,这里面也不过出现了十处实物。
第四章,写到徐先生徐太太上船,又有:
“好容易船靠了岸,她方才有机会到甲板上看看海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这回,不但色彩鲜艳,而且从静态转为动态,一下子活了起来,张爱玲仿佛挥舞了一节鞭子,让色彩任她驱驰。
紧接着的下一段,张爱玲还不过瘾,继续挥墨:
“那车驰出了闹市,翻山越岭,走了多时,一路只见黄土崖,红土崖,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露出蓝绿色的海。”
一句话囊括四种颜色,而且毫不牵强。张爱玲对色彩的运用,并非只是单纯的对所见之景的机械搬运,她笔下的色彩,有时也被赋予她意识中的联想和变形,试问,现实中,又有谁的声音是“灰暗而轻飘”,沾染颜色的呢?这样的色彩,毋宁说是在作者的脑海,对那个时刻,那个人物状态的还原。张爱玲运用色彩的这一特质,让我联想起一位当代作家,也就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阅读莫言小说的读者亦无法忽略莫言对色彩的偏爱,色彩甚至是他营造所谓魔幻氛围的重要工具,要说这种法子,三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已然有意识地尝试,不过,客观地说,莫言在色彩之于魔幻感的渲染上的努力,比张爱玲更前进了一步。
出于好奇,我曾统计过,小说《倾城之恋》中,哪些色彩出现的频率较高(不包括人名地名,同一处对同一事物的重复色彩记为一次,“粉刷”这类词不计入),结果显示:
红色出现次数最多,出现了十九次。第二是黑色,十六次。接下来,分别有:绿色十四次,黄色十三次,白色十一次,金色九次,银色五次,灰色、蓝色、粉红色皆为四次,青色三次,紫色两次,灰白、橘红、蓝绿、玄色、紫蓝、黄绿、青黄、蜜合色各一次。
巧合的是,张爱玲颇喜欢研究的《红楼梦》,正好也有一红字。
以地理小空间,烘托时代大格局
小说总在相似地点发生,空间的格调如出一辙,这是一些批评家断定张爱玲写作格局小的依据之一,不过,以空间大小论格局,未免牵强。否则,写《茶馆》的老舍、滞留高密不走的莫言、呈现《曼斯菲尔德庄园》的简·奥斯汀都得戴这个帽子。
要说张爱玲笔下那些发生在狭窄的空间内的故事,最典型的还得数《封锁》。

电车中的王佳芝与邝裕民(电影《色,戒》剧照)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封锁》着力于描绘一对男女在公车封锁时发生的非常态行为。一段短暂的情愫,封锁结束后,烟消云散,一切又都复原。小说中,封锁的设定为人物的非常态行为创造了合理条件,也从一开始就让小说处于一种压抑、沉静又暗涌焦躁的氛围。
而收入《传奇》的诸多小说,主要人物所游走的空间也非常有限。《沉香屑·第一炉香》,熟悉的香港,葛薇龙、梁太太、乔琪的主要活动舞台在梁太太华贵的家;《沉香屑·第二炉香》,对话大抵在几个人物的住所和华南大学里;《茉莉香片》,香港,人物所在的校园和家庭;《心经》换了个地儿,另一个张爱玲挂怀的城市——上海,《金锁记》也在这;《倾城之恋》,又回到香港了。
香港和上海是张爱玲小说分量很重的地标,基本相当于鲁镇之于鲁迅、但泽之于格拉斯、伦敦之于狄更斯、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克纳。
聪慧比喻难掩世态苍凉
有关张爱玲运用的比喻,我们不妨以同样收入《传奇》的小说《沉香屑第二炉香》为范本。这篇中篇小说不长,却不缺令人眼前一亮的比喻。
且看一处:
“至于其他的人,香港中等以上的英国社会,对于那些人,他有什么话可说呢?那些人,男的像一只一只白铁小闹钟,按着时候吃饭、喝茶、坐马桶、坐公事房,脑筋里除了钟摆的滴答外什么都没有......也许是因为东方炎热的气候的影响,钟不大准了,可是一架钟还是一架钟。”

毛姆笔下的费恩医生,举手投足俨然一只“白铁小闹钟”(电影《面纱》剧照)
这是《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张爱玲讽刺生活在香港的所谓上流人用的比喻。白铁小闹钟是西洋传来的玩意,任务就是报时,给人的感觉是单调和机械,用来形容模仿英国绅士派头,陷入套路而不自知的部分香港男人,新奇、精准且有趣。况且,他们也惯用这白铁小闹钟,在当时,他们好用这玩意看时间。
这短短一段,就展现了张爱玲恰到好处的比喻功力,也是一个天才作家异于常人的敏感、细腻和天马行空的联想的体现,试问,形容生活单调乏味又装派头的男人,想到白铁小闹钟的能有几人?
张爱玲奇妙又贴近生活的比喻,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俯拾皆是。试摘几处:
形容罗杰安白登在高音的世界获取的快乐,张爱玲如是写:
“他的庞大的快乐,在他的烧热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蝉一般,无休无歇地叫着:“吱......吱......吱......”一阵阵清烈的歌声,细,细得要断了;然而震得人发聋。”
形容克荔门婷的稻黄色头发,张爱玲如是写:
“克荔门婷有顽劣的稻黄色头发,烫得不太好,像一担柴似的堆在肩上。”
同样是写头发,形容罗杰安白登的妻子愫细,又有大不同:
“他的新娘的头发是轻金色的,将手放在她的头发里面,手背上仿佛吹过沙漠的风,风里含着一蓬一蓬的金沙,干爽的、温柔的,扑在人身上痒痒地。这痒像蜷缩在你怀里的猫,它的绒毛剐蹭你的肌肤。”
愫细的母亲——蜜秋儿太太,大热天,她的口上满是汗,张爱玲写道:“像生了一嘴的银白胡子渣儿。”而当愫细哭了,泪水糊满了眼睛,又要找手绢子,便是“像盲人似的摸索着”。
张爱玲也没有放过巴克先生头顶正中却只余下光荡荡的鲜红的脑勺子,她说,这“像一只喜蛋”。
也有一些化虚为实的比喻。比如,当我们形容一个人颇让人愣然的笑声,我们如何说?
《沉香屑第二炉香》有:“他的笑声像一串鞭炮上面炸得稀碎的小红布条子,跳在空中蹦回到他脸上,抽打他的面颊。”
张爱玲的比喻大抵不落俗套,可我们仔细留心,这些比喻又都是生活中稀松平常的食物。闹钟、蝉、柴、沙漠的风、银白胡子渣儿、盲人的动作、喜蛋、蜘蛛网、鞭炮上炸碎的小红布条子...当中大多是常人轻易能接触或认知的,这让我们感知这些意向时并不吃力,也更能了解它所要传递的状态。同时,张爱玲的比喻擅长将静物,或者流动的虚的东西,比如意识、思想、情绪,动态实体化,鞭炮上炸碎的小红布条子就是典例。

写作《围城》时期的钱锺书
提及文人的比喻功力,看客往往想到钱钟书,毕竟,《围城》这本知识分子小说留给我们太多令人或是捧腹,或是叹服的比喻,但从晚清、民国一路走过来的那一辈,同时代的张爱玲,比喻的火候也值得一说。如果说,钱钟书的比喻,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狡黠,以及文人嘲弄的戏谑,那么张爱玲的比喻,在戏谑的同时,也时而流露出一位上海女性的聪慧和局外人的凉薄。
结尾流出壅塞的忧伤
张爱玲在《文章存心自己的文章》中如是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事实上,张爱玲也的确长时间内贯彻了她的喜好,最明显的便是她笔下的结尾。
《沉香屑第二炉香》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水沸了,他把水壶移过一边,煤气的火光,像一朵硕大的黑心的蓝菊花,细长的花瓣向里拳曲着。他把火渐渐关小了,花瓣子渐渐的短了,短了,快没有了,只剩下一圈齐整的小蓝牙齿,牙齿也渐渐地隐去了,但是在完全消灭之前,突然向外一扑,伸为一两寸长的尖利的獠牙,只一刹那,就“拍”的一炸,化为乌有。他把煤气关了,又关了门,上了闩,然后重新开了煤气,但是这一次他没有擦火柴点上火。煤气所特有的幽幽的甜味,逐渐加浓,同时罗杰安白登的这一炉香却渐渐的淡了下去。沉香屑烧完了,火熄了,灰冷了。”
张爱玲作品的结尾,往往是冷色调,令人有些怅然的。像苍凉、灰色、冷、眼泪这般字眼,张爱玲在结尾中毫不吝啬地使用,因为,她认为这是对读者的一种启示。
到了《迟暮》,结尾是这样的:
“灯光绿黯黯的,更显出夜半的苍凉。在暗室的一隅,发出一声声凄切凝重的磬声,和着轻轻的喃喃的模模糊糊的诵经声...她心里千回百转地想,接着,一滴冷的泪珠流到冷的嘴唇上,封住了想说话又说不出的颤动着的口。”
《有女同车》:
“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小说《花凋》结尾出奇地简短,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她死在三星期后。”
《茉莉香片》的结尾,女主人公丹朱倒是捡回一条命,但自卑孤僻,伤害了丹朱的聂传庆,恐慌,胆颤,“眼泪直淌下来。嘴部掣动了一下,仿佛想笑,可又动弹不得,脸上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身上也像冻上了一层冰壳子。”
接下来的短篇《心经》,女主人公小寒“伸出手臂来,攀住她母亲的脖子,哭了”。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冷冷清清,这是我读罢这些结尾,映入脑海的头四个字。读张爱玲的小说,令我感到,是凉透的血,熄灭的火,是封锁的城市,冬天的灵魂。张爱玲式的悲哀,是“如匪浣衣”般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杂乱不洁,流出壅塞的忧伤,用江南的人的话说:“心里很‘雾数’。”
张爱玲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冷静地看着自己笔下的人物顺着命运的河流,流走,消失。最后,不过一滴蚊子血的叹息,满是虱子的嘲弄。

责编:杜鑫茂 PN036

不闹革命的文化批评
凤凰网文化出品

时代文化观察者
微信扫一扫

2016-09-06 09:100

2016-09-03 16:510

2016-09-02 13:090

2016-09-01 11:100

2016-08-27 17:300

2018-07-11 14:080

2017-07-26 17:160

2017-06-27 18:510

2017-05-24 12:290

2017-03-16 12:230
2016-07-28 16:250

2016-06-23 12:380

2016-05-10 11:530

2015-12-14 16:310

2015-11-26 15:150
2018-10-27 19:520
2018-10-27 19:510
2018-10-27 19:450
2018-10-11 10:460
2018-08-21 10:200
2018-10-11 10:220
2018-08-31 11:040
2018-08-31 10:400
2018-08-21 10:390
2018-08-21 10:330
2018-10-27 18:330

2018-08-31 17:370
2018-08-31 10:530
2018-08-21 10:160

2018-08-11 12: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