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1-19 14:10:12 凤凰文化 何可人

马家辉(廖伟棠摄)
北方的框,对不起,有点冒犯
香港人马家辉,正在北京做一个直播节目。空荡的书店二层,他和一位北京的书业媒体人对坐而谈,气氛渐渐微妙,甚至有些尴尬。
因为《锵锵三人行》,马家辉成为内地最为人所知的香港人之一。这次来北京,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宣传自己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龙头凤尾》。这场直播,正是为此。
对谈主持人,资深书业媒体人T老师,用马家辉的话来说,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读书人”。乐呵呵的北京爷们,开场时不经意说了句:“这部小说大概草草看过……”“名嘴”马爷,捉住了这个笑点或槽点,笑着捍卫小说家的尊严:“什么叫草草?应该很认真地看啊!哦,才拿到书……对不起,那是我们的错。应该早一点给你。”
一场偏离套路的开场白,预示着一场对话注定的频道错位。《龙头凤尾》,这个发生在香港20世纪三四十年的江湖故事,远离21世纪的中国梦太多,像是巨幅拼图的一块边角碎片,或是一段可以被割弃的盲肠。小说主人公,广东乡下仔陆北才,偷渡到香港求生存,经历青帮、军统、汪伪、英、日间暗战,上位成香港洪门孙兴社龙头“南爷”,并与英国殖民官员张迪臣发生一段“断背”畸恋——故事的语言、故事情节,主人公的性格,都带着极强的香港特性——这带给北方读者T老师许多陌生的阅读感受。
T老师并没将这份陌生感放在心上。像以前主持的其他活动一样,他按照流程对小说作者马家辉发问:“我看这本小说,因为用香港方言写,相对来说难读一点”、“读起来让我满头雾水,为什么要写一个完全凭运气在混的小人物?”、“这个人太现代了,不太容易理解,不像骆驼祥子,我们理解的1930年代的中国人是老实巴交的”……对面的马家辉表情渐渐严肃,他开始意识到,这段南来的香江演义,在这位阅读广泛,思想深厚的北方读书人的经验里,竟遭遇了“霾”。
问题在哪里?收起戏谑和调侃,马家辉逐一解释起种种“费解”处:1930年代的香港大势,岭南的民间语言环境,深入黎庶的市民文化,南方人的生猛精神等等,都是来自北方的读者理解这个故事的必要。
T老师笑眯眯地点头虚应,没想着较真。然而马家辉没打算敷衍这些分歧,操着特色的港普,他语气铿锵地回应:
“你心中有一个框——对不起,有点冒犯——这个框,我称为“北方的框”,北方人某一类很认真、诚恳的、有深度的读书人的框……我觉得有个关键:南北差异。你刚才的叙述,我感觉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人,对于‘一个中国人应该是怎么样’的判断。
但当我们愿意把坐标转出,比如从北转到南,比如从男女之间的角度转出来,稍稍开放,许多我们以前觉得不可能发生、很荒诞的事情,原来对于生存在某个地域,不同环境的人来说,那是很正常,是本来就这样的。只不过时代环境要让它隐藏成为秘密,把它压抑起来。”
尽管T老师谦逊平和,马爷也一再为自己的“冒犯”道歉,但左支右绌间,二人的频道始终难以对接——其实他们之间的年龄只相差三岁,算得上是同代人。
好在直播时间不长,一小时结束后,马家辉去室外独自抽了一支雪茄。上前找他攀谈,他恢复轻松,谈笑风生。只是在被问到对刚刚经历的龃龉作何感受时,默不做声。一支烟抽毕,马家辉推门入室,掀开帘子时喃喃:我太刻薄了。
不够顺畅的对谈,让当事人之一竟需要事后反省,显然,它不那么成功,摩擦出许多毛刺和分叉,隔膜或迷障。但也是因为这些不顺滑的毛刺,激发了马家辉本能的捍卫立场。他曾在小说中说过“香港人什么事都开门见山,不知婉转为何物”,在北京这一遭,他由衷实践了这个内心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对谈算不得失败:它让来自两种历史和现实的人面对面——比如香港的马先生和北京的T老师——用不能被即时修饰的直接,袒露出双方理解和同享经验的艰难。
像是一个时兴的隐喻,种种谬误与层层辩论后,大河还是你的大河,浪花只能是我的浪花。此岸的波浪终究难拍上对岸的河滩。
性史,痛史
马家辉此行北京宣传,曾有一站前往清华大学演讲。讲座由一身西装的年轻女大学生宣布开始,开腔即是一句:“八十年前的香港,这一段痛史……”大的话语套路,和稚嫩的孩子气声和表情形成反差。
马家辉给大学生们讲“中英谈判”,绘声绘色地编排“英国婆娘”与“四川老爷子”相怼的场面。台下笑成一团。讲完段子,马爷归总一句“历史就是历史喇!”
大历史里,1936年,这一年的中国大陆,鲁迅在上海去世;老舍起笔创作《骆驼祥子》;共产党从联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发生;毛泽东填下《沁园春·雪》……对香港来说,1936年,是夹在港英政府、中国内乱与日本侵华的夹缝里的人心惶然。帮英国的是鬼佬走狗,屈服于日本威胁的是汉奸,帮中国两党的呢?也不得善终。香港人在不能自主的感情中,沉默地迎接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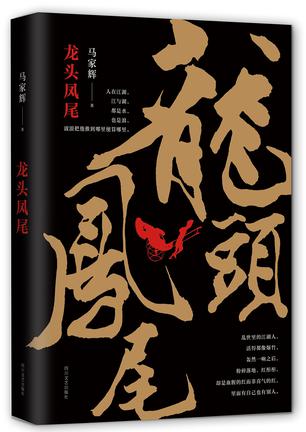
内地版《龙头凤尾》封面 2016年10月出版
1936年的一段狭邪,写成2016年的《龙头凤尾》。国家大史、江湖大势都只是故事背景,被小说里的“情爱乌托邦”切得零碎。有人说,情痴有余,大局不足。以阅读史家正典为痛快事的读者,未必把80年前的一段鸳鸯蝴蝶梦当真。隔岸观火的王德威有洞明,于天地玄黄里,透视《龙头凤尾》:“是性史——及心史。”
“性史”不难理解。《龙头凤尾》开篇,劈头一段是年幼的“我”窥看外公坐食“牛宾周(牛鞭)”的白描。你看马家辉怎么写:“碟子里盛着一根长条状的粗黑物,像塑胶不是塑胶,似木头并非木头,大约有八九寸长,像烤焦了的香蕉,发出吱吱细声仿佛仍有生命,随时会突然跳到半空敲打我外公的头。外公用筷子把它夹起,蘸点橘红色的辣椒酱,放进嘴里一口口地咬吃,眼睛半张半阖,眼珠子悬浮在眼白间,像旭日初升,表情无比满足……”画面暗黑暧昧,让人瞠目。马家辉来北京做新书沙龙演讲,更以书中生猛咸湿的“金盆洗屌”片段开章:江湖响当当的人物哨牙炳,半生无女不欢,59岁忽然要举办“金盆洗屌”仪式,决心以后除了老婆再不碰其他女人。在仪式上,一群往日亲近女子,排着队瞻仰、抚摸,甚至要吻别他的“宾周”……马家辉讲得生动,台下的观众也听得入境。诡异又耸动的片段,男同性恋,拉拉,种种酷儿故事,从尺度上来说,对年轻一代的大陆读者来说,毫无接受难度。
倒是马家辉问,“你们知道什么叫‘一楼一凤’吗?”同学们哑然。是了,“一楼一凤”,对大陆观众来说,常在《陀枪师姐》等上世纪末TVB时装剧里听到。如今华人娱乐中心早已北上,TVB的下坡路不像是走下去的,更似是滚下去的,不怪年轻的观众不识粤语片里曾经亲切的市井名词。
若还要追问30年代的香江风月,能说出电影《胭脂扣》就算是属惊喜了吧。在小说《龙头凤尾》里,从香港北岸的水坑口到塘西风月,从塘西风月到1935年香港全面禁娼,从石塘咀四大名寨里的姐妹到苏丝黄式的酒吧女郎……烈火烹油地铺陈,鲜花着锦地凭吊,小说家马家辉用笔对一段“烟花史话”溢美颇多——并不仅是因为“妓女作为香港隐喻”这种殖民书写套路,而是与他自己切实的个人经历有大关系。童年时代,家里来来往往聊天搓麻的莺莺燕燕,马家辉太熟悉不过。他看多了那些匆匆离开大陆逃往香港,最终沦落舞女或流莺的女人们,也同情她们的不幸。
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做主持的时候,马家辉介绍过香港历史爱好者、收藏家郑宝鸿的著作《香江风月》,从娼妓故事谈了到香港传奇。名妓花影恨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
塘西红牌阿姑花影恨,本名朱秀珍。常在香港组织筹款,支持抗日救援风灾水灾。最后一次搞筹款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名为“塘西歌姬七七义唱”,当夜有五十八位歌姬登台献唱,她独自筹得七百多元,全场冠军。
国民党将军吴奇愇在报上撰诗赞颂她:“短曲长歌吊国魂,几时弓箭靖邪氛?儿家自有兴亡感,脱却金钗为犒军”。
马家辉肯定不止一次想象过“塘西歌姬七七义唱”的场面。五十八位歌女,各自有什么样的心肠,有怎样的故事?现实中的花影恨在“七七义唱”四个月后,在22岁生日的晚上,感怀身世无限悲情,留下遗言“生无可恋甘为鬼”,于家中吞鸦片膏自尽,葬在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马家辉拜访了她,记得她的墓位于“祸”字区,十二段,十三台,廿二号,碑石上刻着简单一行字:朱秀珍姑娘之墓。
念念不忘,马家辉把花影恨故事借由《龙头凤尾》里一群妓女——可爱的“湾仔天使”之嘴,又说了一遍。
小说里对“宾周”也好、对男男女女们的情欲描写也好,不可谓不“淫”。古人力辨“情”“淫”二字,以为泾渭分明,《龙头凤尾》这故事,却写实了“情既相逢必主淫”。陆南才的情欲之路爱恨痴缠,颠龙倒凤——这是通过个人身世,树立一则国家寓言的典型写法。
多年来致力于寻找香港文学源头的学者陈国球说:“由‘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的城市香港,上上下下竞以‘忘情’隐没身世。总有些人希望‘香港’只活在当下,遗落过去,没有记忆,没有‘我’”(陈国球:《香港的抒情史》)。生于此长于此,人们在香港起居作息,在这里喜怒哀愁、恩怨爱恨,在这里言谈歌咏……岂曰无情?马家辉也说:“但凡在香港长大的香港人都有一堆说不尽的奶茶菠萝包的往事,也或多或少孕育出一份香港是我家的情怀,却不是每一个都肯在学成之后对香港有所承担。”他有此大志。曾经的意见领袖,变身成“不愿意再讲‘冒犯’语言”的小说家。收起直白,马家辉在奶茶菠萝包往事之外,偏偏讲一个“情天情海幻情深”的故事。他向探讨国家政治的重压下,“人”与“情”如何进退颉颃?马家辉将此“情”栖遁在这段颠龙倒凤的“香港往事”上,一段性史,方可载心。

马家辉(廖伟棠摄)
“回不去了”
“湾仔少年”马家辉出生在1963年,距香港历史最重要年份之一的1967年,还有四年。四年后,北风把革命浪潮吹送上香港岛,街上红旗插遍,大字报纸处处可见。左仔们拿着红宝书和炸弹上街,与警察对峙冲突,掀起五月暴乱。这一年,是香港人心里难以平复的伤痛记忆。《龙头凤尾》里“金盆洗屌”的故事被马家辉设置在1967,所指明显。
以此为分水岭,岛上心怀各异的移民难民居民们,渐渐不再一心“中原北望”,代时而起的,是“我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识。马家辉生于此间,成长于香港飞速发展的70年代,成为本地成长典型一代。飞扬岁月里,燠热湿闷的夜,和二三知己坐在茶餐厅,饮上一杯咸柠七,打火点烟,吞云吐雾间用粗口探究社会主义未来的光景,这是一代马家辉们的“男人回忆”。
只是这世界变得不可谓不急。无限憧憬,美丽误会,千禧年已然过去,香港已非“独家村”。连茶餐厅内竟然都禁了烟!“飞扬岁月毕竟终结,”人过中年,马家辉感慨:“我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香港70年代、80年代,经历了香港变成香港,经历了1997年的转变,再从97年到现在的转变——你们都懂的——我觉得整个香港变得太多了,好多事情我们回不去,错过了太多的东西。”
2016年,马家辉自称踏入初老之年,除了写出人生第一部小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头一遭——以决审评委的身份参与台湾金马奖工作。这个经历对他来说很重要,虽然他最常公开分享的,是影后影帝台下的逗趣故事——娱乐八卦总是开心又讨喜。唯有一次,在北京《龙头凤尾》的沙龙上,有读者问他,是否给香港参赛电影《树大招风》投票?
“《树大招风》我喜欢看。”他说。金马奖之前他就已看过电影三遍。马家辉喜欢那个故事,都市传奇里,总有一处弥漫着恐惧和自赎般的焦虑。电影参赛时,不少评委——包括来自大陆的陈建斌,疑惑为什么要出现97年的敏感镜头?马家辉对他们解释电影的意义,电影的语言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说:“97年以前香港的情绪是那样的,这是香港那时候的时代精神。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1997年对香港很重要,改朝换代。有好多东西都失掉了,你失去了才知道,才说‘原来回不去了’。”
马家辉认为,这种惘然和自己的小说《龙头凤尾》有相通的地方——错过。“我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我不晓得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是香港人的问题,总觉得自己错过了太多。回不去了。”他反复说。
“册!满城都是汉奸!”
电影《树大招风》的一些情节让部分观众难以理解甚至接受,小说《龙头凤尾》也撞上了“北方的框”。小说主人公南爷,一个身负国仇家恨的中国人,在英国殖民者、军统势力和日本鬼子的三方势力里讨巧发迹;做汉奸,委屈隐忍地爱上男人——一个英国殖民官员。这样的角色“畸形”一览无余。也招来了种种不解,甚至觉得认为“驳杂”:“是不是马家辉写糊涂了?”
被视“畸形”的,不止角色;撞上北方沙文主义的,更有故事发生处——香港。
回溯最初,香港这个南中国无名的边陲小岛,岛民或渔或耕,原是一个“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所在。近代风云里,几番地理和政治上的不同界定,香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放大变形的过程。
《龙头凤尾》里有一段,上海的杜月笙来到香港运筹,望着维多利亚港的金色斜阳,想着岛内诸人诸事,忍不住冷哼一句:“册!满城都是汉奸!”杜老板的生动面目固然是小说家的笔法,现实中各种对香港居高临下的批评也从来不少。
30年代亲临香港的左翼文化人曾明确打出香港“畸形”说:文人石辟澜1933年撰文《从谈风月说到香港文坛今后的动向》,认为“香港是一个畸形发展的商业社会。”茅盾1938年来到香港,也直斥“香港,是一个畸形儿!” 甚至80年后,北京的读书人,会用老实巴交的北平贫民祥子来对照香港地痞陆南才,发出“不太容易理解”之叹(殊不知,祥子式的隐忍和顺命,来自北方农业社会的传承,香港开埠多年,其商业的市侩习气,已经与这种传统伦理秩序渐行渐远。)
至于鲁迅对香港的嘲讽,更是众所周知。“金制军整理国故于香港,可叹也夫!”从鲁迅的讥诮文字里,内地人从此只知港督“金制军”,与前清遗老沆瀣一气,居心叵测在香港“保存国粹”,却鲜知这位“金制军”中文名叫金文泰,是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毕业生,更是少数精通国粤的香港总督。作为一位出色的殖民地管理人,他在香港的任期内支持公立汉文中学,向英国政府申请用庚子赔款成立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启德机场,玛丽医院,这些香港坐标亦是在他的任期内被兴建……内地人若不察明这些,也就难理解在香港岛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帝国权力架构内找到共荣空间的历史情由。
理解不了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为什么《龙头凤尾》里,陆南才作为一个中国人,与英国官员张杭吏、张迪臣并没有势同水火,相反共生共荣。理解不了这一点,也就难免对殖民时期的港人社会生出许多误解。
学者陈国球解剖过英治时期香港人的两难境地:做英国人?大都没有这愿望,也没这资格;做中国人呢?好像离想象中的“中国性”差异越来越大,还往往被中土人士视作“洋奴”。企图别人的“认同”,还是接受自己的“畸形or他异”?一百多年来,香港华人就在这其间,不断探求自我的身份定位。
《龙头凤尾》写成后,马家辉在媒体宣传此书时,多是尽力将话题引向小说创作本身。作为一个职业媒体人,和一个敏感的时评人,他知道什么样的话题有趣、谐谑、又安全。他把那些不欲外道的衷心,写在了小说里。
偶尔和记者聊开之后,他才会说:“我心里有一个大志,这本书写的是30年代、40年代的香港的江湖,通过江湖的眼光看香港,看中国。”他才肯泄露心迹:“香港人一直都有身份认同的焦虑感。香港历史上,这个城市其实从来就不被需要的。40年代以为会被收回——没有;60年代以为会被收回——又没有;结果到九零年代突然说‘要你了’!这种身份认同的暧昧在几种人群身上表现得最明显,就是同性恋、汉奸、黑帮。”(程衍樑:《马家辉:香港女性是华人地区最保守的,这个城市从来就不被需要的》) 马家辉终于承认,这部小说的主题“对香港是很重要的问题。”
2010年代,如今的维多利亚港上红潮涌动,隔岸已无旧城。The city is changing,政治角力,人心激荡的时代里,小说《龙头凤尾》,也许正是马家辉给香港开的一道心门。

马家辉
以下是访谈内容:
凤凰文化:从80年代后期至“九七回归”之间的过渡时期里,“书写香港”这个主题突起,是当时部分香港作家不自觉的集体方向。如果他们处于“九七问题”的历史因缘下做出的探索,那您是出于什么因由,在这个时代,写一个故事来回顾香港这一段历史呢?
马家辉:这里有很自然的部分。因为我年纪大了,毕竟是我第一个小说,通常写第一个小说有点像冒险。你今天去卖保险的话你找谁买?
凤凰文化:亲人。
马家辉:那道理你就懂了。我写第一个小说,难免通常都是把自己熟悉的人事物写出来,所以重点在于之后的考验,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保险人,你能够开拓新的客户,我们一样。接下来才是挑战,我能不能开拓新的题材,新的人物,在我的了解的,点点滴滴我听过的我读的档案里。我有另外一个学术研究项目,是研究汉奸的,抗战里面的部署。所以我就会把这些故事写出来。
我经常觉得我欠湾仔一个故事,好多年前我在内地不同的演讲我就这样说“我一定要找机会把湾仔的故事写出来。”“我要用小说家马家辉的身份出现!”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说得出做得到。所以在这种机缘下面我就动笔。
凤凰文化:书里面陆南才跟张迪臣一开始身份还是蛮对立的,但最后他还是爱上他。我会想到香港这个城市,它的本土意识,其实不太对抗殖民性的,我不知道我这种联想是会不会牵强?
马家辉:没有牵强。
不同的殖民地有不同的殖民方法。英国人是何其聪明的老牌政治国家,它管不同的殖民地比如印度、马来西亚,是用不同的方法。从它接管香港的第一天,他就知道中华文化的传统是很强大的。而且香港绝大部分似乎全部是华人,不像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种族、民族可以被挑拨。所以英国几乎不管。
我在香港殖民年代出生,我们对英国历史其实几乎一无所知。它除了逼我们改洋名学英文,它没有逼我们了解英国历史,或者歌颂英女王,没有的。反倒我们读文言文,读中国文化。
往往我们说,人越看中某个东西,是因为越受到了那个东西的压迫。它没有压迫你的时候——当然确实它会有不公道的地方,歧视的地方——可是它没有压迫你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华人的身份。所以对那个殖民性的反抗没有很大。
而且我们别忘记,我们对某个东西的真实了解程度在于说“你没有了它你会怎么样?”怎么说呢?香港好多都是移民,难民。他们为什么来?因为当时内地太乱,你说难道反抗殖民逃回内地吗?
所以当时是说没有反殖民。我们现在用的词“本土意识”这些都是后见之明。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史,比如用今天的眼光来评价岳飞是个民族英雄还是挑拨民族分裂。那太荒唐了,历史人物有他的局限,和当时的环境视角。
凤凰文化:小说里1967年“金盆洗屌”的那个故事,您是故意设定在那一年吗?1967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
马家辉:是的。1967年,很重要,很关键的年度。
凤凰文化:您是六七十年代出生,后来香港那些社会运动,您还有印象吗?或者甚至您都参与过吗?
马家辉:我出生1963年,那时候还小。印象当中有。
我家就住在休顿球场,那时候英国叫香港政府的防暴队经常晚上在那边演习。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跟我姐姐隔个窗户看外面好多防暴队拿着盾牌。很吵,半夜吵来吵去很恐怖,气氛很萧杀很森严。那时候有左仔,说参加香港左派暴动的或者放英抗暴。我们还看新闻,家里面人说左仔如何如何,会有一些恐怖的气氛。可是如何理解这个事情那要长大之后才能理解。
凤凰文化:人们老说香港因为长期以经济挂帅的政策,政治上会比较冷感一点。
马家辉:这个是绝大部分外来人对香港的一种……
凤凰文化:偏见和误解?
马家辉:香港怎么样可能是对政治冷感?
所谓这种概念有大的误差。我刚说的,香港人有绝大部分——以前是绝大部分,现在还是一半以上的人——不在香港出生。说香港人以前对政治冷感,当然冷感。因为他们根本是中国大陆来的人。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大陆,种种的政治理由,经济生活理由压迫等等……来到香港殖民地当然冷感啊!废话。可是你也可以问,真的能冷感吗?有时你看到其实香港有一场又一场的抗争。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没有停啊,到七十年代,香港人受大学教育的一代,也斯的一代,陈冠中的一代,透过各种方法去争取,去表达。一点都不冷感。假如冷感,我告诉你,大陆就冷感。
你们的角度完全错误,对不起,我可以直接说。我认识的十个内地的,包括我的学生,我的朋友,甚至我的长辈,十个人看的事情的角度有九个是错误的。所谓错就是被你们成长的教育那种观念、框框绑住。
其实我更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我说那个角度一转,其实你要比较冷感的话,中国人就冷,甚至说严重一点——自甘堕落。每天那么屈辱,空气那么差,在其他城市早就抗议,中国人却觉得好死不如歹活。我那个时候的朋友真的十个有九个没有从这些角度去想。你们语言的污染的程度,是让人难以相信。特别看我的学生们的思考。对不起,我不是针对你啊。
凤凰文化:如果抛开个人兴趣,您觉得香港的故事适合从这种——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叫狭邪——这种叙事角度吗?
马家辉:香港的故事等于世界认可的故事。你用什么角度,你用小街的角度也可以,你从大格局宏观也可以。
作为一个张爱玲粉丝,我记得她有篇文章,标题叫《自己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写文章的人,写作的人,作家,写他能写的,写他想写的,没有该不该。一样。
当你讲香港的时候你可以用各种的写法,可以用也斯、董启章,甚至可以用一个外来人的眼光来看也那样,都可以。小说家就是这样,认真的作者,我会想该不该,应不应该,可不可以。这些存在于我们认真写作人的脑海里,不是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凤凰文化:您刚刚提到像董启章、黄碧云、也斯,他们的小说会有意的用种种后现代的方式来写香港,我觉得您这次的小说还是比较写实主义的。
马家辉:选择什么写作策略,或者说写作技艺,会和两个方面有关系:第一个,你的性格,你是什么样的人。第二个,你写作的阶段。我50岁才动笔写的小说,再加上我的性格,从一开始我就想着说要好好来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假如我读起来拿起来看,甚至看到津津有味,停不下来的,我就觉得我成功了——我就往这个目标来进行。所以就用了一个比较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传统来写。
作家有时候写到一个阶段,它不是对读者写,是为自己写,挑战自己,甚至同样的题材用不同的写法来寻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些资深的创作者,不管是音乐家导演什么,许多都停下来。不是他们江郎才尽——有时候有才华的人,再如何江郎才尽,剩下的那几滴墨水都已经还是很精简——重点在于说,已经挑战过自己,要向另外一个新的方向来挑战,门槛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要费更大的心。所以会写的越来越慢,甚至假如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干脆就不行了。
几年前黄碧云写《烈佬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碰面,聊天。我就说你要写的怎么样了?你写了那么久。她说要写快很容易。可是我要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去写不一样的自己,不断找寻新的可能性,我发现很困难。我当时听的大概明白。后来到自己写小说我才真的懂。虽然我之前没写过小说,可是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里面花了好大的力气去。我要不断的修正修改自己以前的框框,以前我写几十年评论那种笔法,内容上要有前因后果,现在写小说不需要,不用“因为所以”。所以,跟我性格有关系,跟我写作阶段也有关系。
凤凰文化:我觉得您刚刚说的,是作为小说家的马先生的一种野心或者是尝试,那作为香港人的马家辉您有自己的野心吗?您也说过想要对香港有所承担。理论上来说,通过个人情欲,树立一则国家寓言,这是一种典型写法。
马家辉:这样说好了,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因为作为一个评论的角度,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度说,除非我不去写那个年代,除非我不去写那个事情。一写就会带出那个事情发生的背景。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乱世,属于人物出身成长的组成部分,在他的身体里,像是他的你的血肉。我除非不写,不然的话我一定要选择这个。可是我不是为了写出某个人的香港而写香港,我是要写某个人。
当然我可能这是我的浅见,我写小说经验不多。我是这样觉得的,我现在要写的是陆南才,而不是透过这个人写香港,这样我才能写出一个像样的陆南才。不然假如当我一开始我就想透过陆南才来写香港,结果很有可能就写不出陆南才。因为我心里总是想写出陆南才那个部分……
凤凰文化:要忘记一些大的束缚和预设。
马家辉:对,没错。
我也知道,不可能不涉及到香港,当我要铺陈1967年金盆洗屌那个事情的前因。我选择是一个地下江湖地下事件,这样的格局下面一定会写出国族里面一些纠缠的部分。比方说华人跟白人,比方说日本人怎么看白人和华人,甚至整个江湖里面南方人北方人。当我写这些的时候,里面与国族相关的部分一定出来。
为了让你更清楚,我再举一个例子——《南海十三郎》。那是一个真实、传奇的一个人物。我们经常说香港的南海十三郎,其实他根本不是香港人。他来到香港,念香港大学,交了女朋友。没想到女朋友被她爸爸赶回北京结婚。南海十三郎决定去找女朋友,连香港大学都不读了。结果他在火车半途中接到信,女朋友病死在北平。他只能算了,就停在上海,狂歌度日,吃喝玩乐,整个人的生命就此改写。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这个?南海十三郎,他本身不是香港人,在香港交了一个在北方的女朋友,结果又流落在上海,生离死别,是这样一个故事。除非我们不写南海十三郎,我们写它的时候就一定离不开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大江南北人和人的种种纠缠。一样的道理,我在写陆南才这样的人,他跟洋人的爱情故事,里面国族的东西就会出来。
凤凰文化:您觉得像你们六十年代出生的香港人跟后来这些世代的香港人,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马家辉:那很不一样,因为不仅是香港,全世界都是这样,已经不仅是不同代,而是不同的人。
假如你说怎么不一样呢?太多的人,要讲的话讲一个,你说我们六七年年代的人比较复杂也行,比较单纯也行,什么意思呢?比较单纯是说,因为当时的积蓄没有那么多,互动没有那么复杂,多层次,所以比较单纯。心中想的那个事情,做一件事情,我想发财就是发财,我想救国救民就是救国救民,我想当医生就当医生,当律师的当律师。这是比较单纯的一面。比较复杂的意思是说那时候可能就会有些有些大志,会觉得大志是好的,没有大志是不好的。
现在不一样,现在有的网络里面,大家都可以互相接触,当然可以生命社会也丰富了,机会也多了。当医生也可以同时去讲一个义工。或者说先做两年什么事情。然后再做医生律师,都有机会。现在是十岁的女生可以躲在家里看A片,性知识比我们丰富。比较复杂。可是说单纯呢,现在也比较单纯,他不一定需要有那种大志,他可以以没有所谓的大志为荣。像香港有所谓的“废青“,本来废青是要来说人家不好,废物,现在好多人都开口闭口我要做废青。可以是自嘲,甚至里面有光荣的、引以为荣的部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有生活里面的小快乐,小确信,小嗜好,透过网络我可以找到同类人,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那个年代没有网络,我们要花好多时间去找同路人,同一类人,往往容易有孤单、孤决,孤立的感觉。现在不会。再怎么样其实怪怪的癖好,都可以找到。甚至一些不正经的癖好,乱七八糟的想法等等。所以当你没有那么严重的孤立的感觉,能找到同类,你是不怕孤立的。不太一样,不太孤立。
现在90后的学生好像心中无所恐惧,无畏惧。就算发生不好的事情,他们也觉得无所谓。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某些人来说,最大的满足感都在网路上可以找得到——“我不管在世界我怎么样的挫败,所谓的没出息,我只要在网络上面打游戏打的成功。“而且我在网络世界我跟别人互动,最大的满足感,I don’t care 现实社会所谓的成就跟挫败。这非常严重,非常明显,已经不是一种讽刺,是真实的发生。太多年轻人,对世界他们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我那个年代的人,现实的世界是我们唯一的世界。所以我们对现实的世界还是比较在意,这是其中一点大的差别。
责编:何可人 PN033

我们时代的心灵史
凤凰网文化出品

时代文化观察者
微信扫一扫

2016-12-21 18:25:050

2016-11-10 20:21:550

2016-10-03 16:30:440

2016-08-26 10:54:580

2016-06-18 20:32:060
2018-12-20 12:500
2018-12-19 10:180

2018-12-17 12:570
2018-11-16 12:210
2018-11-03 12:590
2016-07-28 16:250

2016-06-23 12:380

2016-05-10 11:530

2015-12-14 16:310

2015-11-26 15:150
2018-10-27 19:520
2018-10-27 19:510
2018-10-27 19:450
2018-10-11 10:460
2018-08-21 10:200
2018-10-11 10:220
2018-08-31 11:040
2018-08-31 10:400
2018-08-21 10:390
2018-08-21 10:330
2018-10-27 18:330

2018-08-31 17:370
2018-08-31 10:530
2018-08-21 10:160

2018-08-11 12: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