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尼卡》:拒绝“无色不换”的空洞煽情
2015年04月13日 08:57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云也退
毕加索表现大屠杀所用的视觉语汇,都是一般的象征物,他利用绘《格尔尼卡》的机会,操练自己个性中残忍一面。他提起画笔,就永远在强大创作欲的驱动之下。
毕加索名作《格尔尼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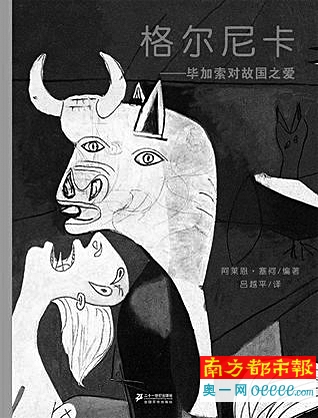
《格尔尼卡———毕加索对故国之爱》,(法)阿兰·塞尔编著,吕越平译,21世纪出版社
架上绘画不同于文学,一首诗、一篇小说可以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如何评价它的好坏,但绘画,很难说你完全“看不懂”。具体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我想多数人的体会可能都是这样的:在杂乱无章、没有具象的画面里,能感觉到作者的意图。这里,这些人、牛、马的身上正在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有人在哭,有人在尖叫,有人已经死了,黑色包围着这一群形象,我们眼前出现了阴天、石头、瓦砾,听到撞击、破碎、爆炸的声音。
这可能是事后诸葛———我们提前被告知了《格尔尼卡》的意义,它所指涉的主题,再回过去解读画面里的细节,赞赏它的伟大。是故,我们需要一本专讲《格尔尼卡》的书,看看这幅画毕竟是怎样从无到有的。
阿兰·塞尔编著的这本图册,很薄,但它满足了我们部分的好奇心。毕加索留下的书面资料十分丰富,书中选入了最重要的几幅《格尔尼卡》草图。1937年1月,他就在日记本里第一次留下了关于《格尔尼卡》构思,你发现,成品中中间靠右上方那个黑黑的窗户,此时已经存在了,尽管只是一些密集的线条;从这一团黑线里向左平行地拉出了几笔,以后,它将变成擎着煤油灯的手,而它下方的那个惶惑的女人侧脸,此时也有了。
诗学有“诗早已存在,诗人不过是去揭示它”一说,大师作画,亦有此种效应。看朵拉·马尔拍摄的毕加索作画照,想象你作为一个外行正在目击,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显影术,他用他的笔,让图画在铺了满墙的画布上显露出来。慢慢地,你便明白毕加索不是兴之所至,画到哪里算哪里,《格尔尼卡》有一个精心构思的“朝圣者”布局:人物并排,注意力朝画面上方的某处聚集,神态凝重。在希腊时代遗留下的那些三角楣上的浮雕,就可以找到这种构图的先例。
所谓“影响的焦虑”,对画家也不是问题,即便是不世出的天才,毕加索也需传承前辈,只是他的传承格外多样。例如巴洛克时代的朱塞佩·里贝拉,毕加索传承了他对荒凉事物的高度敏感,更有名的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毕加索在其“蓝色时期”和“粉色时期”,很多作品都是得自格列柯的启发,不过,他不喜欢后者的宗教虔诚。毕加索忠于自己,只看自己所看,画自己所想画。《格尔尼卡》里也有“圣母抱子”:恸问苍冥的母,抱着已死的子———毕加索眼里的虔诚。
书中写道:毕加索“曾想在画布上滴一团血红的颜料。他尝试了,又改变红色颜料的位置,最后抛弃了这个想法。”———必须的,否则就不是毕加索了。《辛德勒名单》可以在黑白的人群里放一个红衣小女孩,《格尔尼卡》却不行,因为绘画不是电影,不必刻意刺激人的感官;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自我控制的高手。黑、白、灰,即是这样一幅画卷所需要的颜色。同提香、委罗内塞、鲁本斯相比,毕加索留下那么多画作,总的看来,颜色算是单调的,他会把彩色用于强烈的对比,但不喜欢那种无色不欢的感觉。他的长处,还是在于结构和线条,《格尔尼卡》的力量,除了朝圣式布局外,还来自那些分析性十足的线条及其效果———极干,极硬,严峻苍白。
对比书中所配的一幅图———1937年4月26日格尔尼卡遭轰炸后,法国《今晚报》的头版页面,你会发现,《格尔尼卡》的色调就是报纸的色调。报纸,其自然的陈旧感,蕴含的“一切现在都将定格为过去”的意义,也体现在《格尔尼卡》之中;毕加索巧妙地用自己的弱项来展示创作时的态度,他想说的是,战争不是让艺术家沉浸于创作的机缘,观看绘画中的战争,应该像看一张报纸上的图片报道一样,能领会那种距离之外的冷清与压抑。
毕加索不要人们身临其境,去体会格尔尼卡人的痛苦,反而把人推远,他要避开煽情,同时又不让怒火熄灭在漠然之中。他把火的温度调到最低,让它们在画面背后安静地燃烧,他要让战乱同时散发出悲惨和神圣两种气质。那长着人眼的牛,那表情痛苦的马,俯冲下来的幽灵面孔,握紧断剑的手,仰天尖叫的脑袋,哭泣的女人———所有这些,都拉开了《格尔尼卡》同它所诞生的时代的距离。它描绘的这场杀戮,同稍微写实一点的同题材作品,例如马奈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的枪决》比较,你会觉得《格尔尼卡》是有序的。身为达达以后最杰出的现代派画家,毕加索是用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来组织画面中的恐怖图景的,混乱,随机,全面的、覆巢式的破坏,纯然属于现代的战争恐怖,被古典的、富有史诗意蕴的构图给肃正了,或者说,给“扭曲”了。
哭泣的女人,没有争议,是朵拉·马尔(毕加索的情人)的脸。如果你知道毕加索曾说过“女人是用于受苦的机器”,如果你知道他怎样对待朵拉·马尔和生命中的其他女人,你会不会觉得,《格尔尼卡》的伟大有点不纯粹了?看过与《格尔尼卡》同期的另一幅名作《哭泣的女人》,你会不会推想,朵拉·马尔在画家身边受了怎样的苦?他表现大屠杀所用的视觉语汇,都是一般的象征物,女人、孩子、眼睛、泪水、舌和嘴,他利用绘《格尔尼卡》的机会,操练自己个性中残忍一面。毕加索的所有作品,其实都是关于自己的,不管轰炸多么惨绝人寰,毕加索提起画笔,永远只在强大创作欲的驱动之下。![]()
网罗天下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