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懂得汉娜·阿伦特的,或许只有这个美国女人
2017年01月19日 10:58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卡罗尔·布莱曼
有时候,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我们跟随着她们二人,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编者按:汉娜•阿伦特,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女性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玛丽•麦卡锡,美国杰出女作家、评论家、政治运动家。她们初遇于1944年的纽约,随后成为朋友,开始了长达25年的书信交流。在信中,她们辩谈时事,也探讨文学,倾诉情感,也闲聊八卦。
《朋友之间》收录了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的所有通信。以一种私人的方式,为我们近距离展示了两位杰出女性的政治、道德、文学观和思想脉络,也见证着20世纪的文化和思想史;不仅向我们呈现了她们之间漫长而独特的友谊,也提供了艺术和政治批评的典范。
此书已被译成中文,由中信出版社·信睿出版。本文即摘自此书序言,有删节,原题为《书信中的浪漫传奇》,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美] 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著,[美]卡罗尔•布莱曼编,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11
1944年,她们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第一次见面。当时,玛丽·麦卡锡还处于和埃德蒙·威尔森的婚姻之中,陪同她的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其弟马丁·格林伯格是汉娜·阿伦特在修肯出版社的同事。阿伦特的评论和散文最初只发表在《犹太杂志》和《当代犹太人档案》上,后来也开始出现在《评论》、《党派评论》和《国家》上,这使她的名声不再局限于她所属的德国犹太移民圈,而是被更多纽约知识分子所了解。那时,她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但也已经来美国三年。她传递着一种权威——“代表某种更加古老更加深刻的东西,那就是她所理解的欧洲文化”,她的同时代人威廉·巴莱特后来这样回忆——这着实让她的美国新朋友着迷。
1944年的玛丽·麦卡锡被阿伦特怀疑主义者的机智所震撼。后者和她出生在柏林的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的身上都有一种漫不经心的气质,让人感觉很轻松。比如她曾讲过一个关于逃亡者的笑话,说一只逃难的猎獾狗哀叹自己作为圣伯纳犬的前世。1985年我对麦卡锡进行采访时,她回忆说:“她充满了活力,一种让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她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奇。”在莫雷山酒吧,阿伦特笑着说,美国还没有“定型”,这还是一个小店主和农民的国家,与其说这是个新世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旧世界”,这里的社会视野非常狭隘,和这个国家的开国者拥有的政治视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这些观察与麦卡锡1947年9月的一篇文章呼应,但视角有所不同。为了解释美国生活中的游牧性质,解释她所看到的“美国装饰、美国娱乐和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丑陋性”,她在《美丽的美国》一文中写道,这种“庸俗”是不是“以看得见的形式表达了欧洲大众的贫穷,表现了漂洋过海来自欧洲的落后和贫困”?关于美国电影在海外的巨大成功,她指出,“欧洲是未完成的底片,而美国已是样片”。
麦卡锡认为,欧洲拥有“稳定的上层阶级”,而在美国,这种阶级的缺失“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庸俗化”。这和汉娜·阿伦特眼中的欧洲不同。阿伦特经常把美国这个她的移居国称作“共和国”,她眼中的美国和麦卡锡描述的战后美国也不尽相同。阿伦特看到了其他东西。在1946年给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她用赞许的语气提到,美国不存在“民族国家”和“真正的民族传统”。
幻想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对于她们俩来说,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创造潜力的幻想,不仅让她们的友谊在经历了早期的一次误解之后迅速加深,而且也促进了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很多作品都从对方的文化传统中获取了灵感。我们很容易注意到,阿伦特在《论革命》和《共和国的危机》里对宪法与人权法案中所蕴含的政治原则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而麦卡锡写的是《我眼中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的石头》和《美国鸟》,《美国鸟》中处处体现着康德的道德哲学。即使是《群体》这样一本书中全部角色都出自瓦萨学院1933届美国女孩的书,也还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把视线投向了那个远行去了欧洲的女孩“雷姬”,她在战争爆发前夜回来了,带着一个像男人一样的埃斯蒂安纳男爵夫人,后者是个德国人。
晚年的玛丽·麦卡锡把她与汉娜·阿伦特以及意大利评论家尼克拉·乔洛蒙提的友谊看作是一种皈依的体验,后者也是她在1944年认识的。……乔洛蒙提和阿伦特是不同的,他们俩和麦卡锡认识的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也不一样,但他们俩都是欧洲人——“也是柏拉图主义者”,麦卡锡在1980年这么评价道,“更应该说是苏格拉底的信徒”——他们都非常关注个人和政治的道德性,这让麦卡锡感到非常激动,而这种激动是那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政治无法带给她的。例如,阿伦特的信条——用对世界的爱来代替对个人的过分关注,赋予了政治生活某种救赎的力量,而童年时代的麦卡锡是从宗教中获得这种力量的。
不难想象麦卡锡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发现的那些特质,正如一位崇拜阿伦特的耶稣教信徒所写的,她“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但是,她们的友谊也经历了考验,1945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麦卡锡说了错话。在谈话中,大家谈起法国公民对占领巴黎的德国人的敌意,她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因为他竟然会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爱戴。这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风格,她说这话是要故意冒犯那些道貌岸然的反法西斯分子,绝不是针对汉娜·阿伦特的。但阿伦特非常愤怒,她当时就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一个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去过集中营的人!”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道歉。据麦卡锡说,三年后,她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政治》杂志的前途,她们同属少数派。在地铁的月台上,阿伦特转身对她说:“我们结束这荒唐的争吵吧,我们的想法如此相近。”麦卡锡为关于希特勒的话向她表示歉意,阿伦特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只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待过。她们的友谊之花从此常开不谢,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可以媲美。
玛丽·麦卡锡1912年出生在西雅图,六岁时就失去了父母,是被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的监护人抚养长大的。她任性固执,除了学校里的那些知识女性,其他人她谁也不服。这种情况第一次是出现在西雅图圣心修道院的嬷嬷中,后来是在塔科马的安妮赖特神学院,再后来就是瓦萨学院。汉娜·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汉诺威,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长大,她的父母亲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人,她是家中的独女。在某种意义上,阿伦特是麦卡锡所有老师中最出色的一位,但她的权威,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没有阻止麦卡锡对她的思想提出质疑,尤其是当她的思想晦涩难懂,同时又和麦卡锡本人的现实感产生冲突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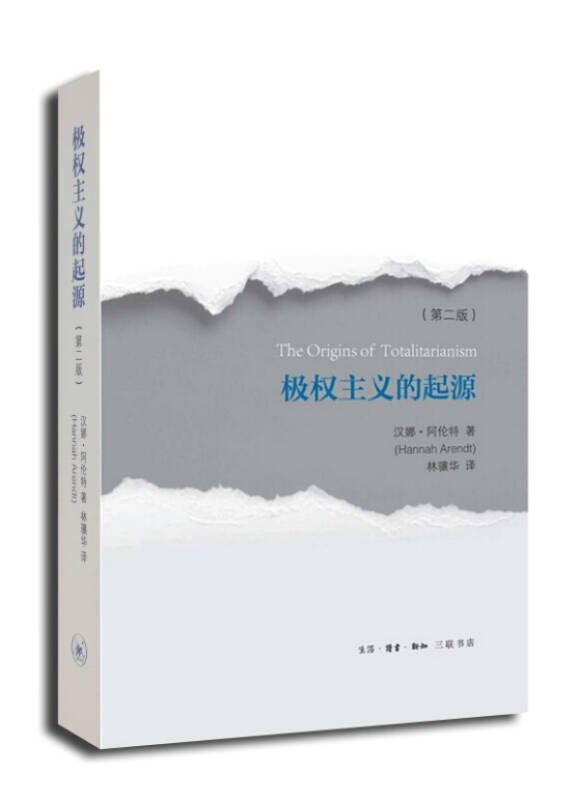
所以,在赞扬《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10年”之后,麦卡锡在她写给阿伦特的第一封信中还是忍不住指出,“书中确实有些不规范的表达,比如用‘ignore’(忽视)来表达‘beignorant of’(不知道、不懂)……再版时也许应该更正”。她还对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观点提出了自己“更重要的异议”——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一些丧失家园的人用来剥夺他人现实感的一种体制”——她触及了她们之间一个有趣的差异,这种差异让她们持续了25年的通信充满了活力,并且为她们之间的几次争论添加了一种“哲学小说”的色彩。
麦卡锡认为,阿伦特削弱了极权主义中的“偶然因素”,她这么说指的是某种可能,即“某些特征被融入了这些极权主义运动中,仅仅因为这些特征很管用”。阿伦特似乎认为“纳粹和斯大林有特殊的方法能够掌握政治行为的法则”,这是麦卡锡在1951年4月的信中写的。麦卡锡承认人们常常有这种印象,但阿伦特没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明清楚,因为她自己有时候似乎也持相反的观点:“人不是理性世界的阐释者或艺术表现者,而是一个无例可循的创造者。”
麦卡锡深信,机会和选择共同塑造人生,而且机会的重要性大于选择。在她的文章中,随处可见各种精彩的创造,任何东西都可以推陈出新,比如家里的旧布、习俗和历史。这种创造不仅出现在她常常用来检验自己创造力、表现个性的回忆录和信件中,而且还出现在对历史的思考中。在《我眼中的威尼斯》中,威尼斯这座具有多元文化传统的城市正好让麦卡锡自嘲了自己多宗教背景的童年,她这样写道:“作为一座城市,威尼斯是个弃儿,像被放在篮子里的摩西一样漂浮在水面上,因此它必须学会创新,必须学会偷窃,必须急中生智。”
她和阿伦特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变化的态度——不是政治上的变化,这一点她们是一致的,在危机时期她们都能勇敢面对,虽然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理解使她的态度更为悲观。她们的差别在于个人的变化,特别是在与异性交往中的变化。麦卡锡相信,在恋爱中,某种个人的改变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是恋爱的唯一理由。(也许,这正是她不断恋爱的原因。在麦卡锡的中年,爱情在她自我提升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阿伦特更喜欢尼采所说的“保持自我”,不愿受任何思想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约束,她坚持一种更为悲观的、更具欧洲人特点的观点,但她也是浪漫的,只是方式不同。
……
和其他作家发表的书信不同的是,她们的通信中不仅有高尚的思考,还有女人间轻松的闲聊—不是八卦,虽然也有八卦,而且不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阿伦特在1960年的信中,描述了“小个子波德霍雷茨看上去像个犹太服务生一样疲惫”,还有艾尔弗雷德·卡津[哈罗德·罗森伯格告诉她的]“走路的姿势和动作就像一头傲慢的骆驼”,这些文字都令人难忘。让麦卡锡和阿伦特的信与众不同,并且赋予它们一种罕见的戏剧力量的,是她们在信中如在耳边的声音,这种直接性有时会产生一种戏剧效果。即使是关于个人私事的评论读起来也像对话—是可以传递思想的对话。

玛丽·麦卡锡
这些信中的思想(“思考这种事”,阿伦特这样称自己最喜欢的消遣)和想法或观点不同,后两者可能产生于思想但不尽然。阿伦特和麦卡锡对于20世纪思想界“习见”的很多思考都是批评性的思考,但这和我们在信中发现的思维活动也是不同的。这种思维活动可以被称为“纯粹的”思想,如果这个定语不违背阿伦特的“思考的自我”这一精神的话。在这种思维活动中——无论是关于感情问题、街头犯罪、学生叛乱或是“黑色力量运动”——阿伦特,尤其是阿伦特,会来回穿梭在日常生活的体验和对此的思考之间,从而填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思维活动的本质在于它具有能够直接关注世界的能力,不仅仅是关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而是关注世界本身,并且剥去了思维中可能存在的迷信、情感因素以及理论的装饰。
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在她的政治文章中还是她的书信中,阿伦特确实都很像苏格拉底,他们都努力让哲学贴近现实,审视那些我们用来判断世事的看不见的标准。我曾经问过20世纪70年代担任阿伦特助教的杰罗姆·科恩,《精神生活》未完成的第三部的主题——“判断”是否会成为阿伦特写作中的一个拦路虎,他说,“根本不会,”他向我指出了一个这本通信集的读者也很容易发现的事实,“汉娜一生都在进行判断,判断各种事件,理解它们给其他人带来的后果,这些对她来说就是运用常识。”
这种多思——不要和“为善”混淆起来——和传统意义上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是一种远离琐屑表象世界的途径。阅读阿伦特关于“知识分子无判断力的多思”的论述时,那些笨拙的德语式英语句子也许会让读者蹙眉(英语是阿伦特的第三语言,排在德语和法语之后),但是如果认真阅读,读者对如何思考这个世界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我们可以用阿伦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喜欢乘坐的小火车来比喻她的这种思考。她把这种火车称为“叮叮当当”,从她避暑的位于山区的台格纳坐到洛迦诺去看马戏或电影。“虽然身边都是朋友,但她却像一个孤独的乘客,一个人乘着她的思想列车”,麦卡锡在《和汉娜告别》中写到了1970年海因里希·布吕歇尔去世后阿伦特的凄凉,这个沉静的形象让我们在阅读阿伦特的文字时感受到了一场神秘的精神旅行。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