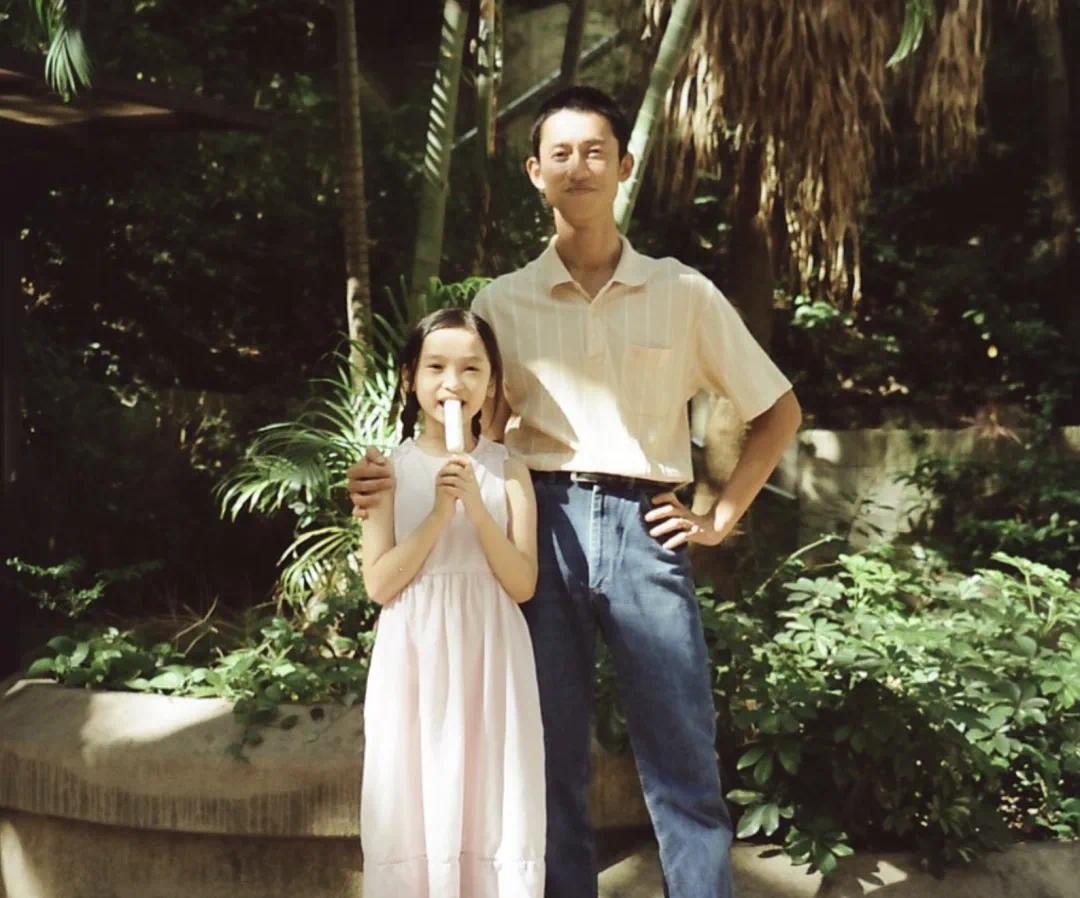“新加的一箱油还没跑完,父亲便去世了”
在传统的教育中,父母之爱仿佛是一种天然的、理所应当的爱,但放眼真实的世界,却并不总是如此。作家赵赵在《闲的》一书中回忆她的父亲,她说,“多年后我翻到那天的日记,当时的我发誓永远不会原谅他。在那之后的很多年,也一直这样坚信。”
她的父亲给她留下了诸多不美好的回忆,但衰老与死亡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软化剂,而这个过程往往迅速到我们永远无法为此做好准备。比如赵赵在书中写到,她去医院看望父亲出来后,去加油站加了一箱油,想着“他总能坚持到我跑完这箱油吧”,然而没有,四天以后,她的父亲就去世了。
那之后,她尝试回忆与父亲相处中柔软的时刻,闯入她脑中的记忆,是一个二十岁时的雨天,她的父亲立在窗边,听着音乐望着雨帘发呆,她写道,“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父母,其实也是有灵魂的。”
以上两个细节,是赵赵回忆父亲的故事时,令人动容的微小瞬间,你与父母的相处中,有这样的瞬间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那些想起父母时,你为之动容的时刻。
本文摘选自《闲的》。经出版社授权推送。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
01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父母也是有灵魂的”
父亲去世的前四天,我把车开出医院,旁边就是加油站,我说:“加五百。”
我想:他总能坚持到我跑完这箱油吧。
然而没有。
那天白天,老家来的亲戚去看他。妈微信里说:“不认人,直到当中医的四叔给扎了一针,他说:‘疼。’才认了会儿,很快又糊涂了。”
我怎么不信呢?晚上我一个人去医院,护工不在,爸冲里躺着,我过去叫他。他的眼神说不上是明白还是糊涂,我就一直坐那儿和他说些废话:你今天怎么样啊?晚上吃什么了?护工对你好不好呀?他去哪儿啦?就把他当没病那样聊。
他瘦了好多,但仍很有力,时不时使劲掐自己大腿。护工回来,我问这是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不拦着的话,能掐烂了。
我的手扶在床围的栏杆上,突然他慢慢伸出细瘦的胳膊,手指落在我的手腕上,轻轻拂来拂去。我逗他:“羡慕吧?看我皮肤多好。”
旁边床上的帕金森病人终于憋不住笑了。
但我却好像听见父亲的叹息。呃,他是要表达什么吗?
我觉得他的意识是清晰的,他就是懒得说话,太耗力气。他不说话没关系,我说。
我说:“你记得我小时候你老打我吗?你记得你从女厕所里把我揪出来打吗?你看我对你多好,我现在都不打你。”
他就开始笑,笑得眼睛都弯了。我说:“你怎么这么坏呀?听到这些事就笑。”他就笑得更像个老坏蛋了。
想起来他最喜欢我家两只猫,我就把手机里的视频给他看,看糖饼怎么欺负二饼,二饼害怕得从椅子翅儿下面退出来,还是被暴打一顿。视频挺长,他突然说:“猫。”
手机里所有猫的视频放完,我就给他一张张翻猫的照片,其实多是以前看过的。他哈哈笑,咯咯笑,还说:“猫猫。老大。老二。”
直到看到有张糖饼背冲镜头的,他突然说:“你看这猫这一身毛多漂亮啊。”
这句话算长了,他说得非常清晰。父亲口吃,从来话少,但这句话说得比健康时还流畅,我就放了心。
当时的我并没想到,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我就开始和他玩打手板。先是我把手放下面,翻上来打他。他躲得极快,眼睛里瞬间闪过从前凌厉的光。几下之后,真有一次被他完全躲开了。他得意地笑,把手放在下面,准备好翻上来打我。我说:“你说你是不是小孩儿?是不是?”
这么又玩了一会儿,我得走了。和护工交代几句,穿好外套,走两步回头看,他似乎很明白我要走,而且是他留不住的,又蜷成我一进门时那样背冲门的小团。
路上我给妈发微信:“我爸好着呢,和我玩半天,你得逗他。”妈一直说:“是吗?是吗?”
三天后的中午他转院,我一个人跟救护车。上电梯前,护士说给他戴个帽子吧,外头冷。他的帽子都是棒球帽,遮不住耳朵,我把羊绒围巾摘下来,给他把头围好。
下电梯到上车,到地方下车,到再上电梯,那两小段路,是他最后一次在户外。他半睁着双眼,我下意识地抬头看楼与楼之间的小块儿天空,他能看见吗?
我和父亲感情并不好。我五岁时他才调回北京,从单身汉般的自由瞬间转入有儿女的家庭生活,他完全不适应。对我和我哥也谈不上教育,只是一种态度吧——粗暴的态度。
我对他的记忆充斥着暴力。从幼儿园不告而别自己摸回家,暴打一顿;没考上附近的小学,暴打一顿;和我妈犟嘴,暴打一顿。且据我妈挑拨,他下手不知轻重,隔着棉裤也能打到屁股上腾起五个指印。
后来我们越来越疏离,这种疏离在我青春期时达到顶点。那年我初恋失恋,又没法在家里哭,就跑到马路对过儿同学家里哭。哭了不知多久,听见有人在楼下喊我名字,探头看,父亲站在“L”形楼下的花园正中,重复着我的名字骂:“你怎么这么疯?这么不要脸……”后面的话都是竭尽所能的羞辱,不想记得了。因为口吃的缘故,更让话一句似一句的凶狠,而且还有回音。一些窗户打开,一些人探头往下看,又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我。多年后我翻到那天的日记,当时的我发誓永远不会原谅他。在那之后的很多年,也一直这样坚信。
关系的缓和,是因为他的衰老。他的高声大气再也没人当回事,在这个家里的存在感越来越弱。他去世的前两年,甚至自觉退出了晚饭后餐桌上继续的家庭聊天,也并没别人注意。先是在社会生活中被无视,然后在家庭生活中被无视,他越来越长时间地待在自己屋里,看最爱的乒乓球和动物世界。因为复杂的人类世界,是他根本对抗不了的。就像《姐姐》里唱的: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他已不是对手。前几年他来我家过冬,因为对时事的看法不同再次咆哮。其实搁平时他也不至于,但那天小时工阿姨在,他一向喜欢在他认为比他弱的人面前装强者。我懒得理,接下来就只和我妈说话。他看我,我知道,他走到我面前,我就绕开。第二天我去院儿里走路,远远看见他裹着羽绒服跟出来。我走到微汗,往家的路上,他斜侧里迎上来。我本来又要绕开的,他做出一个微微阻拦的手势,然后就哭了,说:“别不理我。”
我很震惊,不知道说什么,就这么一前一后回了家。他是否有我当初感受到的巨大屈辱?我不知道,那并不是我的本意。
父亲去世后,我一直机械地按程序做该做的后续,只有睡前才会想:和他的相处,总有些难以忘记的片段吧?
想了很久。不是片段太多,而是都在创伤回忆的Top10(前10名)里。我用了好几个晚上,像巴依老爷费劲地挖金子。
我记得小时候的某个夏天,他带我和我哥走了两里地去法海寺。那时法海寺大殿周围的屋子住着很多人家,像个大杂院儿。父亲举起我,从木门的缝隙里看墙上的壁画。我记得那天的路上,我追了一会儿蜻蜓。
我记得二十岁的某个雨天,他坐在大开的窗前静止如雕塑。雨甚至潲到屋门处我的脸上。录音机里放着我重复录了半面的Right Here Waiting(此情可待)。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父母,其实也是有灵魂的。他当然不懂那是在唱什么,但那个雨天,湿漉漉的土味儿,穿过房间的风和那首歌,让他暴露了。
我记得他六十多时胃部不适,去医院做了检查,害怕是不好的结果。那好像是秋天,我记得安静的走廊里光线很透亮。我试着拉起他的手。他不适,我也不适,但就这么硬着头皮走到医生面前。
我最记得的,是小时候家里还没买电视,周末会跟爸妈去九中的阿姨家看连续剧。一个冬天的晚上,也许是看完了大结局,很冷,但我们往家走时非常愉快。父亲把蓝色的棉猴儿掀开,把我裹在里面,我在黑暗中努力地紧捯小腿跟上他的节奏,我知道我不会摔倒,因为这是信任的游戏。那是我们之间曾有过最亲密的距离,我唯一切切实实感受到父亲的温暖的时刻。
在九中宽阔寂静的操场上,我几度从棉猴儿里挤出脸来。迎面的天墨黑,天空中有很多很多很多星星,那一刻我相信它们是在照耀我们。
父亲在情人节那天去世了。真会选时间啊我想。在我人生中第一次过情人节收到小男友送的巧克力时,怎么会想到这将是父亲的祭日。
父亲去世后,我最想说的话是“对不起”——如果我能在关键处做出更正确果断的判断和决定,也许他可以活久一些。都说子女是父母这辈子的债主,上辈子父母欠儿女太多,所以耗尽此生来还债——所以,我们两清了,父亲。
我和父亲是几乎找不到相同点的两类人,吃力地完结此生共处的缘分。我相信如果有来生,我和他都不愿再做父女,最多是萍水相逢又终究擦肩而过的路人,可能只在目光交会时想:咦,这个人似乎有点儿眼熟。
有一天晚上,我去摘左手上的发绳,当右手触碰到左腕,突然感受到父亲那晚的触碰。我想更真地感受,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就这样轻轻地拂来拂去,我觉得是的,就是那样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与父亲相见时,他已四十,我们共同度过了彼此的半生。余下的此生,或如果真的有来生,当我仰望冬夜的星空,我会记起我曾在这样的凛冽中有过微小的满足。
无论你在哪里,父亲,祝你快乐。
02
“老三,咱就当少受点儿人间的罪”
小表哥是我童年最亲近的玩伴。小时候他摔了胳膊,在老家耽误了治疗,妗子(舅妈)就带他来北京看病,一趟又一趟,所以上学前我总是和他玩在一块儿。他大我一岁,排行第三,我跟着大家一起叫他“老三”。
因为年纪小,他对自己浓重的口音满不在乎。有一次从外面回来,他和我说:“住那边那个娘儿们……”我虽然小,毕竟是女的,觉得“娘儿们”实在难听,长大后才知道他们那儿都这么叫已婚妇女。
老三小时候特好看,浓眉大眼,我老觉得故事书里的小英雄就该长这样儿。他脾气犟,我妈老提起他头上的三个旋儿,然后就会不厌其烦地重复:“一旋儿横,两旋儿拧,仨旋儿打架不要命。”老三并没什么机会和别人打架,可能因为他愣头愣脑的样子和凶巴巴的外地口音,本地小孩儿一看就怕了。我不怕,很多时候是我俩扭打在一起,常常打得翻脸,大人来各骂一顿,一会儿就忘了。
妗子说有一次我在院儿里,一本正经地捧着本书给老三讲,讲几句还像煞有介事地翻页,老三听得也认真。妗子奇怪,因为我上学前一个字不认得。过去一看,书上写的是一回事,我讲的是另一回事。这么看来,老三应该算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读者吧。
我那会儿最喜欢老家来的人,亲戚家的同辈里,我年纪最小,很得宠。以至于我去考就近的小学时,人家看出我啥也不会,最后只问了一个问题:“你户口在哪儿?”我想都没想,大言不惭地说:“老家,农村。”人家就没要我,估计是觉得我智商有问题,不得不去念离家稍远的一个学校。记得到家就挨了我爸一顿好打。
上学后老三来得少了。再来,彼此都知道了男女有别,话比以前少了,更甭提扭打一处。我念高中时,妗子给他相了个对象,但一来觉得年纪还小,二来希望女方多学点儿文化,就把女孩儿送到我家,到我念的中学借读。女孩儿只待了半个月就回去了,跟不上课,口音也实在太重了点儿,和别人互相听不懂。回去后这亲事就没成。
高二暑假,北京很乱,我妈让我去妗子家,我正好失恋,揣着日记本就上了火车。住二表哥的新房,每天背个木篓跟着他们去地里随便摘点儿什么,晚上在院儿里听远处的火车声数星星。心里也没好受,只是自以为好受了点儿。我水土不服,身上起红点儿,他们每天都抢着照顾我,为我专门去买早点,抢着给我洗衣服。后来听说我去之前老三很严肃地和大家说了,谁敢对我不好,他对谁不客气。其实他和我也没说几句话。
他结婚时,也和两个哥哥一样带着新媳妇来北京转了转,住哪屋我忘了,反正回去也生了个儿子。我妈说住我哥那屋的都生儿子。我妈对老三尤其好,好像他俩的阴历生日是同一天,老三长大后遇着什么事也爱和她商量。
舅舅、妗子觉得得给老三找点儿事干,拿钱来北京买了辆二手“拉达”,老三就在县城里开黑车。没开多久就出了事。他没念多少书,不懂法,碰上两个抢劫的包他的车,他只想着自己并没去抢劫,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挣点儿钱,至于别人干什么,他自己不参与就行了。后来这两个人被抓,他被当作同伙也关了进去。妈那几年为这事跑断了腿,四处求人,最后他反正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算起来也关了好几个年头。
我再回老家,看见他还开着那辆“拉达”。老三的面相完全变了,小时候的圆脸变长,颧骨突出,像个藏族人,左右脸严重不对称,像两个人的脸拼在了一起。小时候他一直比我矮,现在长到一米八几,动作迟缓,吐字也不是特别清晰,就笑起来还和小时候一样。
那之后他一直过得不顺利,和两个哥哥的日子差得很远。盖了两层房,一层出租,二层自住,也租不出什么价钱。妗子一直给他操心最多,所以也就住在他那儿,但相处得并没小时候那么好,常有摩擦,他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前几年回老家给妗子过生日,临走时我嘱咐她说:“对老三好点儿。”妗子只是抿嘴笑。后来听说还是吵,家里一直不得安生。去年底老三给我妈打电话,打通了又吞吞吐吐说不出什么,只说“姑你回来一趟吧”。我们都劝我妈别人家的事不好管。
前天半夜接到妈的电话,说妗子让第二天赶紧回去,也不讲原因,只让给二表哥打电话。二表哥说,老三出车祸了,恐怕不行了。大半夜的,挂了电话我就哭了。我觉得老三太可怜了,除去小时候不谙世事那段时间,他就没过过几天好日子。
我到他们县城的贴吧去找,还真有人发帖说晚上八点的时候,他们那儿正修的公路上又撞死人了,是车撞上公路上的一个土包后人摔出去的,还说路障应不应该有明显的标识?我知道这一定说的就是老三了。
我哥带着爸妈中午就赶回去了,给我发短信,说老三死了,下午就火化。紧接着下午发来照片,大表哥和二表哥在拣骨灰。一个人,就这么没了。那么突然。我出门的时候看着天,就想,他昨天出门的时候,怎么知道自己看不到今天的天儿了呢。
哥说老三是骑摩托车,躲对面来的大挂车,应该是压根没看见马路中间黑乎乎的土包,他们那边的路上有没有灯都不一定,就算有,亮不亮也不一定。就撞了上去,车飞出去十米远,他是头着的地,当时人就不行了。
我翻学龄前的照片,好多照片里都有老三,表情专注地看着镜头,而我,不是在吃就是在傻笑。那时候谁能想到虎头虎脑的老三会死得那么惨呢。谁能知道死亡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哪一个转角突然跳出来呢。
老三,咱就当是少受点儿这人间的罪吧。
03
“无聊于我是一种常态,待在里面安全”
终于在长时间的无聊中挤出时间看完《人造卫星情人》和《刀锋》。
明白了为什么总是有大把时间无聊——因为做事情太快了,手脚太利索,总是飞速地干完活儿,再飞速地转身到无聊中。
所以我的无聊繁重而茫然,那几乎是天生要背负的一种使命。无聊于我是一种常态,待在里面安全。
但,我为什么做事快?还是因为内里有苦苦挣扎的底层气质——从没学会去浪费时间和金钱——我不认为拥有或者谁能提供给我可浪费的资源。不浪费,因为浪费不起。渐渐成了习惯,低眉顺眼地高效完成,不给别人或自己惹麻烦。天生的婢女情结。
我大概知道朋友为什么在我说喜欢木讷而天真的男人后推荐我看《刀锋》。失去是早晚的事。或者说,失去的东西从来也不是我们的,都只是人家自己的。
我们只是喜欢,在那上面投注了自己的喜欢。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喜欢的人物事,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喜欢而就是我们的,从来也不是。
要提醒自己知足。也许有一天,连喜欢的能力都没有,那时,该想些什么来令自己知足?总算喜欢过?
前一阵子和朋友一起聊天的播客《后文艺生活》停播了,想起毛姆的话:“一个人能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把这话分享给大家。
本文摘编自
《闲的》
作者:赵赵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长江新世纪
出版年: 2025-3
为您推荐
算法反馈精品有声
热门文章
精彩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