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鲍曼,是为了避免中国社会学错上加错
2017年01月18日 15:49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陈振铎
今天我们要纪念鲍曼,目的不仅仅是总结他的学术遗产,而是要继续他提出的道德社会学问题,直面不确定性和碎片化,打破固化的区隔、让知识和学界流动与协同起来,不要让中国社会学走上异化的不归路、错上加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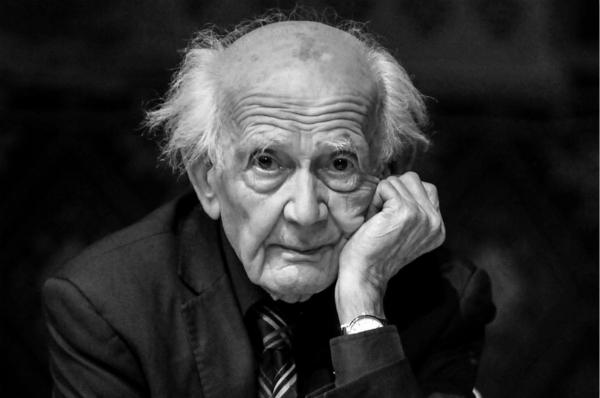
齐格蒙特·鲍曼
波兰裔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于1月9日去世,引起公众讨论。凤凰文化记者专访了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修的中国青年学者陈振铎,从中文互联网鲍曼现象背后的问题,鲍曼的学术思想史,以及鲍曼对中国社会学界和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等方面,向读者介绍这位西方社会学大师。
陈振铎认为,国内学界主要集中于对鲍曼的现代性概念进行的研究,并没有将鲍曼的理论遗产全貌呈现完整。他认为鲍曼的思想分为早期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研究以及后现代研究三个阶段。要理解鲍曼,要从目前中国学界尚未注意的社会学华沙学派入手,才能看到鲍曼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其实是在发展欧洲的人本/人文主义思想。
在专访中,陈振铎借鲍曼关于知识分子的道义问题,呼应目前引起热议的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成伯清的《中国社会学的三种趋向》一文提出的问题,对中国社会学界存在的各派区隔加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以鲍曼的思想,呼吁学界要打破固化的区隔、让知识和学界流动与协同起来,不要让中国社会学走上异化人本/人文主义的路。

鲍曼
以下为对谈实录:
凤凰文化:鲍曼去世后,中国互联网上随即出现了大量的纪念文章,为什么一位社会学家在中文互联网会得到如此重视?
陈振铎:我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看到不下十篇的各种文章在刷屏,腾讯、澎湃、端传媒、凤凰以及一批公号出了一批文章。这是罕见的。我想除了是互联网特有的传播方式外,《纽约时报》发表的长篇讣告,迅速引起了中国新媒体的重视,这和相当一部分人文社科毕业,或接受过人文社科训练的编辑对知识的敏锐又有关系。
然而,在这些文章中,大多数基于其几本中文翻译著作理解,出现了一些盲人摸象、一叶障目的美丽误会。表面的问题是由于理解不全面,但根本源于中国社会学界未对这位西方社会学大师进行系统的理解与批判。
学界之前并没有从思想史层面、对鲍曼的思想做过系统整理和研究,少量研究成果也仅仅是依托于这几本著作。这导致了对鲍曼的思想遗产的总结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或几个点,并未进入鲍曼思想的前因后果和相互呼应的体系,以至于公众仍旧对鲍曼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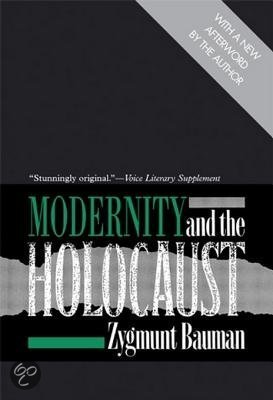
现代性三部曲之二:《现代性与大屠杀》
凤凰文化:公众对鲍曼的理解,主要来自于《现代性与大屠杀》,有人据此把他对大屠杀的研究和汉娜·阿伦特并论。您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如何看待鲍曼的整体思想?
陈振铎:鲍曼研究书目的常识性介绍已经比较多,我不赘述,但要说清楚的一点是,大屠杀只是他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最重要的论述并不是大屠杀或者极权这些表象的机制,而是关系到社会学的几个未竟之题:人在当代社会的位置、理性的多面性、社会学家的道义。
这和中国学界忽略了鲍曼的思想史有关。鲍曼的研究要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去理解:华沙学派、利兹时期,对应了三个阶段:早期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研究以及后现代研究。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思想是相互呼应的,虽然他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利兹时期,尤其是80年代末苏东剧变前后完成的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再加上他之后的流动性研究,这两个领域奠定了他作为西方当代社会学的大师地位。

现代性三部曲之一:《立法者与阐释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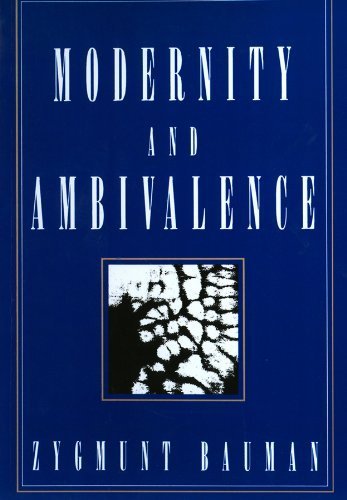
现代性三部曲之三:《现代性与矛盾性》
我们看到,后两个阶段的研究,也是中国学界和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对鲍曼最常见的引用部分。鲍曼不是出世的哲学家,他的每个概念都建立于对具体的社会事实的批判。按照中国现在对鲍曼的理解,就存在一个问题,他不断提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到底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诠释概念吗?
我看到目前的研究中,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因为,若按照一般的社会哲学从概念到概念理解,是得不到答案的。学界从来没有系统地对鲍曼以及与鲍曼关联的欧洲早期冲突论学派、华沙学派等欧洲经典的社会学理论进行研究。如果不进入鲍曼在波兰接受华沙学派的训练和研究,就不能理解后面他对现代性和非现代性这两个非常虚无的概念的具体指向。
实际上,鲍曼和波兰从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分裂出来的波兰早期社会学者是一脉相连的,对社会转型、知识分子的道义等现实问题,只不过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凤凰文化:社会学对思想史的贡献,我们熟悉的有法国涂尔干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但又如何理解波兰的华沙学派?
陈振铎:华沙学派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而是一条学术脉络。指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开创的欧洲社会学传统,他在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建立了波兰第一个社会学系,其贡献了人文主义协作和文化主义两大理论,以此形成学术传统。二战后到六十年代,该大学、波兰政治与社会科学院以及华沙大学,是华沙学派的阵营。我国学界在80年代转型初期,关注过该学派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但之后就断层了。
学派最早的学术思想,要追溯到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同一个时期的波兰裔奥地利经济学与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以及波兰裔瑞士社会学家雷恩·魏尼亚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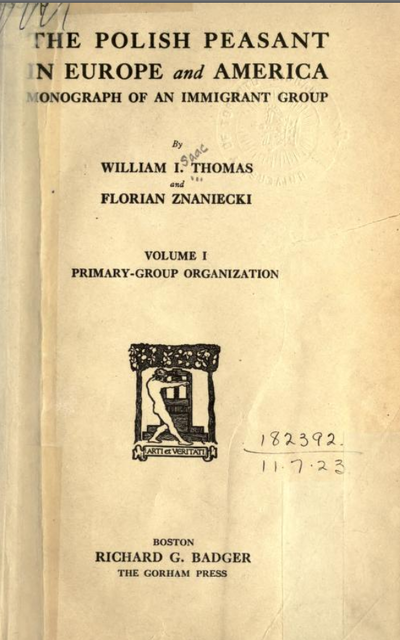
1918年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兹纳涅茨基作为学派创始人、波兰社会学之父,因和美国芝加哥学派威廉·托马斯合著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而享誉学界,后半生基本在美国。他们的这些渊源,以及战后展开的研究,和芝加哥学派以及法国社会学传统相互一致的,即服从于一个主义:讲人性、持人道、捍人文精神的人本/人文主义(humanism)。
华沙学派的门生、波兰社会学家奥索夫斯基,和他的学生、后来在英国的鲍曼,继承了这些理论遗产。华沙学派坚持的是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时被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鲍曼在华沙时期的研究,也主要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运动。这些立场导致了鲍曼等人被视作“毒草”而遭受迫害,最终导致鲍曼流亡以色列和英国。
这些传统,有助于理解鲍曼理论的社会事实来源,但他的理论架构是建立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变化,我们借助学术之外的西方音乐艺术可能来理解他的理论散发的特征更形象。比如我个人认为,菲利普·格拉斯的音乐,是和鲍曼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几个观点问题是有一致特征的:困境、不确定性、被个体、孤立、离散。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
最后,我们也要明白,鲍曼读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最后是指向传统的,即回到他们老师未竟的对人文主义协同和文化主义的思考,他不断提及用流动的而不是固化的、区隔的身份认同建立的共同体,来面对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并强调知识分子面对新穷人等弱者的道义,最后都回到了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命题:知识分子对社会事实的实证研究,解决现代性带来的问题。
凤凰文化:鲍曼的研究是基于西方社会与文化,那他之所以引起了中国研究者的重视,是不是由于他的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社会问题的相似性?
陈振铎:您说得对,谈鲍曼的学术贡献,还是要指向对于中国公众与学界的学术意义。尤其对针对那些从没有系统的理论训练、靠中文搜素引擎做资料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学者,鲍曼是个榜样与示范。
鲍曼不属于英美特色的,更属于欧洲大陆的左派知识分子传统,更像一个标准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理论和社会事实批判互相滋养,始终对社会现实保持孜孜不倦的热诚。鲍曼的著述和他本人算起,用中国互联网时髦语言比喻,他本身就是一个大IP,理论体系并不复杂,始终围绕上述几个概念在展开。
当然,鲍曼同时又提醒我们,紧跟社会事实,并不是要去迎合读者或和营销自媒体一样抢粉丝、增流量多挣钱,也不是像少数“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读了几本哈耶克和汉娜·阿伦特就可以在互联网上指点江山、争做国师,或者用些装神弄鬼的半吊子理论抬高自己的身价。
审慎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学人就应该要坚持独立,要清醒地和现实社会隔离开。这句话听去部分有道理,学者需要与社会保持距离。但从鲍曼的身上看到的是,独立并不是要社会学人离开现实问题,而是随时紧密地跟随社会主流问题进行抽象思考,当然,是经过系统理论训练的、带着理论思维的。

阿兰·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
社会学的本质就是批判与开放性,训练学者捕捉问题、并打破一切妨碍人自由与进步的机制,就这一点来说社会学是个“危险”的行业。因为它本质是让社会动起来的专业,不管是西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运动”,还是阿兰·图海纳的“行动”,或者是鲍曼的“流动”,都是对于现有社会及体制的反思和批判的,而不仅仅是分析它。
当然,有人会说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他们认为反思社会就是反对派,没看到反思和批判是为了更好的“社会”。鲍曼研究的精华部分,比如大家热议的其大屠杀研究背后,鲍曼想呈现的是,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作为杀人机器的概念,是具有普适讨论意义的。而这些讨论,目前显然还是“禁区”。
我们以某位北美的华裔社会学家为例,以研究八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成名。应该说,他和法国的某位华裔社会学家一样,对社会运动的研究相辅相成,在西方当代社会学界,从学术立场补充了关于当年运动的学术理解,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由于话题敏感,这位社会学家受聘于中国某精英大学后,他的研究最精华的部分不能怎么公开讲,变成用社会学研究历史去了。
凤凰文化:面对这种鲍曼的曲解与研究的禁区,从您来看,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应该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陈振铎: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成伯清在鲍曼去世后见报的《中国社会学的三种趋向》,虽然是巧合,但在我看来,成教授的文章在这时抛出,恰恰是对鲍曼最好的纪念。
他文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统计定量化、历史质性化以及没有系统理论训练的社会干预三个特征,认为这三派“真宛如三岔口,各奔前程,不仅互不搭理,还时常相互鄙薄。定量派看不起质性派搞不定统计和编程,质性派瞧不上定量派读不懂韦伯和福柯,定量派和质性派一起嘲笑实践派不够学术,而实践派则对闭门造车的书呆做派嗤之以鼻”。他对社会学界这种已然出现的分裂乃至碎片化的态势,是和鲍曼提出的现代性以及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学家的道义问题是互相呼应的,这些正是中国社会学界目前最需要重视的问题。
当然,中国社会学出现今日这些区隔幻象,非一日之寒。除了体制使然、社会学缺少当代社会学作为批判的天然属性外,主要是社会学教育出现了问题。由于目前就业导向的专业设置,社会学的主要学术和教学力量集中于少数精英大学。对比西方大学中,人类学和社会学作为通识教育,我们还远远不够。而对社会学存在潜在需求的学生,通过互联网的各种碎片信息吸收,以至于看不到整体性。以我自己为例,最早知道鲍曼是从书店和互联网,而不是教材和课堂上学到的。
社会学由于其具有社会调查、定量统计以及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力,在中国被吸收为政府服务,少数社会学学者成为政府的座上宾。社会学不是服务行业,如果有学人做智库,这无可厚非,但不该以社会学家的身份,而是接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咨询专家,要说社会学要不要服务谁,如果一定要说它有服务对象,那就是人,尤其是弱者,所以,”扶务”,从“服务”到“扶务”,这才是符合社会学的应用取向的。
成教授的忧虑,在我看来,就是鲍曼所言的“不确定性”的路,也就是一个没有认同、传统与共同体的原子化学界。我有一个比喻:中国社会学目前的学派,不是涂尔干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及华沙学派这样的“学术协同生产共同体”,更像中国各式各样用围墙围起来的院子,大家把自己圈在围墙内,一亩三分地,旱涝保收,有的是困,有的是自娱自乐。结果是什么呢?各派自立门户,退回到了小农经济的手工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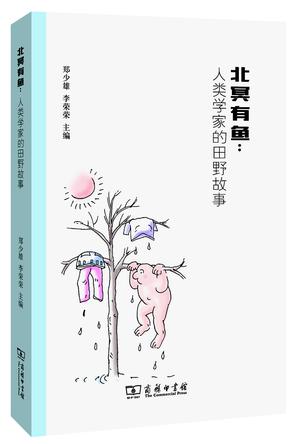
北冥有鱼
我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学的这些偏离人文/人文主义的异化,还造成了和社会学联系紧密的、中国亟须发展的学科——人类学的困境。人类学由于和民族学的历史纠葛,目前尚未成为一级学科,这意味着无法成为独立的教学单位,中国人类学界出现了鲍曼描述犹太人所说的那种边缘的“局外人”情势。最近,由中国人类学界组织编写的通俗畅销书《北冥有鱼》非常火爆,一群优秀的中青年学者面对这种边缘化,只能以自嘲和幽默抱团取暖。而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来看,人类学和社会学是相生相依的,都是直接研究人和社会,都应该是高等教育人文社科的基本训练。
中国的社会学不是没有好的传统的,也不是没有和世界接轨的社会学研究的。以我有限的观察来看,目前仍比较活跃的社会学者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培养的一批学生,在欧洲和美国社会学界接受训练后,非常有潜力。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学教授陈映芳,其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期间,带领自己的学生田野和教学研究相结合,出了一批优秀的都市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十几年过去了,仍在法语和英语社会学界不断地被讨论,成为西方社会学理解中国都市问题的主入口。同在上海交大的高宣扬教授,早年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出了一批成果。
人类学界中,庄孔韶教授、北大高丙中教授、清华景军教授都是打破区隔的翘楚者。遗憾的是,人类学界仍在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陈映芳因各种原因离开华师大后,冷清了很多。高宣扬现在变成了哲学界的人,和其早年在法期间追随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传统,变成了历史。
所以说,今天我们要纪念鲍曼,纪念的目的不仅仅是总结他的学术遗产,而是要继续他提出的道德社会学问题,直面不确定性和碎片化,打破固化的区隔、让知识和学界流动与协同起来,不要让中国社会学走上异化的不归路、错上加错。
(陈振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社会学博士生,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水库移民、中欧穆斯林移民以及城市街区。)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