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南怀瑾是奇人 有一股吸引力
摘自:许倬云口述 李怀宇撰写 《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版
|
阅读提示: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阅读连载】 |
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我毕业之后在美国多待了半年,这半年自由自在,原因是我的奖学金还没用完,顾立雅让我帮他的忙,坐在东亚图书馆,摆个桌子,图书馆正好有块空地,用玻璃圈起来。我的工作是,所有读中国东西的人,要查资料的,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会跟他们讨论。
回台湾,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弯。当时有很多人就留在美国,我在芝大毕业以后,有五个工作随我挑,包括芝大希望我做历史地理研究,不但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且是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还很少人做,是很有挑战的。但我执意回台湾,就没接受,另外四个工作都是好大学的教职,我也不管它了。如果当时留在美国,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貌。
我回到台湾就一头栽进了工作,刚开始情况就非常复杂。我的老师们,一直希望我能在行政和公众事务上帮他们的忙,据说他们从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此期许。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从副教授成了系主任,是个意外。系主任余又荪车祸死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教育部”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在南港,我就变成了李济之先生的助手。王世杰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派我做一些学术外交,要我帮他做院里的涉外事件。钱思亮校长在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派我去做过。他们这几个老先生的意思是锻炼我。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独裁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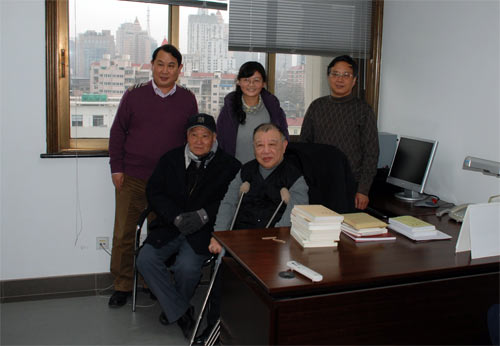
许倬云(来源:资料图)
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

初到台湾的蒋经国一家(来源:资料图)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反驳中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话,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却不签。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成立了民进党,特务非常紧张,要求抓人。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关于党禁的问题,有些学者还说要制定政党法,蒋经国也不理,他说:“政党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党法不政党法。”这话是对的。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增进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台独”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李登辉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