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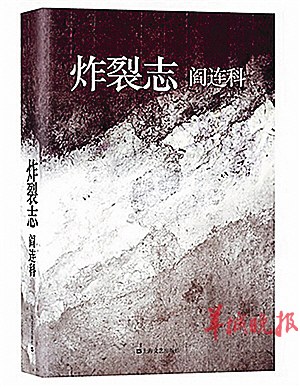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高亚飞 周惟娜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1978年应征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情感狱》、《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风雅颂》、《四书》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言论集十二部;另有《阎连科文集》十六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入围2013年度英国国际布克奖短名单,并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
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20多种语言,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作家。
近日,作家阎连科带着新作长篇小说《炸裂志》,做客方所书店两周年庆系列讲座。他以“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为题,从《炸裂志》及“神实主义”文学谈开去。讲座过后,他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
阎连科自嘲说一直以为自己是“主旋律”、“正能量”的作家,没想到作品却一直被认为是“负能量”的代表。他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这种写作,要告诉读者的正是读者看不到的东西,是那扇光明的窗户后面的内在、本质和人心最复杂的一部分”。
阎连科说今天中国现实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已经到了任何一个作家都没有能力把握的程度。“中国现实的复杂、荒诞、丰富和深刻,已经远远把作家的想象甩到了后面。生活中的故事,远比文学中的故事传奇、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作家没有能力把握这些,也没有能力想象和虚构这些。作家的想象力和现实的复杂性进入到同一跑道进行赛跑,跑赢的是中国现实,输掉的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即便作家有天大的想象力,都无法超越现实本身,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阎连科把《炸裂志》的写作看做是他与中国现实变幻的一次思想赛跑,“输的可能是《炸裂志》,但赢的也可能是《炸裂志》,而读者是这场比赛最好的裁判。”但阎连科以为,他都从来没有像这样真切地面对现实,面对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明确地在文学中和现实构成如此直接的对话。就凭这一点,无论输赢,他相信读者都一定会对他和《炸裂志》表示宽容和理解。
不过,他也说,输掉归输掉,赛跑归赛跑,坚持走过没有光的胡同,终会有一线光明。这一线光明,就是来自读者的认同。“也许你的写作充满争议,也许你作品所表达的艺术性会让有些人怀疑,但你所表达的那种最质朴的良知和正直,读者是会认同的。我想一个作家写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到最后的同一平台上,更见功夫的不仅是艺术和技术,可能更是正直、良知和最独立的人格”。
1、用“炸裂”形容当下中国很精准
“以此表达30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包括社会和人心的现状”
羊城晚报:读《炸裂志》这本小说的感觉是,用“炸裂”二字来形容当下中国的飞速发展十分贴切,西方国家几百年完成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几十年就完成了。这个名称是否隐藏着类似的深意?
阎连科:是。其实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儿,我们谁都说不清,很难用一个字或一句话来形容当下中国的状态。我们可以说是发展的爆炸,也准确,但还不够。而“炸裂”这个词,似乎就准确、深刻了。
“炸裂”是四年前我偶然看到的,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某间教室的海报上,全部韩文中用了“炸裂”两个汉字。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教室人满为患,多得要爆炸了,用来形容有老师讲课学生已经爆满到没有座位。然而我觉得,这两个字非常精准地概括了今天中国的现实,或说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它不仅是爆炸,更重要的是一种分裂。人内心的分裂,人与人关系的分裂,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分裂等等。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两个字实在太精准了,要写的小说就用这个名,以此表达30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包括社会和人心的现状。
羊城晚报:所以您是从四年前就开始构思这部小说了?
阎连科:要说写这部小说,也是靠点点滴滴累积。《炸裂志》里女性人物那条主线,我在十五六年前就想写部小说叫《姐姐妹妹》——想写一群乡村的女孩子都到了南方,比如广州、深圳、海南,或者东莞,不管她们在这些城市做什么,她们的家乡因此富裕了;人,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我不会写她们在南方具体的经营和生活,主要笔墨就写她们家乡的变化和那些不可思议、扭曲变形的神奇故事。然而,真要写时,又觉得单薄,以这样的容量写中篇比较可惜,但写长篇又分量不够。所以没写,直到现在就变成了《炸裂志》的一个部分,一条线索。但具体是从我去年三月到香港浸会大学驻校开始写起的。
2、对历史的书写是一种主客观较量的过程
“地方志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
羊城晚报:为什么小说第一章和最后一章要用小说的形式来写整部小说如何出炉的过程,作家阎连科写虚构出来的作家“阎连科”,可以说这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种“元小说”的设置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安排吧?
阎连科:我们看所有的地方志,开头基本都是主编要出来很牛地说那么几句话,所以也就那么写了。至于结尾,更重要的是,它会给读者带来很多别的想象。比如说写这样一本地方志,书里的孔市长不满意这部《炸裂志》,拿火把它烧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炸裂志》又是哪儿来的?到底哪个《炸裂志》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似乎有种“书中书”的意义。由此,我们会想到我们所有的历史,都是真的吗?但你如果不相信这些,又该相信什么呢?
羊城晚报:这里边其实隐藏着您的历史观。
阎连科:是这样,所有现在留下的历史都是主观的。撰写历史的人,也许他对世界的认识尽可能客观了,但就在他尽可能客观的同时也无处不渗透着他的主观。在历史记忆中写哪些不写哪些?皇帝要求写哪些?而我又不想写哪些?这些都是一种较量的过程,是一种主客观较量的结果。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可能都是被别人过滤过的东西。
羊城晚报:为什么要用“地方志”这样的形式来写《炸裂志》?
阎连科:我的小说从来不缺少故事,不缺少人物,不缺少千奇百怪的情景和细节,而是缺少某种讲故事的方法。这不光是小说的形式,还是小说的思维。比如我用《四书》的方式讲,我用《受活》的方式讲,我用“地方志”的方式讲,同时也都包括小说的叙事和思维。如《炸裂志》中有很多最真实而又超想象的细节,他们的来源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的思维和方法。地方志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思维。思维的方法决定了很多故事最本质的东西。
3、基于非常自私的想法提出“神实主义”
“要尽可能地放弃物理逻辑关系,只强调内因果”
羊城晚报:你称自己的小说是“神实主义”,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阎连科:我的想法是:或者,中国作家的写作可能确实还没有逃离西方文学的框架;又或者,我们早就逃离了,中国的写作已经非常丰富,非常“中国”,可批评家有点偷懒,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去讨论,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说清楚,好像读者才可以理解。
比如今天评论阎连科的小说会说什么批判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黑色幽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套到阎连科的作品头上。你有时候很高兴,有时候心里很不爽。我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小的非常自私的想法提出“神实主义”的。
中国作家无论如何,今天写作怎么样,借用、汲取多少西方的写作经验,但我们最终都必须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不能完成西方的现代性。
羊城晚报:那“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阎连科:你看拉美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魔幻现实主义最大的特点,一是所有魔幻的都是人无意识的,比如所有人会突然梦游,这是最无意识的东西。二是我们认为魔幻的,其实都有内在物理因果关系。比如人生出来都长尾巴,这是和我们人类的进化有物理关系的;再比如磁铁经过家具时家具上的铁钉都会纷纷掉下来,磁铁和铁钉是有物理关系的。包括《百年孤独》里最后主人翁坐着飞毯走掉了,而这前提是刮了一场飓风,那飞毯是借风、被风刮跑的,这也是有着物理关系存在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某种半因果关系,是物理逻辑关系的不对等,很小的原因有很大的结果,或很大的原因导致出很小的结果来。
而“神实主义”,是要尽可能地放弃这种物理关系,只强调内因果。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事情表面的因果逻辑关系完全不存在,但它必然有个内在的、看不见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我强调的神实主义。比如小说的开头,村长特别想和秘书耍一腿,但秘书不同意,后来村长变成了镇长,秘书的衣服扣子自己就纷纷掉落了,主动在镇长面前宽衣解带了。这儿其实是有个“内真实”、“内因果”,而这内在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权力的无所不能。《炸裂志》很多地方都贯穿了这种内因果的关系,根本上是这个区别吧。
4、“炸裂市”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
羊城晚报:可见您这部小说的抱负其实是蛮大的,炸裂村如何变成炸裂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命题。
阎连科:当然有些话不太该说,其实一个作家是可以写出大小说的。为什么要用一滴之水去映照大海,直接写大海不就行了?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写大海,所以才写了一滴水呢?我们有以小见大的传统,那我想就直接写个大的行不行?我以为,一个作家要有能力,要尝试,要有勇气去审视一个民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很早就想写一个“大”的小说。这个大,不是指他的长度,而是指它现实的容量和体积。但在小说中,有些地方最后没有写下去,包括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光只是变成了直辖市,它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这个情节担心不能出版,最终没能写出来。
羊城晚报:所以写这部小说跟之前的长篇感觉会很不一样?
阎连科:写《炸裂志》有种轻快的畅感。之前写《四书》、《丁庄梦》、《受活》、《日光流年》,都非常痛苦,因为那种写作不能给你带来快感。但《炸裂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忽然有了太多召之即来、挥之不去的想象和奇异的情节,好像小说情节就放在书桌上,每天你坐在桌前,拿过来就写了,没有任何地方是卡壳的。小说就这么行云流水地写了出来,好像一提起笔,它就在那里。之前写的几部小说,有时候你还是要去想想构思什么的,而这本小说,最有趣的地方,恰恰是最不需要构思的。
羊城晚报:其实也还是跟您对当下社会的体认有关系,包括你十几年前就想写姐姐妹妹的故事。
阎连科:是,我觉得你对现实的关注,可能是你的命运决定的。比如说你从小来自于最底层的乡村,而今天你所有的亲人、疼爱的人,仍然生活在那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这些亲人,其次才会关心你的朋友,再其次才会关心朋友以外的人,这个关心、爱的次序是非常清楚的。当你最爱的那些人,仍然命运坎坷,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你会去思考许多现实的问题,会和现实有种很紧张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会被你带进小说中。
拿我来说,我的尴尬之处是:第一我绝对不是北京人;第二我也不是原来那个乡村人。那个乡村不会再认同你是那里的人。这种尴尬,其实对写作有好处,这让你可能更客观地去认识那块土地,既保持非常复杂的情感,又有更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果你一直在那片土地上,可能无法认识外面的世界,也无法超越那块土地。你离开了,就可以清晰地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乡俗、权利和婚丧等一切文化的复杂性和现代性。
羊城晚报:“炸裂市”的原型是深圳?
阎连科:至少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圳给了我写作的启发。这个小说直接写一个乡村在三十几年间变成超级大都市,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深圳,从小渔村变成今天这样。小说中某些情节确实也是来自深圳的。比如开头写到孔家弟兄四个听了父亲的话,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那是一个深圳的朋友很早时候告诉我的,说深圳当年来了四个大学生,到了那里什么都不懂,为了生存,为了命运,就果真在某一夜的酒后朝东西南北去冒险了。小说里的弟兄四个的命运方向,其实就是这四个大学生的命运方向。
羊城晚报:您之前的不少小说引起了蛮大的争议,现在也包括对《炸裂志》的某些非议,您一般怎么看待它们?
阎连科:我想首先讲一点,禁书并不等于是好书,这个要搞清楚。第二,在中国写作生态不健全的环境中,作家如果一生的写作都在赞歌中,没被争议过,那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在这个写作环境中,争议是极其正常的。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反过来,每部小说都被禁掉,也是不正常的。当然,今天大家说起阎连科可能更敏感一点,比如说《四书》在法国出版时,几乎所有的记者和读者,都不太去讨论小说写什么,大都讨论你怎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小说,可中国却恰恰相反。我想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对文学认识的一个差别吧。他们更注重艺术的本身,而我们可能更注重内容的本身。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智能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