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中书写“文学文化史”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上卷主编,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负责下卷。
■ 两主编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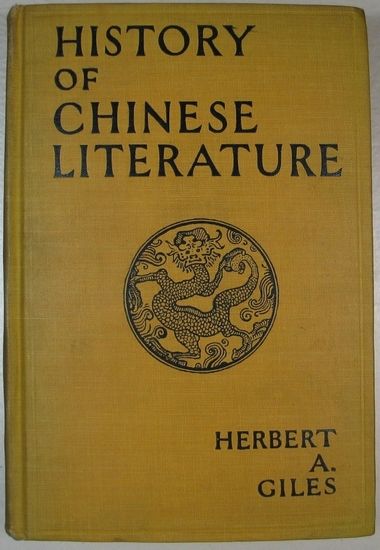



1906年出版的窦士镛《历朝文学史》是如今发现的最早的国人书写的中国文学史,但英国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所著《中国文学史》于1901年出版,更早窦氏5年。从左至右依次为:(英)翟理思《中国文学史》、(日)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胡适《白话文学史》、(日)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是《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上卷主编,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孙康宜负责下卷。这几年,他们俩均在不同场合介绍了这部文学史的编纂进程,这也让整个华语世界的文学史研究者好奇,这部由海外尤其是以北美学者主导的中国文学史将是一部怎么样的文学史?它会有哪些创新或者突破?
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孙康宜教授强调《剑桥中国文学史》不再以传统的“文类”分野来机械地探讨一个文本, 而是把文本视为“文学文化”中一个有机的成分。作者之一、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教授对早报记者说:“任何一部文学史,尤其是一部好的文学史,一定也得是‘文学文化’史。就拿我写的那个时期(注:东晋到初唐)来说,是手抄本文化时代,是宫廷文化时代,要了解那个时期得首先知道手抄本文化和宫廷文化都意味着什么。不知道这些个基本的东西而去谈那个时期的文学,就会犯一些违背基本历史常识的错误。”
为西方读者提供
基本叙述背景
东方早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生活的中国学者或者海外汉学家,并没有召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这是一个怎样的选择?
孙康宜:这绝不是有意的偏见,而是基于实际需要的配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最初构想是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CUP)文学部主编 Linda Bree 于2003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提出的。当时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刚(于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头的、以文类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同时,荷兰的布瑞尔公司(Brill)也正在计划出版一部更庞大的多卷本。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宇文所安以及几位海外汉学者也正在考虑着手为西方读者重写中国文学史, 而碰巧剑桥大学出版社来邀请我们出版一部具有“特殊性” 的 《剑桥中国文学史》。既然我们的研究方向与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标不谋而合,我们很自然就邀请我们原来已计划好的“合作者”(他们大多是在美国执教的汉学家,除了贺麦晓是英国伦敦大学的教授)来分别写各个章节。所以,我们从来也没考虑过作者的国籍问题。此外,这是一部用英文写的文学史,每个作者负责的篇幅又长,而且交稿期限也很紧迫,所以我们也不便去重新召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的学者。
东方早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是西方普通英语读者,这对你们在写作时有何障碍?
孙康宜:从狭义的方面来说,“西方普通英语读者”主要指研究领域之外的那些读者,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背景,以使他们在读完之后,还希望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有关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知识,应当是我们的目标和挑战。话又说回来,我们所谓“普通读者”并没排除在欧美世界研究中国文学的读者。
宇文所安:针对普通英语读者而写,有其难处和限制,这里的挑战正在于把这些限制转化为有趣的新的可能性。如果是面向中国读者或者面向专业领域读者,我会写得很不一样。比如写到唐诗,我会一个诗人接着一个诗人地来写,并且给出每一位诗人的背景。但一个普通英语读者可能才读了二三十个诗人就会对这种写法感到厌倦。把诗人们的生平与作品融入更大的“文学文化”中来讲述,会更容易保持读者的兴趣。
多种体例书写
东方早报:你们把《剑桥中国文学史》定位为一部“文学文化史”,能否先给“文学文化史”做一个定义?
孙康宜:英文版《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和写作是完全针对西方的英语读者的,因而所谓的“文学史定位”也自然以西方的文学环境为主。从前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所盛行的结构主义,主要注重的是分析文本的内容,以及个别读者和阅读文本之间的关系。但在那以后,学院派渐渐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文本的意义必须从文化的广大框架中来看,于是问题就变得比较多面化,也走向“外向化”。目前大家所关心的问题是:一个文本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在同一个时代里,这个文本和其他文本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就使“文学史”的撰写变得更像“文学文化史”了。
宇文所安:“文学文化”是一种把文学作品置于文本生成及相关制度的更大语境中的方式,它能够展现各种文体之间的联系。这一写法并非“西方”,傅璇琮和贾晋华在《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就已经开启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著作让我们看到在一个特定时段内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事情。
东方早报:《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有很多位,是否可以这么理解,通过这些作者的视角重新定义何为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
孙康宜:文学中“何为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绝不是某个人的主观意见可以决定。例如,现代的读者总以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类是长篇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等,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去认真阅读那个时代各种文学文化的作品,就会发现当时小说并不那么重要 (至少还没变得那么重要),主要还是以诗文为主。小说之所以变得那么有名,是后来的读者们喜欢上那种文体,并将之提携为经典作品。
所以应当说,撰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几位作者都很关注“何为经典,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的问题,他们也会思考与接受史有关的问题。但不能说《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作者只是用自己独特的“视角”来“重新定义何为经典”,或决定“哪些作品可以进入文学史”。“何为经典”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宇文所安:关于经典,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是经典一直在变化,并且还要继续改变——除非它已经僵化。虽然我们不能展现这个(变化)过程的全貌,但一部好的文学史可以向我们提示这一过程,比如可以谈论哪些作品在唐代被认为是重要的,哪些在清代被认为是经典,可以探讨哪些作家和哪些书写形式在20世纪变得重要,并指出那些被忽略、但值得关注的作家。
东方早报:整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体例很多,有围绕人物而写,有断代等等,你们怎么尽量减少体例繁多带来的阅读障碍或困扰?
孙康宜:如果把《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剑桥意大利文学史》相比,我并不觉得我们的体例特别多。其实剑桥文学史的每一本“欧洲卷”也同样具有各种不同的体例——有围绕人物而写,有按不同的分期,不同的文体分类来写等等。我想《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特别的地方乃是它所包含的“文学史”的时间长度。因为剑桥史的“欧洲卷”均各为一卷本, 唯独《剑桥中国文学史》破例为两卷本,这是因为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悠久的缘故。
宇文所安:按照传统的分类法(重要作家作品、文体)来写很容易,但把那些不同的片段相互串联交织、形成一个单一和完整的叙事则很难。而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文化史,它的确是一个单一完整的叙事。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国文化世界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文学史影响阅读实践
东方早报:这一二十年,各类中国文学史的著作非常多。在你看来,文学史对文学的意义在哪里?
孙康宜:在我看来,文学史的意义就在于它代表了某个时代(或地域)的特有文化阐释方式。同样在“中国文学”这样一个语境下,在西方用英文写的“中国文学史”自然会与在中国用中文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不同。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害怕国内的中文读者会对这部《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中译本产生某种误解,甚至失望。当初如果我们是为了中国读者而写,我们的章节会用另一种角度和方式来写。现在我们既然没为中文读者重写这部文学史,我们也没必要为中文版的读者加添一个新的中文参考书目。的确,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会产生不同方式的“文学史”。
宇文所安:文学史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阅读实践之中(在欧洲也是如此,但在南亚可能没到这个程度)。比如说,我给你一首律诗,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美;但如果我接着告诉你它是来自明代,你再去读,很可能会得出与我告诉你“这是一首唐诗”后不同的评价。因此,一部好的文学史会使我们已有的阅读方式更加丰富。
东方早报:宇文所安教授在上卷导言中说道:“所有这些现场都为文学史带来了难题:这些现场清楚表明,作为一项现代工程的文学史,在何种程度上与民族国家及其利益绑缚在一起,为民族国家提供一部连绵不断的文化史。……”这里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语言政治”问题。你认为,你和其他几位学者在编写这部著作的时候,总体上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孙教授又是怎么看的?
宇文所安:一般来说,古代文学曾经是一个特定阶级或性别的占有物。在现代民族国家,它通过被纳入由国家建立的学校系统而得到转化,作为国民共同的占有物被教授,为创立 “国家文化传统”作出贡献,而这种国有文化传统是国民对其国家产生认同的主要方式。现代国家政府大笔投资于这一事业,是有目的而为之的。这比任何意识形态都更加影响深远。在这一(创立国家文化的)过程中,从过去流传下来的文学材料被重新设定以符合这些新的目的。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历史事实。
孙康宜:文学史当然会涉及“语言政治”。我想有关这一点,宇文所安教授是同意的。但下册有关现当代文学的篇章, 以及“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诸问题,不会出现在这个北京三联的简体版中。《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英文版早已于2010年出版,读者可以参考。![]()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