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辛丰年

辛丰年 1923-2013.3.26 生于江苏南通 蒋立冬 绘

辛丰年的第一本音乐随笔《乐迷闲话》(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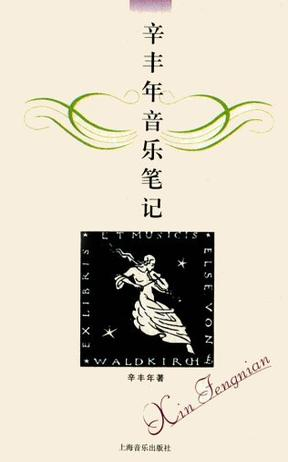
集其艺术精华的《辛丰年音乐笔记》(1999)弥足珍贵。

《和而不同》(2005)是辛丰年与严锋谈书文章的第一次结集。
昨天中午,古典音乐评论人、作家辛丰年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在南通去世,享年90岁。
辛丰年的儿子、复旦大学副教授严锋昨天在微博上通告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他说:“我父亲严格(辛丰年)因突发疾病,今天中午12时20分在南通医院中去世,终年90岁。父亲一生忠厚老实,善良正直,在极艰难的困境中把我们兄弟带大。他在任何时候都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追求,从未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念。他这一生过得很苦,也过得很好。”
严锋昨天在从北京回南通的高铁上对早报记者表示,父亲的后事将遵从他的遗愿一切从简,“具体安排,还需到家后和家人商量。”
在辛丰年去世前一天,他的家人给他播放《蔷薇处处开》等几首老歌给他听,他像初次听到一般,欢喜赞叹:“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的音乐。”
辛丰年身体一直很好,几乎没有去过医院。这些年年纪大了,体力一点点衰弱下来。最近半年,多半卧床,但最近精神又好了许多,所以昨天去世,非常意外。
辛丰年,原名严格,1923年生,江苏南通人。1945年开始在新四军军中从事文化工作,1976年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新开始写作,长期为《读书》、《音乐爱好者》、《万象》等杂志撰写古典音乐评论,驰誉书林乐界,著有《乐迷闲话》、《如是我闻》、《处处有音乐》等十余种作品,在年高之时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
辛丰年最初的文章都在《读书》上发表,后来还开了音乐评论专栏“门外读乐”。《读书》杂志创始人之一的董秀玉昨天对早报记者表示,“辛丰年最早是自己投稿过来,我们都觉得很好,就长期约稿。在他慢慢成名之后,虽然很多杂志比如《爱乐》也约他写乐评,但大部分文章仍在《读书》上发表。”董秀玉说,“虽然我们把他的文章称为古典音乐乐评,但其实他写的是文化。他写的乐评不是技术性地谈音乐,而是借音乐谈他对文化的理解。”
《爱乐》杂志前主编、《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昨天也在微博上悼念先生离世,“老先生选此花香月圆之日,愿一路都有他一生喜欢的音乐相伴。我不认识辛先生,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在《读书》杂志漫谈古典音乐的《乐迷闲话》是影响了无数人的。身在南通这样一座小城,因古典音乐而联通了那样大一个天地——他被音乐温暖的一生是幸福的。”
因为在《读书》上的乐评吸引了大量读者,辛丰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一直为他的读者所好奇。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辛丰年的儿子严锋曾说:“辛丰年不是音乐家,不是音乐评论家,不是作家,不是评论家,不是学者,甚至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因为他的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辍学。”
辛丰年小时候从4岁到10岁在上海生活过,家庭教师中有复旦大学教授王蘧常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辛丰年在家自学,在教科书中读了关于贝多芬《月光曲》的故事,从此迷上音乐。辛丰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做过很不好的官,他是孙传芳的部下。1938年,我逃难到上海又住了一年。但是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就又回到沦陷区,这时我主要就是自学了。还学了古琴,也是一知半解的。”
辛丰年父亲名叫严春阳,是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下,据说曾从死人堆里背出孙传芳,后任淞沪戒严司令、淞沪警察厅厅长、淞沪商埠卫生局局长,后来下野在上海淡水路法租界里做寓公。
“对于祖先,辛丰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赎罪心,这种原罪的意识,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接触革命思想,到‘文革’中的吃尽苦头,一直到发家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严锋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透露。
在严锋看来,父亲辛丰年首先是一个老干部。辛丰年22岁加入了新四军,先做文化教员,后来又到文工团工作,“可是一个坏人也没有杀过”。严锋回忆说,“无论如何,辛丰年身上军人的痕迹还是很浓的,在60岁以前,他走路都是大步流星,昂首挺胸——哪怕是去上厕所。另外,有时候说话间也会带出一些当兵人的粗口。家里三分之一的书是和军队有关的:从拿破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聂荣臻回忆录。我的弟弟和我从小就是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和《志愿军一日》这样的书长大的。”
“文革”期间,辛丰年本来是个逍遥派,后来因看不惯一个林彪在他们军区死党的飞扬跋扈,说了几句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又因出身不好,被开除党籍军籍,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回他的老家监督劳动。“那个地方叫作××省××县××区××公社砖瓦厂。他的工作,一开始是用手工做小煤球,供厂里的工人取暖用。”就算在这样的劳作生活中,他还会在下班后拿出小提琴来拉上几段,最经常拉的是萨拉萨蒂的《流浪》和马斯南的《沉思》,后者是他最喜欢的音乐之一。严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琴声和歌声响起来的时候,窗子上就会映出大人和小孩一张张好奇的脸。”
1973年,随着林彪的倒台,辛丰年恢复党籍,就地复员安排工作。严锋写道:“草屋改成了砖屋,一下子工资狂涨到五十二元一月,周末吃点肉是不成问题了。所谓‘就地安排’,就是在五窑砖瓦厂做了一个理论辅导员,人称‘某主任’,小小的公社砖瓦厂,主任不下十来个,但是工资最高的居然就是这位从最低级的工人超拔上来的‘主任’。”1976年,粉碎“四人帮”前夕,辛丰年终于彻底平反了,复员改转业,完全恢复原来的待遇。但53岁的辛丰年提出退休,“退休手续一办完,他就拿起一根扁担,用补发的工资到新华书店里去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买了回来。鲁迅全集、资治通鉴、艺苑掇英、文物杂志……要看的书实在是太多了,怎么来得及呢?连吃饭的时间都只好也用来看书。”严锋在回忆文章中说,“还有音乐。”他去买了一台上海录音器材厂的601型盘式录音机,一个在当年骇人听闻的奢侈品,当时要四百多元一台。然后开始自己录上海调频台的古典音乐。1986年,终于花两千多块钱买来了他平生的第一台钢琴。在63岁的年龄,一个人开始学钢琴,一上来就弹舒伯特,弹肖邦。辛丰年是古典音乐原教旨主义派。对“流行音乐”从一开始就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
辛丰年人生的好戏从60多岁开始,1980年代中叶,辛丰年的生平好友章品镇先生(章品镇先生就是当年指引他走向革命的那个人)推荐他为三联写一本关于音乐的小册子《乐迷闲话》,在这过程中,就结识了三联的宋远先生,后来就开始为《读书》写稿,开设了“门外读乐”专栏。辛丰年的名气就大起来了。严锋曾说,之后朋友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逐渐也就会加上一句‘他的父亲就是辛丰年’。而辛丰年自己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点都不知道自己早已行情大涨,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了。”
在严锋看来,父亲的文字精练而老辣,但是过于锤炼,文气太紧,信息量过于密集,总是梦想把大量的内容浓缩在最少的文字中,有峻急之嫌,犯了时文的大忌。“这也是迄今为止辛丰年的文章如此之少的原因吧。他写得太吃力。早上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把炉子点燃,烧上一壶开水,然后拄着拐杖,拎着菜篮子到离家并不是很近的菜场去买小菜,回来的路上买好儿子媳妇和孙女的早点。其实这两年家境大有改善,孩子们的工作都不错,自己稿费也有一些,请个保姆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不愿意,基于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剥削阶级人压迫人生活的永恒的厌恶。回到家,听完BBC的早新闻,就开始伏案写作。他总是一遍一遍地修改,每改一遍就要自己重新认认真真地用圆珠笔重新誊写一遍。”严锋在《我的父亲辛丰年》一文中写道。
辛丰年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听音乐的时候绝对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严锋说:“听音乐就是听音乐。这样一来,时间就更少了。我基本上接受了辛丰年的这种对待音乐的态度,并把那些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的人看作西贝货(‘西贝’组合为‘贾’,通‘假’,意为假货)。”
现在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严锋写了多篇关于父亲的文章,不过辛丰年生前却说,“严锋的文章用了夸张的手法,不可信。”在大学时期,严锋和父亲有了一些矛盾,因为那个时候严锋在大学里见识了不少的世面,回来以后认为父亲太正统太传统,所以每次和父亲谈话父子俩都会产生一些争执。反而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就是严锋大学毕业十年之后,严锋渐渐发现,当年父亲说的很多话是对的。严锋感叹,人生其实也是这样的。于是严锋变得宽容了,而辛丰年也变得更宽容了。两个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后来,他们父子合写过一本书,名为《和而不同》。说起父亲和自己的交流,严锋最难忘的还是在下放时期,每天一个多小时的散步非常难得也很重要,培养了父亲和自己之间的认同。
晚年的辛丰年,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晚上8点睡觉。在家里做点家务和体操,其余的时间都用于看书。他曾说:“我现在很少听音乐,几乎不听。没有时间,时间用在看书上。我要补课的书太多了,有些书过去读了不求甚解,现在要重读,而且不是一次地重读。现在我的眼睛越来越不行,看书很吃力,很慢。要休息,不然就看不见。所以不能耗费宝贵的时间在听音乐上。我就把音乐忍痛戒掉。这个说出去也一定很奇怪。香烟都戒不掉嘛,怎么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戒掉了呢?不得已。我现在就是抢时间,在自己眼睛没有瞎之前,能多看一点书。”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