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微妙的情感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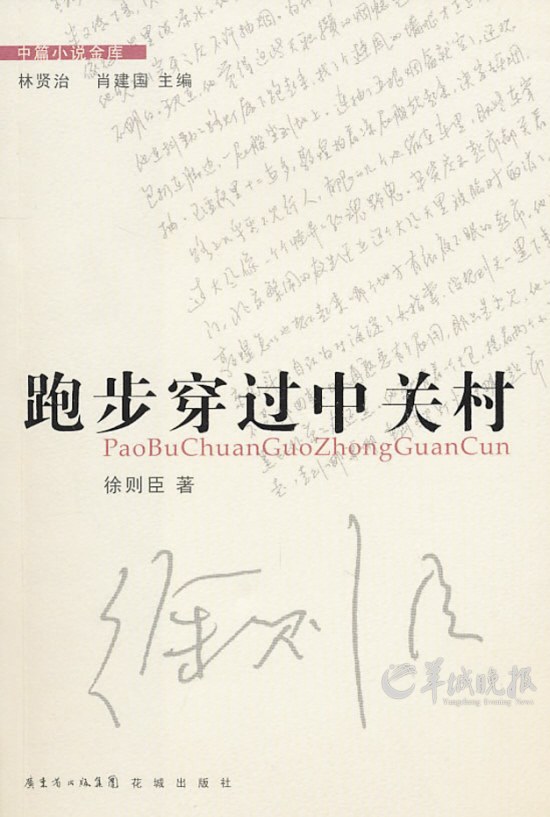


□张鸿
徐则臣
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夜火车》、《水边书》,小说集《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人间烟火》、《居延》等。曾获春天文学奖、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庄重文文学奖等。根据中篇小说《我们在北京相遇》改编的《北京你好》获第十四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电视电影奖,参与编剧的《我坚强的小船》获好莱坞AOF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赴美国克瑞顿大学做驻校作家,2010年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张鸿:你是70后的代表作家,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是一般人所认为的“科班出身”,从我个人感觉来说,大学培养不出好作家。你是否认为你是先拥有作家的天分,然后在经过北大熏陶、老师的指导之后,才有今天的成就呢?
徐则臣:北大对我的作用非常大。我知道,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你说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也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北大的一个老系主任,杨晦先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学者。在他执政的好长时间,乃至他执政以后的很多年,一直到现在,每年新生的开学典礼上,中文系的领导或者老教授都会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好好做学问、安安心心看书,别想着当作家,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这个传统一直到现在。我想这里有些偏见。可能是我入学之前就入了道,有了一些感性地进入写作的经验。我在很长时间内也有困惑。当我做论文,把理论的书看完以后,直接过来写小说,会觉得那个思维完全不对,转不过来。北大中文系又是一个特别讲学术的地方,用我个人的话来说,北大中文系有一种学术意识形态。一个学生优秀不优秀,不看你的才学,而是看你的学问做得怎么样。有很多人其实是没什么才华,但是他懂理论,他记得很多的死知识,能张嘴跟你说这个理论那个理论,你会觉得这个很牛。如果你写小说,你要把很多的时间放在阅读名著上,要放在编故事上,放在琢磨小说技巧上,你跟人家谈的时候,理论的霸权就会笼罩住你,你会觉得特别孤单、特别自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痛苦,我的导师曹文轩老师跟我说,没必要,如果你想知道哪个理论,花几个小时、花两天你就能了解得差不多,大概的东西你都知道,谈起来没有障碍就行了,你要知道你究竟想干什么。因为这些话,我才放松下来,把更多的精力偏向写作上,然后慢慢地就发现,写作和做学问之间逐渐能够转换和互动了。
学理论对我有一个很好的思维训练。我觉得,一个好作家需要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必要的反思与自省的精神。
写边缘人感同身受
张鸿:你的代表作“京漂”系列,《跑步穿过中关村》,《夜火车》等使你在同年代作家中别具特色,办假证、卖盗版光盘等小人物在你的小说里经常成为主角,你擅长将这些小人物的命名放在一种很动荡的生活的旅途中去加以描写。为什么会去写这种边缘人?
徐则臣:很多人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些人,跟我的生活的确是非常不搭界。但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后来我很认真地考虑了这个问题。他们是边缘人,我觉得我也是边缘人。我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在北京待可能跟在深圳和上海待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在北京要有一个身份的问题。外地人进北京,要有一个进京指标,拿不到进京指标你就成不了一个北京人。尤其是在一些所谓的事业单位或者是衙门里面,你会发现你在编跟你是个打工的,完全两回事。别人享受的福利你享受不到,别人可能有的发展空间你没有,你的工资永远固定在一个数上。签协议时,一个月拿一千五,干了三两年后你可能还是一千五。可能你并不在乎那些福利的变动,也不在乎那个发展的空间,你觉得这样待着也很好,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别的人和别的事不断地提醒你———身份!过去的好几年里,我户口不在北京,需要办一个暂住证。为这个证我跑了五趟派出所。第一次说不在这个派出所,要到另一个派出所;我就去另外一个派出所,到那边人家说我马上下班了,你下次再来,然后我就下次去;下次再来,工作人员说办事的那人不在,你下次来;然后我再去了以后,让我回去拿别的照片,说我的照片不合格,我又回去拿照片了。回来以后说不行了,我们剩十分钟,我们电脑系统要关了,你只能下次再来;第五次我终于把这个暂住证给办好了。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断提醒你,这么多麻烦“就因为你不是北京人”。这种边缘的心态,我觉得跟所有在北京的打工的、卖盗版碟的其实是一样的。我认识一些朋友,或者办假证的,或者卖盗版碟的,租的民房,梆梆梆半夜警察敲门,拿暂住证。你会觉得很痛苦。它不断地让你知道你是一个边缘人。因为有不少作为边缘人的朋友,所以对他们的生活很熟,慢慢地就无意识就把他们写进来了。进入得非常顺利,因为很多心态是共通的。这是最初写作的一个原由,后来是有意识地去挖掘,我想把这一块弄得更明白。
“李白、屈原、杜甫,还有张艺谋”
张鸿:你前几年在美国一所大学当过住校作家,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有什么体会?
徐则臣:我觉得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比较低。你要到国外去问一下,知道中国文学的人非常少。比如说,我在克瑞顿大学听到学生谈中国文学,说“我很喜欢中国文学,我知道很多中国作家”。我说,“哪些作家?说来听听”。他说“李白、屈原、杜甫,我还知道张艺谋”。我说“张艺谋是个导演”。你会觉得他们对中国文学、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很隔膜的。比如说《红楼梦》,我们中国人,但凡是搞一点文学或者和文学沾点边,都要把《红楼梦》挂在嘴上,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但对他们来说,理解《红楼梦》非常非常之困难,有一个学生说他根本搞不懂。林黛玉喜欢贾宝玉,你喜欢就喜欢,按照美国人的风格,要么冲上去说我爱你,实在不行我害羞,我可以写个纸条、写一封信、写封情书告诉你说我喜欢你。他就搞不懂林黛玉既然喜欢贾宝玉,为什么这么哭哭啼啼的,整天搞得很忧郁,最后把自己给弄死了。他不清楚,怎么会是这样一种表达爱情的方式。《红楼梦》这部小说早就翻译出去了,但是受众特别少,很多人看不懂。
张鸿:书名都被改了。
徐则臣:对。对中国人微妙的情感表达方式,他们搞不懂。他们都是直肠子,不擅长拐弯。比方说美国人不会脑筋急转弯。他们干什么事,就是由因到果,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逻辑,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我就这样来。他就搞不懂法律和人之间或者人操纵法律或人篡改法律,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有的时候很不可思议。比如老师跟孩子说,今天你要干什么什么,那小孩就干什么什么,很听话。很少有那种总要讨价还价,耍耍赖,看看有没有中间路线,非常之少。那次到爱荷华,顺便去了克瑞顿大学玩,他们请我看一场话剧,把契诃夫的几个短篇小说如《小公务员之死》等放在一块排的一个话剧。正演着,因为舞台上有喷雾,烟大了一点,整个剧院的报警突然就响了。警报为什么响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中国,看电影和看戏,你会知道这是因为烟雾放多了才有的警报,把烟雾停下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不行,警报一响起来,警察立马出现,要求紧急疏散。大家都往外面跑,一边跑一边说没必要,一起嘻嘻哈哈往外面走。明知道没大问题,他们还是疏散了。五分钟以后,消防队员,工作人员,冲进来都检查一遍,又等烟散了,跟大家说可以进去了,戏接着演。这种事在中国很难出现。我当时就跟我那个朋友说,如果是中国人,做得最好的可能就是你们走你们的,我坐在这儿。我等烟消了,反正也没有什么危险,也不会发生火灾。如果有人驱赶你,你说我不怕死,我就待在这儿,不关你们的事。你能怎么着。但是他们不一样,所有人都出去,里面空空荡荡的。所以我开玩笑,说美国人都是直肠子,不会脑筋急转弯。
张鸿:你还参加过一个很有影响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据说很多作家都到那里去过,可以介绍一下吗?
徐则臣:这个国际写作计划,是爱荷华大学搞的,可能是目前国际上最著名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国际写作中心。这个大学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就有一个作家写作坊。他们的普利策奖和别的重大文学奖项的得主,有一大半是从这个学校的作家坊出来的。要么是在那边教过书,要不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像菲利普·罗斯,美国最有名的世界级的一个大师,在里面教过书。有一段时间特别热的一个女作家奥康纳、2006年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帕慕克也在里面待过。著名的华人作家白先勇、聂华苓,都在这个大学里念过书。现在在美国用英语写作的一个比较著名的年轻作家李翊云也在这个大学里待过。《纽约客》杂志搞了一个40岁以下的最优秀作家的遴选,20个人,李翊云是其中之一。我在爱荷华的一个朗诵会见到过她。她刚拿了一个基金,50万美金,三年里可以啥事不用干,专心写作。
这个作家坊出了特别多的人。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写作中心也去过很多著名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李锐、毕飞宇、迟子建、王安忆、刘恒、西川,等等。那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很小的一个城市,大概就6万多人,大部分是学生,爱荷华大学的学生有3万多人,如果放假学生一走,这个城市基本上就是空的。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64620
1林志玲求墨宝 陈凯歌挥毫写“一枝红杏 -
42654
2曝柴静关系已调离央视新闻中心 旧同事 -
37237
3人体艺术:从被禁止到被围观 -
28599
4老战友谈王朔:在新兵连曾以“神侃”天 -
21714
5李泽厚5月将在华东师范开设“桑德尔式 -
19652
6作家李翊云推新作 曾称莫言某作品“像 -
15979
7独特而温暖的画作 -
8591
8刘益谦举证功甫帖为真 称上博专家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