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和互相之间的联系很强。形成的新家庭总是建立在原来家庭的附近。这样,子女的家庭就会聚集在父母的家庭周围。
有的村子只是由一家人组成的,包括这家人的三四代。例如:史密斯村,约翰村。如果翻译得更准确一些,张家村,王家庄,路口的李家村。这类名字的小村庄,乡镇,城市遍布全国。他们占据了一大部分国家地名。每个家庭的财产,尤其是房产是共同创造,共同所有的。分家只发生在男性家长去世之后。所有家庭成员,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劳作。如果是农民,他们清晨一起出发,在田间劳作一日。女人也同男人一样干活。我曾经见到一个推着犁的中国农民。他的犁由三个上了马具的劳力牵引着,它们是一头牛,一只驴,和他的妻子。
富有的阶层,人们有些不敬的称他们为“环球快马”(the globe trotters)。他们四处游览,形成一般中国人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中国人与家庭的联系很强,从不为享乐而出游。他们离家只是因为要处理公事或者私事。离家之后,无论是在异国,还是在他乡,他总认为这是一种流放,多少都会思乡。无论他的家乡多么落后,他把回乡看成人生的主要乐事。
中国人的天性如果不彻底改变,他们不是,也成不了殖民者。虽然在南美和北美,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在缅甸,暹罗,在东印度群岛,爪哇和日本都有中国人的身影,但是哪一个都不是他们的定居地。他们不是殖民者,只是暂时的移民。他们很像候鸟,在一个地方生活几个月,然后在记忆中远方的某个地方建巢,养育后代,长此以往,没有改变。他们因为急事,被迫离家,流落他乡。但是在他们出发前就已经做好了周密的返乡计划。这些计划和希望他们始终铭记在心。如果认真调查一下那些坐在来往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目的的国家航道上的轮船里的统舱里的乘客,如果这个调查可以持续几年,就会明了离开中国的人又都回来了。就像刚才说的,他们如候鸟一般来来往往。那些客死他乡的人几乎都做出了同样地安排。他们要人把遗体运回故乡,埋在他们祖先的身旁。如果美国人把在过去20年中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总数,与葬在美国的中国人总数对比一下,他们会感到惊讶的。那些葬在美国的尸骨,毫无疑问,是属于流浪者和无家可归的可怜人的。
中国人是敏锐小心的商人,是耐心、忠诚、勤劳的劳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家的民族。虽然他闯荡四海,历经磨难,但是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返回故土,颐养天年,落叶归根。
他不仅在被迫流落异国时有这样的愿望,在他乡建功立业后也有同样的想法。他的这种特点不仅是源于对国家的爱,更是源于对故乡的眷恋。例如,一个广东人不会定居在北京。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因公来到这里。他们始终都是“朝圣者和外人”。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他们的出生地定居。如果其中的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人死在了北京,没有丝毫钱财,那么乐善好施的好心人就会将他的尸骨运回家乡安葬。中国的各大城市都有协会和慈善机构。这些机构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把不幸客死他乡的人送回家安葬。旧金山的所谓的六个中国同乡会(人们对他们有许多的不实评论)就承担着这个主要任务。去中国的旅行者偶尔会碰到这样的棺材,它吊在两根长棍之间,棍的两端固定在两头驴的背上。在棺材的前面有一个柳条筐,筐里装着一只雪白的大公鸡。棺材里装着死在他乡的人,就这样被抬着,也许要穿过这个中国,到达他安息的地方。这只公鸡必须是雪白的,无一点杂毛。它在长途跋涉之中要引领死者的灵魂,或者说服他跟随着他的肉体。这只大公鸡越活跃的在笼子里昂首阔步地走,打鸣的声音越响,就说明它能更加成功的完成它的使命。
这种浓烈的乡情经过千秋万代,逐渐发展,日益加强,变成一种宗教,一种无论生死的最后回归。它是每个中国人心中的神圣的需要。如果我们参考“祖先崇拜”,就会对中国的这种现象增进一些了解。
我们必须谴责偶像崇拜。我必须承认,每次看到中国人的棺椁从海路或从陆路,经过长途跋涉,重返故乡,圣经旧约中的美丽的历史故事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这个故事中,亚伯拉罕在希伯莱给他的妻子萨拉买了一块田和一个洞穴作为墓地。亚伯拉罕,以撒,瑞贝卡死后也都葬在那里。雅戈死后,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把他们父亲的遗体从埃及抬回了加南,并葬在利亚旁边。约瑟夫要求他的孩子们承诺在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葬在同一个坟墓里。这个承诺在他去世后两个世纪完成。人们一定会崇敬中国人的这种感情。人类的先民就拥有这种感情。中国人在几千年中把它,世代传承,付诸实践。
中国政府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利用人们的这一特点。对于那些想要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他要在中华帝国版图内拥有一块墓地。
一小块墓地的所有权被看成他有意成为永久定居者的上佳证明。
周末文化看点:
|
编辑:
彭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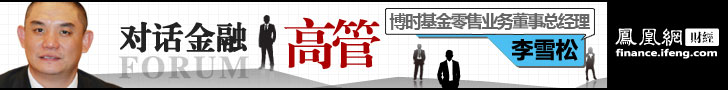




















 南海新贵:三亚海军基地
南海新贵:三亚海军基地 俄印边境军演矛头指中巴
俄印边境军演矛头指中巴 邓小平叮嘱朱镕基搞好上海
邓小平叮嘱朱镕基搞好上海 周恩来为何喜欢毛岸英
周恩来为何喜欢毛岸英 女子站街招嫖 警方蹲点实拍
女子站街招嫖 警方蹲点实拍 巩俐胸贴刘德华倾情热吻
巩俐胸贴刘德华倾情热吻 花花公子推裸女瑜珈惹众怒
花花公子推裸女瑜珈惹众怒 选美皇后涉性交易细节曝光
选美皇后涉性交易细节曝光 解放军攻克微波雷达技术
解放军攻克微波雷达技术 北海舰队驱逐舰大队备战
北海舰队驱逐舰大队备战 中国有多少汉奸为日军服务
中国有多少汉奸为日军服务 日本曾想在投降书上做手脚
日本曾想在投降书上做手脚 中国“飞豹”对抗美军F22
中国“飞豹”对抗美军F22 解放军12个导弹旅瞄准印度
解放军12个导弹旅瞄准印度 揭秘印度瑜伽念力飞行术
揭秘印度瑜伽念力飞行术 扼颈魔频作案 单身女遭殃
扼颈魔频作案 单身女遭殃 文涛:小时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时见过女老师裸体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