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诺斯:我如何理解暴力、社会秩序与中国问题
2015年11月26日 11:32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杨松林
对于暴力的现代性反思,最初来自20世纪中期,在后殖民主义逐渐兴起时,诸如萨特、福柯等法国思想家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诺斯和阿马蒂亚森?

道格拉斯·诺斯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11月23日逝世,享年95岁。
诺斯是一位在政治、社会和其他与经济增长相关方面研究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因其创造性建立了新制度经济学派而闻名。其在晚年对中国问题、社会制度与暴力等议题尤其关注,尤其是其和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合著的名作:《暴力与社会秩序》,更是将暴力、现代性、国家政权、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几大重要议题结合思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制度经济史”理论框架。
诺斯晚年对于暴力问题的关注,在于其欲建立完善理论体系的需求和对长时段历史的敏感度。如其所言“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至于暴力如何形塑制度?制度又是如何保证经济发展?在这本书里,依托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这三大理论基石,诺斯深入探讨了上面两个问题。这充分显示了暴力与现代性问题,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对于暴力的现代性反思,最初来自20世纪中期,在后殖民主义逐渐兴起时,诸如萨特、福柯等法国思想家与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诺斯和阿马蒂亚森的暴力反思?
另外,诺斯的《暴力与社会秩序》,因其基于英美的范本分析,而是否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存有某些力不从心之处?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建设与暴力问题?这份书单或许能给大家一个好的思考。
一、《暴力与社会秩序》:制度性的暴力解读,僵硬化框架的典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尤其关注制度在建构社会形态、型塑人类各种行为上的基础性作用。其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提出,并结合了产权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及国家理论,最终形成了“制度变迁理论”。
这本《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集上述三点所成,以一个非常宏观的复杂线性框架:“觅食秩序(foraging order)-权利限制秩序或自然国家(the limited access order or natural state)-权利开放秩序(open access order)”集中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如何通过制度体现与塑造。而这个群体组织方式变迁框架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暴力行为的规避。如诺思所言:“所有社会都必须设法抑制或制止暴力,但不同社会采取的方法是不同的。比如最普遍的自然国家对暴力的控制,是通过赋予那些有暴力潜能的个人或组织以一定形式的特权或政策红利,从而了建立在政治对经济的操纵基础上。”
换句话说,现在绝大部分国家所处的所谓“自然国家”,其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规避暴力。这种暴力并不直接保障精英和高阶级分子的特权,而是“稳定或部分稳定整个社会或政体中那些强有力的和潜在的暴力集团间的关系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就诺斯思看来在当前的自然国家阶段,尤其是中国社会,普特南强调的“社会资本”的争夺并不集中在社会个体中,而更多来自于国家的政治控制和与精英的博弈调和。
但这种暴力的调和是极其不稳定的。在权力限制秩序中,一旦支配联盟更迭(政府换届)、对精英间的租金洗牌出现混乱(统治阶级的利益分配不公)、或者租金压榨过大导致底层人民的生活难以为续(人们连基本生命要求都无法达到),就会循环式产生暴力。
笔者以为,诺思在这本书中的最大贡献,在于其解释了目前一系列接近哈耶克式新自由主义经济解决方案,比如产权调控、货币政策、投票权与言论自由,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依然缺乏从权利限制秩序到权利开放秩序的门阶条件,包括对精英的法治、公共或私人领域内的永久性组织存在、对军队的统一控制等;而那些哈耶克式方案,更多建立在门阶条件已形成的成熟自然国家或权利开放秩序中,而在门阶条件未成熟时,运用在中国社会里,就会造成一种“政策错位”。为此,他提出只有打破旧有既得利益团体,增强社会资本的流动性,创造真正全民参与的制度建设,才能摆脱现在引发的种种可循环社会暴力,达到转型的门阶条件。
这自然一个很敏锐的发现。笔者以为,作为一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能从建构话语中发现其存在基础上的线性的进步逻辑,并从中初步挖掘到由此带来的暴力性后果;他甚至意识到了这种单一框架下,诸如民主自由与市场化调控,等非结构性的抵抗暴力手段,最终很有可能只是另一种暴力的循环,这一点非常难得。
令人惋惜的是,他看到的只是这种线性逻辑的结果,却未能更加深入反思这种话语为何能从多元性变成单一性;也因此,他看到的暴力,只是某种直接可见的战争暴力和物理暴力,而对于更加深入的结构性暴力,他只能选择视而不见。更严重的问题是,多元性在现代性话语中被消解的过程存在不同地区的程度差异。诺思分析框架更多基于欧美文本,对于在发展中地区诸如文化、价值观等更为软性的因素无法被考量,其给出的制度性方案,也因过度僵化而也无法真正解决现代性的暴力问题。
因此到了最后,当诺思企图通过精英的“非人际关系化”(比如官二代依然有红利,但红利尽量减少其中的“吃老本”成分)来达到所谓的门阶条件时,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借助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性实现自己的国家威权愿景。Svolik在其书《The Polit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已经明确暗示了“一些威权国家的官方政党制度,很有可能通过利用社会流动性,提拔聪明能干、有政治野心的年轻人纳入体制内,避免革命的威胁”。由此,中国政府依托诺思给出的解决方案,将很有可能依旧停留在现代性的循环论证中。这恐怕是诺思始料未及的。
二、身份性的暴力解读,但还是经济人假设
今天推荐的第二本关于暴力的现代性解读书籍,同样来自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印度经济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教授,在公共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无与伦比。他在公共选择理论中创造性提出了价值限制、个人选择等概念,不仅将社会选择的元素扩大到私人领域,并提出“没有一个集体决议机制能与尊重个人并存”的矛盾,还首次将个人间满足程度比较进行所谓的量化解析,最后成功解决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中制度下人满意程度不可比的问题,这在福利经济学中是创造性的。(注: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定理)是指,如果众多的社会成员具有不同的偏好,而社会又有多种备选方案,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令所有的人都满意的结果。定理是由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J·阿罗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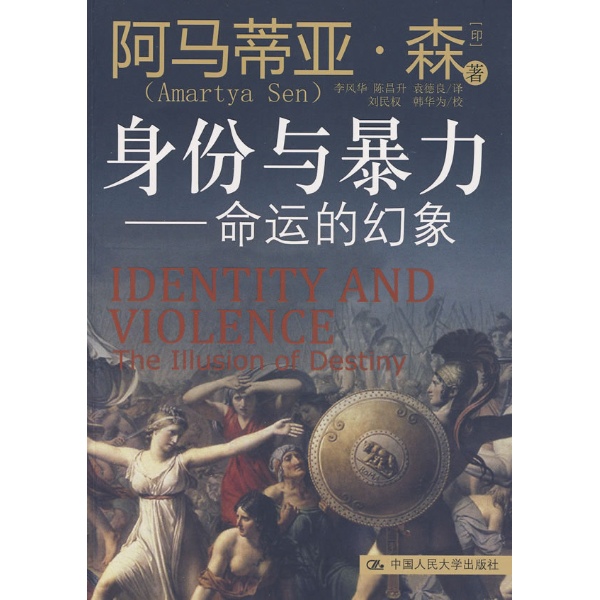
对阿马蒂亚·森关于个体、私有权利的聚焦有助于解释其随后在政治、文化、社会等重大议题上的思考模式。尤其是这本《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他的探讨已经延伸到了纯粹人文学科或文化人类学中的,和身份、话语、主体性、仪式等抽象式概念相关的讨论。这显然受到了存在主义学者的影响。比如他文章多次引用了萨特,就是一个明证。
这本书中,森多次强调了人身份的多元性。这可以从写这本书的动机谈起:森曾经担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他是印度人。当他有一次回到英国希罗思机场的时候,移民局的官员询问了他与三一学院院长的关系,是不是关系很好。森教授认为自己通常善待自己,所以答曰还不错。但中间的片刻疑虑加深了移民局官员的怀疑。尽管事情最后解决了,但关于“身份认同”的疑问就此展开。
这个故事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人身份的多元性本质和他人解读时的有选择性与单一化。为什么人的身份认同会出现某种单一化倾向?森指出,对一个人的身份认同,“是因为这个人与某类群体之间共享了某种价值”。 这有可能是他共享了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也有可能是这个人与其他人对分类者的价值来说是等同的。所以说,森的敏锐,就在于他能明确发现“多元到单一”的现代性危机,并认识到了这种社会价值、身份认同和标签的单一化带来的暴力后果。这相对于诺思而言,更进一步,不仅看到了结果,也看到了过程,甚至看到暴力话语的多样性,以及产生其暴力的结构性因素,这相当难得。(比如他指出的而“中国-西方”式的话语论述模式,不利于增进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这和后殖民学者的提法几乎一模一样)。
人身份的本质是多元的,由此产生的暴力也应该是多元的。认识到这点,我们才能真正逃脱所谓的单一逻辑,从更加广阔的脉络认识和消解多元性暴力。在跳出单一化逻辑框架的意识上,森的见解显然是卓越的。然而,他的建议却值得怀疑。在《理性与自由》中,他就对理性对于多元化的宽容作用大加赞赏;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暴力的解决方案:“理性的审视自己则要求我们注意到人性之丰富,身份之多重,文化之多元,寻找交叉重叠的共识,努力推进相互的理解和尊重。”
这种提法的最大问题在于,他的方案依然毫无保留地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中。他过度强调了理性的力量,因而最终形成的反抗式解决方案,还是会沦为单一逻辑框架下的循环论证。比如,他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宽容多元,推进沟通,来免除战争和冲突,从而到达正义之境”,可现在的问题是,当依托理性实现这种多元的结果时,很有可能的,多元也会变成某种标签。比如当我们去指责后殖民学者的话语霸权时,就在于认为“多元”经过了理性推演,成为了一种霸权式研究范式,统治了思想套路;这里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森期盼依托多元实现社会正义,其多元很可能沦为社会性相对主义。多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单一逻辑与话语暴力,这是后殖民学者,包括森本人都始料未及的。
三、《本雅明文选:暴力批判》:以抒情取代理性
既然任何单一依靠理性的方式都无法消解这种多元化的暴力,那么对理性的全面否定,或者依托感性的力量是否就能实现?比如,写出《单向街》的本雅明,又比如强调“诗意栖息”的海德格尔,他们能做到这点嘛?

这第三本书,把对这一问题探讨的宗师级人物瓦尔特·本雅明的论文《暴力批判》推荐给大家。其实若论叙事的可读性,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也许更有意思,而若论表述方式的严谨性,福柯的《词与物》不得不说;但我仍任性地把本雅明拿出来,是因为其思想的本源性,基础性,都不是有当代外延式诠释的齐泽克与福柯可以比拟的。
在文章的开头,本雅明便指出了暴力的多元性含义:在现代性话语未出现时,“神性暴力与神话的暴力(全面的暴力和单一逻辑框架下的暴力)是多元而融合的”。与诺思和森同样,本雅明指出了这种多元性在现代性话语出现后被迅速抛弃,这体现在“神性暴力与神话性暴力的被分离”。启蒙的法学家们,通过建立一套属于神话性暴力(其实就是理性话语下)的法律系统,并对其进行规训和约束。而正由此,暴力出现了“从多元到单一”的转变,在现代的法律框架下变得难以消解。
这种难以消解主要体现在自然法和历史法的循环论证中,“正义的目的只能通过正当(justified)手段来实现,而正当的手段只能用于正义的目的。自然法试图,通过目的的正义性,来“正当化(justify)”手段(使手段“正当化”),实证法则试图通过证明手段正当,来“保证”目的的正义性。”目的和手段的循环论证,这便是单一逻辑框架的吊诡之处。和诺思、森一样,本雅明也发现了这点,并且其描述显然更为深刻。
为此,本雅明认为若要跳出这种逻辑,就需要回归到那种原始的,神性暴力与神话的暴力结合阶段,依托“神性暴力”完成对原有单一逻辑框架的暴力冲破。这种冲破的力量,因属于纯粹抒情,无法使用理性框架束缚而变得无穷无尽。通过使用这种抒情性暴力,本雅明认为旧有的理性框架将会被彻底摧毁,从而回归到真正的“弥赛亚”。
本雅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过分强调夸大了情感的暴力作用。不得不承认,情感是具有强大的解构和冲击作用;但这种暴力作用在表现形式上,不能通过,也不需要通过直接与劝说的方式实现。简单的说,当一个人尝试用感性说服他人时,他本人已经陷入到了理性的魔咒里不能自拔,因为劝说(persuade)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理性行为。也因此,本雅明是注定的:因为他永远不认清,或者不敢认清自己的真实定位,而陷入在某种知识分子的“情怀”幻想中不能自拔;就像他们不能认清抒情本身的局限性作用,以感性冲破理性框架,过犹不及。
四、《诗性正义》:当代消除暴力的感性尝试:各司其职还是沦为鸡汤?
现代性建设从来都不是一个解构性的过程,用一种思考方式推翻或者统治另一种的努力都只是无意义的尝试。只有真正认识到暴力的积极性建构性作用,而不仅仅是某种通过摧毁来实现的负面性建构,我们才能真有可能将超越暴力的单一话语逻辑,回到真正的“暴力”。美国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或许就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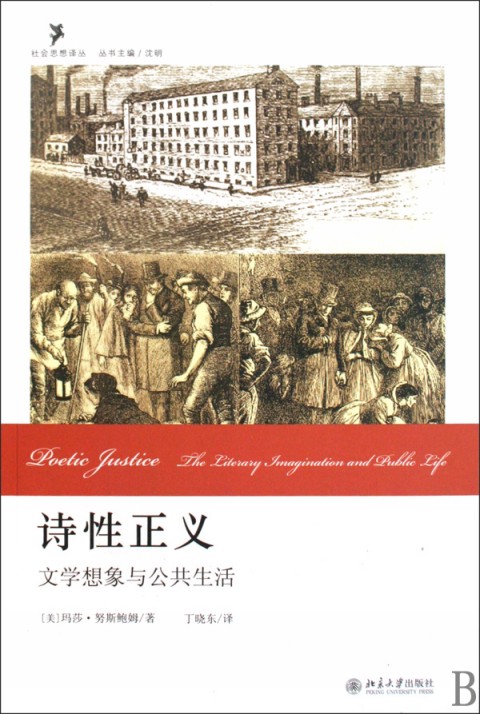
和本雅明观点一致,努斯鲍姆也承认现代性的危机是抒情传统的丢失。也因此,她提出要“重拾诗歌在当代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但与本雅明有本质区别的是,本雅明强调取代和暴力,所以他需要一个本体和形而上的抒情来表达;而努斯鲍姆更注重各司其职,感性和理性都在自己的定位中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在这里,她和哈贝马斯共享了一点:二者都没有完全否定掉现代性的建构性价值,也承认“现代性”是一项仍在进行中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中,开始思考“抒情和启蒙如何构建现代性多个层面”的问题,以及论证这些层面需要重新被还原的原因。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还原既不是完全依托森讲述的那种“纯粹依靠理性尊重多元”,也不是本雅明式“以抒情抵抗、冲破乃至取代理性”,而是两者学会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沟通。这比阿马蒂亚森与本雅明都要进一步,因为这种沟通不存在理性或感性的二元假设。
虽然观点和逻辑对路,但努斯鲍姆也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当今理性的单一逻辑框架带来的暴力力量显然是统治性的,这也能解释本雅明式的感性抵抗需要更为强烈表达,即使其注定失败,毕竟“反对力度不大,统治者视而不见”;而努斯鲍姆更为温柔的交流,是否能“以柔克刚”,避开理性的侵扰,不会被陷入理性的论述框架里,最终成为理性下的清怀式牺牲品:心灵鸡汤?
我们拭目以待。
延伸阅读:抒情的中国语境,及其现代性暴力建构作用
陈国球《抒情之现代性》
林郁沁《施剑翘复仇案》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
方东美《生命情调与美感》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