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访]“迟到者”陈传兴:在黑暗中与怪兽搏斗
2015年11月06日 09:12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胡涛
在陈传兴所说的“摄影成熟年代”的今天,他带着四十年前的影像到来,作为迟到者讲述岁月的故事。观众像吸血鬼,被邀请来黑夜赴宴。
导语:站在40年前拍摄的影像前,陈传兴说“我不懂它们是些什么”。
彼时,少年陈传兴漫山疯跑,用手中的镜头记录下台湾土地的种种事物:残破的田园,废墟,悼亡,子弟戏,戏班,淡水,花莲轮,台北车站,兰屿……透过影像,他学习去认识台湾土地的细部。
仅有的一次展出后,这些底片便被搁置暗室,雪藏于黑暗之中,直到40年之后,以“未有烛而后至”之名重见天日。陈传兴好奇于它们与时间的搏斗痕迹。他说,自己既是那名执烛的少年,也是一位迟到的客人,“我用一种迟到的方式来等待。因为历史在前进,我只能看到历史已经完成了的。或者历史已经被终结掉,变成一种废墟的状态。
黑暗对陈传兴有一种莫名的致命吸引力。他喜欢在黑暗的角落里观察展厅里的人们,一位观众轻微的触碰动作,引起了他无限的惊奇,仿佛看到了作品转世的光芒。执烛人具有通灵的本领,“吸血鬼只有在黑夜里面才能存在,然后你们是在黑夜里面被邀请来参加的盛宴,然后你们被吸进去,然后你们生命的某一天某一刻某一个片段,来交换这个观看。”
陈传兴的生命也曾像吸血鬼一样疯狂。1976年,陈传兴告别台湾远赴法国求学。那一年,彼岸大陆正值疯狂年代的末期,四人帮倒台,领导人逝世。而陈传兴尚不知晓他即将在异国见证另一场疯狂。
七十年代末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正沉浸在所谓“68年思潮”的思想遗产中。历经彷徨的陈传兴,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找到了影响自己一生的老师,电影符号学宗师克里斯蒂安·麦茨。八十年代到来,随着巴特、福柯等大师辞世而远去的是思想的黄金时代。思想的断层引爆了学界新一轮狂潮,受不住前辈重压的人们自杀的自杀,疯狂的疯狂。“黑夜降临,八十年代没有大师”,陈传兴这样说。
陈传兴庆幸赶上了黄金年代的尾巴,异国的求学经历让他脱胎换骨,他形容“坐在船上看到自己的尸体飘过”。在往后的作品中,不论是《他们在岛屿写作》还是《银盐热》,法国左翼思想的痕迹都可见一斑。
陈传兴说自己是一个“高度复杂性的动物”。他长期耕耘美学、哲学、精神分析与影像论述等领域,同时是作家、摄影家、艺术评论学者与电影创作者。
“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跨好多领域,穿越在非常多的这种境遇、场域,游走这样子。在某些程度有点像一个很撒野的小孩子,一直在玩,玩到现在还没有放手。也可能这一点导致我现在60来岁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但至少靠着游走在不同境遇的快乐支持我,挣扎也可以搏斗也可以。不管你搞创作,搞思想工作,搞写作,搞理论等等,都要面对一些怪兽,要去跟他搏斗,你才至少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大师隐去的年代,数码时代也悄然降临。陈传兴信奉“抵抗无意义”,“为什么不去寻找两种界面,两种技术,两种时代对话的可能?”在陈传兴所说的“摄影的成熟年代”的今天,他带着四十年前的影像到来,作为迟到后至者,静静讲着时间的故事。而观众像吸血鬼,被他邀请来黑夜赴宴。
如同评论家顾铮所说,陈传兴是在酿酒,而时间本身,成为了酿酒所需的酒曲。“这是能够战胜时间的照片,而不是可能会被时间打败的照片。”

陈传兴
以下为对话实录:
我在不同境遇游走像撒野的孩子
凤凰网文化:我不知道如何定义您。像您这样从摄影到摄像,到摄影理论,到符号学,到哲学,到艺术评论家、作家、电影创作,把学术跟这个实践都结合在一起,就共存在一身,这个是很少见的。你自己更钟情于自己哪一个角色,还是说我根本就不在意身份界定?
陈传兴: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性的动物。所以我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可以跨好多领域,穿越在非常多的这种境遇、场域,游走这样子。在某些程度有点像一个很撒野的小孩子,一直在玩,玩到现在还没有放手。可能是这点我跟其他人不一样,也可能这一点导致我现在60来岁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但至少靠着游走在不同境遇的快乐支持我,挣扎也可以搏斗也可以,在不同领域里。因为不管你搞创作,搞思想工作,搞写作,搞理论等等,都要面对一些怪兽,要去跟他搏斗,你才至少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20岁曾经是离经叛道的台湾文青
凤凰网文化:顾铮老师说您的作品是很沉稳,我就特别想知道,您是一个特别早慧的人,您20岁之前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
陈传兴:其实我20来岁,我就是跟一般的台湾小孩子一样,就念书、考试。但是因为又不太适应那个环境,所以我初中考高中重考,高中考大学也是重考一次,所以当我进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比同年龄人来讲成熟多了。我初中跟高中都是念夜校,都是晚上上课的,所以基本上是比较差的学校,所以白天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让我去玩耍。可能就是因为整个成长的过程跟走正常轨道的小孩不一样,让我跟同班同学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经常在街上晃,大学基本上我上课,大部分时间要么在图书馆,要么在外头拍照。跟我们那个时代的刺青、文青蛮像的,会听摇滚音乐,读文学作品,哲学翻译等等。那个年代我们这一类的这种比较怪异的青年都是留长头发。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又留长头发,穿凉鞋,穿很贵的,背着相机。那时候在那个年代是警察可以剪头发的,街上看到你,你就是不良少年,就可以把你抓到警察局剪头发,所以我们那个年代是留长头发的,看到警察的就要跑,是一个蛮有趣的年代。
凤凰网文化:大陆会尽量把一个学生定义成好生跟差生,有的考试成绩很好,有的很差,你们那边也会这样吗?
陈传兴:我们那边当然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念的大学出来不是说太坏,但并不是顶级。我念的是天主教的,就是辅仁大学。可是也因为念了天主教学校,领略了磅礴的耶稣神父的知识,所以在大学阶段已经透过一种比较曲折的方式,跟外国文化建立了接触的可能性。

陈传兴摄影作品
在法国经历了后六八时代我像坐着船看到我的尸体飘过
凤凰网文化:您离开台湾的时候是在1976年?
陈传兴:1976年9月离开台湾,差不多9月底到达巴黎。刚好是四人帮倒台,毛主席周恩来逝世,台湾这边是蒋介石刚过世一年多。
凤凰网文化:那个时候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去法国留学的人多吗?
陈传兴:少之又少。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如果他家庭的环境允许,大部分第一个选择是的去美国留学,90%都到美国。去的学生里面又会有90%的人会选择留在美国,就变成美国人了。所以当初去欧洲到法国的不到十个人,到德国的也差不多这样。到最后拿到学位的不超出四三个人。欧洲的,法国的很多留学生大部分在第三第四年已经准备要放弃了。放弃并不是说想回台湾,是比如说去念书成为学者。因为法国、德国的教育方式是跟美国不一样的,它并没有要求固定修几个学分,写一篇论文就拿到学位。这对培养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挺重要的,所以巴黎那么多学者,思想家在那里开课。在教室里或者在不是正式的学校里面教,可以听的学者不可胜数,可以买的书多到你简直都要疯狂了。
所以我一直讲说老天特别眷顾我,我去的时候是法国思想的后六八,1968之后的黄昏时期,很快就是黑夜降临了。所以当时死的死,疯狂的疯狂。我刚好碰上那个。
凤凰网文化:您刚到法国的时候,是不是经历了文化震撼?
陈传兴:我当然多少都有。而且刚去的时候法文还不好,所以我们大部分去的时候都要在语言学校念法文,但是语言学校的那种经验不太好,从像ABC那样程度教。对我们这种已经念完大学的人来讲,总觉得这根本是一种浪费时间。所以我到语言学校大概两个礼拜就开遛了,我宁可每天看报纸,读法国的报纸、小说,听收音机。
在这种情形下,念艺术学校好像在知识层面,思想层面不够,所以我就转到正常大学去。用了很大决心,也蛮挣扎的,当然更不用说最后念硕士,念博士,已经重新念语言学,甚至还要去念希腊文等等。就是硬要把听不懂的听懂,搞不懂的搞懂。所以那十年里哪都不敢去,除了英国、德国。
凤凰网文化:70年代台湾跟法国关系如何呢?
陈传兴:基本没有外交关系。所以法国人会觉得台湾是泰国,挺歧视的,拿签证还不太容易,学生居留也不容易。台湾那时候相对法国人来讲比较落后,所以选择法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法国念书不要钱,只要注册拿学生证,只有大概几百块人民币的注册费。你要听什么课都是你的事,学生有各种优待,有学生食堂,你可以买学生食堂的饭票。你在美国一年的念书的钱可以在法国活四年,我当然选择去法国。
但更吸引我的可能是因为法国的左翼思想,西方思想大源头。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对法国思想界,比如结构主义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出去大部分人都知道沙特,存在主义,卡梅伦,有新浪潮电影,有高达(大陆译为:戈达尔),这几点就够吸引人一头撞上去。
凤凰网文化:能不能分享一下您上大师课的经历?
陈传兴:他们会开两种课。一种就大课,开放的课,就是一般外面人也可以来听,那种课基本上都是一个像那种剧场一样的,就是五六百个人挤在那里爆堂。常常要提前两个小时抢位子,不然到时候根本进不了,或者挂在窗上。像我听德勒兹的课,外面在下大雪,我提早一个小时还只能挂在窗上。听到在讲贝克特的电影,虽然外面下雪的,但还很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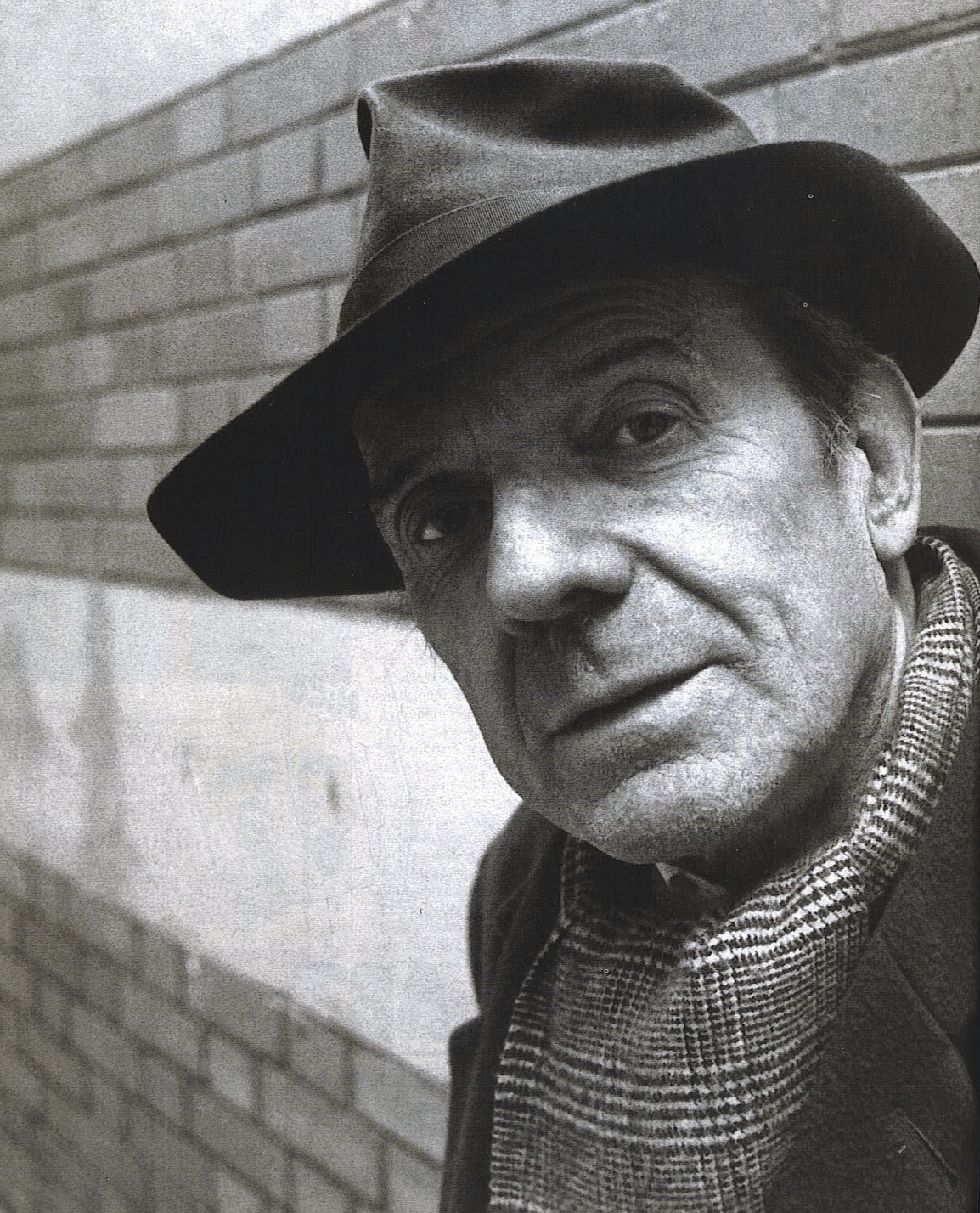
德勒兹
我在陈丹青那里也讲过,完全戏剧的状态。可是那种封闭的课只跟他指导学生讲,一般外人就是不会去的,他也不给外人听。可是那个时候你跟他的互动是很直接的,比如说我听过克里斯蒂安·麦茨,像机场庞大的三四百人的讲堂,那种氛围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也是我博士论文导师。他可以一篇文章几乎讲两个月,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地讲。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电影符号学的开山祖师爷,开创新的一代。他写完那一本精神分析跟电影之后,几乎不发表文章了。因为觉得他要找出一条新的电影理论的可能性,所以他回头去整理刚诞生时候的电影理论。他有一种对于学问的谨慎,认真深入,不会骄傲,真的很感触。他随时都可以发表,他也可以写十几本书,但他不需要,那样的态度就让人很钦佩。
所以倒影响我博士论文就像他一样就做小题目,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个小题目,那时候你会觉得心里很落实,很踏实。
凤凰网文化:这一系列的学习经历,让你拥有了自己的大师标准?
陈传兴:包括现在在国内琅琅上口的拉康,他一辈子事实上也只有那一两本书,还是他上课的讲义,学生帮他出的。当然也有些像德里达五六十本,六、七十本,所以在那里你就看到各种各类的这样,也有像克里斯蒂娃,他可以搞理论,搞论述,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他也写小说,而且小说写的好的很,还获奖。所以整个经历让我脱胎换骨,有点像西游记里面的,我坐了船过去看到我的尸体这样飘过去,真的有那一种感觉。所以回到台湾我也自我期许,不敢乱写,不敢乱发表文章。所以我教书教了二十来年,累积很多上课的讲义、笔记,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微小。
凤凰网文化:法国的求学经历,在您身上最大的烙印是什么?
陈传兴:最大烙印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国家会把思想家,作家,当作最崇高的,所以它不会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而台湾岛刚刚相反。法国会以他们思想的先进,文学艺术上面的杰出,而感到骄傲。
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寻回思想家的能动性
凤凰网文化:到了80年代之后,像萨特,福柯,巴特等都凋亡。目睹了一个盛衰的过程,甚至很多的延续,您对这个时间和对死亡的思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陈传兴:当大师一个一个走了之后,他们其实也已经开始在哀叹,思想的黄金时代要结束了,他们一直在等待。包括大师最亲近的第一代,第二代的门生弟子,他们都感受到来自他们老师的重压,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所以甚至有一些学生选择自杀,疯狂。那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时代,那种死亡的感染力非常强。
凤凰网文化: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会不会跟时代有关系,比如说在二战之后跟六八之后?
陈传兴:完全不一样。二战之后就产生存在主义,萨特,卡缪,然后是一种改造过的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把它法国化。很快到50年代末期,就结构统一起来了,是一种高唱所谓的知识论至上,先前是存在本体论。李维斯托,巴特就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借用过来。然后强调就是认识论,强调所谓的认识源。可是这个路走不久之后,德里达起来了,虚无的怀疑论又摧毁他们,把结构主义又一一的瓦解掉,就是产生所谓解构主义。当然又有所谓的精神分析,又有马克思主义,简直是百花齐放,你会眼花缭乱。你如果不定下心来,你就很容易会心猿意马,而且你会被整个时代的狂潮卷走。
这些人的思想从哪里来?他们绝对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一定有本有原。我们是不是念完它们之后,把它的思想脉络抓到之后,要上锁?他的思想本源比如来自尼采,来自黑格尔,不只是来自海德格。甚至更早,来自希腊,罗马,伯拉图,亚里斯多德,圣·奥古斯丁等等。我们会一路溯源,比如说我们研究圣·奥古斯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跟伯拉图谈爱情,弗洛伊德谈爱情等等都有关系,跟神的信仰有关系。你就可以铺成一整套新的谱系,非常有趣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整个西方大的文化历史里穿越游走呼吸,那个时候最过瘾。
凤凰网文化: 80年代之后,法国也在思考为什么黄金年代不再的问题,其实很多国家也是在思考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现在也是说没有大师。这个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吗?
陈传兴:我想其实也不一定是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把问题看简单化了。法国50年代的存在本体论,然后就是后来的知识论、认识论至上,后来就改意识形态,谈所谓的精神分析。回到尼采,回到海德格尔,回到马克思、福柯等等,他们就觉得这个不足。所以在70年代末期,逆学回来了,取代结构的,因为结构让他们陷入一种怀疑论的,虚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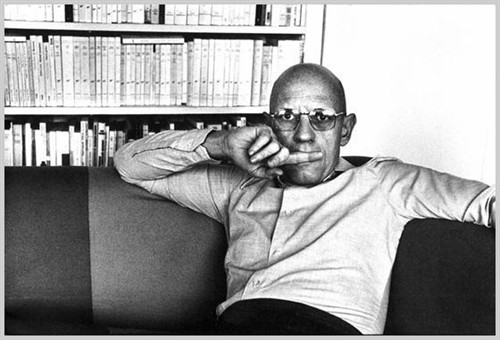
米歇尔·福柯
所以伦理学在80年代又开始起来,当那种李维斯托,犹太哲学又回来了,甚至一些基督教神学也回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思想里面是有一种内在的病症的。矛盾病症的转换,这个矛盾病症里面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所以80年代没有大师,他们确实是这个矛盾病症的所谓的这一种爆发力。好像突然之间断裂了,停顿了,所以当然让他们非常惶恐。
可中国的这种状态,我们知道是由整个外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等等的因素决定的。而不像法国、欧洲的,他们这种内在思想决定的,所以这两者还是很不一样。所以中国它可能要面对的问题是,它如何选择一个思想家的他的自主性跟能动性,也就是黑格尔、马克思他们的。一个思想家如果缺乏一种能动性,你的思想就会被一些东西所牵动,没办法去跳脱,没办法去建构一整套的系统性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