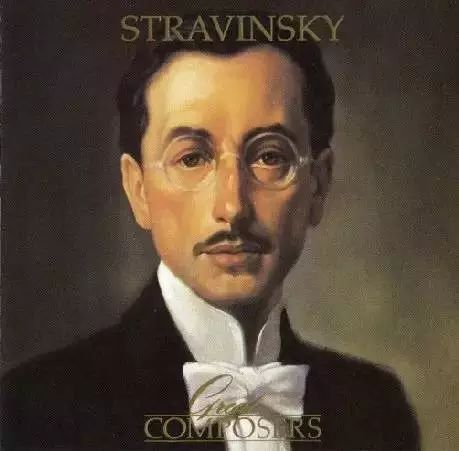他是音乐界中的毕加索,他无法回自己的国家,他每部作品都充满颠覆


独家抢先看
ID:YISHUZHONGWAI
引言
斯特拉文斯基一生风格多变,却又能保持其独特性。他曾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在二十世纪艺术史上,也许只有毕卡索能与之相提并论,而他也确实被人们誉为是“音乐界中的毕加索”。
1920 年 5 月的一天,38 岁的斯特拉文斯基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从意大利回瑞士的火车上。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几部音乐的创作。
这位来自俄国又无法回到家乡的作曲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充满颠覆性。他的曲风有时候神秘婉转如《火鸟》,有时原始古朴如《春之祭》,有时又刺耳荒诞如《彼得鲁什卡》……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
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曲子都出自斯特拉文斯基之手,恐怕很多听者都会把它们的作曲者认为是不同的人。
坐在火车上的斯特拉文斯基,心里也很有数:那些音乐评论家是有多恨自己这个没谱的人。不过他不在乎,因为他想在音乐史上留下的名声,也就是一个“不落俗套的音乐家”这样的评价。
这一次的意大利之行,他又给音乐界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正当所有人都期待着从他这里,再次获取不按套路出牌的乐曲时,他编写的芭蕾舞剧《普尔钦奈拉》曲风一转,变成了向巴赫致敬的优美舞曲。
这就好像是听惯了德国战车死亡摇滚的粉丝,突然有一天发现德国战车改唱《董小姐》了;又像是唐伯虎提枪上马变成了忽必烈。这种强烈的反差又一次让人无所适从。
也许斯特拉文斯基也是厌倦了自己的实验性质的作品,想把心思再转到古典曲风当中吧。这会的他不会料到,自己今后还是无可避免地,被音乐史归为了“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
看着窗外呼啸而过的森林,斯特拉文斯基有点瞌睡。他的思绪开始飘荡在自己已经走过的人生。他不禁想起,人生的反转在这一生中实在是太过稀松平常。
身为圣彼得堡一位广受赞誉的男低音歌唱家之子,斯特拉文斯基可能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会在音乐之路上行走。他的父亲也竭尽所能地,把自己的音乐知识传授给儿子,让他熟悉了剧场里的套路和人声与乐器的精妙组合。
很自然地,斯特拉文斯基想要走上音乐之路,就必须要学上一门乐器。在浪漫主义大潮之中的音乐家,大多喜欢弹钢琴,斯特拉文斯基自然也不例外。
尽管很早就掌握了钢琴的基本技巧,也勤学苦练了很久,斯特拉文斯基似乎在演奏方面没有什么天赋。当时圣彼得堡音乐界的教父级人物,格拉祖诺夫就评价这孩子技术不行。
受到音乐大佬这么低的评价,想要再在音乐之路上走下去难度可就大了。但也得混口饭吃啊,斯特拉文斯基的父母就把眼光投向了更稳定、也受人尊敬的法律行业。
圣彼得堡大学
斯特拉文斯基也许仍然记得,自己提着皮箱来到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大楼前时,惴惴不安的心态。不过他倒不是在紧张,自己是不是能够适应大学的学习,而是更多地在计划着,怎么重新捡起音乐的梦想。
也许正是格拉祖诺夫的负面评价,引发了他立志要做好一个特立独行音乐家的决心。即使是身不在音乐界了,也可以玩个自学成才。正是在这一段频繁翘课的日子里,他遇到了另一位俄国音乐教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1901 年他们相遇的时候,斯特拉文斯基只是一个 20 岁的大学生,而功成名就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已经 58 岁了。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下,即使是社会名人,活个 60 来岁也应当心满意足。
两人倒是一见如故,和历史上所有的忘年交一样,他们的感情真挚地奠基在音乐的创作才华上。斯特拉文斯基这时候才些许找到了一点自信,音乐之路重新打开。他很希望能从这位充满争议性,但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嘴里,得到一些建议。
我建议你学习作曲。不过不要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了,你年纪已经偏大,还是跟在我身边上私人课吧。——里姆斯基·科萨科夫
海德堡
今天的我们好像已经很难想象,一个在校大学生翘课,跟着一位老艺术家全家,流转于世界各地的场景。然而当年的很多大师,好像都走过这样一条人生道路。
从遇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开始,斯特拉文斯基就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打磨自己的作曲技艺。至于那谁也不感兴趣的法律,就随他去吧。他甚至在 1902 年,花了一个夏天在德国海德堡师父的家里学作曲,都没有想着回家看看。
唯一可惜的是,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没有能够看到儿子后来的成就。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人生选择的老爷子死于 1905 年。他甚至没有赶上儿子在 1906 年的婚礼。
摸着无名指上标志性的大戒指,斯特拉文斯基仍然能想起,新婚时的甜蜜和那一年发生的太多变故。老父亲死了,他自己也因为 1905 年的工人学生起义风波,没有能够拿到毕业证书。当时的俄国一片混乱,造反派占据各处机关,以前的成绩概不承认。
不过他也无所谓,反正平时上课也不过是混混日子,四年的大学读下来能拿一张两年制学业证明也已经不错了。这张法律毕业证书不过是他此后人生的一张装饰,跟随恩师继续学习作曲才是正事。
可是到了 1908 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也去世了。斯特拉文斯基等于是失去了第二个父亲。葬礼上他悲恸的心情,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好转。
不过恩师的去世,也打开了斯特拉文斯基的自己独自闯天下的新窗口。这时候他已经接触作曲 6 年了,还有着钢琴的基本功,想要写出一首好曲子来易如反掌。
于是,一年以后他就写出了第一部公演的管弦乐曲《烟火》。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受到后来一直帮助他的俄罗斯舞蹈团经理,迪亚基列夫的邀请,斯特拉文斯基开始创作芭蕾舞曲。后来让他名声大噪,又身背争议的三部作品《火鸟》、《春之祭》和《彼得鲁什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
《 春之祭》公演剧照
从 1915 年到 1920 年这五年来的日子,对他来说不算顺风顺水。一方面,一战爆发,他客居瑞士和外界全都断了联系,连老朋友迪亚基列夫也没法给他汇钱。
另一方面随着沙皇俄国被推翻,他一个客居外国的先锋艺术家,已经很难回祖国看看了。
加布里埃·香奈儿
本来名满天下的作曲家一下子变得穷困潦倒起来。不过好在朋友们都鼎力相助,给这个陷入尴尬的音乐青年各种精神和物质帮助。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两个朋友,就是香奈儿的创始人加布里埃·香奈儿女士和另一位先锋艺术家毕加索。
斯特拉文斯基和香奈儿的故事,实在是容易让人老脸一红,不如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和他并称“20世纪三大艺术家”的毕加索吧。
科克托、毕加索、斯特拉文斯基和毕加索夫人
毕加索一生也是画风多变,时而玩印象,时而玩立体,时而玩解构,甚至还画过端端正正的油画,让人实在很难评价他的流派。
就连他自己也说:“我从来不是超现实主义者,我没有脱离过现实。”言下之意是看客眼拙,看不出他的作品所包含的真意。正是因为两人的风格实在多变,斯特拉文斯基也被认为是“音乐界的毕加索”。
毕加索为《游行》设计的幕布
他们的相遇充满了传奇色彩。当时毕加索受邀在罗马为一场名为《游行》的芭蕾剧绘制布景,邀请人正是迪亚基列夫。
这个一见如故的感觉,可能不亚于伯牙钟子期的相会。证据是毕加索居然能静下心来,愿意听斯特拉文斯基谱的曲子。
他曾亲口吐槽过所有形式的音乐,觉得听到乐器的声音就头疼。能把古典音乐的效果听成摇滚乐,说不定这也是绘画大师和我们的脑回路不同之处……
不论如何,这对伯牙与钟子期不再是一个弹、一个听的状态,钟子期也献出了自己的礼物。在罗马期间以及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两人只要相遇,毕加索就会忍不住要给斯特拉文斯基画肖像画。
回到 1920 年 5 月的那一天,斯特拉文斯基的行李箱里,就有一张这样的肖像画。火车从意大利驶入瑞士境内,乘客们下车准备过海关。斯特拉文斯基把箱子放在检查桌上,伸了个拦腰。
长居多年的瑞士,现在就像是家一般。看着站外西沉的夕阳,我们的大作曲家现在心里有些怀旧的情绪泛起。终于回家了。
一大波毕加索为斯特拉文斯基的画像
等一下,我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先生!请您开箱检查!”海关人员指着这个棕色的皮箱要求道。最近意大利的确有些乱哄哄的,有一个名为法西斯的乱党正在四处活动。一向追求和平中立的瑞士人有此警惕也属正常。
斯特拉文斯基慢慢打开箱子,其中的内容一览无遗。一些换洗衣物、作曲用的稿纸、文具、两本书和毕加索临别时赠送的大作。
海关人员戳了戳衣服,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便把目光投向了这张图画。
“先生,这张画您不能带走。我们要扣留。”海关官员一本正经地说。
“为什么?”
“请问这上面画的是什么?”海关官员仍然一本正经。
“这是毕加索给我画的肖像画!”斯特拉文斯基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不,我们认为因为这是一张平面图,可能涉及国家安全。”说着,海关官员已经开始动手收拾这幅画。
斯特拉文斯基觉得哭笑不得:“对,这是一张平面图,是我脸的平面图还不行吗?”
海关人员没有再理他,卷起画作离开了。因为这帮瑞士人觉得,这真的是一副经过伪装的战术地图。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
为您推荐
算法反馈精品有声
热门文章
精彩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