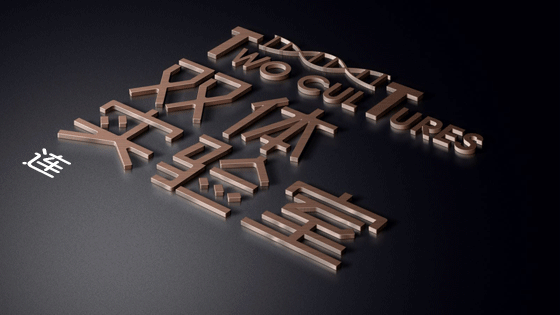对创造的渴望:威廉·哈维


独家抢先看
刘宁(刘青峰)
文艺复兴运动所复活的自由探索精神,由一批实验科学家转变成为近代科学的最初成果。只有经历这一深刻的转变,才能真正结束人类历史上黑暗和愚昧的时刻,产生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精神和物质文明。
伦敦东北郊有一所绿荫环抱的小教堂。威廉·哈维的坟墓就在里面。令人奇怪的是,在哈维去世二百年后,教堂周围的居民只知道他是个伟人,却说不出他是干什么的。
确实,哈维既没有伽利略、牛顿那样出类拔萃的才华,也没有布鲁诺那样以一死殉真理的经历,他甚至没有公开反对过宗教。然而,他确立的血液循环学说同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给宗教以沉重的打击。在探索科学真理的道路上,哈维只不过是一个不倦的步行者。他不是借助灵感和偶然的发现,而是靠几十年扎扎实实的工作,奠定了生理科学的基石。哈维的道路向世界宣告了一种新的精神:仅仅只有“破”、只有批判是不够的,重要的是“立”,是创造;而“立”是更艰巨的创造性的工作。正因为曾经出现过哈维这样一大批在不同领域中探索前进的步行者,人类才走进了近代科学文明的新时代。
科学的目的是在万物中寻找神吗?
1600年二月底的一天,天气阴得可怕。中午,一个爆炸性新闻在威尼斯共和国的帕多瓦大学传开了:前几天,布鲁诺竟被宗教法庭判处极刑,烧死在罗马百花广场。年轻的大学生们议论纷纷。不少学生涌到“当代的阿基米德”——伽利略教授的屋里,倾吐不平。傍晚,在简陋的学生食堂中,新教徒和旧教徒争吵不休,打起群架,甚至还有人拔剑格斗。同学们的情绪十分激动。那个平素爱恶作剧、好热闹的英国学生——二十二岁的威廉·哈维,却一反常态,不置一语。他匆匆吃完了自己那一份粗糙的晚饭,离开了学校。
夜黑沉沉的。哈维在亚德里亚海滨走着,沉思着。因个子瘦小,他获得了“小哈维”的绰号。然而他很结实,生有宽厚的双肩。现在,他那黑得近乎橄榄色的脸颊紧绷着,一双小而圆的眼睛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没有发觉涨潮的海浪早已浸湿了他的鞋子。一天来,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始终压迫着他的心。他甚至想喊出来:“呵!什么是真理?!”哈维早就熟读布鲁诺的著作,并喜欢布鲁诺的锋利的思想和勇敢的热情。而今,布鲁诺和他的著作都已化为灰烬了……。布鲁诺的殉难使哈维意识到自己在走一条同样危险的路。哈维在走着,想着。
布鲁诺信仰并宣传日心说,触犯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教义。哈维研究的是人体小宇宙,他怀疑的是基督教教义中的盖伦学说。
盖伦本来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位名医。据说,他父亲曾梦见神告诉他说,他的儿子长大后应贡献给医学。果然,盖伦成为医学界的王太子。在古代,盖伦达到的成就是惊人的。他的解剖观察细致而又精巧,他的理论体系和谐而又完整。他高超的医术则传为历史佳话。哈维怀疑的是盖伦关于心脏血液运动的见解。盖伦认为,肝脏产生“自然之气”,肺产生“生命之气”,脑产生“智慧之气”。这三种灵气混入血液里,在血管内像潮汐涨落那样来回做直线运动,供养各器官,造成奇妙的有智慧的生命现象。盖伦的心血潮流运动说,使后人叹为观止,虔诚信奉。不幸的是,基督教使盖伦学说僵化了。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三”的。上帝即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人可以分为僧侣、贵族、平民。自然界亦可分为动物、植物、矿物。而其中每一种又可以继续一分为三。如动物可分为鱼、兽、鸟。盖伦用三种灵气来解释生命现象,正好符合宗教的需要。基督教对盖伦学说采取拿来主义,并抽去其自由探索的精神,贴上神学的标签。这样,盖伦的自然科学家的形象就逐渐消失了,他的学说同托勒密的地心说一样,成为基督教解释自然和生命现象的理论基础。到哈维的时代,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引起一场思想革命,而统治医学一千余年的盖伦学说依然牢固地屹立着,并没有因为文艺复兴以来进步学者对它的批判而动摇。
哈维曾经深深迷醉于盖伦学说的美妙和博大。那些看来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能的庞大体系往往成为热爱真理但尚未成熟的青年的崇拜对象。但是,哈维越是深入学习和观察,就越来越多地发现盖伦学说漏洞百出。怀疑自己崇拜过的事物是非常痛苦的。
哈维在黑夜中痛苦地思索着。黑夜尽管漫长,但也有光明。哈维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明月。哈维毫无倦意,不知疲劳地漫步着。他想使人拜服的医学王太子呵,难道你不能减轻热爱真理的青年的痛苦,使他在你的错误中发现一点真理吗?
清晨,哈维赶回学校。这时,早祷的钟声响了。那威严庄重的钟声似乎在警告哈维:“可怜的孩子,不要相信魔鬼的诱惑。科学的目的就是在万物中发现神的存在。一切真理都在圣经上写着。”哈维抬起头来,看见自己亲爱的学校的那幢米黄色的主楼,那显得有点狭窄的校门上,精雕细缕的带翼石狮子依稀可辨。光明的亲切感涌上哈维的心头。
正是为了追求真理,哈维在先后读完坎特布里中学和剑桥的开司学院后,离别了故乡和亲人,投奔帕多瓦。当时,宗教一再宣称“上帝厌恶流血”。著名的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连人体解剖也不敢做。这使哈维深感失望。而帕多瓦却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她为伽利略这样受排挤的进步学者提供自由的讲坛,为哈维这样热爱科学的青年创造自由探索各种问题的学习环境。伟大的哥白尼也曾在帕多瓦学过三年医学。帕多瓦造就出一代伟人决不是偶然的。早在1222年,保守、腐朽的教会学校波罗纳书院中逃出来三个人。他们厌恶枯燥沉闷的神学教条,向往自由讨论。逃到威尼斯以西的帕多瓦后,他们在简陋的旅馆中开办了自己的书院。后来,它发展成这座著名的学生大学。它是由学生组成评议会管理学校、聘请老师的。学校对学生的宗教信仰采取不干涉的方针。尽管帕多瓦大学的物质条件菲薄,但是她那自由、宽厚、进取的精神,召唤着欧洲最聪颖的心灵、最能干的青年。
哈维加快了脚步,走进校门。
哈维是这么年轻,他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会成为哥白尼那样创立新学说的思想巨人。他只是渴望在黑暗中寻找生命科学的太阳。他结实而又年轻的身体内,热血在沸腾着。对真理痛苦而又执着的追求使哈维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望,这就是创造!
寻找新的路
在那连绵不断的白垩陡岸后面,故乡福克斯通市渐渐临近了。哈维站在甲板上。眼前混浊的海水浸染在单调的时深时浅的灰色之中,使人感到压抑。他把手伸进紫褐色的紧身上衣口袋里,摸着柔软的羊皮纸的医学博士文凭。那上面写着:“持此证书者,可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行医、讲课、任教、组织答辩、开药方……”他想:有了它,可以告慰年迈的爸爸和病弱的妈妈了。但是,为了它,同学们是怎样嘲笑过哈维呵。这一切,已无法解释清楚了。
1602年,著名的解剖学家法布里斯主持了哈维的毕业答辩。在圆形的讲演厅中,法布里斯威严地坐在讲台上,他的前面点了一排蜡烛。
“请谈谈,生命之气,是怎样流到全身去的?”
哈维避开老师的自光,用流利的拉丁文答道:“肝脏把食物变成血液后,一部分由静脉送出去,被各器官吸收;另一部分送到右心室,通过心厢间小孔渗入左心室,在那里和来自肺的带有生命之气的血液混合,再由动脉输送到全身……”
哈维摆出一副忠于盖伦经典的好学生的面孔,一字不差地背诵着,甚至他通过解剖观察明明知道心膈间并无小孔,他依然按照盖伦的说法背诵。考试顺利地通过了。
宿舍寒冷阴暗。小窗户上蒙着粗亚麻布。哈维在床边埋头解剖一条活鱼。他常常从市场上买各种活的小动物回来解剖。“小哈维,你仔细看看吧,心膈上有没有小孔?”一个同学趁机挖苦哈维。另一个法国同学凑过来说:“我们的小博士恐怕有记忆障碍。前天我还听他说过塞尔维特的肺小循环有道理呢!”照哈维的脾气,他会神经质地跳起来吵架。但是现在哈维咬紧了牙,没有听见似地继续解剖。他的心里却热辣辣的,再也不能平静下来。
海风吹拂着哈维的乌黑的头发。他把手放在栏杆上。是的,盖伦错了,错了。文艺复兴以来,有多少人批判过盖伦呵!最早对盖伦学说提出异议的是天才的艺术大师达·芬奇。他一生解剖过七十余具尸体,发现心脏有四个腔,而不像盖伦说的只有两个。还有两个著名的批判者。一个是半个多世纪前在帕多瓦创立解剖生理学派的比利时医生维萨里。当他还在保守的巴黎大学读书时,为了做人体解剖实验,常常深夜溜出学校,去偷挂在绞架上犯人的尸体。他的老师西尔雅是盖伦学说的忠实信徒,维萨里就据实物指出盖伦的错误。老师无言以对,大骂维萨里是卑贱的疯子。西尔雅声称伟大的盖伦决不会犯错误,凡是解剖观察与盖伦著作不符之处,只能用人体在上一世纪里发生了变化来解释!1543年,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的同时,二十九岁的维萨里出版了解剖学巨著《人体结构》。这本书大胆地纠正了盖伦著作中二百多处错误。维萨里立即遭到整个社会的攻击。甚至有人造谣说他解剖活人。最后,维萨里被迫去耶路撒冷忏悔旅行,归途,船只遇难,横死荒岛。哈维的另一个先驱者塞尔维特是西班牙学者。他是维萨里的同学,生性好辩、锋芒逼人。塞尔维特在《基督教的复兴》一书中,用六页篇幅批判了盖伦的心血潮流说,提出血液由右心室流到左心室不是经过心膈上的孔,而是经过肺作“漫长而奇妙的迂回”。结果,他被教会判处火刑,烧死前还把他活活烤了两个钟头。所有医科大学仍然严格按照盖伦学说讲授。学生也只有精通了盖伦学说,才能拿到医学博士文凭。这就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为什么无数解剖事实证明了盖伦的错误,盖伦学说依然处于正统地位呢?这真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哈维想:盖伦错了,百余年来,多少人都指出过这一点。但是,什么是对的呢?心脏为什么会跳动?一切就这么简单吗?盖伦学说的大厦为什么推不倒?难道先驱者的鲜血不能提供有益的教训吗?如果我们不能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理,只是一味地指出盖伦的错误,那么我们能有立足之地吗?不,我要走一条新路。
哈维回到故乡,又来到大伦敦。在亲友们看来,小哈维还是那么年轻。然而,他已经不再是一只向往科学真理的热情的小鸟,而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他坚信,只有通过实验才能实现他对科学真理的追求。而实验需要他付出一辈子的精力和创造性劳动。
1604年,哈维成为皇家外科协会的会员。1605年,他娶了名医布牢温的女儿,有了一个温柔贤慧的妻子。1607年,他在著名的圣巴托罗谬医院当了医师。
哈维的住宅离医院不远,在著名的史密斯广场附近。“血腥的玛丽”统治时期,曾有四十个新教徒烧死在那里。每天上午,哈维匆匆穿过又窄又弯的街道去医院。下午,他在家里的私人诊所接待病人。晚上,他有时和妻子一起去看戏。那些年代,大戏剧家莎士比亚正活跃于伦敦的舞台上。哈维的生活真是舒适极了。他有一种喝上等咖啡的嗜好,这在当时也显得有点奢侈。哈维的六个弟弟都是商人,一个在中东贩卖香料和饮料的弟弟每年供给哥哥咖啡。哈维把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科学实验,家里有一间他称为“博物馆”的大房子。大书架上排放着瓶子、罐子和木桶。里面养着鱼、青蛙、鳗鱼、蝾螈。大小不一的笼子挂在天花板上,养着各种鸟。另一间大得有点出奇的屋子里放有兔笼和狗窝,还有一张工作台。台上整齐地放着带刻度的容器、哈维自制的解剖工具,还有一个用猪尿泡做的注射器。哈维一有空闲就要钻到里面,常常通宵不眠。他每天都要在羊皮纸上认真记录他的观察。这是他最大的乐趣。
哈维比他的先驱者看得更远。他决心建造一座新的大厦。他深知,新学说的大厦不建立起来,那么旧学说、旧体系既使再陈旧腐朽也不会倒塌。思想的垦荒者如果只去清除愚昧的野草,而没有在这块空地上不失时机地播下真理的种子,那么,要不了多久,这块浸满先驱者血汗的空地就会重新长满宗教迷信的荆棘。哈维决心做一个播种者。而培育科学种子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他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哈维已经用解剖刀割取过智慧之树上的禁果,深深为探索真理时那种严肃认真、充满希望的内心感受所激动,新思想在召唤着他,无论如何,他都要走下去,奋斗一辈子……
“地上也有天上的运动”
夜深了。蜡烛在桌子上闪着光,照亮了写在羊皮纸上的一大堆数学符号。哈维在空空的大屋子里走着,一只手来回抚摸悬挂腰间的长剑的剑柄。哈维在帕多瓦就养成了佩剑的习惯。几天来,他几乎是在狂热地计算着。
据测量,左心室的容血量约为二英两。因心室有瓣,左心室收缩后排出的血不能倒流。而心脏每分钟大约要跳72次。这样,一小时内心脏要排出多少血呢?2*72*60=8640英两,差不多有540磅,几乎是一个肥胖成人体重的三倍!如果盖伦的心血潮汐运动说是对的,血液排出后就被各器官吸收,那么,肝脏在一小时内就必须造出三倍于体重的血,一天要造七十倍于体重的血!哈维由此得出结论说:“其数量之大决不是消化的营养所能供给的”。
哈维想:一只羊全身的血不过只有四磅多。一条牛在戳破颈动脉后不到半小时就会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既然身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造那么多血,那么,心脏从什么地方得到源源不绝的血液呢?血液流出后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还在帕多瓦读书时,哈维就具备了循环的哲学思想。在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启发下,哈维想:血液为什么不可能是绕着心脏做循环运动呢?心脏难道不是身体内的太阳吗?
伟大的科学家从来不拘泥于传统观念的框架,而善于从他生活的时代吸取最先进的思想,站在新的角度来考察前人的遗产。在盖伦生活的公元二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完美的圆周运动只属于天界,地上只存在有起点和终点的直线运动。所以,盖伦学说里,血液产生于肝、消失于全身的理论,显得合情合理,天经地义。不!地上也有天上的运动,哈维从来没有忘记时代赐予他的豪情。古罗马的哲人,眼界是狭小的。而现在,整个地球向我们敞开着,伟大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航行不也是循环运动吗?哈维的思想集中到循环这一点上。
他说:“潮湿的土地被太阳晒热时水分就蒸发,水蒸气上升,下降为雨,再来润湿土地。一代代的生物就是这样产生的,暴风雨和流星也是这样由太阳的循环运动引起的。”当哈维站在这样的高度来看待世界时,他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了。地上的人并不比天上的神更卑贱。人的身上也存在着和日月星辰一样伟大的运动。
几天来,这关键性的计算使哈维确信:血液犹如德莫克里特的原子一样,既不可能在一瞬间被创造出来,也不会在一瞬间消失。哈维激动地来回走着,似乎感到鲜红的血液在体内不停地循环着。而心脏呵,难道不就是生命的不知疲倦的太阳?
妻子走进来。她那温和的目光似乎在责备哈维通宵不眠。她拉开厚厚的紫色窗帘。哈维笑了,紧张工作的一天又开始了。
对于一个严肃的自然科学家来说,决不会陶醉于新思想的光辉之中,他必须认真细致地为新思想打下牢固的实验基础。布鲁诺也曾经提出血液循环的设想,但那还不是科学。现在,哈维要用实验来奠定循环思想的科学基础了。
银色的解剖刀闪闪发亮。哈维像一个勇猛沉着的战士,眼睛熠熠闪光。一条活蛇被固定在木板上,半透明的肉在解剖刀下分开了。鲜红的管型心脏在有节奏地缓慢地跳动着。这样的实验他做过千百次了,但他还要重复地做下去,因为这是关键性的实验。根据循环思想只要扎住与心脏相连的静脉,血液不能流回心脏,心脏就应该变空变小;相反,如果扎住动脉,心脏就会因排不出血而胀大。哈维用小镊子紧紧夹住静脉,蛇心马上变小变白了。一松开镊子,心脏又立即充血。再用镊子夹住动脉,心脏就胀大变紫,似乎倾刻就要爆裂,蛇身抽动着。哈维松开镊子,兴奋地抹去额头的汗珠。再也没有比这简单的实验更有力地证明血液是循环运动的了。
有的人做到哈维这一步就会以为大功告成了。但哈维是个十分严肃的科学家。荣誉和成功,年岁的增长并没有使他失去纯真。他像孩子一样,总是不断地向大自然母亲提问为什么。为什么血液能在体内循环?血液又是怎样循环的?不弄清这些问题,哈维是不会满足的,通过多年的实验,哈维终于证实了:由于心脏跳动、动脉搏动和静脉瓣结构,保证了血液在体内循环运动。但由于显微镜尚未发明,哈维当时也就无法解决动脉血是如何流到静脉中去的问题。他认为血是通过肌肉中的细孔流过去的。
哈维从来都是把生命看作高度协调的整体,总是力图从功能来理解结构的意义。他不做没有思想的实验。实验是验证他对生命理解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所以哈维并不是重复古已有之的解剖观察和分类描述,而是在活体上做功能实验。这样,哈维在创立血液循环学说的同时,也创立了生理科学的基本方法——活体解剖。一门崭新的科学——生理科学诞生了。
认识真理的过程是复杂的。要从现象到本质,从思维到实验,千百次循环往复。哈维说过:“学问不在教条中,而在精巧的大自然中。”他一辈子都在研究生命。但他的实验决不是盲目的。建立新学说与革命性的新概念的引入,新方法的应用,关系极大。科学家不仅要有献身真理的精神,还要有把科学实验和哲学思想融为一体的气魄,有不怕失败,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工作的毅力,这样才能把新思想立起来。而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科学家的怀疑精神和探索毅力,则始终是推动他登上科学高峰的源泉。
“一切都托付给爱真理的热忱”
1615年,哈维应聘为医学院解剖学外科讲座的终身教授。
哈维走上讲台,看了看讲稿上写的讲授原则:“不要称赞或贬低别的学者,因为他们很好地工作过,即使有错误也可以原谅”;“不要和别人争辩”;“不要讲得太烦琐……”哈维有些激动。他决心把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众。不是去指责别人的错误,而是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
讲台下面放着六块木板。哈维精心解剖出来的心血系统、神经系统的标本分别放在上面。哈维教授用流利的拉丁语很快地一直讲到下课,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失望地离开了课堂,在阴冷的街道上徘徊了很久……又一头扎进实验室。
哈维行医的名气与日俱增,很多上流社会的人找他看病。1616年,英王詹姆斯一世聘请他当了御医。詹姆斯一世很喜欢哈维的稳重,却派给他最无聊的工作。哈维要为一些被诬为巫女的妇女做生理检查。哈维没有利用职权把这些可怜的女人送到火刑场上。
1628年,也就是在哈维公开演讲血液循环说十三年以后,一天午饭后,哈维和妻子正在喝咖啡。光线透过镶有彩色玻璃的窗户射到一只毛色美丽的鹦鹉身上。这只懂事的鹦鹉不停地做出一些可笑的动作、发出奇怪的声音。它多么想给这对结婚二十余年而无子女的老夫妻以家庭的欢乐呵!这时老仆人送来一封信。
“我们不要失去一个让全欧洲都知道您的思想的机会。”德国出版商菲茨(Fitzer)在信中热情地写道。他说他决定支付出版的一切费用。哈维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个商人竟有这样的眼力和魄力是他万万想不到的。哈维想起,两年前,他为病重的国务大臣弗兰西斯·培根看病时,曾多次向培根讲血液循环的问题。而培根这样伟大的哲人竟然认为那是无稽之谈。同事中反对哈维的人就更多了。而现在,他五十岁了,头发已经花白,一个出版商对人类思想进步的高度责任感使他下决心把文稿送出去。
一种新学说一旦以著作的形式出现,那它就脱离了个人的思想,而进入历史的行列,就将受到历史的惊涛骇浪的冲击,在批评和争议中鉴定自己的价值。
《心血循环运动论》很快就在法兰克福印行出版了。
在这本书中,哈维写道:“以下要说的乃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我不仅怕少数人的猜忌对我不利,而且怕全体人类要和我作对,因为人人都会被成为人的第二天性的习惯、经过传播而深入人心的学说以及尊古心理的影响所支配。”“但我意已决,把一切付托于爱真理的热忱和思想开通者的同情。”
这本专著分为十七章,行文简洁,朴实无华。哈维用非常干净有力的几句话总结了他的学术思想:“一切推理和实证都表明血液是由于心室的跳动而穿肺脏和心脏的,由心脏送出分布全身,流到动脉和肌肉的细孔;然后通过静脉由外围各方流向中心,由较小的静脉流向较大的静脉,最后流入右心耳。由动脉和静脉流出流进的血液量,绝不是消化的营养物质所能供给的,也比专供营养用的血液量大得多。因此,有绝对的必要作出结论:动物的血液是被压入循环而且是不断流动着的,这是心脏借跳动来完成的动作和机能,也是心脏的动作和收缩的唯一结果。”
不出哈维所料,真理很快招来反对它的风暴。来自巴黎、威尼斯、莱顿的反对信件和文章潮水般地涌到哈维的写字台上。带头反对哈维的是巴黎医学院院长里阿兰。里阿兰也以精通解剖享有盛名,同哈维关系不错。但他解剖的目的同哈维相反,是为了捍卫盖伦的权威。每当一个庞大体系面临瓦解的危机时,总有一些最有名望的权威出面捍卫它。里阿兰的拼命反对,使哈维的学说超越英伦海岛,在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对哈维的抨击简直是五花八门。威尼斯有个学者,叫巴里撒纳斯,硬说肺静脉里流的是空气,而不是血。哈维反问他,为什么肺静脉的结构像静脉血管而不像气管?对方强词夺理道:“事物就是这个样子,因为造物主要它们这样。”著名的爱丁堡大学教授普利姆罗兹则嘲笑哈维学说无用,他挖苦地说:“以前的医生也不知道血液循环,但也会看病。”哈维顽强地宣传他的学说。1636年,哈维奉王室之命到纽伦堡,那里有个著名的老医生霍夫曼。哈维写信邀他来看解剖示范表演。老先生来了。哈维的演讲已使大多数听众信服,只有霍夫曼摇头不已,频频提问刁难。谨慎耐心的哈维终于忍无可忍,掷刀而去。
哈维的学说影响非常深刻和广泛,甚至在莫里哀的剧本和法国诗人布阿罗的作品中,都出现了反对血液循环的保守者形象。这种角色总是预先拒绝一切新事物,并通过作出大学决议这种行政手段来“禁止血液体内徘徊的学说”。据说,哈维的医生业务也受到损害。只不过因他又继任了查理一世的御医,受国王保护,才没有受到人身的摧残。
赞成哈维学说的有著名的进步哲学家笛卡尔和伽桑狄。笛卡尔赞同血液循环的观念,但反对哈维把循环的动力归之于心肌的运动。笛卡尔是机械唯物论者。他认为机器要凭借外力才能运转。人体也是机器,不能例外。笛卡尔找不到人体的外力,于是就求助于上帝和灵魂的观念。这就是影响欧洲思想甚深的二元论哲学。
发人深省的问题是:为什么盖伦学说被批判了百余年却没有动摇它的统治,而哈维的学说一问世,盖伦学说的卫道士就感到了可怕的威胁呢?为什么塞尔维特、维萨里把批判的锋芒指向盖伦却没有推翻它的力量,而哈维的著作没有一句直接批判盖伦的话却一举摧垮了盖伦学说呢?这一历史事实,恰恰有力地显示出“立”的力量。只有把经得起实践考验的新事物“立”起来了,旧事物才会被取、才会消亡。很多人以为,只有布鲁诺、塞尔维特那样的殉难者才称得上与宗教斗争的勇士。事实上,焚烧宗教叛逆者的火光,更加衬托出宗教统治的黑暗,激发起人们的义愤。而唯有科学的创造,才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
蝌蚪的尾巴带来最后的胜利
1657年6月2日。初夏,黄昏。
在敞开的百叶窗前,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安详地坐在大安乐椅上。今天的太阳迟迟不肯下落,老人慈蔼的目光恋恋不舍地望着夕阳。他已经七十九岁了,他不知道是否还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半个多月来,哈维每天都这样坐在窗前。他是那么地悲伤。因为,他再也不能走了。他曾经是个不倦的步行者。从中学时代起,小哈维就是一个杰出的步行者了。在剑桥开司学院东北部的河谷里,他穿过美丽的石楠丛,踏着浓密的青草,在星空下沉思着,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科学的向往。在帕多瓦,在湛蓝的大海边,在清澄的咸水湖畔,他低头走着。在伦敦那弯曲的街道上,他出诊、讲课……在科学的道路上,他始终不知疲倦地向前走。他晚年醉心于鸡的胚胎受精和发育问题,甚至还研究数学。尽管在这些方面没有取得像血液循环说那样杰出的成就,他仍然作为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家活在世上。
哈维的晚年是痛苦而又凄凉的。妻子早已去世,又没有子女。1642年,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哈维是查理一世的御医和友人,又是王子的监护人。他认为这次革命是叛乱。在连年战争中,哈维一直追随王室。革命党攻占伦敦后,抄了保皇党哈维的家。1649年,查理一世被判处死刑。哈维灰心已极,认为世界的末日已经到来。好友们逃散了,国王死了,他经常出入的宫廷焚毁了。哈维感慨万分地说:“国家布满了风浪,而我是风浪中一只颠簸的小船。”克伦威尔执政时,皇家医学院推选哈维当院长,他以年老为理由推辞了。他内心实在是认为,在一个没有国主的国家出任院长,是对国王的背叛。
6月3日,哈维终于因中风而躺倒了。黄昏时,他静静地躺在床上,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哈维看了看夕阳,又看着周围的亲友。他似乎想说话,但已经不会说了。他慢慢掏出怀表,深情地注视着它。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解剖实验中,这块怀表始终是哈维最忠实可靠的助手。哈维是那样地热爱生命,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从不停步,现在,他就要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哈维慢慢阖上双眼,与世长逝了。他把所有的财产捐赠给皇家医学院,奖励那些从事发现自然奥秘的人。
哈维去世后没有多少年,血液循环学说中的最后一个疑点也消除了。1660年,意大利的马尔皮基用显微镜看到了青蛙肺里的毛细血管。1688年,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用他自制的精致显微镜观察蝌蚪的尾巴。他惊喜地写道:“最初看着,真使人欢喜之至,血液像小河流般循环流往各处。”他宣布:“所谓动脉和静脉,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这就是毛细血管。科学仪器的进步,终于使人们亲眼看到了血液循环。任何科学诞生之初,都不会尽善尽美。它也绝不会摆出俨然是绝对真理的架子去阻塞人们前进的道路。哈维学说中的疑点,正是后人前进的起点。二十世纪以来,哈维在生理科学中采用过的数学方法和力学方法,正在生物科学中大放异彩,产生出富有生命力的新分支。
哈维生活在人类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近代科学诞生了。这个时代需要而且产生了一批伟人。但是,他们同任何时代任何伟大人物一样,不可能是完人,第谷不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培根反对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牛顿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哈维忠于腐朽的王室;大化学家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了断头台……。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他们是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这些伟大人物,只可能在某些方面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都是从旧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当他们抓住真理时,便所向披靡,成了新时代的创造者。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阵地上,点燃了进步的火炬。正是这星星点点的火光,汇成了新时代的黎明。
哈维的一生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家决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他们只不过是科学上的老实人。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在政治上曾经是时代的落伍者,但子孙后代将永远纪念他们对科学的贡献。四百年过去了,哈维对真理的追求,在科学实验中的赤子之心,犹如他那不朽的学说一样,仍然闪烁着动人的光辉。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