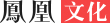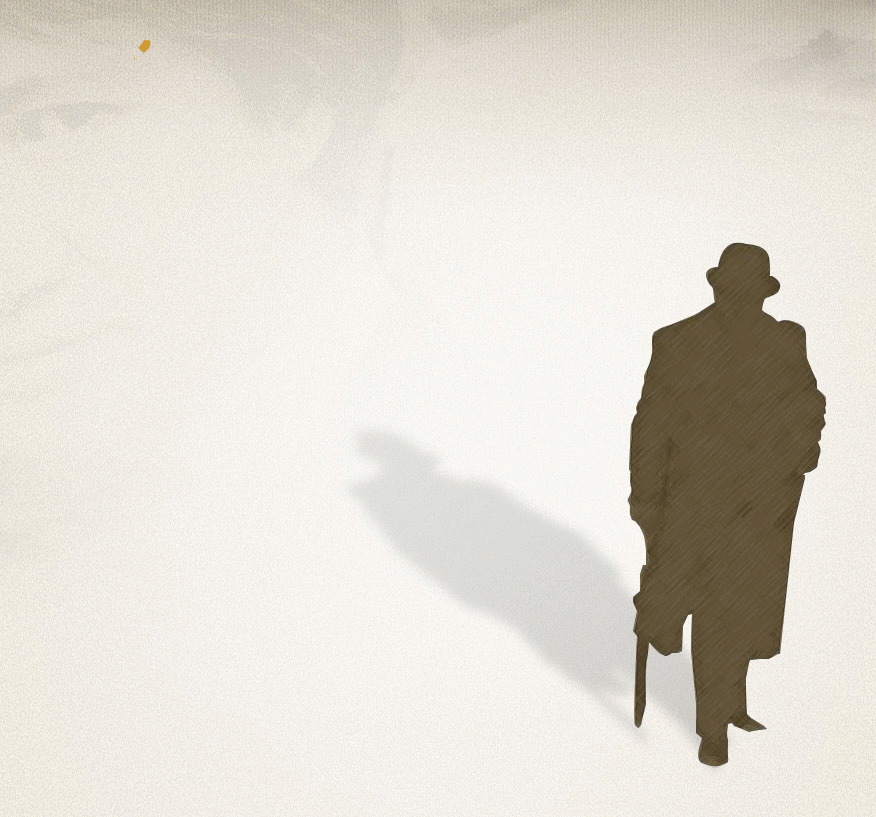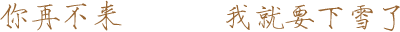-
陈丹青:木心一边被神化 一边仍然被看不起
时间:2015年11月16日 地点:乌镇 讲述:陈丹青 采访:胡涛"我58岁经历了木心的死,这是一堂课。"2013年,陈丹青接受凤凰文化专访,对着镜头袒露出他的生死课题。2年后,在乌镇西栅甫落成的木心美术馆里,62岁的陈丹青再次接受凤凰文化的专访。这一次他知道,木心已入梦。
几十年桀骜名声在外,眼前的陈丹青却让我们觉出他已多了一份让灵魂安身生立命的平和,不肯再事事沾身,轻易针砭。他将自己定义为木心美术馆的建设者,虔诚求问"我怎么能够做的更好一点?"他希望自己从谈论木心的高台上退隐,对记者和颜道:"你们多听听其他人讲木心"。
"这是他的命",木心一课经年,陈丹青明白世上有许多珍重事比爱憎更大。建设,承担,守住,传续……陈丹青说"我是个老人了,我可以平静的做这些事。"

我终于梦到木心 我盼他"鬼魂归来"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我在维也纳,梦见了木心。梦很短,我立刻惊醒了,但是已经梦到他的样子,包括他火化的时候……我看到他开门走出来,样子是我跟他最多来往的那段时间,也就是60出头,不是他老了以后的样子。此前有人告诉我,他有好朋友走了,很想梦到他,很想他变成个鬼,见见他,我当时不会有体会。现在我有体会了,因为中国人说一个人死了叫"没有了"。"没有了",这个说的很好,他真的没有了,一个没有的人是找不到的,就觉得你变成鬼也好。
木心去世后,我很少无故去晚晴小筑里。我没有那么浪漫、伤感。一般去都有事情要做,尤其在做纪念馆的时候,我每天要在木心花园里面进进出出,一会去房间里去翻点东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
如果我现在是二三十岁,我可能会让自己扮演一个很哀伤的角色,现在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就是我是个成人了,是个老人了,可以很平静地去做这些事情。
昨天巫鸿说了一句话,非常对,他说命运嘛,都是偶然的。一个艺术家一段历史可以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回来了。一切都是天意。怎么会有一个乌镇的出现,成就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乌镇还没有改造,先生不会回来,就算回来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现在都发生了。一东一西,一个纪念馆,一个美术馆,照老话来说"告慰在天之灵"。
但是先生也未必就是要这个,他晚年一直在想身前身后事,我想他最在乎的还是壮志未酬。我也亲眼看到他发昏以后,一个人一生写的东西就此扔下了。
他烧过稿子。冬天他们在楼上客厅,用火炉取暖。通常都是小杨在点火,他就跑回房间拿出一大摞,一张张往里扔,烧掉。这事据小代回忆大概发生在2009年。所以我这次专门布置了一个展柜,全是他很杂乱的碎稿,把它堆起来——其他都放得平平整整,经过选择,这个就无法选择了。他的写作很奇怪的,就是不标明日期,也不归档,不归类,就是杂处在一起。
木心与两岸都处于"错位"状态
木心在1983年到1990年左右,密集地在台湾发表作品、出书。在时间上,他跟大陆新文学起来是同步的,但是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当时很少大陆作家知道有一位上海出去的作者在台湾很火,但除了极少数人能够在香港书市买到他的书,台湾版的书,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去年读了王鼎钧四部回忆录,他最后一部叫《文学江湖》,我才完整知道1950年以后国府退守台湾文坛发生的事情。
王鼎钧没讲到后面一段,因为他也到美国去了。五、六、七三个十年过去以后,在八十年代,他们发现了木心,他们把木心抬起来。回到中国大陆,这个就不太可能,因为前三十年正好是所有民国老作家销声匿迹的时代,也是有数的几个无产阶级新作家起来的年代,而且在文革中又被打倒。像写《金光大道》的那个浩然,还有写《欧阳海之歌》的作者,这些人都在文革当中给灭了。所以大陆当时的文学环境不但跟传统文化的断层,跟五四也是个断层,跟1949年也是个断层,然后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后来的事情发生。
我们返回去看台湾就不是这样,所以你只要对照一下台湾从痖弦,一直到这一代文学人,他们在议论木心的时候,是在一个常态中议论。尽管他们也把木心看成一个奇人,一个特殊的现象,一个阶段,但是跟大陆在议论木心或者不议论木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可以以此看出来两岸的一个文学圈、文学人的一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大陆来说,木心是一个错位的状态。但是他在台湾,也是一个错位。他绝对不会想到他1948年、1949年之间去过的那个台湾,后来变成他文学第一次呈现的区域,他绝对不会想到。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有耐心一直等到过了二十多年——他是1986年在台湾出书,一直到2006年才在大陆出书。这些都构成他的文学生涯和中国的文学生态的之间戏剧性的关系,或者说戏剧性地没有发生关系。
中国的文学界,如果指作协或者指所有现存的文学刊物和文学圈,木心真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不仅是说他们不关注木心,是木心也不关注他们,是双向的。如果木心非常愿意跟这个圈子发生关系,他只要一回国,我相信文学刊物会对他开放,愿意他来供稿。可是2006年考察下来,他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在《南方周末》,叫《鲁迅论》,此后他没有在任何的中国文学刊物发表过。如果他愿意会发表的,不一定有人关注,也不一定会持续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文学圈会接受他,如果他愿意交朋友,我相信会有一些作家愿意去看他,陈村孙甘露就去看他。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不是这边不理他,是他也不理这边。他不要入这个局,所以当我说这个的时候,并非怪你们为什么不理他,不是这样的。应该问木心为什么不理他们?这个很有意思,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和非或者对和错,或者贬和褒。
很多人到今天还是看不起木心
木心不是张爱玲不是沈从文,后两位被活埋再被夏志清打捞,可是木心活活就在我们面前,没人看得起他。现在基本还是这样。这个社会势利,这是最有意思的事。
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张爱玲出来十来岁,傅雷马上就叫了。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现在不要说一个老头子出来,一个年轻人出来,大家要么不吱声,要么弄死他。所以现在用不着上面弄死你,同行就弄死你。中国从来都是这样,这30年来,这个现象越来越厉害,尤其这20年,就是稍微有好的人出来,他马上想到我怎么办?我算什么?我已经名片上那么多?这么多人出来,不是这样吗?
我也不太看重文学批评,中国哪有什么文化批评,哪有争论?文学批评,王朔大家骂他,那不叫批评。王朔只是一个最特殊的例子,因为他也批评,他也叫骂,那文学界也只能骂他。但是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例子,敢批评的人已经很少了,可能哪个人敢批评,一定会有很多人骂他。但是那不叫批评。
我看重的倒是老百姓,所谓老百姓,就是木心说的潜流。不属于哪个学院,哪个机构,一个一个的归起来,这个是最珍贵的。木心的有意思不在这个版图里面,而且他不该在这个版图里面,为什么要放进去现代文学史?我们看重的就是读者,没有什么一般不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读者,他在读你的书就可以了。随便什么人,就纪念馆有一句话,木心说的,他说什么送邮件的,什么工人、农民,我想象的都是这些读者。
木心有一个非常东方式的结局
木心的确是文学一个局外人,如果你定义这一个局的话,局有一个边界、入口、出口,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木心还真的是一个局外人,而且他不再可能是一个局内人,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我相信在捷克不是每个人都读卡夫卡,德国不是每个人都读尼采或者海德格尔。我写过一篇文章《鲁迅的价值》,在正常的情况下鲁迅应该只是有限的一些读者,很稳定的。在隔代的一直会有一群有限的读者,绝不是像我所看到的那样,到处都是鲁迅在文革当中,现在又没有人去读他。正常情况下像鲁迅那样的人,像木心这样的人,像卡夫卡、尼采这样的人,就是在他的母国只会拥有一小群读者,但是一直会有读者,这就对了。读得对不对,咱怎样解读,它自己会发生,或者自己会消失。
木心其实已经被神化、被符号化、被标签化,包括《从前慢》。他已经是这样了,我慢慢在期待他进入一个正常状态,就是人群中还是只有很少的一群人,但这群人你仔细看看其实又蛮多的,真心喜欢他,在读,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来,你看美术馆开馆了,好像又是个大新闻,我相信很快会冷掉,会恢复常态。纪念馆开馆那天下着大雨,涌进涌出全是人,但现在纪念馆一年多以来,已经恢复一个常态,蛮稳定的一个数字,人其实不多,这样很好。美术馆将来也会这样,空荡荡的有那么几个人在看,我相信会这样。
我蛮相信杜尚所说的那句话,人们每过三十四年,会主动为一个被遗忘、被忽略的人平反。我相信这包括一群人,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年轻人,一零后或者二零后说咱们去看看北京那个文学馆,它是这样此起彼伏的一个状态。我2010年的时候去俄罗斯看托尔斯泰的故居,到他的坟上去,我去了我才忽然想起来,他正好死了一百年,他是1910年死的。可是我回来以后读到《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专题报道,就是托尔斯泰的专题,说俄国很平静,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纪念。我读了真是很会心,这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文学家,照中国的说法可以光照千秋的,可是他一百年以后,我相信一定有人纪念他。但是这个媒体很平静,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
晚年木心回归乌镇的这个选择,对比尼采他们的下场和ending,木心是一个非常东方式的方式——他跟自己和解了。因为照他的意思就是"孔雀西北飞,志若无神州",这句话很重的,中国艺术家说不出这句话,非常重的一句话。故乡、故国、母国,可是他说了这句话。另外他还说了这样一句,我用在我去年纪念他的文章里面,"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浪到中国故乡"。他把回来仍然看作是流亡或者流浪,从现实层面来说,他没有选择,因为他没有家庭,独身,我也一直担心他一直老下去怎么办,但是真的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他的家乡在找他,叫他回来,请他回来。在我的解读就是他跟自己的立场和解了,就是这样子。
-
梁文道:读者更想见的是木心 而不是莫言
时间:2015年12月08日 地点:北京 讲述:梁文道 采访:杜鑫茂我之前常说,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只有两个作家对读者产生过这样的一个效应:让读者会觉得很想见到他们,是谁呢?不是沈从文,不是茅盾,更不是莫言,而是鲁迅和张爱玲。现在有了第三个,就是木心。我们吃鸡蛋的时候不会想看鸡,但木心就是那种让人格外想看看那个鸡长什么样的作家。这不是一个文学成就高低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个文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围绕着木心的这群年轻读者们,就像英文词中的corp,像一种宗教,但又不完全是宗教,是一种亚文化。而这种文化之中的参与者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这种不同会使他们对他们所喜爱,所崇拜的对象更加投入。

木心是现代华文文学史的一个局外"怪胎"
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很欣赏木心,他会也许觉得木心是不错的作家,但不至于对他评价太高,又或者有些人根本看不上也木心。
木心跟张爱玲不一样,张爱玲的作品常常有一些自传性的描述,因为张爱玲写散文、杂文,很难不写自己,她整个性格跃然纸上。但是另一方面,张爱玲又那么隔绝,所以大家就会对她特别好奇。而木心其实没有写太多极深的事,没有写太多很关乎自己切身私隐的事,可是他的文字,他的思路跟别人不太一样,会让你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大部分木心的读者第一次接触木心作品都会有类似的疑问。
文革,把一个作家的全部的作品都毁灭掉,至少到那个阶段作品毁尸灭迹,那的确是一种"屠杀"。但是那些文字本身对那个作者的意义在哪里,还值得考量。比如木心的狱中笔记,那些蝇头小字几乎不是让人看的,我猜他也没有想过要把他那时候的作品公开。那他当时写的这些东西到底为了什么?我觉得那是他用来困住自己的另一个"监狱",或者另一堵"墙"。他已经坐在监狱之中,外面已经有一堵墙,他在用文字帮自己建造另一堵墙。目的在于,自己打造的这个文学跟思想的"墙"是可以保护自己不被外面那个墙所伤害的。那是他用来自我治疗,自我拯救,跟自我保存的一个手段。
为什么我们说他后来的文字,几乎没有任何今天常见的新中国文坛腔调?不是要判断现在的新中国文坛腔调好或不好,也不是说木心更好,而是说恰恰因为他把自己隔开了,与文革时的毛式文体隔开了,造就了自己独特的文风。当然,这样一种近乎独白的写作也会造成一些问题。当一个人很久不说话,与外界彻底隔开是不健康的。
很多年轻读者跟我说,他们看木心作品的时候感受到一种老派中国的味道。很多人说,如果过去的中国文学没有在1949年被摧残得这么厉害,传承下来的话那就是木心了。这个讲法也有一点问题,真正的文学传承不可能是这个样子,因为在开放的环境下,自由写作一定会变,不可能原封不动。木心是另一种变,有点像你把一颗树苗从树林移植出来,放到盆栽里头。也许某天整个树林被消灭了,于是我们说,现在盆子里头的这颗树,就是原来那个树林的真相的遗留。不是的,因为那个盆子也改变了这颗树。
当然,木心的这种改变不是被动的过程。任何一个有志气的作家,他总会对自己有要求,尤其像木心。他是1949年的时候整个被毁灭掉的一代里面的一个孤种,但是在一个很特殊的环境底下,被禁锢在一旁,然后自己摸索,挣扎长出来的东西。
他坐过牢,但他要假装那个事情没发生过。这段经历对他当然有影响,他临终甚至对陈丹青发出文革的梦魇。但是他这么多年一直把这段回忆压住,不愿像别的作家一样去写文革回忆录,他要假装整个事情没发生过。这个可能是他觉得不屑,他觉得,"我是这么一个追求纯美的文体家,不要让那些东西弄脏了我正在雕的这个大理石的像。"
木心像是出土文物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看当代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没有一般的大陆文坛的样式,又不是台湾式、香港式,甚至是马华式,但是那种古老又好像很先锋。你觉得他像年轻人,他不太可能是年轻人,他是个"前朝遗老"吗?他明显又不是。所以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的坐标来看,都掌握不住他,他是整个现代华文文学史的局外的一个"怪胎"。
《圣经》的精华滋养了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世界
木心把耶稣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源泉,一个思想家。他把《圣经》当成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作品来看待。其实自从新世纪之后,《圣经》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坛影响很大,那时候大部分年轻人想要学习各种的人文社科知识,很多人都会读《圣经》。
那个年代很流行讲整个西方文化的基础,那你要了解西方文化,你就要读西方现代小说,你读托尔斯泰,尤其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你怎么能够不追根溯底,回到源头呢?回到源头,当 时他们的知识视野所提供的那个源头就是《圣经》。当时的知识青年对基督信仰的熟悉程度比今天要深,我们现在是一个无神论时代,那个时候不是。沈从文的小说文字都受到《圣经》和《圣经》译文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教、新教的合本对当时很多的中国作家产生过作用的,木心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木心一路流亡到了故乡中国
木心还有一句话: 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他把"归来"看作是一种流亡。之前很多流亡作家或有流亡经验的作家都会有类似的感慨,二战的时候,纳粹控制整个德语世界,当时有很多德语世界的伟大的作家被迫离开祖国。这些流亡作家有很多都觉得他再也回不去,就算他二战结束之后回去,那也已经不再是他认识的当年的那个魏玛德国了。同样的,木心回来,这个国家早就不是曾经养育他的那个国家了,那是一种流亡。他年轻的时候,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他在这里经历过许许多多。但是问题是那时候他采取一个内在流亡的策略,或者被迫内在流亡。他所写的东西就像是一个局外的人写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虽然同样是用中文,但是不像中国人讲的中文。
我不太敢说木心已经"归来"了,"归来"的意思指的是回到了你原来的地方,但这个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吗?如果他真的是再来中国是流亡的话,这不叫"归来"了。他从中国出去,又去到了中国,而不是回到了中国。他从一个中国出去了,从一个中国里面很早就把自己流放了,后来真实的肉身跑了,再后来他去了另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了。
-
童明:你读"不懂"木心,不是他的错
时间:2015年11月14日 地点:乌镇 讲述:童明 采访:何可人第一次见到木心的作品,是他的《散文一集》,感到惊喜:怎么还有这样的中国作家!他和世界文学的规律合拍,又深谙中国的传统。很会写,善于创新,是少有的文体家。
木心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心灵自由,他对东西方文化多脈相承,形成对艺术和艺术规律的独到的看法。我跟他说过:世界上有一批作家和你一样,他们不仅对本民族的艺术感兴趣,对全世界各种艺术传统都感兴趣,想象力和创作都是跨文化跨文明的。
木心年轻时就做了一个选择:"我要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我问过他:"怎么成为艺术家?"
他说:"连生活都要成为艺术"。
"生活怎么才能成为艺术?"
"你要自己悟,"木心回答。

木心的先锋性
木心善用故实手法写抒情诗,读起来像散文诗。还写散文体的评论,散文小说。他的散文小说都是短篇,数量并不多。这种小说的重点不在情节,不在构建故事,而在于营造诗意的氛围,以揭示某些道理,有布宁(又译蒲宁)、博尔赫斯的味道,可是和他们又不同。
他的"闲笔"很见功力,能用艺术家的观察能力,把本不相关的东西相关起来,嵌入淡淡的哲思氛围,文字似有神力。他是个艺术性的哲学家,是尼采般的作家,看到我们所能看到的,又看到我们通常看不到的。这种双重的眼光极为难得。此处强,就强出别人许多倍。
你说,有人认为木心小说写得不好。是吗?我猜他们的意思,可能是木心的小说和他们习惯阅读的小说不一样。我们现在盛行的文学观本身需要更新了。木心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而是现代主义作家,是现代主义中的先锋派。先锋派并不脱离现实,他们看重文学概念的革新,走在文体和思想的前沿,以艺术本身的力量来面对现实。
中国作家中并非无人尝试先锋派或现代主义写法。从世界文学的大局看,欧美、拉美、非洲都有比较坚实的现代主义时期。中国的现代主义却时间短,仅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一阵。这个浪潮虽然对固有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一个反叛,但是太仓促,不彻底,仅涉及了皮毛,留下诸多遗憾。
读"不懂"木心,不一定是他的错
木心的诗,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比较真实的情况是,一个喜欢读木心诗的人,说他的诗好,指的是读懂的一小部分,没有读懂的那一部分,就会说:哎呀,这个读起来怎么这么累?
累, 因为还没有懂。你感到累的作品,或許是个学习的机会,有一天突然读懂了,那是另一种的好。
木心反感套话、空话,也反感太顺溜的话语。顺溜话是惯性思维的产物。不是有一个艺术的规律叫做"陌生化"吗?艺术偏偏要把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和观念变得陌生起来。木心的文字也是时不时地陌生一下。
另外一点,木心觉得中国古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其中一些精华已经被忘却了,所以他要适当复古。他的复古并不是大面积的。当这种复古出现在文字里,有些读者又表示反感:怎么这样写,太拗口了。文学的文字是可以玩的,游戏才产生新意。用非常顺溜的语言写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当然,木心不愿意叫人读不懂他。有些诗,大家读懂了,觉得真的好,比如《从前慢》,朴实的诗意,暗暗批评现代化中的异化现象。木心还是主张文字平实而不做作。他厌恶靠词藻堆砌來卖弄,主张故实,用故实的方法来抒情。
木心和我专门讨论过"故实"。为了把问题讲清楚,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以李清照为例。我也举了美国诗人的例子来佐证,比如Elizabeth Bishop. 有一段时间,木心老和我开玩笑:"童明教授在金发女郎里发现李清照了"。
看"不懂"木心,不一定是他的错吧。我们要更多关心的,是他到底是怎样在写,为什么要那样写。八十年代时,大家心智活跃,谈到我们正处在文化断层。文化断层至今还在那里,没有人再提,不等于没有文化断层。
评论一个作家,不可以信口开河。坦白地说,在艺术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不是一句"我看不懂你"就可以否定一个作家。我看不懂,因此你就不好?当我们慢慢阅读木心、了解木心时,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还有这么一个人,怎么把他和中国文学史联系起来?
木心与文学史
目前而言,木心确实没有写入中国文学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第一,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首要条件就是心灵的自由。在当下的历史状况里,艺术家真的心灵自由吗?我们怎么评价一个心灵自由的作家?第二,文学参照体系应该随着文学创作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固守成规,一直用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标准来考查作家和作品,木心这样的作家就的确不在你的雷达之内。
有意思的是,任何人在评论一个作家的时候,本身就带着一种文学史观。评论者的文学史观在评论时显露了出来。当然,坚持说你是对的,那是你的权利。不过,文学评论这件事要按文学规律做,如果不按那个道理讲,就只能靠权力讲话。现在有个时髦词:"话语权"。很多情况下,是看谁人多势大,山头大,声音也大。如果不靠权力的话,那就要谈文学:文学史是什么?小说有哪些规律?散文有哪些的规律?为什么一个作家这样写,既是散文,又是小说?
文学评论家应该谦虚一点。文学现象在前,文学评论在后。因为有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我才去思考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我觉得应该怎样怎样。文学评论者自己不懂创作,或者没有足够的阅读和知识,就去评论,那就有点傲慢了。体制内的文学评论也傲慢惯了。傲慢来自权力。权力说,应该开个什么大会;权力说,文学应该如何如何。权力一掺合文学,权力和文学都腐败了。
木心的作品,不仅给我们当代人看,留下来给未来的读者看吧。
木心改稿非常仔细。我和他做的访谈,我会整理出来第一稿,他提修改意见,我同意之后,他又誊清一遍,再寄过来,我再提点意见,他再修改。我问他为什么要改这么仔细,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多厚的一部作品,托尔斯泰让他太太帮助抄了两遍。巨大的工程。稿子誊清后,装上马车去送给出版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托尔斯泰又想起来什么,说:不行,快把稿子追回来。太太就问:为什么改稿要这么仔细?托尔斯泰说:我要对未来的读者负责。
-
巫鸿:文革对文学作品的毁灭是一场"屠杀"
时间:2015年12月04日 地点:北京 讲述:巫鸿 采访:杜鑫茂上世纪8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攻读美术史和人类学,当时也有很多艺术家从中国去美国,不少人在纽约。因为我,美术史的兴趣,就认识了一些这些艺术家,特别是陈丹青,通过他我认识了木心。那是1984年,陈丹青跟我说有一位奇人,从上海过来纽约。他画的画非常有意思,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说愿不愿意看一看。我当时很有兴趣,所以看了一些作品,也见到木心,所以非常觉得觉得人是一个奇人。他非常与众不同,很难想象他是中国来,而且经过这么多沉浮,但他表现得他非常超然,而且很有一种国际化的味道。但实际上他没有在国外住过,所以他是超越时空的一个人。我还是先看他的画,因为当时他的文学作品发表的还不多。

木心来自文艺复兴
我觉得木心的作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和别人一样拥有具体的生活经验,但我们在他的作品里面,很少直接看到直接的描述。他自己设想成一个超越时空的人,一会儿到古罗马,一会儿可以到中东,一会儿和伯拉图谈话。他是这么一个天马行空,超然的人物。他把自己放在宇宙时空里,一种跨越文化、跨越国界的境界里。于是也就造成了一种隐身,他到底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他的画也不签字,不写年代,所以现在研究起来,也不太知道他具体的创作时间。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广大的模糊的艺术里,而他真实的存在有时候看不见了。这是非常有趣味的做法——,不是藏起来,而是把他转化成一种艺术。所以这时候我用"隐身"来归结他的创作。
木心说他在美国的艺术上有自己的地位。我认为不是指哪本书里写了他得了什么奖,而是观众在欣赏他作品之后的惊叹和认可。
在美国,人们主要通过木心的画来认识木心,在华语圈则主要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来了解他。这非常错位,但也是一个现实情况,我觉得历史充满了偶然,因为木心就是这样被介绍出去了。他的文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翻译,不能说他的文字佶屈聱牙,但是不是通俗易懂的故事。但可能将来能把他这种文学上的造诣,在翻译上体现出来。但国外是不是有像国内的这种读者群,我怀疑这种可能性。反而将他的艺术介绍到国内是相对容易,因为艺术是比较直观。
木心不是前卫式艺术家,他很古典,像文艺复兴。他不是故意要模仿哪个人,也不是把自己想成是某个派别。他的绘画有点像他的文学,就是他在脑子里把很多东西都融合起来,没有历史、中西的沟壑,然后揉在一起它自然就发生了,有点像作诗的感觉。
文革对文学作品的毁灭是一场"屠杀"
对任何的书的毁坏,还有对于作品的毁坏,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比毁坏人的生命更加深刻,因为这些知识书籍绘画,它是人的精神的结晶。把这些东西毁坏了,那等于把人最纯洁的,最结晶的东西从历史上抹杀掉。所以用"屠杀"这个词肯定不是过分的。
木心生前写过一篇文章《木心:一个没有乡愿的流亡者》,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也是对自己发问。因为我是一个美术史家,所以在研究艺术家的时候,很自然地要把他们放在历史里去解释他们的作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专业上的方法论。但是在研究木心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被研究的这个艺术家是你朋友,而他自己拒绝被这样分析,那作为历史学家你是不应该强加于人的。
当他把自己都转化为一个非历史性存在的时候,这便是他的一个艺术和文学的目的——,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目的。所当时我用的方法就不是把木心放在某个年代,去研究他的作品,而是要懂谁是木心,他想做什么。但是现在木心已经是一个古人了,我觉得这两种方法都可以采用。一是我们还是要问:木心是谁?他的艺术有什么特殊性?他到底想做什么?但另一方面,他已经属于历史,我们现在肯定会把他放在历史里研究。
木心不把自己看成一个过去的一部分,不把自己看做"废墟"。因为"废墟"总是一个过去的东西,有时间的痕迹。他是这个与时俱在的一个人,他是不是属于过去,他肯定属于现在,他也说他也可能属于将来,所以他是把自己看成一个和时间一起流动的人。
木心对故乡没有情感和期盼
我用"没有乡愿的流亡者"去形容木心,其实是故意的跳出一般的意思。他首先是一个流浪者,甚至原来在国内是。他好像没有根的一个人,他不断的在走。"没有乡愿"就是没有对故乡的情感和期盼,或者就是不谈。他是一个超出绝对意义的流浪者,他流浪变成他的艺术,变成一种生活状态。
如果我们把中国,或者大陆的文学圈定位为一个局的话,木心应该算是局外人。即便是在美国的文学圈,他也是局外的,是绝对的局外,就是对于所有的文化或者国界来说,他都是局外的。但他同时又在更大的局里,一个人类文化,艺术的局内。他是在一个更高层意义的局内,但是在低层他就很安于局外的角色。这种局外的角色绝对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人生经历很难和他的作品联系上,他在写天马行空的东西。这是他一种选择——,选择做一个局外的艺术家。其实真正艺术家永远是局外的,卷进去圈子的成不了艺术家。
我觉得随着木心的这种"归来",他会慢慢的在更大程度上被理解。有时候要承认一个很特殊的人的精神价值,艺术价值,不一定从派别的角度去考虑,他的光芒他的语言就是财富。木心不会变成一个流派——,既不必要,他也不想那样做。所以我们要承认他的价值,以及在世界艺术史上的存在。
-
牛龙菲:木心的遗憾也是世上所有天才的遗憾
时间:2015年11月13日 地点:乌镇 讲述:牛龙菲 采访:何可人
因缘和合,曾经的文学"局外人"——木心,如今"回归"了。
其中最重要的因缘,就是木心有陈丹青这个学生。尊师爱道,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可惜如今古风不再。现在学生对老师全心全意的爱戴、敬仰、推崇、宣传,已经少见,但还有这样的人和事。比如朱天文对她的老师胡兰成,叶嘉莹对她的老师顾随。陈丹青对他的老师木心。
一个天才,要由另外一个天才来认识。木心这个天才要陈丹青这个天才认识;顾随这个天才要叶嘉莹这个天才认识;胡兰成这个天才要朱天文这个天才认识。一般人见了胡兰成可能唯恐避之不及;一般人见了顾随可能会认为不过是一个旧式的、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老夫子;一般人见了木心可能会觉得不过就是一个上海老克拉,但是陈丹青独具慧眼,他不遗余力的宣传木心,这是最关键的因缘。
几十年来,叶嘉莹先生一直保存着听顾随先生讲课的笔记,不管如何颠沛流离。她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房子可以丢,家具衣服都可以丢,但这本笔记不能丢,丢了就永远找不回来。一直到前几年回国的时候,叶嘉莹先生才把这份笔记交给了顾随的后人,由顾随后人出版。陈丹青先生也一样,把几本听木心讲课的笔记一直保存在身边,最后发表出版。
有叶嘉莹先生对顾随先生几十年的师生情谊,和对老师笔记的珍重,顾随文学的造诣、诗学的造诣,才慢慢被我们知道。同样,木心先生能被世人知道,陈丹青先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当然不能忘记,这里还有陈向宏先生的远见卓识、魄力才干。
司马迁《史记》说,经典名著,要"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名山"过去一般理解为"深山老林"。其实,并非如此。"名山"是指有一定人文内涵的文庙或佛寺的藏经阁这种地方。
"副在京师",是要在一个文化中心保留文脉。这是经典名著能被后人接受的重要前提。如果木心这些东西都丢了,那他能不能"回归"、能不能被接受、尴尬不尴尬的种种问题都将不复存在。所幸,有陈向宏和陈丹青,木心这些东西还都还在这里。
天才一定要有自己的知己,有了这样的知己,任凭世事如何变换,任凭局势如何险恶,都还会有一线生机。如果没有知己,天才的光芒就会被遮掩,天才的成就也可能会被后世慢慢遗忘。历史上这样被遗忘的天才一定还有许多!我相信除了我们现在知道的老子、柏拉图等等,恐怕还会有一些被历史帷幕淹没的天才。这些天才,由于因缘不能和合,不被我们知道,不被我们了解。
知音难得。木心的遗憾恐怕是世界上所有天才的遗憾,所有的天才都缺少知音。我们现在不大讲天才,一般都是讲群体、群众,说是"要有群众观点"。木心说:"群众没有观点"。只有天才才能了解天才,一个天才需要另外一个天才把他推举出来。
我力图成为木心先生的知音,但是每个人都有才情、学识、阅历、修养的局限。能不能真正成为木心的知音,不由我说了算,也不由我的愿望来决定,要看我的努力,看我的造化,看我的禀赋,能不能到那一步。如果能到那一步,也许会是木心的知音。
多数人比较欣赏木心的文采章华。木心的遣词造句,的确非常巧妙。但木心自己则说:"别人煽情,我煽智。"木心的哲思智慧,比较难以理解。我对此,格外关注。木心是哲性的诗人,也是诗性的哲人。《诗经演》,就有许多木心式的哲言。
木心《诗经演》说:"大哲无侣"。伟大的哲人,没有友朋,没有行侣。木心不但断言"大哲无侣",而且放言"始作俑者,乐其无后。" "乐其无后",比"大哲无侣"更狠。
木心很推崇老子,他说老子是世界第一大智者,像老子这个品级的哲人很难有知己的友朋、行侣。甚至可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没有知音。木心,算是老子某一个方面的知音。
"大哲无侣",木心的尴尬也在于此。
不过,木心还有另一句话:"徯我后兮,后来其苏。""苏",就是"复苏"。他期待着后世有一个文艺复兴。
这句话不要理解为木心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和知己。也许,几十年以后,几百年以后,甚至几千年以后,陆续会有那么一个一个的知己出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能会有那么几个木心的知音出来。未可预料,上帝会给我们多少个木心的知音?也不知道上帝会给我们什么品级的木心知音?一切都在未可预料之中。
我欣赏木心的,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他的美文。他对汉语之美的发掘,可以说到了很高的境地。胡兰成的也是美文,但是胡兰成的美文跟木心的美文不一样。胡兰成更有人间气,而木心更有贵族气、仙气。
第二,木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我很欣赏:他不声张,默默地逐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在《热读木心——微型文艺复兴》那篇文章里说:他是植物性的。他不是动物性的,他不是像狮子一样的咆哮,他不是这样。他是植物性的生长,慢慢长,慢慢长,最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
陈巨源:国外对木心的好评缘于宣传炒作
时间:2015年11月19日 地点:乌镇 讲述:陈巨源 采访:杜鑫茂
我是1963年左右认识木心的,那时候文革还没开始。应该说,在木心生前跟他保持联系时间最长的只剩我了。
在我认识木心之前,王元鼎跟木心都是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的非正式职工。他们每天到公司拿稿子,然后回去画,算计件工资。他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穿着打扮都很洋派。因为我跟王元鼎是画画的朋友,他就把木心介绍给我认识。他说:"介绍你认识一个我很崇拜的高人,叫孙牧心。"
要见木心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就在上海新亚大酒店请他吃饭。在饭局上,木心侃侃而谈,引经据典,饭局上的人都对他十分佩服。我就这样跟木心结识了,之后他经常到我家里来聊天,有时候也一起到别的朋友家里聚会,听他讲古今中外的奇闻异事,讲林风眠的故事。
文革时因为木心被定为"五类分子",大家跟他来往都不是很自由,有要很多避讳。那时候我们大多是研究艺术的,所以跟木心在一起时一般讨论艺术。文革期间话不能乱讲,如果几个人在小房间里讲不三不四的话,很容易就被揪出来,相互之前出卖的情况是常有的。所以谈艺术,喝酒就没有问题。我们一般都听木心讲,就像他的学生一样。
他的绘画技法说穿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把油墨涂在纸上,用另一块东西粘上去然后拉下来,就完成了。但是要控制它像山水就有一定的技巧。我以前也会做,但没有他做的好。
木心之所以会变"局外人",就是因为他长期被定为"五类分子",无法正常生活。他跟外界接触很少,所以他想的东西跟写的东西都是跟别人不一样,他看的都是国外的,古代的,而不是大家熟悉的本土文化。最终造成他的这种"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局外"的身份从他的作品就可以看出来。能够归类到特定文学艺术类别的就是"局内人",没办法归类的就是"局外的"。木心虽然作为"局外人",但他的作品依然能打动人,这就是他的特别之处。
木心在出国前夕,我们还经常在他家里一起喝酒,我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但是他的单位《美化生活》杂志社在他走了以后才知道。木心到美国以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2007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乌镇旅游公司的一个报道,说当地很多文化名人,有茅盾也有木心,我才得知木心回来了。于是,我立刻写信给乌镇旅游公司,他们很快就跟我取得联系,安排我到乌镇来见木心。我们来的那天,木心家里做了很多菜。我们一起吃饭,回忆了很多往事。他感叹说我们都老了,我那时候68岁,他说他已经80多岁了。
之后我跟木心就一直有电话联系,他说住在乌镇朋友来往不方便,希望我在上海给他找一个居所。我跟他说,"你在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房子,要在上海找这么大的房子很困难。"这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木心逝世几年了,很多报刊每年会发纪念文章,但是在文学界里很多人对木心不了解,很难评价他。很多人觉得很木心很神秘,但为什么国外对他评价那么高,国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其实都是因为宣传的,都是炒作,要先让大众熟悉。尤其散文是很难评价的,假如是一个著名作家写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当做宝贝来看。
如今,随着木心回到中国,他的书也在陆续出版。木心"回归"到国人的视野当中,不过年纪大的读者还是不太能接受他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跟一般的当代文学不一样,看不太懂。但反而有很多年轻人对木心产生浓厚的兴趣。
-
曹立伟:特殊国情下,木心这种私人性艺术很罕见
时间:2015年11月14日 地点:乌镇 讲述:曹立伟 采访:杜鑫茂上世纪80年代末,木心在纽约开讲文学课期间,他的房子租约到期。我那时刚好在纽约购置新居,就跟他说你过来,先住下再慢慢找。后来别人都说我把"文艺复兴"请到家里,这个说法让我惭愧,"文艺复兴"进来了,可是我自己却没复兴起来。
木心是看上去很"弱"的人,可是又是一个生存力顽强的人,各种苦难坎坷,他都熬过来了。这个也映照了他对老子对"弱"的赞美。他有一次讲,"你看老子对孔子张开无牙的嘴,意思是说,牙齿硬吧,没了,舌头软吧,还在"。他开玩笑说,"你要不活到两百岁,能叫老子吗?"。他认为自己是晚成的艺术家,所以他觉得要写出作品,首先得活下来,活得久,这是一个前提。为了活下来,他采取了一种"弱"的策略。

木心:"黑"是与人同归于尽的颜色
木心的画绝对不是简单重复中国山水画的优雅、闲逸、悠远的那一套,绝不是模拟重复古人的风景精神,他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他的绘画风貌的形成也是多源的,不仅仅就是从中国传统那里来,你如果留心的话,他的画里有许多西方传统的元素,此外是整体布局和透视,你看他根据需要,分别取焦点透视和散点透视,他的艺术是多源多维并存的。
我曾经写过他的对于黑暗的凝视,说那个黑暗不一定是伦理的,但肯定是审美的。这次我在木心美术馆里面看到他有那么几句关于黑色的话,如此直白坦荡,他说:"黑是与人同归于尽的一个颜色,一个绝望的颜色",说的太好了!在他的山水画里,中国山水画的精神性得到复活,只是这种"活"的精神内核是木心自己的,是他自我的精神呈示。
一个艺术家的画如果没有特点,签十个名也没有用。木心的画辨识度非常高,不用签字别人就知道这是艺术家的,甚至不一定要知道木心这个名字。
所谓的纯粹的"私密性",我想不是他后来突然形成的,他少年时期的诗里就有,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譬如说我要说一段官话,你马上就知道你跟我有距离,但是我说的是只有朋友之间才能听到话,那我们的距离就近了。艺术是艺术家最有灵性和真挚的领域,那肯定是内在的。私密性实际上也反映的是你内心是否坦诚,跟别人的距离有多远。
在木心的眼里,艺术是魔术性的。所谓魔术性就是进退裕如,不可预测。 木心说塞尚对他影响十年,其实何止十年。塞尚作为美术史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大家都从他身上都得到惠泽。塞尚艺术是比较核心的,不仅在他的表现形式。如果仅仅讲形式的话,塞尚的形式不一定就是塞尚的独创,因为既然造型艺术史已有这么久了,会有很多散逸的"塞尚"不时显现,我想,任何某一种形式,某一种规律不大会无中生有的。木心讲塞尚对他的影响,是有感而发,然而从木心的山水画本身来讲,他没有受到塞尚的任何的局限,他的绘画从形式上有点像中国传统画,有"塞尚",但后来消失了,或者已经隐藏起来了。
任何一个成熟艺术都有他的辨识度,也就是被重复的东西,一个要打引号的"套路",一种固定的模式。但如果把套路作为终极目的话,这就是"臼"。但是你如果把套路作为一个媒介,那么"它"也为你表达自己提供了一个工具。
新经验让木心保持对生活的好奇心
我有一个设想,假如我掉到水里去了,岸上站着我父亲和木心。如果我又浮到水面,看到他们两个人,我会从我父亲的眼光,看到对我的安全的关怀。但木心,他会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并祝贺我终于浮上来了。他会对我的经验感到好奇,就是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是怎么浮上来的。
所以他喜欢纪德也是因为这样,他说纪德就像一个潜水员,潜水下去以后回来,纪德不大说话的,你得问他,他才会告诉你一部分。这是一个对新经验的好奇心,比如他跟我们讲过,他说我看了几个电影,那个小偷偷完东西以后都要在那儿尿尿的。为什么都是偷完东西尿尿,不是偷之前尿尿,这是有原因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释放紧张感吧,或者是别的什么,但原因是次要的,只是"偷完东西都尿尿"这件事本身有意思,一种好奇。
即便历史重写 木心依然会选择当"局外人"
在他后期作品里,常出现"窖藏"两个字,以前没有出现过。这跟他个人的写作经验密切相关,一个年轻的作者很难说出这点,只有经历丰富的,上些年纪的艺术家,才可能有这样的体验和感悟。这和年轻艺术家创作不大一样,年轻勇猛稚嫩,虽"瓜熟蒂落",但也有瓜不熟也蒂落的,但味道就不一样了,同样的道理落在一个具体的艺术家身上,也许就是不要急于求成。他有一句话:"原来是我着急,命运不着急,后来命运着急了我又不着急了,因为我有我的脾气",这就是注重时间的磨炼和淬火。
我觉得木心这种"局外人"的身份,有时势的原因,但更是他的选择。有些艺术家跟社会,跟现实保持距离,但也有很多艺术家不是,所以有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局外"的,一类是"局内"的,那么木心是"局"的。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即便历史可以重写,我想他依然会保持这种"局外人"的身份。
随着木心的"归来",他的绘画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欣赏和理解。他似乎正在重复历史上的某些艺术家的经历和遭遇。艺术有很多类,有时尚的,有游戏性的,有魔术性的等等。木心的艺术有非常强的个人性。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情下,具有如此私人性的艺术不常见。也正是因为少见才会给人一种陌生感,甚至是距离感。所以读者和观众刚开始接触木心的艺术时,可能会有距离感,觉得他是"局外人",但我想这种情况会慢慢改变。
-
李静:木心的归来是他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
时间:2015年11月16日 地点:乌镇 讲述:李静 采访:何可人导语:适值新文化运动百年,凤凰文化通过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联系到其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再复,围绕“启蒙、革命、文学”进行了一次仓促、粗陋而又意犹未尽的独家访问。再复先生对于采访极为认真,不仅拉来了老友李泽厚共同参与,还亲笔致谢采访者并附上自己对于标题的建议。经整理,凤凰文化现将访问内容编辑成系列,连续三天呈现读者。

有人说,木心先生是文学的局外人。我觉得,木心是"文学界"的局外人,却并非"文学"的局外人。
在木心纪念馆里,我见到有一块木心自己题写的匾额,叫"卧东怀西之堂",这表明了木心对自我处境的看法。哪怕身在中国、东方,他仍然在怀想着西方那种个人的充分自由,那种精神源泉的丰富性。
木心对中国,对西方的认同,有自己的取舍。木心的归来,可以说是给中国人的一个礼物。他晚年回到中国,把他的作品——无论是文学的还是美术的作品——带回来,这是对我们当下空间里的读者和观众的滋养。
"文学"的局外人和"文学界"的局外人,一字之差其实是反映了木心在中国文学史绕不开的问题:他被接受的程度。
文学界这个词,它指的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现在有一种体制化的倾向。文学圈它是由比如作协,以及大家相互熟悉的作家群此类形成的。木心显然不属于这个圈子的,所以可以说他是中国文学界一个"局外人"。但木心绝对是文学之内的人。
木心往往被人看作美文作家,这并不太公平。美文写作是稍微有一点才华的人就可以做到的事。木心不止于此,尽管他的文字的确唯美,但他还抵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哲性的层面。而且木心是用一种非常轻松的,具象的语言抵达到了哲学本质层面。
木心所用的语言多为譬喻和象征。他的一个词可能象征一个世界,他把几个世界非常轻松地缝合在一起,放在你面前,如果你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会觉得这是一具很漂亮的画,但是如果你意识到他这个词背后象征一个世界模型,你会知道他把这个模型给你勾勒出来了。
木心最初震惊我的一个俳句是"寂寞无过呆看凯撒大帝在儿童公园骑木马"。你会知道凯撒大帝象征着什么。儿童公园、骑木马,这同样是一些象征性的词,还有"寂寞无过旁观"。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就是木心想表达的一种非常阔达的心情:一个人,正在旁观一个废黜的权力者以及他非常童真的行为。这其中多少个层次,多么复杂的情绪!但木心在一句话里表达了。
所以我觉得木心在汉语层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他在最小的单位里表达了最复杂的含义。他用排句这个形式做了自己的探索和成就,他让汉语在单位面积里实现了最大程度的艺术化和哲学化,他把俳句这种形式发展得非常成熟。当今汉语越来越碎片和粗糙,如果你钻进到木心的俳句里,沉浸到他里面去的话,会看到完全另外一番风景——这是木心开发了汉语的潜力。
我有篇文章,标题来自木心的俳句——"你是含苞待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的确很好的概括了木心的状态。含苞欲放是一个生命的,绿色生命的状态。就像歌德说的,"生命是绿色的,理论之树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木心把这个所谓灰色的理论之树和常青的生命之树合在了一起。
如果没有一个哲学性的视野,那艺术家是不成熟的,或者说是肤浅的。但如果一味的沉浸在哲学的层面,没有能力呈现一个生命的世界的话,那这个艺术家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木心强调"含苞欲放的哲学家",就是在表明艺术的本质。这是木心的一个理想,而且我觉得他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理想。
-
刘瑞琳:木心始终是在生活中,但是又在生活外
时间:2015年11月14日 地点:乌镇 讲述:刘瑞琳 采访:胡涛
第一次见到木心先生,是2007年的5月份。陈丹青和我们出版社工作人员,一行四个人到乌镇来见先生,谈他的作品系列出版的事宜。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到了乌镇已经大概傍晚了,就直接去他居住的晚晴小筑。他确实跟别人不一样,见到他的时候,我感到跟他之间有差距有差距,不是一个简单的差距。但依然觉得他这个人又神秘又亲切,仿佛他像个艺术品一样,可能很不理解,可能只能看到他的表象。但他又很亲切,就是像个长者,笑咪咪的,而且调皮,愿意给你讲笑话,偶尔给你开个玩笑。
木心先生自己很在乎读者。第二次我来看先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晚晴小筑里,有两个晚上可以长谈。第一个晚上,他见到我们就一直问:"什么人在读我的书?"、"都有哪些反映?"我们挑选了一些读者来信,记者提问,包括在一些活动现场木心读者提出的问题反馈给他。当说到有很多读者很喜欢他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他在窃喜。他说他一直想写一本书,就叫《论读者》。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居然说他已经开始写了,写很多字了。当然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仔细地整理他的遗稿。
我们曾试图鼓励木心先生直接跟读者见面。在2010年,我们举办第一场"理想国"沙龙,希望邀请先生来北京。陈丹青也帮我们联系先生,一开始他一度答应,于是我们密切地安排准备。但是后来他还是以身体原因推辞了。那次机会错失,我就知道,可能他再也不能这样与读者对话了。
这次木心美术馆开幕,"理想国"在网上招募50位读者来乌镇,一个小时就报名就报满了。读者年龄段从60后到90后——每个年龄段都有木心的读者。木心的读者都是关注内在精神生活的人,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和木心之间惺惺相惜。
作为木心先生的出版人,我最大的安慰是做了最该做的事情,我非常幸运。陈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介绍木心先生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犹豫,就想马上把木心推出来,送到读者面前。
我认为,木心以"局外人"的姿态的归来,这是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始终是在生活中,但是又在生活外。这既是他个性的体现——他作为这个时代的"局外人",也是他有意追求的结果。每个人在过着一种现实的生活,木心要远离这个现实,而这种远离是他有能力,自觉的去远离,他做到了。从一个出版方的角度,这个"局外人归来"的过程也同时是读者逐渐发现木心的过程。对于出版者来说,要把他的作品尽可能地呈现到读者面前,创造机会让读者与木心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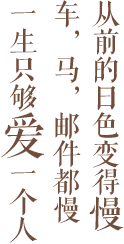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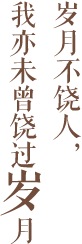

 扫一扫,转发精美H5到手机
扫一扫,转发精美H5到手机
编导:杜鑫茂 制片人:胡涛 摄像:马赛 郭澄子
设计:尹志 冯婧 制作:马慧霞 剪辑/包装:杨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