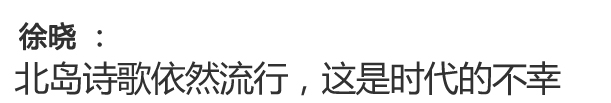
他对社会的批评,现在仍然是现实的,并没有过时。仍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喜欢,可以从中得到力量。
 1《今天》诗刊的诞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80年代的思想解放很不彻底
1《今天》诗刊的诞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80年代的思想解放很不彻底 2我入狱期间目睹太多中国农村情杀 我不喜欢把这作为炫耀资本
2我入狱期间目睹太多中国农村情杀 我不喜欢把这作为炫耀资本 3我这代人对两性的理解有强烈英雄主义情节 最深刻关系并不是最舒适关系
3我这代人对两性的理解有强烈英雄主义情节 最深刻关系并不是最舒适关系 4北岛对自己早期诗歌很否定 但今天依然流行是社会不幸
4北岛对自己早期诗歌很否定 但今天依然流行是社会不幸
人物背景:徐晓,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人:于一爽
徐晓
《今天》的诞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凤凰网文化:从《今天》开始吧?
徐晓:这个有点老生常谈,我不是特别想谈,其实我当时在《今天》是一个特别次要的角色,有点像现在的志愿者。
凤凰网文化:但是你有一个见证的意义。
徐晓:从见证这个角度当然是没错,对我个人来讲,不管我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它影响了我的生活和我的道路。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青春期放大了幻觉?
徐晓:这是任何一代人都会有的一种现象。前几年跟一个外国朋友聊起文革,他们说看到很多人写文章赞美文革,我说有人赞美文革吗,他还说出了具体的人名,比如提到徐友渔、秦晖,我说你搞错了吧,他们不是在赞美文革,他们是在回忆他们自己的青春。
但是说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今天》到底有多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比如当时民主墙兴起。那我相信《今天》的诞生,也是因为这些人受了这样的一种启发。

《今天》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在人格上有意放大《半生为人》里的一些角色?
徐晓:这和你写那个人物时候的心理、情感有关,我觉得我还是在尽可能真实写。有些话我可能写得不是那么清楚或者仔细,比如说我写赵一凡,我们后来的那种疏远。我说我们俩是他对,还是我对,或者是他更对,还是我更对,就是说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些反思。
凤凰网文化:再版的时候,有没有把这种反思的结果加进去。
徐晓:我得尊重我自己的写作历史,我不能一篇文章觉得它不够的时候,就随时把它给改写完整。
凤凰网文化:什么叫完整?
徐晓:把它的美好和它的阴暗,它的缺陷和它的完美,都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讲,这真的不是我的目的,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人物背景:徐晓,1979年起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和散文。1982年至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作为《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徐晓是历史的见证人,更是历史的参与者。以下为对话实录:
对话人:于一爽
徐晓
《今天》的诞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凤凰网文化:从《今天》开始吧?
徐晓:这个有点老生常谈,我不是特别想谈,其实我当时在《今天》是一个特别次要的角色,有点像现在的志愿者。
凤凰网文化:但是你有一个见证的意义。
徐晓:从见证这个角度当然是没错,对我个人来讲,不管我在《今天》是什么角色,它影响了我的生活和我的道路。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青春期放大了幻觉?
徐晓:这是任何一代人都会有的一种现象。前几年跟一个外国朋友聊起文革,他们说看到很多人写文章赞美文革,我说有人赞美文革吗,他还说出了具体的人名,比如提到徐友渔、秦晖,我说你搞错了吧,他们不是在赞美文革,他们是在回忆他们自己的青春。
但是说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今天》到底有多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合力的结果,比如当时民主墙兴起。那我相信《今天》的诞生,也是因为这些人受了这样的一种启发。

《今天》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在人格上有意放大《半生为人》里的一些角色?
徐晓:这和你写那个人物时候的心理、情感有关,我觉得我还是在尽可能真实写。有些话我可能写得不是那么清楚或者仔细,比如说我写赵一凡,我们后来的那种疏远。我说我们俩是他对,还是我对,或者是他更对,还是我更对,就是说实际上这里面是有一些反思。
凤凰网文化:再版的时候,有没有把这种反思的结果加进去。
徐晓:我得尊重我自己的写作历史,我不能一篇文章觉得它不够的时候,就随时把它给改写完整。
凤凰网文化:什么叫完整?
徐晓:把它的美好和它的阴暗,它的缺陷和它的完美,都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写作来讲,这真的不是我的目的,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赵一凡跟我说:自尊心有时是没用的

赵一凡
凤凰网文化:赵一凡到底是谁?
徐晓:对我是把他当成精神导师。我那个时候在小学当老师,我们当老师的地方就是人艺,人艺旁边有一个胡同,现在叫报房胡同,文革的时候它叫瑞金路十九条。我当年在那儿工作,从那儿骑车过一条马路就是演乐胡同。那边有一个电影院叫做工人俱乐部,然后演乐胡同进去以后再往左边一拐就是前拐弯胡同,就是赵一凡的家,前拐弯胡同的这个口接着演乐胡同,那边那个口,出了口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这么一个关联。
所以我从我们那个小学到赵一凡家去,骑车大概就是五分钟到十分钟的距离。那个时候也没别的事儿,也没有什么负担,然后上放了学就往那儿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去,我是通过我当时一个男朋友认识的赵一凡,那个男朋友跟赵一凡家就是住隔壁。可能去赵一凡那儿三次,我才能见到他一次,就是那种吸引力特别大。
比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跟赵一凡争论什么呢,当时正在宣传一个英雄。那会儿是1971年,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教室里头挂着那个人的照片,现在我有点记不起来他那个英雄事迹,好像是拉了一头战马,然后那头战马他要是不拉的话,就把那个铁路就给挡上了,好像就是拯救了一列火车,然后我们聊起人到底是自私还是不自私,我记得特别清楚赵一凡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做那个咱们看来把他说成是那种英雄行为,但实际上他是为自己好。因为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会很难过。他是出于一种自私的目的做了一件无私的事情,这个观点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太新颖了。
其实后来我也读了霍尼雪斯基的《怎么办》,他那里面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当时我17岁,我们天天在学校被宣传学雷锋,是有一点颠覆的感觉。比如赵一凡还跟我讲,人的自尊心是很没用的,当然后来我发现赵一凡真的是挺没有自尊心的。他常常为别人做很多事情。换成我们,我就想,我为什么为你做,为你做完了你还说我不好,你还反而来责备我。
我不喜欢把监狱经历当作炫耀资本
凤凰网文化:书里写:有天夜里有人喊你去楼下听电话,然后你就入狱了。
徐晓:其实当时大概在我入狱半年之前就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被人盯上了。
凤凰网文化:整个经历对你来说代表了什么?
徐晓:我觉得这种经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都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如果你把这种东西给它稀释成一种调侃,甚至是一种酷的行为,或者是一种值得炫耀的东西,我觉得很不合适.它永远给我带来一种痛感。也正是这种痛感让我还有勇气说真话,拒绝我该拒绝的东西。
因为我当时不懂被调查了意味着什么,你也想象不到你可以进监狱,现在中国人可能整天在说监狱的事儿,说得都已经没有神秘感了。但是当年你想想我身边没有那么多人进监狱,你自己又年轻,家里又是良民。
凤凰网文化:有没有直接的原因导致他们下手?
徐晓:不知道,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案子涉及到好几个省的人,所以后来当时公安部把它定性为是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叫做第四国际,把它当成一个大案来办的。那我的逮捕证上都是华国锋签的字,华国锋是当时的公安部的部长。当时把我从宿舍楼叫下来,进到那个传达室那个小房子里,让我签字的时候我根本就没看那个逮捕证,完全就吓呆了,就不知道去看一下,也不会问说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头脑就完全一片空白,哭都没哭,就不会哭了。
凤凰网文化:你父母怎么办当时?
徐晓: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那个情景,我父母才跟我说,我被抓的当天晚上实际上我们家就被抄得底儿朝天,就是公安局在抓我的同时,因为他不能提前走漏风声,如果先去了我们家可能我就会跑掉了,就是在他们想象中,总之这是一个同步的行动。那后来就是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带着好几个大灯去的我们家,都把那个灯支起来照着,这样可以搜查得特别的仔细,连床板都给掀起来,连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水箱的盖都会爬上去打开去看看。
所以1978年我接手《今天》的时候,我们家就为这个事情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我妈就说你都已经坐过一次牢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然后你现在又参与这种事情,你也许又会去坐牢。先不说你自己那么年轻,别的女孩子在这个时候都在打扮自己,在谈恋爱,然后你在这儿干这么危险的事情,然后你还可能影响到所有的家里人。这是我后来特别深的一个记忆。那你说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当时是一点没有愧疚的,就是投身到了这个事业。这是我后来回忆起来,我一点儿没有矛盾,我就觉得这是我该干的事儿,我愿意干这件事儿,你们不应该阻止我。我当时没有那种说我应该孝顺,我应该出于孝顺而放下这件事情。我有过这个反思,就是对我父母的这个反思,所以我承担的压力我不会抱怨,我觉得我该承担。就是你把他生出来了,他不是为你而活的,但是他是你的亲人,你该承担的你就得承担,这就是亲人,那当然我要是这么说我的父母为我承担的,显得我特别的没有心肝。但是我现在愿意用这种话,对我儿子说。
监狱里我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大量情杀
凤凰网文化:你书里写了好多儿媳妇杀公公的事儿?
徐晓:对,因为女监嘛,那个时候文革的时候,除了政治犯,大概也就是一点这种。就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经济犯罪。那时候社会治安实际上比现在好,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去溜门撬锁。
凤凰网文化:这就涉及到一个当时的农村现状。
徐晓:对,我挺吃惊的,因为在那之前我对农村一点儿都不了解,因为我父母都是大城市出来的,我家没有什么农民的亲戚。我自己也从来没下过乡,等于在监狱里接触那几个杀人犯都是农村人,我才知道,而且一直就是中国人很保守。
比如说有一个老太太我没有跟他同监,但是我可以听到她,因为她老吵闹,好像是已经六、七十岁了,她经常大声的说话。然后我的那个监狱就有一个,我那个号儿里曾经就有一个跟她同一号儿的人,说这个老太太一共结过七次婚,她最后把她的老公给杀了,她说她完全没有想到需要受这么大的惩罚,有可能给她判死刑的这样一个惩罚。第一感觉到,她完全没有法制的观念,就是杀人需要被制裁。然后我还知道了实际上中国的农村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保守,那关系都很混乱。
凤凰网文化:都是免费的、当代的、中国的题材。
徐晓:然后还有那一个案子就是基督教的一个案子,那个印象也特别深。当时说是在北京的房山有一个28岁的女人,这个女人自称是圣母的徽号,特别奇怪,就有好多人都信她。而且这个好多人里有的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然后我认识的这个老太太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辈子没有结过婚,就是一个工人。那个年轻的三十多岁的女的呢,也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她们都信那个教,然后她们去保护28岁的那个,因为政府要抓那个人,她们去保护她。
她们给我讲那个场景,就是说她们人摞人的,把这个人给保护在中间,就是不让你政府的人把她抓走.其中就有一个小女孩,也是我那个同案给我讲的说,她老在监狱里头喊,她一喊我们就能听到,一听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她告诉我说她是一个中学生。说她妈妈也在这个监狱里,也被抓起来,也是同案,但是她妈妈悔改了,就是我们那个监狱里过一段有一个广播大会,就是改宽严大会。它会宣布一些因为认罪态度好,而所谓从宽处理的典型,还会宣布一些从严的典型,当时呢就在那个广播里宣布了她妈妈,说因为她妈妈认罪揭发别人,然后就对她妈妈好像就是要释放,就是宽待处理,然后她这个女儿就开始大骂她妈妈。后来就给她戴上脚镣了,给她戴上背铐了。哗啦、哗啦就给她拉走了,那我不知道她的命运,她是不是真的被杀了,我不知道。
凤凰网文化:因为你有面对媒体的话语权,那我们只能放大你的这种经历。
徐晓:对,那天我还跟年轻人说,我说你们不用羡慕这种生活,如果你让我自己选择的话,我肯定也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你让我重过一遍,我肯定受不了,我不愿意。只是因为那你生命中,这种因素出现了,出现了其实你面临一个你怎么对待的问题,俗话说所谓苦难就是财富是吧。
政治犯不会考虑国家大事 觉得“这辈子完了”
凤凰网文化:想过把这种生活写成小说吗?
徐晓:也许吧。那个人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特别清楚,因为她就是挨着我睡。然后她有一天晚上自己自杀,然后我一睁眼,睡眼朦胧的,队长把那个铁门哗一开那就吵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她的样子特别可怕,眼睛都凸出来了,她自己拿一个裤腰带在勒自己,然后我们就长久的在讨论,人能不能自己把自己勒死,就是自己用手把自己勒死。
1976年地震的时候,下着大雨,然后他们在外面弄了一个地震棚,他们那个地震棚是只有棚子没有门,然后我们都能从这个,趴着窗户能看见他们,然后我们就把被子垛起来,看看外边,然后就告诉屋里面的人,说他们今天吃扁豆,要不然就说谁谁谁今天穿一件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有外号,就是我们给他们起的都有外号。他们统一的,我们都管叫队长,他们也不告诉我他们姓什么、叫什么。那我们就只能给他们起外号。然后我们就会说谁谁谁,今天穿一个色的衣服,穿一双什么色的鞋。
凤凰网文化:你说当时能看到《人民日报》?你觉得外面的世界还和你有关吗?
徐晓: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的视野,你能从报纸上读出很多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那时候我还什么都不懂事,你可以想想二十岁的孩子,就是现在他也不见得会对整个的国家的形势什么都那么关注。我觉得没有那些所谓的真正的政治犯去琢磨那些事儿。
凤凰网文化:爱情呢?
徐晓:没有爱情。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
凤凰网文化:当时是什么条件下知道可以出来了?
徐晓:就是突然一下开门,说你出来,收拾你的东西,这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出去了,一种是被判刑了。现在还有一个上诉期,那个时候我们没听说过。
凤凰网文化: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儿做什么?
徐晓:我爸我妈给我做了一大桌子菜,但是我吃不下去,虽然在里面的时候天天都想。
凤凰网文化:很多人后来又见过吗?
徐晓:没有。就是我出来以后只见过一个狱友,就是我说的那个天主教徒,她没有结过婚,没有亲人,她后来到了福利医院,再后来她就去世了。
凤凰网文化:当时赵一凡呢?
徐晓:他比我先出来几天。
凤凰网文化:你去找他了?
徐晓:我也不敢找他去了,我们两个人互相写信,不久我们就开始跑这个平反的事儿。因为他腿脚不方便嘛,就是我一个人去跑,一直到1978年下半年。
凤凰网文化:你后悔吗?
徐晓:因为现在也不知道是我牵连他,还是他牵连我,除非我们可以拿到当年的档案。
我对我丈夫的付出是美德也是绑架
凤凰网文化:讲讲你的前夫。
徐晓:不是特别想讲。
凤凰网文化:比我们能看到的还复杂?
徐晓:每个人的感情都特别复杂,并不是说我特别复杂。
凤凰网文化:你在爱情上有一点英雄主义情结?
徐晓: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有一点儿。所谓的英雄主义情结里面有一个元素就是牺牲,都觉得牺牲是一种美德。
凤凰网文化:牺牲是不是为了争取更大的回报。
徐晓:反正我一直觉得在感情中付出也是一种享受。
凤凰网文化:这是自我暗示?
徐晓:在情感关系中女人常常抱怨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其实这是对别人的一种绑架。我控制自己不这么想。
凤凰网文化: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付出一定是他要的吗?
徐晓:不是,但是这个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最深刻的关系往往不是最好的关系
凤凰网文化:如果他还活着会怎么样?
徐晓:我想过,如果那个时候的我是现在的我,也许我们的关系会更好,但是更好不证明更深刻。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理解生死。
徐晓:我怕我活得长。我从来不戒烟。
凤凰网文化:但是怎么面对自己的孩子。
徐晓: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写一个遗书,我就坐在这个这,我就死掉了,我的孩子三天、四天不回家,那他发现的时候会不会内疚后半生。
北岛诗歌依然流行 是社会不幸
凤凰网文化:聊聊北岛咱们。
徐晓:我在坐牢之前,我在赵一凡那儿看到过一本诗集就是手抄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首诗就是那个《金色的小河》,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坐牢出来以后,1977年认识的北岛,也是通过赵一凡,才知道他就是那本诗集的作者。
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理解纯文学,如果存在这个概念的话?
徐晓:我觉得事实上纯文学是不存在的。我觉得这种纯,你从哪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纯文学,如果你说我不参与政治,那什么叫政治?是吧。不要把政治仅仅看作是一种组织行动,或者是一种权力斗争,我觉得那是一个传统的政治概念,在现代生活中政治就是我要发表我这个诗,我要争取我发表这个诗的权利,这本身就是政治。你维护自己特别个人的权利,它本身就已经是政治了,那你说我不要政治,那你可以不维护你自己的权利吗,不可以。我觉得事实上这种意义上的所谓纯文学,那你的诗里面你光写风花雪月吗,事实上今天的诗,包括北岛本人的诗是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的。特别著名的那个《回答》大家都知道,那么多人被引用的那个话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然后后来我们就有两年的时间在一起办《今天》,经常会有很多接触,当然两年之后《今天》就停了,后来到八十年代北岛就走了。大概是80年代初他就开始出国,然后又回来,来来走走。
凤凰网文化:当时出国的政治要求是什么。
徐晓:他是1989年出去,1989年4月份应该是,一直到九十年代后期吧,才有了一点联系,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先生生病的时候,他托人带来过信,还有一点钱。北岛这一点特别好,谁要是有个困难,他马上就想到我是不是该给点钱。
凤凰网文化:这很能说明他是什么人。
徐晓:我觉得他生活中挺实际的,特别不像诗人,甚至他有一点古板,我们给他起外号叫老拧骨。
凤凰网文化: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是毛的吗。其实他再用意识形态反对意识形态。
徐晓:实际上他对他自己前期的诗是采取否定态度的。自己觉得那都是一种革命话语的延续。但是我是觉得因为他写的那个诗里面表达的思想,他对那个社会的批评,现在仍然是现实的,并没有过时。
凤凰网文化:这二十多年什么变了,什么没变?
徐晓:它整个社会制度没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岛的诗仍然有魅力,仍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喜欢,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力量,这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幸。
中国出版审查制度特别因人而异
凤凰网文化:其实后来这几年你还出了北岛的书?
徐晓:2004年他第一次回国,我们聚会。北岛在国外写了很多散文,大家都认为北岛的书是不能出的,他人都不能自由出入,书怎么可能出呢。但是我就觉得什么事儿都是可以试的嘛。
凤凰网文化:突破口在哪儿?
徐晓:我这个人没什么自我限定。
凤凰网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被警告?
徐晓:这个不会给我个人警告,因为我不是出版社,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标准,其实这个制度特别因人而异,有的出版社它需要通过一个上级机构来审查,有的出版社自己就是终审,那么也就是说你那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如果同意了这本书就出来了。那为什么那么多书出不来呢,那个总编辑是自律的,越是把这个权力给他,他越自律。就是说我们的那种文化机构,太体制化了,太官僚化了,就是说不是文化人,而是当官的人,是官员,官员就要保自己的乌纱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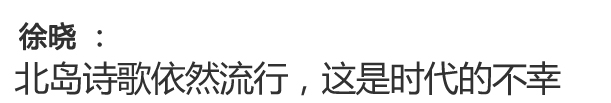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