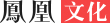刘再复:我和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不是否定革命
导语:适值新文化运动百年,凤凰文化通过任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剑梅教授,联系到其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再复,围绕“启蒙、革命、文学”进行了一次仓促、粗陋而又意犹未尽的独家访问。再复先生对于采访极为认真,不仅拉来了老友李泽厚共同参与,还亲笔致谢采访者并附上自己对于标题的建议。经整理,凤凰文化现将访问内容编辑成系列,连续三天呈现读者。
刘再复,这是一个在一九八零年代“文化热”潮流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以文学研究之笔写下对于科学、民主、自由的反思,高扬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努力呼唤重新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与那个时期所有灵魂复苏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刘再复用自己的勤奋和勇气弥补着“十年无成”的历史缺憾,又凭借着天生的才气和深刻的思索,一跃成为彼时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一九八九年,刘再复辞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去国离乡,开始了“漂泊者”的生涯。这是一次自我流放,也是一次自觉地探索。
一九九五年,刘再复与同样旅居美国的老友李泽厚携手出版长篇对话录《告别革命》。这对叱咤中国八十年代思想史的“双子星”再一次爆发出巨大能量,其“告别革命”的宣言就像一声惊雷炸响了整个华人知识界甚至政治层面,无论认同还是否定,任何人都无法忽视这一观点和理论的存在。出版二十年,这本书成了改良、革命与近代化等相关学术课题中绕不开的经典。
在争议面前,刘再复一再强调“告别革命”是有具体历史语境的,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都不能轻易评论,他和李泽厚当年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末风波两个历史事件,必须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运动进行反思。同时他还强调革命的概念被应用得太广泛,需要做出详细明确的界定:他们要告别的是法国式的暴力革命,而非英国式的“光荣革命”。并且这种告别并不是否认革命的历史正义性,而是认为这种性质的革命,不应当成为历史的唯一选择,即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刘再复告诉凤凰文化:“我们的《告别革命》只是在‘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这两种基本方式上作出选择,即认为阶级、阶层矛盾永远都会有,但选择‘阶级调和’的办法比选择‘阶级革命’办法好。”
去国二十余载,刘再复始终不曾停止对中国的观察和思考,就像他始终不曾改变的福建乡音。并且由于“他乡观照”的间离性,刘再复的所思所述都获得了更多的客观性和独到性。2004年,作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的刘再复首次回到大陆,到广州进行学术演讲,引起国内知识界极大轰动,成为了当年的文化公共事件之一。一时间,“刘再复热”被再度提起。

刘再复(图片来自网络)
(提问:张弘,约访、采写:徐鹏远)
我和李泽厚要告别的是法式暴力革命,而非英式光荣革命
凤凰文化:您和李泽厚先生曾经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当年反响巨大。现在,你们提倡的“改良优于革命”基本已经成为共识。可以说,你们的前瞻性已经得到了印证。请问,当时的想法从何而来?
刘再复:二十年前提出“告别革命”的命题有两个历史背景: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八十年代末的风波。我们当时就认为,“文革”确实是“继续革命”,其结果是民族生活的重心转到无休止的阶级斗争,而在我们展开对话的前前后后时民族生活重心变化了,转向和平建设,我们希望这种历史性转变应当成为全民的“自觉”。不过,李泽厚先生早在七十年代,他的著作就高度评价康有为,积极肯定改良思路。而且比较过“法国派”和“英国派”,对后者很肯定,对前者却提出怀疑,李泽厚在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论严复”。文中就说:“严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了解比改良派任何其他人更为深入,他把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以个人为社会单位,等等,看作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指出,民主政治也只是‘自由’的产物。这是典型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强调平等的法国派民主主义政治思想有所不同。在中国,前者为改良派所主张,后者为革命派所信奉。然而,以‘自由贸易’为旗号的英国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确建立了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更为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其优越性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他是中国学界最早对革命和“辛亥革命”在理论上提出疑义的学者。文化大革命很像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的大规模的群众暴烈行动,全国各地都在“夺权”,都在实行“群众专政”,干部、知识分子、教师等随时都可能被送上“精神断头台”,整个社会只有情绪与混乱,没有生活、没有理性,斯文扫地、法治扫地、尊严扫地。回顾文化大革命,我们觉得有必要作一次认真反省。以对历史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在整个对话与整理的过程中,我一直带着一个大问号:“八亿人民老是斗,行吗?”回应的是“八亿人民不斗行吗?”。
此外,我们那时刚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风波,也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对此,我们也作了反省:中国要好起来,只能通过改良、协商、谈判等柔性、维新性办法,不能通过“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种刚性的对抗性方式。总之,是赞成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赞成自下而上的革命。
对于学生运动,李泽厚先生和我的态度也不完全相同,他只是同情,并不支持。因为他一直不赞成这种大规模的对抗性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总是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一九九二年他出国,但每年回国一次,对中国一直抱着“谨慎乐观”的态度。我讲这些只是说明,李先生怀疑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大规模群众激进对抗运动,其态度是一贯的,《告别革命》只是一次理论上较完整的表述。
凤凰文化:你们所说的“告别革命”应该是指法国大革命开创的传统,以及由俄国、中国继承的共产革命。但是,革命还有另一种传统,就是由英国、美国所开创的自由革命。这种革命,以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建立自由、民主、宪政、法治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其烈度和范围都很有限。对于这种自由革命,您持何种态度?
刘再复:革命这个概念被应用得太广泛了,谁都可以脱口而出地列出“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文化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艺术革命”、“民族革命”、“种族革命”、“土地革命”等,甚至可以说出“生态革命”、“服装革命”、“医药革命”、“食品革命”等等。所以对“革命”一词,首先要作界定。我和李泽厚先生在《告别革命》中,一再说明,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即包括三要素:一是暴力行为;二是具有大规模群众性对抗;三是以推翻现政权为目标。我们要告别的革命,是此种性质的革命,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革命。
但我们的告别,并不是否认它的历史正义性,而是认为这种性质的革命,不应当成为历史的唯一选择,即不是历史的必由之路。就以辛亥革命而言,它也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当时的改良派主张和立宪派主张,其实也可作为一种选择。不能说维新派与立宪派的选择就是走向历史的死胡同。我们的老朋友、老院长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就表述过这种观点。
《告别革命》首先给我国的近代史提供一种新的认识。至于对世界上的各种革命,我们确实认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实际上是改良、妥协)比1789的法国革命更可取,更值得借鉴。我们要告别的是法国式的暴力革命,而非英国式的“光荣革命”。《告别革命》对法国大革命开创的近代革命传统,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中国,这是比较早的反思。当然,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也经历过暴力的流血革命,例如1649年初的那场革命,革命主体就宣布国王为“暴君、卖国贼、杀人犯、国家公敌”,并把他送上断头台。然而,这种砍头革命手段在1688年的光荣变革中就不再被采用了。即“革命对象”国王詹姆斯只是逃亡法国,换上的是他的弟弟奥兰治亲王威廉和他的妻子玛丽,避免了流血战争。我们倒是比较欣赏这种方式的政治变动。从十七世纪末至今,英国的社会比较安宁稳定,就因为他们采取君主立宪制,告别了砍杀国王的暴力革命。英国这种选择,比较保守,但对人民和对国家都有益。我个人在思想上虽有自由主义倾向,但政治上则比较保守,不喜欢“翻烧饼”式的激进主义。
继续革命还是告别革命,只能从大多数的人民利益出发
凤凰文化:对于1989年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波兰革命,以及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变化,您怎么看?还有就是21世纪之后,革命出现了新的命名和形式,人们称之为“颜色革命”,以您的国际视野,颜色革命与以前的革命有哪些异同?您对此持何种态度?
刘再复:革命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都难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情景去评论。我和李先生提出“告别革命”,其语境是已经处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国,但不意味一切革命都可以告别。我觉得要看两条:第一,本身的历史传统。比如中国的古代是王朝政制,一家独裁,所以往往无革命便难以另寻出路,故倡言革命的“孟子”列入了四书。而西方多数发达国家有法治传统,对革命便评价不高,对革命的血腥性也格外警惕。第二,具体的情形。如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结果是平和的,就算导致后来的分离,人民也是接受的。但阿拉伯颜色革命,就革不如不革。它们是大国政治一手导演的,小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不管是主张“继续革命”,还是主张“告别革命”,所有的思考只能从大多数的人民利益出发。李泽厚先生和我所作的判断和选择,着眼点也是多数人民的利益和人类的共同进步。
关于这个问题,那天我请教了李泽厚先生。他说,“天鹅绒”本身就是一种柔性意象,“天鹅绒革命”实际上只是改革,不是我们所指涉的那种暴力革命。而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情况更为复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情况也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大规模的对抗性的群众运动。对于这种革命的性质与后果,我是深深怀疑的。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在《告别革命》中讲历史主义,就是讲具体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要的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笼统地讲“革命”或把革命抽象化,没有意义。有些批评“告别革命”的文章,离开语境,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论是在近代改良思潮与革命思潮相互对应的历史语境中进行,也没有注意我们所定义的“革命”是什么,而是把革命概念泛化与抽象化。批评者没有受过分析哲学的洗礼,对日常用语不作分析。所以其论述和批评都显得含混不清,不得要领,过于笼统。
凤凰文化: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良的道路被堵塞,而皇族内阁的出台成了最后的诱因。如果既得利益集团拒绝民众的呼吁,继续垄断权力予取予夺,这种情况下的革命是否具有了正当性与合法性?综合您自己的切身体验,阅读和思考,以及这些年来的国际视野,您认为革命的边界在哪里?
刘再复:关于这两个问题,李泽厚先生也发表了意见。什么叫做“正当性”?什么叫做“合法性”?什么叫做“边界”?这些词又涉及其各种不同的含义,首先必须辨析、辨明、界定清楚。还有,说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良的道路被堵塞,这也很不清楚。什么叫做“堵塞”?谁“堵塞”?是慈禧太后吗?她并未堵塞。慈禧的确打击过维新派,但庚子事变后她吸取了教训,并不堵塞改革,可以说,清末的改革还相当顺畅。如果慈禧早死十年,戊戍运动就可能成功,光绪维新就可能实现。如果慈禧晚死十年,改革也可能成功,革命派未必能够胜利。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否则就不会演出皇族内阁铁路国有这种种愚蠢闹剧。如果慈禧不死,光绪也没有随之死亡,中国的情况就会很不相同。康有为很聪明也很清醒,他知道光绪年轻,可以借天子以革新,实现其改良之路,没想到光绪却突然死了,这完全是历史偶然性。暴力革命并非历史必然,就算文革也不是历史的必然。
我记录下李先生的意见,你可参考。他这么一说,我就省得回答了。不过,那天他讲完后,我觉得他强调谈论革命概念需要“分析哲学”这一点对我有启发。一是唯有分析,我们才能找到讨论的真问题,即首先定义好“革命”,才能避免无谓的争论;二是具体的情况确实需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的《告别革命》只是在“阶级斗争”(革命乃是指极端性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这两种基本方式上作出选择,即认为阶级、阶层矛盾永远都会有,但选择“阶级调和”的办法比选择“阶级革命”办法好。调和并非没有斗争,但不是大规模的流血斗争。
版权声明:《年代访》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