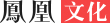陈丹青:木心一边被神化 一边仍然被看不起
导语:“我58岁经历了木心的死,这是一堂课。”2013年,陈丹青接受凤凰文化专访,对着镜头袒露出他的生死课题。2年后,在乌镇西栅甫落成的木心美术馆里,62岁的陈丹青再次接受凤凰文化的专访。这一次他知道,木心已入梦。
几十年桀骜名声在外,眼前的陈丹青却让我们觉出他已多了一份让灵魂安身生立命的平和,不肯再事事沾身,轻易针砭。他将自己定义为木心美术馆的建设者,虔诚求问“我怎么能够做的更好一点?”他希望自己从谈论木心的高台上退隐,对记者和颜道:“你们多听听其他人讲木心”。
“这是他的命”,木心一课经年,陈丹青明白世上有许多珍重事比爱憎更大。建设,承担,守住,传续……陈丹青说“我是个老人了,我可以平静的做这些事。”

陈丹青在木心美术馆开幕现场
我这十来年做的事情都是全新的经验
凤凰网文化:木心美术馆开馆仪式上,你几乎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献给了合作伙伴,比如陈向宏(注:乌镇旅游公司总经理)、建筑师、室内设计师、还有工人,你为什么把自己“隐藏”起来?
陈丹青:是这样啊,没有他们我怎么可能,我一个人怎么可能弄一个美术馆,不可能的,我只是很幸运,总是被放到台前,然后好像是我做的。其实不是我做的,我怎么可能建一个美术馆?根本不可能。
凤凰网文化:两年前你谈到这个美术馆的建设的时候,你说乌镇本来就有一个茅盾先生的故居博物馆,以及木心的纪念馆,但是关于美术馆,你说“我喜欢做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比较了解木心先生的美学风格,但是我又不能问他,自己决定,我想会很简洁,东西不会很多。”今天已经落成了这个美术馆,如今看来是否到达你的预期?
陈丹青:我对美术馆实际上没有预期,因为我没有做过美术馆,我甚至想象不出来这个美术馆是什么样子,这是第一。第二,美术馆是两位美国公司的设计师设计的,馆内部分是那位法国的法比安设计的。但等他们弄好以后,我跑进去看,我觉得他们虽然跟木心不熟,法比安甚至从来没见过木心,但还是从他的作品上一下子抓住了木心的一个特质,就是简约、少、尽量空灵、整洁,尤其是他们选的这个底色,他们选了五块灰色,作为整个美术馆各个馆的基调,再加上清水混凝土的那个浅灰色。我很惊讶,因为木心在纽约自己墙上挂的画,后面放的衬板就是这五块灰色,我非常奇怪他们不知道这个,可他们选了这个颜色。所以我相信一个人的作品,如果交给一个对的艺术家、设计家,他真的不必认识这个人。我真的很感谢这三位设计家。
凤凰网文化:整个美术馆最体现你个人意志的地方在哪里?除了跟建筑设计师的沟通之外,你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陈丹青:我的作用到后来就很有限了,很有限了,就是我手上这些手稿,这些画作,我能做的就是把他分类到各个馆区,按照他们的设计尽量能够放到一个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状态,但一定不是我个人的,说实话,让我个人来做,一个空的馆给我,让我来弄,我不会弄的比现在还好,可能会有很多遗憾,因为毕竟我不是专业的做空间设计的人,我做平面还可以,我只能在单面的墙上怎么把这些东西挂得大约好看一些,但是在一些三维的有通道,有四面墙,这么一个空间里面,我其实经验很有限。所以我从那个法比安身上学到很多,学到很多,他可能会影响我以后的设计,如果可以说我也可以设计的话。
当然最难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墙面上的字是由我决定,所以我可能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细细地翻找木心留下来的遗作,我这次用的词语和纪念馆不一样,纪念馆的词语大部分是从他已发表的著作里找出来的,可是这一次几乎全部都是在他晚年遗稿当中找出来的,就东一句、西一句,序厅是一部分,两个画廊是一部分。然后还有文学墙,文学墙我也选择了大概上百句,最后选出目前的大概二三十句吧。
凤凰网文化:以馆长的身份,还要去处理很多琐碎的事情,要打交道,还要去跟国外的机构去沟通,还要复原木心的想法,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全新的一个经验?
陈丹青:其实我不是一个馆长,如果是个馆长不应该一个字一个字计较,应该下面有专业的人在给他做,但我没有办法,我这是个干活的人,同时身兼一个所谓馆长,我对这个馆将来怎么运作,结构怎么弄,我到现在都没有静下来想过,这大半年主要就是把这个馆能够开成,下一步就要想这些事情了。
我这十来年做的事情,都是全新的经验,比方我从来没出过书,然后我也没有参加过比方说奥运会这种策划,然后我也没有做过《局部》的视频节目,然后我也没有做过纪念馆和美术馆,这都是新的经验。就是不知道做的好不好,我自以为尽了力,但我很乐意听到批评啊,告诉我怎么能够做的更好一点,哪里做错了,通常到我这样子很难听到人跟我说真话。

木心
不是我一个人在用情 是一群年轻人在用情
凤凰网文化:中国美术馆的副馆长张子康先生说话很实在,他说对这个木心美术馆的感受就是四个字:用心、用情,区别于其他的美术馆。你怎么理解他所说的“用心、用情”?
陈丹青:我很谢谢他这个评价,因为用心的活我相信在其他美术馆一定有,一定有看得出来,但是不一定有情,有情的话我也看到过,可是不知道怎么用心。你比方中国遍地都有老画家、老作家的纪念馆、美术馆都有的,那么做这个馆的人,有些就是家属、孩子、晚辈在那做,有些是门生,或者是当地政府,其实也都放了感情在里面,非常想做好,但是所谓用心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技术要求,而且要很懂怎么用心才会出什么效果。所以子康是不但实在,而且他很懂,他知道一个馆怎么叫做用心,怎么叫做用情。
你看我这些团队里的年轻人,其中有四个都是木心的晚年的小朋友,他们对木心的感情跟我还不太一样,等于是爷爷。我在很多小事情上很惊讶,他们是这么在乎这个老头子,比我要在乎,真的,这个情是我都没有的,我都没有的。你要是知道这里面都有说不完的细节,比方什么东西拿出去,不拿出去,小代(注:木心生前照料者,乌镇员工)的意见非常强烈,坚持不可以拿出去,我们得说服他。纪念馆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我请他把眼镜、钢笔放在那的时候,他很久不说话,我知道他不愿意拿出来,因为这是他每天经手的事情,他要伺候先生,他不愿意拿给大家看,那这个关他现在过了,他愿意拿出来了,可是每次取出来试着摆的时候,他的那种虔敬,那种担心,我不会像他那么担心,我是蛮粗鲁的人,我的细心是另外一种细心。所以这不是我一个人在用情,是一群年轻人在用情,包括那些没有见过木心的人,后来介入进来的,他会带进这个气氛里头去,他也会当件事情去做。
凤凰网文化:小代、小杨之前一直在照料木心先生,现在调到美术馆来,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陈丹青:是我的意思,因为我跟你说,所有老艺术家、老作家到晚年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底下的孩子或者是学生,他得找一个牢靠的、可靠的人交代后事,每个老艺术家都有。大家会认为我是木心最相信的一个人,而且木心临死把他的所有东西都交给我和陈向宏来处理,那么陈向宏没有得到木心一张纸片,除了写给他的一封信,他从来没给先生要过画,但是他成立了木心基金会,把画全部挪到基金会,然后造了个美术馆,把基金会的这些画全部放进去,这是他做的。
就是当初我是不是决定他们就是但问题是这只是我和向宏之间的事情,向宏今后能做,因为他工程上的事太多,他就等于对我很放心,这次纪念馆你来做,美术馆你来做,但问题是我只是一个人,我也要人帮忙的,木心要我帮忙,我也要人帮忙,那毫无疑问我在木心暮年看到这两个忠心耿耿的小伙子,我第一想到的就是他们。就是小代、小杨还有一位小匡(匡文兵),小匡也是决定性的人物,他是我的文学老师,就是我所有木心要查阅其他文学著作,要查阅,或者我弄错了,全是他在管,他几分钟就可以把正确的资料交给我。
对我来说,他们可遇不可求,可遇不可求,差不多在先生逝世的那个时候,他们俩像孤儿一样,我走的时候哭的非常伤心。我说你们不要吵架,他们就一直看着这个晚晴小筑(注:木心晚年定居地),一直等我回来开始做那个纪念馆,三间空房间,一个板凳,一个烟灰缸,一杯茶,然后小代就拿着尺开始量,一边量一边我就开始画图纸,就这样一件一件做起来。然后纪念馆做完我已经很放心了,你们跟我到美术馆,小代、小匡都是要走的人,他们在乌镇,小代待了十年了,小匡待了四年,他们正当年轻,当然要出去看世界,去找新的饭碗,我说你们走我不留你们,但你们帮我把美术馆做出来,他们做出来了,我一个人绝对做不了的。

木心美术馆
我终于梦到木心 我盼他“鬼魂归来”
凤凰网文化:昨天我们跟童明先生聊天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期待木心的那个鬼魂归来,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巴不得他鬼魂归来。你上次也对我说过,木心去世之后,反而总是梦不到他,也讲到所以中国会有鬼故事出来。很想知道两年又过去了,有没有梦到过木心?
陈丹青:我去年在维也纳梦到过他一次,4月份的时候,非常短,但是立刻就惊醒了,但是我梦到他的样子,包括他火化的时候,我看到他开门走出来,都是我跟他最多来往的那段时间,也就是60出头,不是他老了以后的样子。你们得经历过这个才会有感触,此前有个人告诉我他有好朋友走了,很想梦到他,很想他变成个鬼,然后见见他,我当时不会有体会,现在我有体会了,因为中国人说一个人死了,叫没有了,这个说的很好,他真的没有了,一个没有的东西人要找嘛,找不到就会你变成鬼也好。没有了。
凤凰网文化:你过去几年一直在忙木心美术馆的建设,单独去故居跟先生相处的时间还有吗?
陈丹青:那不会,我没有那么浪漫、伤感,没有,都是在做事情。尤其在做纪念馆的时候,我每天要在木心这个花园里面进进出出,一会就得去房间里去翻点东西,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没有,我相信我现在要是二三十岁,我可能会让自己扮演一个很哀伤的角色,现在我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就是我是个成人了,是个老人了,可以很平静地去做这些事情。
凤凰网文化:现在木心美术馆跟木心纪念馆都有了,而且分别位于乌镇的东西两栅,可不可以说木心先生已经真正安顿在乌镇了?
陈丹青:可以这么说,因为昨天巫鸿说了一句话,非常对,他说都是偶然嘛,命运嘛,一个艺术家一段历史可以完全消失,你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是一切真的都是天意,怎么会有一个乌镇的出现,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乌镇还没有改造,第一先生不会回来,就算回来后面的事情都不会发生。但现在都发生了,一东一西,一个纪念馆,一个美术馆,照老话来说所谓告慰在天之灵。但是先生也未必就是要这个,他晚年一直在想身前身后事,我想他最在乎的还是所谓壮志未酬,最在乎的是这个。我也亲眼看到他发昏以后,一个人就一生写的东西就扔下了,如果没有人保管,没有人把他收起来,你去想吧,二楼那个馆有两个大柜子,其中有一幅画是朝霞,我用在大广告上面,这是被他扔掉的一幅画,然后我问小代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有一堆纸要清扫,他就把他扔在那里,那小代看看不错,就拿回放回他的案子,他说怎么又捡回来,他说还好你别扔了,看看可以。过几天他有把它扔过去,还是幸亏小代收起来了,我把这个过程写在那个展墙上。
再有就是他烧过稿子,因为他们冬天是在一个火炉里取暖,就是楼上那个客厅,通常都是小杨在点火,然后他就跑回房间拿出一大摞,一张张往里扔,就烧掉了。据小代回忆大概2009年的样子,所以我这次专门布置了一个展柜,就是全是他的碎稿,很杂乱的碎稿,把它堆起来,其他都放得平平整整,经过选择,这个就无法选择了,因为他的写作很奇怪的,就是不标明日期,也不归档,不归类,就是杂处在一起。
两岸谈论木心 心态全不一样
凤凰网文化:台湾的陈英德先生重新激发了木心的创作,痖弦在《联合文学》创刊号上刊登他的文章、作品,为什么木心反而在台湾率先获得承认?
陈丹青:陈英德很有作用,当然第一个是陈英德,后来接着马上在纽约的其他报人立刻就发现这个人,然后就跟他要稿子。我记得的是《华侨日报》,还有香港的《中报》,还有美国的《世界日报》,还有《中国时报》,差不多这几家报纸在那几年里面,几乎每周都有木心的文章和诗刊登。重要的倒不是木心有稿子给他们,而是那是一个微妙的时刻,从1983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整个台湾解严,蛮微妙的一个时刻,这段日子里台湾绝大部分读书人不知道对岸的文学。当时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文学也还没有到那去,阿城当时也还没过去,阿城是到1984年、1985年《棋王》什么才介绍到台湾去,也是迅速就轰动。此前就有一个木心,陈英德就是第一个把稿子寄给痖弦的人,后来有《华侨日报》的副刊主编,也是寄过去,还有一个《中报》的曹又方,迅速就在那几年火起来了。
我想这里面一个是台湾的文学场有那么一个语境一直在,此前有张爱玲、金庸,所有你能想得到的这些作家,余光中,还有那些诗人,包括痖弦,这个文学活动没有断过。再有一个就是,隔绝这么久,当然很想知道对岸的人在做什么,我想木心是个特殊的例子,他正好出去了。这一段其实还需要有个人整理的,为什么在那段时间会有?所以你翻回去看看木心纪念专号第二集和第三集,你看一看就有一位叫刘道一的年轻人,他个人征集了大概有十多位文学人对木心的评价和回顾。其中有好几位在当年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现在他们变成岛内比较重要的作家、撰稿人、主编、诗人。就像木心讲的他的读者在长大,在成长,他们现在也才看清那段时间,尤其是痖弦给了这么特殊的版面,所谓散文个展,这个对他们自己岛内的作家都从来没有这样过,那其实是个传奇,很有意思的。
我相信除了刚刚改革开放前后这段时间,大陆对对岸的文艺特别感兴趣,像邓丽君、三毛、李敖,有一股台湾风吹过来,因为当时大陆刚刚过了文革,非常荒凉。但很快大陆自己的文学起来了,到了九十年代新世纪,大陆文学的量起来了,还有它的内容上非常丰富,而且立刻被世界各国翻译,那个时候一个比重就换过来了。那时候台湾开始关注大陆的文学,也陆陆续续请这些作家过去。但在这个当中,木心在那个时间点上,1983年到1990年左右密集地在台湾发表作品、出书。他在时间上跟大陆新文学起来是同步的,但是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当时很少大陆作家知道有一位上海出去的作者在台湾这样子火,除了极少数人能够在香港书市买到他的书,台湾版的书,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去年读了王鼎钧四部回忆录,他最后一部叫《文学江湖》,我才完整知道1950年以后国府退守台湾他们文坛发生的事情。
王鼎钧没讲到的后面一段,因为他也到美国去了。五、六、七三个十年过去以后,在八十年代,他们发现了木心,然后他们把木心抬起来,说大家看,我看了他前面三个十年,我觉得他在逻辑当中。但回到中国大陆,这个就不太可能,因为前三十年正好是所有民国老作家销声匿迹的时代,也是有数的几个无产阶级新作家起来的年代,而且在文革当中又被打倒。像写《金光大道》的那个浩然,还有写《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所有这些都在文革当中给灭了。所以不但跟传统文化的断层,跟五四也是个断层,跟1949年也是个断层,然后到八十年代才又有后来的事情发生。
那你返回去看台湾就不是这样,所以你只要对照一下台湾从痖弦,一直到这一代文学人在议论木心的时候,他在一个常态中议论,他也把他看成一个奇人,一个特殊的现象,一个阶段。但是他跟大陆在议论木心或者不议论木心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两岸的一个文学圈、文学人的一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凤凰网文化:所以从大陆来说,木心是一个错位的状态。
陈丹青:非常错位,但是他在台湾,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错位。他绝对不会想到他1948年、1949年之间去过的那个台湾,后来变成他文学的第一次呈现的区域,他绝对不会想到。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有耐心一直等到又过了二十多年,他是1986年在台湾出书,一直到2006年才在大陆出书,这些都构成他的文学生涯和中国的文学生态的戏剧性的一个关系,或者说戏剧性的没有发生关系。
木心有意躲开大陆文学圈 躲了一辈子
凤凰网文化:与此相对比的就是大陆这边的挖掘,竟然要靠一个艺术家来挖掘。所以我想问的就是,你昨天说木心跟中国文学界艺术届是毫无关系的,这个是不是对中国文艺界一种委婉的批评?
陈丹青:我不是一个批评,第一我没有资格批评,第二我要是说出这样的话,不是批评的意思,而是指出事情是这样的,而且他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你说中国的文学界他是指作协或者指所有现存的文学刊物和文学圈,木心真的跟他们没有关系,不是说他们不关注木心,是木心也不关注他们,是双向的。如果木心非常愿意跟这个圈子发生关系,他只要一回国,我相信文学刊物会对他开放,愿意他来供稿。可是2006年考察下来,他只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在《南方周末》,叫《鲁迅论》,此后他没有在任何的中国文学刊物发表过。如果他愿意会发表的,不一定有人关注,也不一定会持续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相信文学圈会接受他,如果他愿意交朋友也会的,我相信会有一些作家愿意去看他,陈村孙甘露就去看他。所以我只是告诉大家他真的没有关系,不是这边不理他,是他也不理这边。他不要入这个局,所以当我说这个的时候,没有意思说怪你们为什么不理他,不是这样的,应该问木心为什么不理他们,这个很有意思,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和非或者对和错,或者贬和褒,不是这个意思。
凤凰网文化:你个人推测,木心为什么“不理”?
陈丹青(沉默):你看他的写作就可以啊,他在语言上就不认同这样一个语言场,他只是躲开,我用不理可能有点严重了,他只是躲开,他躲开各种各样他也许不认同、也许不同道的那样一种区域,他躲了一辈子。
新人出来要么被闷死 要么被弄死
凤凰网文化:木心在你的“推销”下已经广为人知,但是直到今天,大陆文学界对于木心的文学价值是否有清晰的认定?
陈丹青:这个社会势利,最有意思的是,他不是张爱玲不是沈从文,这两个人给活埋了,然后被夏志清打捞出来, 可是木心活活就在我们面前,没人看得起他,什么了不起什么吹牛,怎么样的,看不起他。现在基本还是这样。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况,张爱玲出来十来岁,傅雷马上就叫了,谁就叫了,可现在没有这样的事情了,现在不要说一个老头子出来,一个年轻人出来,大家要么不吱声要么弄死他,就是这样。就不自信嘛,就没有文化的才会在那儿,一个正常的有文化的你去看好莱坞,好莱坞老的致敬死掉的,可是年轻人一波波上来,新人讲三代关系很正常,一直是这样下来,我们就都不吱声要么骂你要么笑你,要不不吱声,你要做的好的话他就不吱声,闷死你就这样,所以现在用不着上面弄死你,同行就弄死你。
凤凰网文化:对木心的“闷声不做响”,有出于忌妒的心理吗?
陈丹青:忌妒国外也有,人类就是个忌妒的种类,这个挺好,没关系。中国还不是忌妒,就他对自己不信任,他才会对别人那么敏感。中国从来都是这样,这30年来,这个现象越来越厉害,尤其这20年,就是稍微有好的人出来,他马上想到我怎么办,那我算什么,我已经名片上那么多带着这么多人出来,不是这样吗?
凤凰网文化:但你会看重文学批评吗?
陈丹青:我也不太看重文学批评,中国哪有什么文化批评,哪有争论文学批评,王朔大家骂他,那不叫批评。这个分析的当然也有,那王朔只是一个最特殊的例子,因为他也批评,他也叫骂,那文学界也只能骂他。但是你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例子,你告诉我还有谁,你敢批评的人已经很少了,可能哪个人敢批评,一定会有很多人骂他。但是那不叫批评。
我看重的倒是老百姓,所谓老百姓,就是木心说的潜流,就他不属于哪个学院,哪个机构,他就是一个一个的归起来,这个是最珍贵的。因为木心的有意思,他不在这这个版图里面,而且他不该在这个版图里面,为什么要放进去,现代文学史。我们看重的就是读者,没有什么一般不一般,就是只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读者,他在读你的书就可以了。随便你什么人,就纪念馆有一句话,木心说的,他说什么送邮件的,什么工人、农民,我想象的都是这些读者。
木心已经被神化和标签化
凤凰网文化:梁文道认为木心是局外人,他用局外人的视角写他这个文学史。但是木心已经回到了大陆,重回读者的视野当中了,你怎么看待他这种局外人的归来?对于中国文化而言,木心现在还是一个局外人吗?
陈丹青:对,是一个局外人,如果你定义这个一个局的话,局有一个边界、入口、出口,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木心还真的是一个局外人,而且他不再可能是一个局内人,对他本人来说,对他身体来说,因为他没有了。对他的作品来说,据我知道,比方说上海《小说月报》还是什么刊物,好像还有地方转载了他的《上海赋》什么这些,我没有准确的资料。我说实话不太关心这件事情,最有意思的我看到就是他是一个局外人,但是他又拥有很多读者,在他的文学能够拥有的读者数量上来说,已经超出我的意外,那么多年轻人会真的读他的书。今天上午我跟读者团见面,我多多少少有点以为年轻人来凑热闹,来高兴,但是等他们一个一个发言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是真心的,他们真的读过,有他们的解读。这是真的发生,没有人要他们非要去读,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认识木心的场合和状况都不一样,都蛮个人的方式忽然遇到他。比起那年葬礼遇到的又是另一拨人了,最年轻的是1997年的。
凤凰网文化:说木心是“局外人”,但是实际上他也在慢慢从一个所谓的小众的空间里面走向了大众。某一部分对文艺有一定需求的人,对精神生活有需求的人,他可能会木心会很感兴趣,我想知道这种所谓的流行,这种风潮是不是呼应了现在时代人们对于审美生活的一种需求,成为了一种标杆?
陈丹青:就是中国又多了一个作者,又多了一群这个作者的读者,就是这样。然后此外中国已有的作者和已有的读者,又多了一块出来,这一块有多大,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新的作者,一个很老的死掉的一个新的作者,有了一群对他有兴趣的读者,这就很好。我相信我们还是要摆脱一个思路,就是谁最好,谁有最多的读者,谁最畅销,我们应该告别这个时代了,所谓多元就是这个意思。
我相信在捷克不是每个人都读卡夫卡,德国不是每个人都读尼采或者海德格尔。我写过一篇文章《鲁迅的价值》,在正常的情况下鲁迅应该只是有有限的一些读者,很稳定的,在隔代的一直会有一群有限的读者,绝不是像我所看到的那样,到处都是鲁迅在文革当中,现在又没有人去读他。正常情况下像鲁迅那样的人,像木心这样的人,像卡夫卡、尼采这样的人,就是在他的母国只会拥有一小群读者,但是一直会有读者,这就对了。读得对不对,咱怎样解读,它自己会发生,或者自己会消失。
凤凰网文化:木心未来是否也会面对一种被神化、被标签化、被符号化这样一个情况?
陈丹青:他已经被神化、被符号化、被标签化,包括《从前慢》。他已经是这样了,我慢慢在期待他进入一个正常状态,就是人群中还是只有很少的一群人,但这群人你仔细看看其实又蛮多的,真心喜欢他,在读,就可以了。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什么时候来,你看美术馆开馆了,好像又是个大新闻,我相信很快会冷掉,会恢复常态。纪念馆开馆那天下着大雨,涌进涌出全是人,但现在纪念馆一年多以来,已经恢复一个常态,蛮稳定的一个数字,人其实不多,这样很好。美术馆将来也会这样,空荡荡的有那么几个人在看,我相信会这样。
木心和尼采一样 一定不是大众的
凤凰网文化:李劼说木心是一个幸存者,其次才是一个天才,而且他的幸存是双重的,既是生存意义上的,也是审美意义上的。那么在哀叹木心先生时遇不济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为这个幸存暗自庆幸,比如说他毕竟躲过了那个劫难,在生命意义上毕竟是存活下来了。
陈丹青:对,你要我毁灭,我不,他没有毁灭,他现在可以存在下去,有两个馆可以让他存在下去。有一部分人知道这个存在,而且珍惜这个存在,那就很好。有一天如果这个人群越来越少,那就应该是这样,或者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在世界上那么多文学家,那么多馆,你知道北京有个现代文学馆,那么多人在里面,可是我有一次去开会,门庭冷落,根本没有人。我问年轻人你们为什么不去,他们还很惊讶,不知道有这么个馆。可是当时是老舍的儿子,还有北京文学界一大群人很花了心血建起来的的。
所以我蛮相信杜尚所说的那句话,就是人们每过三十四年,会主动为一个被遗忘、被忽略的人平反。我相信这包括一群人,我相信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年轻人,一零后或者二零后说咱们去看看北京那个文学馆,它是这样此起彼伏的一个状态。我2010年的时候去俄罗斯看托尔斯泰的故居,到他的坟上去,我去了我才忽然想起来,他正好死了一百年,他是1910年死的。可是我回来以后读到《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专题报道,就是托尔斯泰的专题,说俄国很平静,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纪念。我读了真是很会心,这就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文学家,照中国的说法可以光照千秋的,可是他一百年以后,我相信一定有人纪念他。但是这个媒体很平静,这是一个媒体的时代。
再有就是今年九月我到德国去借这批文献,我就去了瑙姆堡,然后在附近有一个尼采的故居,尼采小时候的教堂,里头有尼采一家人的坟墓,包括他的坟墓。一个人都没有,安安静静,两个欧元一个入场券,很小的,就像农村房子一样,里头是他的小小的纪念馆。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埃森博格先生,这次他也到了乌镇,非常兴奋,他一个人在管瑙姆堡的尼采故居和文献档案中心。他告诉我一个很动人的事情就是1990年两德刚刚开始统一的那一年,是尼采逝世九十周年,尼采是1900年死的。他是其中一个青年,现在他四十出头,当时才二十来岁,他就去尼采那个墓前看,结果发现有二十多个青年,来自德国各地,还记得尼采,去看他。结果他们彼此遭遇了,就觉得很有意思,坐在尼采的墓旁,大树下面谈了一整天,我还看到了那个照片。
我忽然明白过来,太对了,它一定不是大众的,一定不是流行的,一定是在接近被遗忘的状态中,可是还有人记得他,最朴素的方式就是在他逝世九十周年,到墓前去看他,然后彼此发现还有别人跟他一样,他们变成了一个不严格的一个像小小的协会那样,以后每年就在那见面,这其中就有一个傻X,就是埃森博尔格,他就接下了这个事情,像政府申请了资金,盖起了那个文献馆,又拨了一个房子就在尼采家隔壁。
而另一个事情更有意思,我不断地到每一个场合我都会问到,叔本华的故居在哪里,他的纪念馆在哪里,每个人都回答我,有些说不知道,有些说没有。后来我就说你们还记得他吗?他们想了一会说,Yes,德国人好像忘记他了,叔本华启示了尼采,而对我来说木心这么爱尼采,我更爱叔本华,因为尼采的书我不太看得懂,我也看不下去,我不是木心的好学生,在这方面。我这回让尼采跟木心见面了,其实我自己更喜欢叔本华的东西,可是居然在德国已经忘了他了。我在瑙姆堡借给我的八个肖像当中,我立刻发现了有一个叔本华的版画肖像,我说这是叔本华,他说你还能认得出来,有一个小小的叔本华协会,也是有一群人定期聚会的。他们看到这个,认不出这个是叔本华。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但是我觉得这事最对的,这是一个很孤单的不容易被理解的,不容易被认同的一个作者,他在身后,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木心回国依然在流亡
凤凰网文化:木心美术馆今后的展出计划包括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等,对于中国的艺术场馆来说,我觉得这是蛮新的一种做法,就跟评论家对木心的评论是一样的,就是他在不断地返回,比如说从希腊里面去攫取一种美出来,包括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你现在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作“艺术的复返”吗?
陈丹青:不是复返,这应该是一个常态,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更多的是这些当代艺术馆,我大约了解他们在做什么展览。我发现整体性的一个情况,大抵没有历史感,所谓历史感就是你今天这一堆展览,今天八零后也好,六零后也好,有个展览在那,他跟过去是什么关系,他跟这一切发生之前发生的事和人是什么关系,我不太看得到。可是在木心身上一切的一切都跟过去有关系,他自己说没有尼采不会有我,他说我今天知道的是别人告诉我我才知道的。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念这些书,蛮少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忠实他年轻时候念过的书。这其实应该是一个常态,这样的想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在国外看来的。他们的美术馆会展文献,会展除了艺术家之外的其他人的文献,我们很少这样做。要是做也就是档案馆、文物局或者博物馆在做,蛮生僻的、蛮冷的、蛮学术的,不会变成一个像今天你们看到的这样一个展览方式。
你说有多重要吗?也就是几片纸放在那,可是从王国维介绍尼采,一直到李大钊、胡适、鲁迅谈尼采。一百多年以来,不管怎么样,尼采本人的手记到了中国。那天藏品晚上的车到了,汉莎公司运来了,我们如临大敌,把它迎进来,我全部都录下来了,如幻似真。他的东西起箱子拿出来一件一件再清点,放在桌子上,我们专门弄了一间房间来放尼采的东西。我也不懂尼采,我更不是尼采的读者,不要说研究者,但是我很高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它跟木心碰头了。到此为止更深的意思我谈不上,至少我在墙上罗列了从王国维一直到木心这一百年以来,中国有人谈过尼采,有人这样的谈过尼采。德国人也很惊讶,原来我们在远东、在中国是这么回事,就像我们也会很惊讶老子原来是德国学哲学的青年曾经人手一册的《道德经》在那念,我们也会有想法。
凤凰网文化:李劼还说过,尼采最后发疯,拜伦战死在沙场,托尔斯泰是晚年出走,这些跟木心有些精神联结的人,用这种方式去谢世,那么他认为木心的人生到了最后这个阶段,毕竟没有那么决绝。那么在你看来,晚年木心回归乌镇的这个选择,是不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陈丹青:你要对比你刚才提到这些人的一个下场和一个ending,一个结尾,木心是一个非常东方式的方式,他跟自己和解了。因为照他的意思就是“孔雀西北飞,志若无神州”,这句话很重的,中国艺术家说不出这句话,非常重的一句话。故乡、故国、母国,可是他说了这句话。另外他还说了这样一句,我用在我去年纪念他的文章里面,“从中国出发向世界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浪到中国故乡”。他把回来仍然看作是流亡或者流浪,你怎么解读这个话?从现实层面来说,他没有选择,因为他没有家庭,独身,我也一直担心他一直老下去怎么办,但是真的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他的家乡在找他,在叫他回来,请他回来。有这么一个陈向宏,我们大家认了一个爷爷,在我的解读就是他跟自己的立场和解了,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