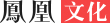阿乙:我的这条命为文学而准备

阿乙(单向空间供图)
阿乙坐在嘉宾席上,一张脸圆成了巴尔扎克。
那是吃激素的副作用,相比从前照片上一头卷发、下巴尖瘦的艾国柱,阿乙嘲笑如今的自己“脑满肠肥”。
生病之前的阿乙有着圣徒式的写作追求,每天24小时的主题都是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4小时写作,剩下20小时都在焦虑,甚至做梦的时候都在解决写作问题。年轻,狂热,不知身体危险,以为扛得住一切,直到肺部出现问题,入院,治疗,出院,反复三次,前后半年时间。
度过一劫的阿乙,将自己的病因归结为不要命的写作,生病成为他噩梦般的记忆,“我印象很深刻,从我这里动手术进去,后来提着引流管,提着一个桶子,桶子都是你的血浆。”
刚出院的时候,阿乙一度怀疑自己再也写不下去,准备告别文坛,然而天性里的写作基因,加上那份为了文学事业建功立业的虚荣心,让他在两个月后又提起了笔。
现在的阿乙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生活好青年,从前不舍昼夜的文学青年变成了固执的早起派,自己做菜、买菜,按时吃药、锻炼。每天的写作任务全部在上午11点前完成,雷打不动。如果11点以后还在写作,阿乙会骂自己“贪婪”。
每天几百字到两千字不等,一点点积累下来,数量蔚为可观。这本新作《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是他2011年至今写的随笔文字与小叙事,有相当数量是生病后创作的篇章。
书中文字简洁、犀利、准确,相比小说,随笔文字更像是他的私货,更真诚也更冷静。如他的朋友郑超所说,随笔比小说更能直探一个作家的机心。
死亡、疾病、身体……这些词语频繁地成为阿乙写作的主题。一场病痛过后,命运神秘地睁开了第三只眼。在一篇名为《等待》的短文中,阿乙写道,“(老人)朗诵进行至一半时,双扇门被悄悄推开,穿着呢子料制服的死神走进来,摘下手套,坐在空荡荡的最后一排,一言不发地端详着他。”
得了“疑病症”的阿乙说,“我是很害怕再回到那种状态,接近崩溃的状态。”
他痛惜好友朝格图和孙仲旭的死,觉得“人间痛失好青年”,而自己由于懦弱而继续活着,“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长一点,更健康一点,看到蓝天次数更多一点,如果死的话谁记得你。”
既然活着,就要写作。从基层警察到媒体编辑再到知名作家,阿乙一路收获赞誉。他承认卡夫卡和加缪对他写作的巨大影响,卡夫卡片段式的短篇小说甚至成为他写作的入门教材,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但丁等相继进入视野,阿乙“见异思迁”,通向伟大的高阶,层层叠叠。阿乙的志向和野心,也水涨船高。
他不再仅仅执着于县城经验、警察生活,而从自身延伸向这个焦虑的时代。他渴望在文学史上建功立业,渴望为英雄人物立传,他说,我这条命是为了最重要的事情来准备的,过去是为了某个女人,现在是为了文学事业。
但是阿乙焦虑的,却是他所身处的时代。“小镇青年”如今已经不再恐惧大都市生活,他恐惧的对象,变成了当下无聊而平庸的生活。
“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太好描写的时代,因为人处在一个比较犬儒的状态,中国现在人的麻木的状态比较多,现在的人无论多么优秀,或者是个吃货,都已经抵挡不了对拍照,对食物的分享,或者是别的方面的诱惑。在朋友圈或者在微博里面我们不会谈尼采,不会谈康德,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读过。”
阿乙在谈论吃喝的时代氛围中,发现了人的意义的丧失。他更愿意写英雄的悲剧,不愿意写懦夫的平庸生活。小人物的挣扎?阿乙写了太多,他现在的目标,是史诗,是英雄。他想回瑞昌老家,从过去朋友身上汲取养分,写10个精彩的警察故事,这或许承载着他的一部分英雄情结。
许知远说,“他(阿乙)有一种对于更崇高情感的孜孜追求,这种虔诚在我们这代人中已相当罕见,我们普遍深陷于被现世承认的诱惑里。”
普鲁斯特的卧床成就了《追忆似水年华》,身体限制之下的阿乙,也许就此获得一个观察世界的绝佳视角。“人间是个欢场,偶尔屠刀落下”,挨过一刀的阿乙,这份清醒与冷冽化为生命的自觉,将加深他的文学底色。
在这个意义上,一场病痛,也许反而成为上帝给阿乙的神秘馈赠。
(对话人:阿乙、吴琦 撰文&整理:凤凰文化胡涛
注:对话节选自2015年9月13日阿乙新作《阳光猛烈,万物显形》分享会,北京单向空间与青橙文化授权凤凰文化发布。)
言论精选:
“我曾经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写下去了,是出院之后,出院之后代价太大,一个金钱代价,一个是健康代价,我印象很深刻从我这里动手术进去,后来提着引流管,提着一个桶子,桶子都是你的血浆,你每天缠着一个绷带在医院里很滑稽上厕所,睡觉时候也放在旁边,非常羞耻。”
“每次只要我11点过后还在写作就会骂自己,我觉得把自己弄得太累了,反而适得其反。我生活太规律以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上午11点之后写的东西因为是贪婪造成的,结果也不会好,因为你最好状态已经用完,再写已经不好了。”
“我认为我这条命或者我这个人是为了最重要的事情来准备的,过去是为了某个女人来准备的,现在是为了文学的事业来准备的。驱使我的不是钱,推动我的是文学史上有所建功立业的虚荣心。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很见异思迁,谁给我冲击力更大,谁把我弄得绝望我就非常佩服他。我一生中上天给我八百年我也写不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大的东西,我感到很绝望。我越是绝望越是对这种作家感到不易,只有去膜拜他。但是对于原先我喜欢的作家我就会背叛他。”
“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太好描写的时代,因为人处在一个比较犬儒的状态,还有中国现在人的麻木的状态比较多,现在的人无论多么优秀,或者是个吃货,都已经抵挡不了对拍照,对食物的分享,或者是别的方面的诱惑。在朋友圈或者在微博里面我们不会谈尼采,不会谈康德,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读过。”
随笔比小说更宝贵
吴琦:更多的读者对阿乙老师的小说无论短篇还是长篇很熟悉,虽然之前零散看过他的随笔,在网上的还是出版的,《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是他第二部随笔集。想知道这本书的来源,我看里面文字有长有短,有破碎的,有诗,构成的方式是怎么设想的?
阿乙:跟《寡人》是一回事,我有一个习惯,如果我看到什么东西我很感兴趣,或者是突然有一个感触的话,我就会随时拿出笔,我没有笔记本,但是会记在书的边上,或者是记在手机的便签上,差不多都是这么来的。据说有很多古代或者近代的作家也这么干,只是我干得比较熟练一点,我写博客的时候写大量当时认为没有用的文字,写的过程中,曾经有一个愿望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天它们能换回一点稿费就好了,当时写的时候没有任何心机,不像写小说,写小说之前就知道一定会发表,如果不发表就不写。写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心机,只是做一个盼望,假如说有一天这些文字会有人来埋单的话,我感到很幸福。我出版所有的小说之后,基本上潦潦草草地翻一翻,甚至都不会去读完。但是这个随笔集我会细致地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自己跟自己有很多记忆的东西,有很多真实的情感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东西。
吴琦:是不是其中有很多创作的起点?有一些小的片断或者是动机,之后有可能发展成短篇小说或者长篇?
阿乙:对,里面有非常多,作为一个小说的起点,有时候认为自己还是个哲学家或者数学家、物理学家,要留下来笔记一样的东西。像我从小城市出来的青年有很多奇思怪想,经常会把它记下来。比如这本书102页有一个《构陷》,那段时间网上老流传学校的老师怎么去猥亵他的学生,就是幼女,大家群情激愤。其中有一个是我老家的老师姓陶,陶老师,我不认识他,但是跟我是一个乡的,那个乡总共才四个村,上过英国《卫报》的就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是因为我的书参加伦敦书展,《卫报》登了我一篇小说,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陶老师,他奸淫幼女上了《卫报》。后来我因为这个事情想到一个问题,我可以侧面想一个问题,你如果去构陷一个人的话,如果构陷吴琦的话,用什么方式最好,我说他奸淫幼女,大家一定会把他给踩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都有女儿,没有女儿他朋友也有女儿,大家都会有一种危机感,这就是我突然想到命运的黑洞。
吴琦:我拿到这个书不像读小说,从第一页端端正正地看到最后,我可能随时翻,翻到哪里从哪里读起,这也是暗合这本书本来的构成方式。下面这个问题想问,这本书有分章节,这些章节的结构和潜在的逻辑是什么?
阿乙:没有很大的逻辑,每次编这样的书的时候,我的出版方和编辑协商一下,我自己自作主张,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编辑,对书的构成做了编辑,因为写的这些东西会非常碎片化,非常散乱,所以我就采取字典的方式,就是从A到Z的排法。基本上是每个标题都是一个名词,类似是字典的方式,但是也不冠名为字典。上一本《寡人》也是类似这样的编辑,但是是倒流的模式,从现在到过去,有一个返回的过程,所以翻开《寡人》的时候你能够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你发现时光在倒流,那种倒流的感觉有一个古巴的作家叫卡彭铁尔,他写过一部小说叫《回归种子》,写到时光在倒流,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家具又长高了”,其实就是反方向的模式,人在变成童年的自己,你从现在一米八变成童年一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现在看到的家具实际是长高了,所以是倒流的模式。那种模式当时我觉得很奇异,我一直想尝试在我的书里也出现一种倒流的模式。从第一页时候你发现我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恋爱失败者,到最后一页发现我刚刚喜欢上一个姑娘,就会发现一个人从黑暗的井底走向了他最开始光明的一刻,那本书是倒流的原则。
剁了手也不愿意重复自己
吴琦:我看到这个书发现阿乙老师的阅读,或者他对这些作家的判断在变化。他里面写到马尔克斯或者博尔赫斯的看法或者评价,这构成这个书的一部分。我很好奇在您阅读的范围里,是不是也出现一些变化,对于这些作家的判断、他们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在随着创作的推进有一个相对的运动。
阿乙:我非常快的容易“见异思迁”。假如说我读到了一个后来的作家,他超越前面作家的时候,我对前面作家的保护欲就是非常低的。比如我对加缪的那种喜爱简直是到达一个顶峰,甚至我用很大精力模仿他的小说,以此来完成对他的致敬。后来读过福克纳以后,或者读过但丁以后,你会发现加缪的人生其实非常寡淡,他只不过在28岁写了一部成功的小说,这部成功的小说是来自他对詹姆斯·凯恩犯罪小说中一个典型人物的非常好的提炼或者是借鉴。还有一个是当时他在巴黎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他在出庭,所以他对法庭的情况非常熟悉。这个小说的长度非常短,你可以称它为短篇小说,但是这个小说构成他成名于整个世界的基础,我认为这个小说写完了,它也就完了。
第二部小说《鼠疫》我认为对他是一种背叛,虽然哲学上面是往前面解释了,但是文学方面是一个背叛,是一个跌落。后面还有叫《第一个人》未完成的小说,因为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也不好对他进行准确评价,但我觉得也不会超过《局外人》,《局外人》虽短,恰恰因为它就是那么大,就像邓紫棋她个子就那么大,就那么美,再稍微长高一分就丑了。《局外人》如果再扩充一千次,扩充五百次就是一部伪作,不是一个很好的小说。之所以对加缪是这种评价,是因为后面有福克纳、但丁有这么伟大的作家在那,后来我读了托尔斯泰以后,我又觉得福克纳有时候拘泥于技术方面的东西。像俄罗斯他们天生到大海里捕杀鲸鱼的作家,力气特别大,我是伪成功论者,你给我的东西冲击越大,我越服从你,你给我的冲击越小,我服从的就越少。
但是很多情况是这样,我很多年已经不看卡夫卡也不看博尔赫斯,你偶尔看的时候会非常亲切,有乡愁。因为很多年你的枕边书就是他。但是后来你也知道他对你有一种控制,这种控制就是来自于他的有趣,博尔赫斯他的趣味性对你的控制很深很深,我认为它像一个妓女一样,或者像毒品一样控制着你,但是你总有一天要离开它,你不离开博尔赫斯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会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也不知道托尔斯泰会写那么多。很多的短篇小说也是这样,包括现在我对美国写作班出来的作家,美国的作家有明显的趋势,写作班的味道特别重,耶茨的味道就是卡佛的味道,他们的味道越来越像一个导师教出来的,你会觉得这种写作也是有弊病的。那么他们的弊病是怎么出现的,肯定是有历史上更大的作家把他们比较下去的。
我很见异思迁,谁给我冲击力更大,谁把我弄得绝望我就非常佩服他。我一生中上天给我八百年我也写不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大的东西,我感到很绝望。我越是绝望越是对这种作家感到不易,只有去膜拜他。但是对于原先我喜欢的作家我就会背叛他。
吴琦:这种绝望反过来怎么影响创作呢?如果之前用模仿的方式向先辈致敬。现在面对这样体量作家的时候,在写作上会有些更多的紧张或者是焦虑,还是说彻底放弃跟他们进行对话?
阿乙:有时候你去一个山里面拜一个老师傅学艺他可能瞧不起你,但是你如果能得到他十分之一的功力也是很好的。我印象很深刻,包括我每次身体不行的时候都到医院去大剂量的输入激素,好像叫激素冲剂,连续三天,每天上午输激素,袋状的,直接把那个东西输到你的体内去,你感觉那几天浑身是劲,好多力量都到了你的身体里。我就觉得读那些人的东西也是这样,你虽然对他感到绝望,但是他巨大的营养,或者巨大信心的源泉也会支撑着你,那种力量也会到你身上。每次读了很厚的一本名著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身体内进入巨大的营养,这种营养是我一时半会儿感受不到的,但是隔两年你一定在阿乙身上看到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很多文学青年都有的,但是是很多作家都没有的。这个时候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学习型的写作者,我还是文学青年的这一拨。
我跟有一些作家不一样,我觉得有一些作家他在自己的领域内越写越会复制自己,我也大量复制自己的情感,复制自己的思路。但是你会发现我在变化,可喜的地方是在于我始终不停的变化,在往前走,我走的步子比较保守,但是你看我的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本书改变不多,因为是很多年的合集。但是你看我小说时候能看出来,有一些人他会说我今天写的东西不如昨天,听起来挺伤心的,但是我实在没办法才告诉他,如果我再写昨天的东西,重复复制东西的时候,我宁可剁了自己的手也不愿意干那个事,因为这件事情非常耻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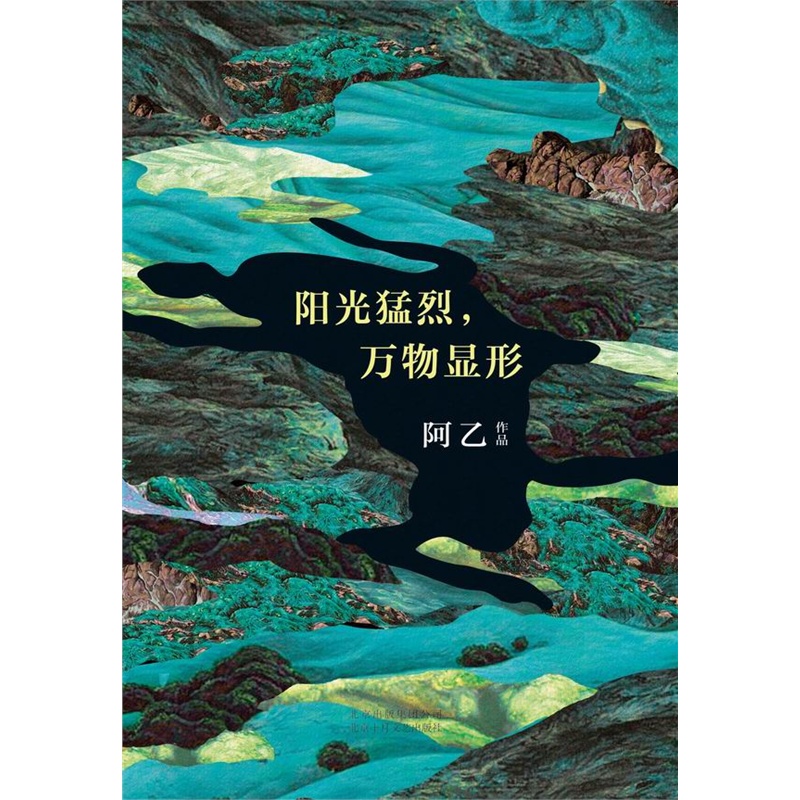
最大的负罪感是时间流失
吴琦:刚才阿乙老师说激素的事,之前阿乙老师得了一场病。在采访的时候我是很早之前,那时候我记得你的写作状态很纠结,一天前20个小时在浪费,把自己逼到绝路,最后4个小时写作。但是这期间好像生活变得更忧虑,我不知道写作上纠结紧张的状态还在吗?还是随着你的生活慢慢调试过来?
阿乙: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很光彩的事情,今天网上做了很多宣传,头发是一个卷的,是非常帅的,现在就像一个倒过来的失败的案例,就好像我非常放纵地让自己成为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人。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是我写小说时采取了一个失败的方式,导致现在这样的局面,当时失败的方式,比如写作24个小时,20小时在焦虑,4小时在工作,整个人处在一种非常不幸的状态,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不当一回事,总是在那思考怎么样去写作,甚至在做梦的时候都在解决写作。当然这么说好像有一点表扬自己的意思,但是实际上我是很害怕再回到那种状态,接近崩溃的状态。
现在我写小说,每当我写到两个小时的时候身体就会累,累的过程中我就会想到可怕的过去,过去我真地不愿意回顾,做梦的时候跟醒着是一样的,在梦里你甚至突然爬起来拿起笔把梦里的情况记录下来,因为你误认为你梦里面解决写作里的难题。那个小说现在已经写完了,当时是写到9万字还是10万字的时候崩溃住院去了,因为那个时候肺已经不行了,长时间不吃饭,加上抽烟,不吃饭是因为你认为吃饭打扰自己。那时候我每天都在想这个世界上科学家发明一个药丸就好了,一个人每天吃一个药丸也不用排泄,保证营养的摄入,可以整天用来写作,那多好。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个疯子,后来导致这个局面,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是我住院的时候当时带了电脑去,想在医院里至少利用住院的时间把它完成,结果医生说你的情况很严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当时正好焦虑得不行,那一段时间写得比较失败,就强行停止了。
大概住了半年的院出来以后打算告别文坛,从此游山玩水,立下过这个志愿。但是后来发现过了两三个月以后还是会去写,但是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生活好青年,自己做菜、买菜,生活上面日子过得不厌其烦的,按时吃药、锻炼,早餐也吃,各种水果什么都来,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长一点,更健康一点,看到蓝天次数更多一点,看到吴琦得机会更多一点,如果死的话谁记得你。
对写作来说,你上午刚写两个小时,吃了午餐就缺氧,缺氧就午睡,午睡到下午三点,你开始写,写了一个小时,五点钟家里又有什么,有时候一个电话就能把你整个一天计划全部打乱。因为自从你接触上手机以后你就看微博、看微信,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一天就过去了。对写作的人来说时间一旦流失了,负罪感会非常强,他会觉得对自己特别有罪。我还记得毕飞宇根本不用手机,把电话给他的老婆,我跟他打电话是他夫人接,为了拒绝外面对他的骚扰。所有写作者都有怪癖,这种怪癖就是你不要在没事的时候打他的电话。
吴琦:现在写作状态会舒缓一点吗?随着生活变得更健康。
阿乙:我现在把写作时间改成11点之前完成,11点之后大家可以打电话了,11点之前处在那个时间,谁打扰都是很糟糕的,觉得你剥夺了我的写作时间。有一段时间我是早上6点钟开始写作,因为越早写作你完成得越早,你整个时间,比如6点钟开始写,你9点钟就写完了,你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都可以在北京的街道上走来走去,游山玩水,多开心,可以去菜市场买菜,可以看电影,看什么都行,你甚至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发个呆,公园里面看看全国各地的游客,像秦始皇一样的。这种感觉非常好。但是你一旦是从上午9点钟开始写作,整个就完了,没有办法写了,9点钟开始写,写到10点钟的时候饥肠辘辘开始准备午饭,午饭就要缺氧,你就要开始睡觉,下午三点钟起来,觉得整个一天过了三分之二觉得很毁灭,马上到五六点天又黑了,你的进展又很慢,就毁了。我现在是早起派,如果我有什么计划一定会在上午11点前完成。每次只要我11点过后还在写作就会骂自己,我觉得把自己弄得太累了,反而适得其反。我生活太规律以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上午11点之后写的东西因为是贪婪造成的,结果也不会好,因为你最好状态已经用完,再写已经不好了。
吴琦:11点之前大概还能完成多大的写作量?
阿乙:好的情况下两千字都有可能,不好的状态也能确保七八百字,或者五六百字,其实一天有那么多字的话,一年下来是产量很高的。
生病后的写作没有从前激烈了
吴琦:在豆瓣上经常看见生病之后很多时间用来看电影。
阿乙:看电影其实不是为了娱乐,我最大的毛病就是学习,看电影是为了摄取营养。每天带着书也是为了摄取营养,我全身心充满焦虑,这种焦虑可能上学时候我父亲带来的,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严格的要求带来副作用就是我高考考得很差。这种东西压到我性格里来,把你面临的事物会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有用的,一个是没用的,是非常强的实用主义者。所以我在很多时候,有时候在生活中和我妻子做一些判别的事情,我有时候也是会很极端,我会判别这个事情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这个东西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的,很多东西就会趣味弄消失掉,因为我过于强调这种实用性。如果我上厕所不拿一本书进去,我认为上厕所的功能就变得非常剥夺我存在的意义。在浪费我的时间,我就要看书,不看书的话我就拉不出屎。看电影也是这样,很焦虑,有时候看十分钟就扔了,因为选择恐惧症,往下看会浪费你的时间,你看十分钟不看下去也是浪费时间,所以人莫名其妙一个下午看五六个电影都没看全,就很恼怒。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超大的怪物,有时候想撞墙。
吴琦:听起来规律健康生活没有让你变得更加不焦虑,其实该焦虑的还是在焦虑。
阿乙:比以前更知道健康的代价,累的时候代价特别大。我有时候处在这种状态,突然有一天累了,就会非常懊悔,觉得自己这么多天每天坚持散步,坚持到公园里面吸氧,到各个地方观察,我坚持三十天我认为养个好身体,一天就报废了,今天何苦把自己弄这么累,前面三十天做的东西今天全部没了,通过这种苦口婆心地劝自己,第二天才好一点,一般第二天放自己一天假。
吴琦:生病前后具体写作上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变化?
阿乙:我曾经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写下去了,是出院之后,出院之后代价太大,一个金钱代价,一个是健康代价,我印象很深刻从我这里动手术进去,后来提着引流管,提着一个桶子,桶子都是你的血浆,你每天缠着一个绷带在医院里很滑稽上厕所,睡觉时候也放在旁边,非常羞耻,就决定出院以后不写作了,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自己这种心理状态,包括自己的生理条件不适合写作了。就像不适合做一个搬运工,不适合做一个军人一样,体检你不适合写作,自己这么一个判定。但是在家养了两个月手痒,贼性难改,还是去写作了。你会发现写着写着你又有可能进入那个状态,又把自己给耗进去,这个时候就会把自己控制住。我会说你还是有病的人,所以现在基本上把自己磨合成一天只允许自己写两到两个半小时,以前写八到十几个小时,跟出租车司机一样,现在是两到两个半小时就够了。发现有一个比较的结果就是一个人效率很高写两个小时的时候,比他效率不高的时候写十个小时写的东西可能好一点。
吴琦:不好意思一直问生病前后的事,这前后有没有什么变化,生病本身有没有对文章、文字感觉产生影响?
阿乙: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以前写的东西,以前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危险。就像一个打牌的人不知道自己身体的危险,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得住的,可以连续通宵打很久麻将,打麻将的时候可以得心应手,没有后顾之忧,现在有后顾之忧不敢使全力。过去我写的东西可能有的人能感受到,情感的力度倾注得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是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任自己精神上磨练跟小说的人物一起磨炼,你是全部投入进去,你是无代价的,是毫不在乎自己身体,你认为自己很年轻,也有能力达到。所以主人公他是什么状态,作者基本上也是什么状态。我记得我当时写死尸的时候,尸体漫山遍野的时候,就去网上把所有照片拿过来,写完的时候我快要吐了。主人公到了什么状态我基本也到了他的状态的40%-60%,那种陪同感,写作的时候你就是一种陪同感,你都进去了。但是现在你不能这样,你再也没有这种能力了,这种能力已经消失掉了,是因为你再这么把自己身体用下去,你可能跟他一起完蛋,所以现在在艺术或者在创作其他方面努力一点,但是在作者精神投入方面远远不如以前。
我的这条命为文学而准备
吴琦:今天翻这个书其中有一个地方说到不愁没有东西写,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素材可以写,而是要一个选择的问题。之前跟许知远的采访里阿乙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之前很多是自己的经验,或者警察那段时间这些经验进入写作。现在小说创作里那些经验,或者这里提到无穷无尽的创作经验来自于哪呢?还有可能来自正常健康的生活吗?还是说是其他的地方?
阿乙:目前我对自己容易开掘的那一部分其实已经开掘光了。很多潜意识里面,或者是自己目前没有能力去开发的东西还在,但是要等待机会,或者等待自己有更大的思考,长时间的思考。或者是有一天你认为它更有价值去挖掘的时候才开始挖掘,所以那一块是悬置的。现在处在这种状态是在虚构,就是你去了解别人的生活经验,还有一个就是你去想象。所以目前我就处在这种状况中,但是这种状况这两年好像因为吃激素,有一个坏处就是健忘,也不是很得心应手。所以我最近有计划,因为我的资源不太多,但是我的同学资源太多了,我有五六十个警察同学,我打算每个同学,大概有十个,十个或者六个,他们每个人给我讲一个人生中最好的故事,差不多就能贡献中国最好的犯罪作家。我的同学经常说有一个好故事讲给你听一定能写好,我相信我一定能把它写好。包括我老家也有一些故事,但是就是因为我懒,我说我今年回老家住两三个月,但是我又不愿意回家,但是我相信故事不会跑。再加上有一些案犯还没有抓回来,等我回去的时候他就抓回来了。
吴琦:现在对于北京这个地方,或者在北京的生活是什么感觉?因为之前刚刚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一些紧张局促,但是现在阿乙老师已经非常流利,是不是也有对大城市的生活有适应和调整?
阿乙:也没有想去适应它,外部环境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说出来有点自吹自擂,我认为我这条命或者我这个人是为了最重要的事情来准备的,过去是为了某个女人来准备的,现在是为了文学的事业来准备的。说起来很感人,但是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我生命中很多东西我是很冷漠,很不在乎,这些东西不在乎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也挺在乎的,比如说钱,但是它并不是最重要来推动我,或者驱使我的不是钱,推动我的是文学史上有所建功立业的虚荣心。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想清楚生命中很多东西不重要,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这个地方做活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有社交恐惧症,我甚至为了避免自己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出现在主席提上而逃避领奖,就不想得这个奖,就是为了避免到台上领奖,这几秒钟的行为,破坏自己比较美好的形象,德智体美劳一定把自己削弱一下。但是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面红耳赤的怪物,到现在变得在台上油腔滑调毫无廉耻感。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变化,从最开始非常局促紧张的人到现在一个滔滔不绝这么说话的人,他都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并不很在乎你。我说这个话可能有点冒犯,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把这两个小时度过去。
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处于麻木状态
吴琦:也是之前跟许知远的访谈里面谈到了,你对写这个时代心灵史诗有兴趣,这是长期的目标还是说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或者是积累?
阿乙:这个只是为了给自己茫茫的未来插一个坐标,放在那,我觉得可能不太会去完成,我怕有一天自己迷失方向不知道要干吗,但是我其实现在根本没有欲望去写。但是我有时候害怕自己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迷失了方向,所以我会给自己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比如说我在乡村做警察的时候,到处都是尘烟滚滚的空气,没有一点柏油路,到处都是村姑。这个时候我立下志愿要去纽约,当时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后来谁知道有一天还去纽约玩了一趟。就像跟许老师说的一样,我要写像克里斯朵夫或者什么样的心灵史诗或者什么伟大的著作,这个肯定不可能,但是一定插在未来遥远的某一个地方,有一天隐隐中你可能往那个方向走。有一天晚上我还做梦说,去火星,火星肯定去不了,但是万一呢。有一天说不定呢。虽然在我身上不可能实现,愚公移山一样,在你重孙那一代实现,重孙那一代讲起来曾爷爷,他想去火星,现在就在火星。我觉得人类做梦的时候做大一点,只要你是做自己的梦,不靠别人去实现,不像毛主席一样用别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就是成功的人。
吴琦:还有一个问题不得不继续问你,提到心灵史的问题,可能自己也是谦虚,自己写不出什么东西,但是不担心同时代其他作者写出太惊世骇俗的文章。这个判断不知道是随口说还是有待观察?
阿乙: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太好描写的时代,因为人处在一个比较犬儒的状态,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形容好不好,但是最近谈得越来越多。还有中国现在人的麻木的状态比较多,我们已经不像80年代时候的青年有那么多于连的因素,有那么多向上的因素,现在的人无论多么优秀,或者是个吃货,都已经抵挡不了对拍照,对食物的分享,或者是别的方面的诱惑。在朋友圈或者在微博里面我们不会谈尼采,不会谈康德,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读过。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很年轻叫徐兆正,他天天跟我聊天就会讲到康德,讲到尼采,讲到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曾经有一个人叫徐沪生,我很欣赏,他做了一个成功的视频,一条视频,他曾经学哲学的,但是这些东西在他生命中已经消失了。但是我非常珍惜徐兆正这个朋友,他还在讲这些东西,80年代的青年现在大量存在,在格非身上,他总是讲康德,讲尼采。现在没有人谈这些,现在谈的更多的是吃喝,或者是汽车。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人的意义在丧失。这个时候写这一批人的时候觉得意义不是很大。我更愿意写英雄的悲剧,不愿意写懦夫的平庸生活,没什么可写的。现在的状态是没什么可写的,只是小人物的挣扎,小人物的挣扎在我的书里很多,但是我不认为有特别大的冲击力,也不认为构成这个史诗。
我对自己总是心存不满
吴琦:谈话中这种持续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妖魔的情绪是常态写作当中有这样的情绪,怎么和这样的一种东西共处?
阿乙:自我的这种反省其实在我身上总是存在,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不满,这种不满其实就是我父亲对我不满。从我小时候开始他就对我不满,我从背第一首唐诗的时候他是很急功近利的人,对我很不满,他让我一天背一首唐诗,我被到第七首的时候就崩溃了,结果我现在唐诗功底不好怪他,他对我精神殴打,觉得我没有背好。这种来自我父亲他的不满在你的血液中,我自己也会不满。但是我这个不满跟你刚才讲的自我反省不是一样,这种不满即使我自己做得非常好,我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也不是那么高,因为骨子里对自己不满太强烈,不好解释。卡夫卡也不满他的父亲,不崇拜他的父亲,因为带给他太多的压力。但是我想如果没有这个压力的话我也走不到今天,不会把自己用的这么透彻,不会用的这么惨,用的这么多,可能会变得浅尝辄止,在走向文坛的路上发几个段子就OK了,不会这么变态地往下走,把自己身体弄这个样子。讲到最后很俗套,是双刃剑。
(鸣谢:吴琦 王二若雅 徐新芳 单向空间 青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