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6》:文学中的暴力和社会上的暴力都是次要角色
2017年07月09日 14:41:57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冯婧
《2666》描写了大量的谋杀,但正如波拉尼奥所言,“我作品中的暴力如同社会上的暴力一样是次要角色”。在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始终是波拉尼奥书写的重要对象,在亲身感受外,好友马里奥·圣地亚哥更是他理想化的主角,“他所写的精神苦闷其实是这个世界知识界的精神苦闷,他们走投无路”。

波拉尼奥
凤凰文化讯(冯婧报道)波拉尼奥一生坎坷,流离四方,从青年时期热情支持智利左派政府,到军事政变后被捕入狱,逃回墨西哥后他和好友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运动,意图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但也很快归于沉寂。
总体而言,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贫病缠身。他以诗人自居,却在四十岁后为了糊口养家开始写小说,产量极为可观,身后留下十部小说、四部短篇小说集以及三部诗集。《荒野侦探》、《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美洲纳粹文学》、《护身符》等小说都已经有了中译本。
波拉尼奥在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访谈中说:“我更喜欢带点自传内容的作品,因为这是讲‘自己’的文学、区别自己与他人的文学,而不是讲我们大家的文学。大众文学是那种肆无忌惮侵犯你和我的文学,要求和大众保持一致,而打成一片的结果就是万人一面啊。我写东西,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根据读书和文化生活的体验。时间一长,这三种经验就合而为一啦。我也根据人们常说的集体经验写作,但与理论家说的‘集体经验’不同。我的集体经验仅仅是个人经验幻想的侧面,带有神学意味。按照这个角度,列夫·托尔斯泰也是自传体作家。当然,我是追随托尔斯泰的。”
《2666》描写了大量的谋杀,但正如波拉尼奥所言,“我作品中的暴力如同社会上的暴力一样是次要角色”。在这些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始终是波拉尼奥书写的重要对象,在亲身感受外,好友马里奥·圣地亚哥更是他理想化的主角,“他所写的精神苦闷其实是这个世界知识界的精神苦闷,他们走投无路”。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恶?如何面对世界的冷峻?如何面对暴力?
在话剧《2666》即将登上舞台之际,译者赵德明与范晔、止庵一道,结合《2666》及波拉尼奥的其他作品,为我们揭示了全景小说的阅读密码,也勾画出了“亲爱的王子”波拉尼奥的形象,并指出他不同于前辈“魔幻现实主义”的“下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在回答凤凰文化记者问题时,赵德明老师也强调,20世纪这一百年来,拉美文学的特点就是不断翻新、不断实验、不断否定、不断创新。
以下为活动实录,感谢知乎live与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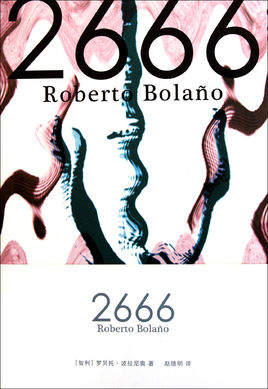
作者: [智利] 罗贝托·波拉尼奥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者: 赵德明
何为全景小说?如何阅读全景小说?
赵德明:我对《2666》的认识,从它的作品结构、人物、故事,还有它背后的想传达的思想感情,尤其是它的那种神韵。我也是在翻译前后,一直到现在逐渐认识的。从阅读方式上来说,这里提到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全面体小说,或者叫全景小说。这个概念的提法,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已经有作家提出来了,像略萨的《世界末日之战》提出来之后,已经有评论家说有点像全面体小说了。
《2666》的全面体表现有几个:
一个就是舞台很大。从欧洲、美洲,甚至还有一点点中国。国家上来讲英、德、法、西、意大利、美国、墨西哥都涉及到了,这个是从舞台上说。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差不多一百年,从阿琴波尔迪的经历来讲,纵深的时间有一百多年。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历史感。第三个来讲,就是作品的人物多,故事情节复杂,很多细节和细节之间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这样在阅读上来讲,首先得解决一个阅读者站在的角度。如果我们的观念还是停留在一乡一地,我只看到自己的家乡,或者自己的国家,对于世界性的文化发展不大了解,就很难理解它为什么要这样写。一个智利作家从智利走出来,从墨西哥又到了西班牙,居然要写德国的一个虚拟的作家阿琴波尔迪,一定要写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的文学评论家,一定要写美国记者,一定要写一个智利教授,智利教授这还有一点点可以解释的,就是有波拉尼奥自身自传的因素。
第四部分的罪行那一章,200多个杀人案,显然不是波拉尼奥所知的范围,但是他进行了调研。他为什么要设置一个人物多,结构又复杂的大舞台?主要想表现“人性恶”。虽然从2500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提出来,中国哲学家也提出来了,但很重要的是,“人性恶”的当代表现是什么?艺术表现是什么?从人性的思想深处、灵魂深处是什么?靠说教不行,要靠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阅读的时候要跳出我们自己原来的读书习惯。
止庵:我接着赵老师的说,我觉得全景小说是一种形容,不是说有那样一个专门的写法,全景小说是针对那种不全景的、或者非全景的小说而言。不全景小说就是聚焦的小说,聚焦于一个主要的情节,一个故事,一个或者若干个人物,这是我们习惯看的。而全景小说是比这个范围要大,它没有中心的情节,也没有主人公。
反过来看《2666》,首先应该从第四部分罪行看起,这部分写了很多个女人被杀的事情,但是每个人物都是一个小段,其实这里边每个人物都是我们过去意义上的主人公。但是这里边出现了一大堆人,这些人的死法有差异,但是差异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么多人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个氛围,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如果我们通过一个故事来写是不可能实现的。第四部分真的有必要写这么多吗?我觉得真的有必要,这部分在篇幅而论是整个全书中是最长的,它必须得写这么多才有效果。
全书五个部分除了第四部分是小说的核心位置外,其他都是散点的。另外四个故事也是分别涉及到不同的方面,互相之间都有一点点联系,但是它们不是一个故事,这个书里面也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公。我们可能觉得阿琴波尔迪接近主人公,但是阿琴波尔迪在第一部里是这四个研究者所关注的对象,但是他并没有出场,在第二、第三、第四部里没有这个人,第五部才写到他,所以也不能说是这本书的真的主人公。我们应该从场景、结构、人物这些方面来理解全景小说,这种写法使得小说的局面变得非常大,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非常大。它对我们就具有了过去那种小说所没有的影响和作用。全景小说是很难写的一类小说,但是它确实对小说的形式做出了一种突破。
范晔:可能是作为文学研究者的职业病发作,我比较愿意从全景小说这个术语最早出现语境来做一点观察。一般我们会认为这个术语的出现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1968年,略萨为《白骑士蒂朗》写的书评。《白骑士蒂朗》实际上是15世纪末的西班牙的骑士小说,我们知道略萨年轻的时候是狂热的骑士小说爱好者,和我们今天读网文差不多,他认为在众多的骑士小说中,《白骑士蒂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就认为这是一部全景小说。略萨说《白骑士蒂朗》里面反映的中世纪,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反映的俄罗斯,或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法国是一样的真实。可能像《战争与和平》一样,具体的历史的数据可能会有错误,也可能像《人间喜剧》一样会有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些错误和夸张也是一个时代的表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略萨把《白骑士蒂朗》跟《战争与和平》、《人间喜剧》相提并论,认为都是一些典型的全景小说,也可以看出他这里面勾勒出这样一个全景小说的这种谱系。略萨还说《白骑士蒂朗》是一部骑士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幻想小说、历史小说、爱情小说、社会小说……同时是这一切,但是又不能用其中任意一个标签把它全部概括,或者说你可以根据不同阅读的角度,小说就可以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像波拉尼奥有一次在访谈里面说略萨小说里有千万个入口,马尔克斯的小说也一样,也恰恰符合略萨当初对全景小说的观念。
止庵:这个书作为全景小说,在结构方面是非常周密的,不是说想怎么样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还是有方法的。
在第一部分里边,讲到有四个研究者研究一位作家,阿琴波尔迪。他们找到这个作家的一些线索,其中有一个线索是一个出版社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在第五部分里面是很重要的人物,而且是阿琴波尔迪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一个男爵的小姐。这样就把一和五建立了联系。意大利研究者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另外两男一女来到墨西哥,因为有另外一个线索:有人说在墨西哥见到阿琴波尔迪了。他们到那个地方去,接待他们的人就是第二部分的主人公阿玛尔菲塔诺,这是一和二。阿玛尔菲塔诺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在第三部法特的部分又出现了,所以这两部之间又有联系。在第一部里边,这些人到墨西哥去的那个地方,就是第四部罪行发生的地方。二和三都是以这个地方为背景的,所以到了第四部出现罪行就顺理成章,因为这个地方已经被提了好多次。到了第五部,阿琴波尔迪有个妹妹,这妹妹有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第四部分的一个嫌疑人。所以这个故事实际是相当周密的作品,虽然是全景小说,虽然局面很大,但是作者用一个网络把这些东西编织在一起的。
《2666》还有一个特点,也是波拉尼奥和前辈作家有差别的地方,就是他特别注意作家、读书人、记者这些与写作和阅读有关系的人。阿琴波尔迪是个作家,第一部分四个人是研究者,第二部分的阿玛尔菲塔诺是个学者,第三部的法特是个记者。如果我们读了他的《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短篇小说集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波拉尼奥对这样一种人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说他对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他所写的精神苦闷其实是这个世界知识界的精神苦闷,他们走投无路。而且波拉尼奥大量采用阅读作为素材,这个书里边提到好多真的书,甚至他在里面还有关于写作、阅读的很多议论,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一个特点,跟魔幻现实主义前一代人比较起来就很鲜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作家不爱写知识界的人了,不爱写读书人了,愿意写比较蒙昧的的人,或者说那种不读书的人。但是波拉尼奥又重新回到这里了,他又重新把这部分人的内心世界加以深刻的揭示,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关于知识界的心理或者是精神世界的揭示。
范晔:我接着止庵老师说两句,关于结构性的线索。我也非常同意止庵老师的看法,这样一部煌煌巨著有非常多草蛇灰线的地方。
比如说巨人这个形象,阿琴波尔迪这个神秘的作家到底是谁,可以说是整个《2666》最主要的谜题之一。 实际上他在第一部分就已经出场了,作为一个神秘的德国老人,关于他的形貌描写一开始就有比较突出的特征,他大概有一米九五差不多两米,后面好几个部分也多次出现过关于这个“巨人”的意象。大家可能还记得,第四部分里的嫌疑人哈斯,大家以为他已经发疯了,但是他一再说会有一个巨人来救他。到了第五部分的时候阿琴波尔迪的妹妹也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巨人去救她的儿子。阿琴波尔迪自己还说,我可不是什么巨人。
除了贯穿全书巨人的形象,其实还有一个线索:在第一部分阿琴波尔迪作为一个神秘老人出场的时候,当有人问他去墨西哥看什么?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直接用西语回答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我们硬译过来的话就是“我去了解一下”。因为goduosa本身就有了解,认识,获得知识。他并没有说去看亲人。事实上我们发现他到那儿实际上是去搭救他的亲人一样,但又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当然也知道,全书最后一句话就是他去了墨西哥。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2666》的两大线索,或者两大谜题,一个是神秘作家阿琴波尔迪到底是谁?还有一个谜题就是连环凶案背后的凶手又是谁?这两个谜题到最后好像纠结在了一起。全书最后一句话说阿琴波尔迪去了墨西哥,他去那干什么?他能把他的侄子救出来吗?书里没有给出答案。凶手到底是谁?也完全没有给出答案,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波拉尼奥在小说当中的思考,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本来也不是说要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特别是作为一个现代小说。但这里面能表现出这样一些思考,就是文学面对这个世界的恶的时候,能做一些什么呢?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给出一个黑白分明的答案,或者说给出一个解决之道,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文学的功用,但是可以在小说里面表现出他自己的立场和思考。

波拉尼奥与家人
在现代语境下,如何理解奇书《2666》?
赵德明:《2666》的所揭示出来的方方面面有很多,但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人性恶的问题。第四部分罪行当然表现的最为血淋淋,人性恶的顶端就是杀人。那么在其他的所谓一般人中间,有没有人性恶的问题?
第一部分的四个文学评论家,为什么非得要选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各一位?我觉得是波拉尼奥别有用心。他们的所谓文学评论和研究是什么?里头有暗暗的嘲讽。他们四位聚在一起开会,固然是因为对阿琴波尔迪的研究的共同爱好,但是实际上,在这爱好的下面有很多谈情说爱,游山玩水,最主要的就是当他们在墨西哥遇到了华雷斯(墨西哥城市名,书中以圣特莱莎的名称出现)杀人案的表现,就露了本相了。这种对恶的对人性恶的默认、忍受,实际上就是纵容。也就是说他们骨子里还是明哲保身,见到恶的罪行却不能仗义执言,也没有这个胆识。这些文学评论家、研究家,可能在道理上来讲知道的比常人要多得多,都知道什么是罪恶,可是实际上行动起来的时候,却暴露了他们的弱点。
第二部分里的智利教授的遭遇,他的问题在于面对苦难,先是出走,离开智利逃难到墨西哥,后来又出现了妻子的离异和女儿被绑架,他很愤怒但他也无奈,这又是一个类型。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深深的感觉到,一个人在面对着这样一种强大的恶势力面前,的的确确是非常无能的,没有办法的。
很典型的是第三章的美国记者,美国记者是仗义执言的,也知道是非。他在遇到华雷斯凶杀案的时候,他也是要说话和报道的。但是他背后还有他的报社老板,这个报社老板不允许他跨出体育界的报道去做这种业余的事情。他要不要丢掉饭碗去仗义执言?还是不行,他自己也有一个生存问题,这是很合理的。
也就是说,这些善良的人在面对着恶的时候选择很不同,但是都表现了一种对恶和对罪行的态度。阿琴波尔迪这一章的艺术性在于,他纯粹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人物?这就很有意思了。阿琴波尔迪这一生遭遇里头,遇到了苦难、战争,也碰到了法西斯的和前苏联的镇压,尤其是在德军溃败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混乱。让我感到很惊讶的是,作者在写这一段的时候的那种冷静。比如说,一个德国火车站站长组织十四、五岁的小孩,让他们喝醉酒去枪杀犹太人,作者的笔墨写的不是激昂愤怒,是一种非常冷静甚至带有一点麻木的感觉,像那些个少年行刑队似的,麻木地开枪,然后麻木地回来。这也是一种态度。
所以阿琴波尔迪这个人物,串联起来看,从第一章没有出场的隐形,到逐渐呈现出来的始末,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人物还是贯穿全书的,其他人都没有,他的一生遭遇很可能就是解读《2666》的一把钥匙。
止庵:谢谢赵老师的分析,我接着往下说。我想起福楼拜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世界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绝对是一回事。我在读《2666》的时候,一直想到的就是福楼拜的这句话,这个世界的严酷性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无能为力,无论你出于善意、出于恶意或者无动于衷也好,其实结果是一码事,这个世界该发生的事情都得发生,而且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不想要的。所以我觉得《2666》这本书,我们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第一点,为什么要有第四部分罪行这一部分?为什么要这样去描述这么多人都死掉?我们注意到在第三部分法特这部分,有一个黑人记者和一个女记者,本来想去报道这个事情,他们甚至见到了可能是凶手的这个人,但是他们如果写出了报道是什么样子?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部分是怎么样来写的?真正的第四部分跟法特想写没写的报道之间完全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小段话交代过去,然后又写第二部分,一个个女人以各种方式被杀。如此冷静地叙述这个事情,使我想起中国古代一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些被杀的人对世界来讲微不足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冷酷,就是完全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切。这是我读这个小说最受震动的地方,最有力量的地方,我觉得第四部分是整本小说的核心。
在其余几个部分里边,作者也是用一种特别冷静的态度来讲这个事情。尤其第二部分写了一个非常痛苦的故事,一个人的太太出走了,他自己逐渐地进入疯狂状态。虽然比起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甚至第三部分来讲,作者稍稍靠近了人物一点,但他还是没有表达出他的态度或者立场。为什么他不表达呢?是因为这个世界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它像一列火车一样,自己往里边开。面对着一列飞驰而过的火车,我们喊什么?我们不喊什么?我们根本无能为力。这是这个小说最有力量的地方。
回到第五部分,我们看阿琴波尔迪的一生,作者同样是用这样的态度来描述的。我觉得体现的是这样的视点:假如还有一个人间之上的、造物或上帝的视点,他就是这么看这个世界所有的黑暗和痛苦的,他无动于衷。
范晔:上次和赵老师聊《2666》是2011年,现在离2666又近了6年。我有一些阅读的感受发生了变化,但有一些当初觉得是秘密的,可能依然还是秘密。比如说,全书第三部分快结束的时候,墨西哥的女记者说,这些妇女被杀害的案件其实是无人在意的,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世界的秘密。原文用了一个定冠词,就是“世界的秘密”,不是随便什么秘密,或者某些秘密。我们也可以说,波拉尼奥在他的小说里面也给出了一些姑且可以称为答案的东西,或者说对恶的思考贯穿了他整个创作,不管在《2666》里面还是他其他的作品《护身符》里面,还有《美洲纳粹文学》,或者《遥远的星辰》里面,有不同类型的恶,这里面有独裁者的恶,但是也有可能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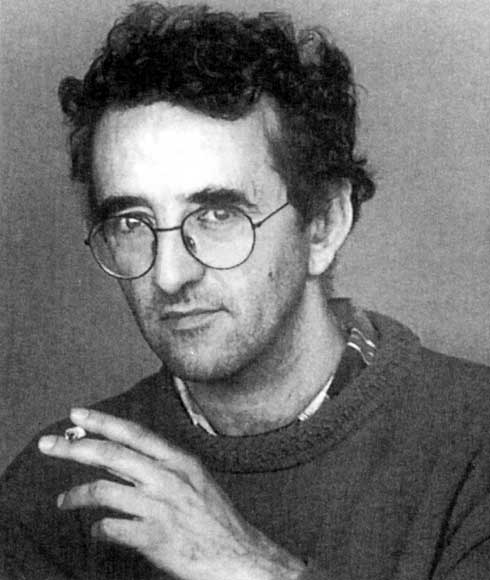
波拉尼奥
《 2666 》的符号意义与预言性
赵德明:2666这个数字,波拉尼奥的其他作品里明着和暗示着它的意义,《护身符》里面明确指出2666就是人类走向坟墓之年。《护身符》里有很多解读波拉尼奥的钥匙,它甚至列了一个表,从文学衰退的角度,他都列出了哪年哪年,未来的欧美文学是朝哪儿发展。所以《2666》这本书本身没提,这个没提,我觉得比提了还好。因为不提,读者一定会很好奇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2666》的符号意义有好几个:一个就是人类走向灭亡的这样一个时间;还有一个它是一个过程。波拉尼奥到2003年勉强写完这本书。那时他已经病很重了,备受折磨的情况下,他已经绝望了。过去,他的家史,他的遭遇没有给过他欢乐。他在墨西哥曾经有过一段和文学青年的友好交往,算一个友情安慰,但是总体上来讲他的情绪很郁闷,很绝望。所以《2666》也表明了一个人类往前发展的走向。
2003年波拉尼奥去世了,此后14年的欧美方方面面的危机看,恐袭、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本身还是人的危机,金融家的贪婪、诈骗是人心,然后恐怖、难民,是很大的问题。前天一个从美洲回来的朋友说,美洲的难民问题也很严重,从哥斯达黎加秘密上岸准备穿越北部国境打算偷渡到美国的也很严重,很多人在途中死掉了,最糟糕是妇女和儿童。为什么非洲的、中东的、美洲的大量的难民要冒着生命危险涌入?为什么恐怖主义猖獗?为什么发生了欧洲内部的种种矛盾?就表面现象来看可以说一个危机,但是从骨子里真正要分析的话是在灵魂深处,当然里面有大善,有大爱,可是有更多的是大难,有更多的是灾难,而这些灾难谁制造的呢?《2666》里边也给了明确的回答。所以《2666》的预言性,经过14年以后初见端倪,很可以体会它的远见性。

亲爱的王子
“亲爱的王子”波拉尼奥其人
赵德明:结合现已出版的波拉尼奥作品,如《荒野侦探》、《护身符》、《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美洲纳粹文学》、《遥远的星辰》等,再讲讲波拉尼奥这个作家。“亲爱的王子”,是波拉尼奥喜爱的诗人尼卡诺尔·帕拉给他的一个称呼。波拉尼奥的作品除《2666》之外,我还翻译了其他几部中短篇,还有一部叫波拉尼奥短篇小说集还没有出版,把这些作品串联起来看波拉尼奥其人的话,有几个个人感受:
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个人的痛苦经历,和对这些痛苦经历的思考,以及转化为文学表达形式的工夫,让我感到惊讶、佩服。因为这个痛苦这个问题,很可能病的时候很难受,很可能想七想八,但是在贫困、病痛,还有外部压迫这些问题面前要进行思考。波拉尼奥不是思想家,不应当要求一个文学作品非得要有什么什么思想,但是从文学表现形式上来讲,要把这些个思考表现出来,他的一系列作品很成功的做到了。波拉尼奥这个人很显然是文艺青年,从早期的生活来看,所谓早期就是到墨西哥那段,和诗人们和青年文学爱好者们在一起聚的时候,还真的是一种玩闹阶段。我忽然想到了北漂的文艺青年,到北京来大家聚一聚,玩玩文学。据说后来成立了什么组织,但是从其他作品上来讲,我看波拉尼奥还是有他自己的思考。他这些思考是在墨西哥已经开始了,到了墨西哥以后他这些个思考就逐渐逐渐成熟了
他给我很突出一个印象,就是他文学技巧的功底很深。这里就有一个很好的优势了,就是说虽然法国、意大利、美国文学上老出现所谓新潮,但是你那套我知道。比如说前不久我翻译了阿根廷作家皮格利亚的《艾达之路》,是写的美国的学校生活,没有写拉美,但一个拉美作家写美国教授的心态可以写得那么深刻。这就值得我们思考了。如果是波拉尼奥一个人,还可以说是特殊性,但是有一批作家,而且时间比较早了——像墨西哥作家费尔南多·德尔·帕索写《帝国轶闻》,就说法国入侵墨西哥的事,他骨子里就是说,你们法国文化到了我们墨西哥就得败下来。所以他既有“我是在经济文化上不发达,但是我肯向他们学习”,但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有超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个超出部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米·安·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参加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古巴作家卡彭铁尔,参加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但是一回到拉美,阿斯图里亚斯回到危地马拉,卡彭铁尔回到古巴,就明确指出,超现实主义这一套在我们的土壤上行不通,超现实主义追求的东西在我们这儿来讲就是现实。所以这个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问题,早在1922年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在他短篇小说里,中国也有介绍,就明确提出来我们借用了一些意大利画派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后卡彭铁尔在《这个世界的王国》的序言里鲜明地提出来“魔幻现实主义”这个宣言。魔幻现实主义到了波拉尼奥手里,为什么不是继续走个这个所谓的流派?这就是拉美作家的特点,不是脑袋跟着主义或理论走,而是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遭遇进行反思。他们对美国和欧洲文化的熟悉程度是非常令人惊讶的,而且从全球的作家熟悉欧美国文学发展的情况来讲,拉美作家真的是做了很深的工夫,在那儿生活,在那儿写作,在那儿出版,大家都知道,几个拉美作家的出版都不是在拉美本身,《2666》也是在西班牙,这本身就告诉我们这个作品的分量、质量、影响。
止庵:我稍微补充一点点,波拉尼奥的叙述方式跟前面的作家都不太一样,实际上他的叙述真是很奇怪。第一是很舒服,很自然,把描写和叙述融合在一起,不太讲究渲染或者铺垫。他的叙述方式使我想到以前读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叙述到一个人之后就开始讲这个人的事,又回来继续讲原来的故事,碰到那个人又开始讲那个人的故事。波拉尼奥实际上是一个把他之前的这些小说的章法都打破了的一位作家。
再就是他叙述的冷静、克制,这个也是和他的前辈作家很不一样。其实马尔克斯也不是这种写法,虽然他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写法和《百年孤独》《族长的秋天》或者《霍乱时期的爱情》都不太一样,但总的来说马尔克斯还是写得比较隆重,比较渲染。波拉尼奥实际上已经把这个都放弃了,更接近我们说的“零度写作”,一个说了很多遍的老词。他的这个态度我刚才其实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刚才有一个朋友问我我顺便回答一下,我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一个客观叙述。什么叫做不仁?就是一视同仁,大批的人死了跟没死一样。
我觉得在波拉尼奥写作的时候,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已经走到末路了。《百年孤独》当然是不得了的杰作,《族长的秋天》、略萨的《绿房子》、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在最早的大批作品里边,这种魔幻现实主义非常有活力,确实是对整个世界的冲击,我还记得当年《百年孤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的作家们是如何受到触动,从而产生了一批写类似这样作品的作家。但是这个玩意儿不能没完没了的用,而且不能学,所以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是把自己给葬送了,不能再这么写了,而波拉尼奥正好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作家。你看在《2666》这本书里边,写过不少梦境,但是这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它跟魔幻现实主义那套写法完全不一样,他已经不这么写了,时代确实也不允许一代一代的作家没完没了地去制造这种作品,所以就有了波拉尼奥。
范晔:先回应两句止庵老师的“天地不仁”。我个人倒是觉得天地不仁用来形容《百年孤独》的那种叙述口吻更加契合,我觉得《2666》好像也有这种很高高在上的超然,但不是那么明显。就像序言里提到,根据波拉尼奥的设计,《2666》本来就是以《荒野侦探》里的主人公之一贝拉诺作为叙述者的,而且我觉得在他的这种叙述中,当然我基本上同意止庵老师说的是非常冷静的调子,但是我觉得个别地方也能看到一些亮色。
我们还是举第四部的例子,因为第四部是最残酷的一部,但是就在这样一部里面也会有一些很有人情味的描写,比如说第四部分的最后几句话,他是以圣特莱莎的圣诞节的这样几句描述来结束的。几年前读这一部分的时候,我基本上把这个当做是一种反讽,圣特莱莎的圣诞节像往年一样过,大家吃吃喝喝,好像更能体现冷漠,但今天我有了不一样的阅读的感受。他说连最贫困的街区也有欢声笑语,我反而觉得这里面有对人性光明的希望,因为他觉得圣诞节这样的一些节气、节日,它代表的温暖可能是更加恒久的东西。即使有一些像黑洞一样的黑暗街道,这个当然我们可以很容易跟邪恶作一种比喻,但是他也说有一些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欢声笑语,能够成为大家不至于迷路的信号,我个人感觉里面还是有一些隐含的希望在的,虽然不知道这个笑声会从哪里传出来,就跟《护身符》的结尾一样,有一些年轻人尽管走向深渊,但是他们是唱着歌走向深渊的。
我个人觉得谈到波拉尼奥其人至少绕不过去两个关健词:一个是地名就是墨西哥,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好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帕帕斯基亚罗。如果说我们要是给波拉尼奥的一生写一部成长小说的话,可以说墨西哥是其中最重要的舞台。我们会发现,自从70年代末离开墨西哥去了欧洲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墨西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祖国智利他回去过两次,但墨西哥一次也没回去过,甚至有几次他已经准备好行李了但仍然没有回去,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回不去当年那个墨西哥了。
我们也说过《2666》最后一个词就是墨西哥,波拉尼奥的无论是文学还是诗歌里,都大量地出现了墨西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其实他在不断的写作中一次一次重返他的青春现场。我记得有一次他说过,他当年在墨西哥看见过一个涂鸦说:波拉尼奥滚回圣地亚哥去,带上你的圣地亚哥滚回圣地亚哥去。当然第一个圣地亚哥指的就是智利首都,第二个当然就指是他的朋友。我们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在76年、77年离开墨西哥去了欧洲,马里奥后来还去了中东,而且据说他们离开的原因都跟失恋有关系。但是几年以后,马里奥做到了波拉尼奥想做但是没有做到的事,他回到了墨西哥,死在了墨西哥,而且继续写诗,这一点波拉尼奥后来也没有做到。可是他回去的时候,当年的这些“下现实主义运动”(即“现实以下运动”)——我喜欢把它翻译成下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做一个对应——其实那时候成员可以说都已经分道扬镳了,大家各干各的,干一些可能更实际的事情,这场运动渐渐被遗忘了。
但是马里奥·圣地亚哥还是那个马里奥,据说他是可以在任何时候看书,走路时候也看书,洗澡时候也看书,而且边走还边写,他过马路从来不看路,所以他有一次被车撞了,他从此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还得随时拿一个手杖。波拉尼奥其实也非常关心他的好朋友,虽然没有再见过面,就常常给他写信,说马里奥收到以后立刻在原信上回复,结果回复完了之后他很少记得还要把信寄出去。但是波拉尼奥说,没关系我知道他会看我的信。98年的时候,就在波拉尼奥完成他的《荒野侦探》的第二天,马里奥·圣地亚哥在大洋的彼岸在墨西哥街头就被车撞死了。所以波拉尼奥说,马里奥知道自己会成为尤利西斯·利马,但是他没有看到。波拉尼奥1977年的时候给朋友写信就说过,我所有的剧本都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就是马里奥·圣地亚哥,他是我所有梦想的主人公,可以说马里奥·圣地亚哥这样一个诗人就是波拉尼奥想成为但并没有成为的人,他是波拉尼奥想象中的一个完美的诗人形象。所以我们说波拉尼奥有自己的《荒野侦探》,但是马里奥·圣地亚哥也有他的代表作——就叫做马里奥·圣地亚哥的一生。
赵德明:我最后说一点,关于《2666》和波拉尼奥其他作品的亮色问题,这个作品里面,像爱情、亲情、友情的确都有笔墨。问题在于,这些亮色衬托的是什么?衬托的是一种很凄苦的爱,很悲惨的结局。大家可以看智利教授那一段,可以看阿琴波尔迪在战后也谈过恋爱,也可以看三个文学评论家之间的友情甚至爱情,但是是怎么落墨的?用这些个爱情、友情、亲情衬托了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就不多说了。

剧照
12小时的马拉松戏剧《2666》
赵德明:我只看了天津大剧院的那个介绍,我感觉从简短的文字介绍来看,这个事就不得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看过这样一个大剧,一下子看12个小时,然后把方方面面的艺术再现到舞台上,活灵活现地演一遍,不得了。所以我衷心祝愿《2666》落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能够成功。
止庵:我对《2666》搬上舞台,其实第一个担心的是我自己的身体扛不扛得住,但是我一定坚持把这个剧会从头看到尾,这对我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挑战。这个小说搬上舞台,我其实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很多难度,它是全景小说,这一点怎么搬上舞台?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第二点就是作者这种很冷静甚至到冷峻的叙述怎么搬上舞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表演比起叙述,怎么说也是一种更不那么平静的东西吧。第三点我担心的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事,特别是第四部分,怎么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确实对我来讲,几乎是一个不是很可能的事,但是我确实充满期待,因为越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世界上越有人能够去做。
范晔:我觉得要把《2666》这样一个巨著搬上舞台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像我几年前看的一场一个舞台版本的《百年孤独》一样,它是一个独角戏的这样一个形式。虽然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情节,但它用独角戏的形式来呈现,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是一个呈现《2666》的思路。当然还有一种思路就是这种,我们以全景戏剧对全局小说,以疯狂对疯狂,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这个12小时版的《2666》,如果是2666小时版的那就更好了。
提问环节
凤凰文化:如今“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向汇流,那么波拉尼奥是在什么坐标里、怎样定义自己的作者身份的?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拉美文学?
赵德明:当代的拉美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问题太大,我只从我切身的经验来讲。在翻完《2666》之后,我又翻了波拉尼奥其他的四、五部中短篇小说,又翻译完了古巴作家莱昂纳多·帕杜拉的《爱狗的男人》。大家都知道,古巴作家局限于古巴岛那样的政治、文化语境,我们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他们能写出什么?但这部作品让我拍案叫绝,他居然写到了西班牙的历史,前苏联的历史,墨西哥的历史,托洛茨基被杀的经过,和古巴一般老百姓的境遇。作家的视野不关注历史写不了这样的书,不关注国际焦点问题写不了这样的书,眼睛不看着社会现实就更写不了。你在那样一个环境底下,对周围人如果是麻木不仁的话有可能是与无动于衷。
从我经手翻译的拉美文学作品来看,最早翻译拉美小说是从智利作家布莱斯特·加纳的《马丁·里瓦斯》开始的,这个作品写的是1860年的事,下限到了2015年古巴作家帕杜拉的《爱狗的男人》,这么长的历史里,拉美文学的叙述方式在不断地翻新、变化。趁机说明一个误区,在马尔克斯《百年孤独》最红的时候,在拉美文学史中地位相当的还有其他的几位作家,像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而且当时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米·安·阿斯图里亚斯等老一辈文学大师还都健在。所以当我们在谈拉美文学的时候,不能就某一部作品或者某个人来谈,那就闹大笑话了。从拉美文学史的发展变化来看,它总是有一批人、一代人,而且是旗鼓相当。魔幻现实主义最红的时候,结构现实主义也很红,现实社会主义也很红,心理现实主义也很红。我们对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乌拉圭的一位专门写心理现实主义的作家的介绍很不够,其实他在很多方面都远远超出了前面那四位大红大紫的作家,所以略萨就说我们欠奥内蒂的。
在同一个时期,有前辈当代,同时下一波又出生了,波拉尼奥就是下一波,所以他这一波有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题材、故事、结构都在不断翻新。我刚刚翻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换皮》,在当代文学史上评价很高,被认为是实验小说的典范,和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不相上下,那里面的时空、故事、人物、人称交替对换,简直让你目瞪口呆,我在翻译的时候极为痛苦。不断翻新、不断实验、不断否定、不断创新,远的不敢说,这至少是20世纪这一百年来拉美文学的特点。博尔赫斯是大师,但是没有博尔赫斯主义,大家跟他走,马尔克斯很了不起,也没有说他这一派,连他自己都在不断地花样翻新。他们懂得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新,不搞划地为牢,不是跟着谁,而是要超越,波拉尼奥在好几篇文章里面都有讲这个,他对所谓的大师级的诗人、作家是很不以为然的。
问题:范老师,你觉得波拉尼奥的创作和科塔萨尔的创作有可比之处吗?
范晔:首先波拉尼奥对科塔萨尔的仰慕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很多地方都有明确的表达,比如他在访谈里说,我们在这儿谈论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就好像蚂蚁在谈论大象经过的脚步声。而且他也说了很多他在遇见科塔萨尔时候那种作为粉丝的感受。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科塔萨尔的创作对波拉尼奥创作可能性的影响。科塔萨尔晚期有一个短篇叫做索论迪纳美的启示录(音),主人公也叫科塔萨尔,是一个记者,他去尼加拉瓜支持当地的解放运动,参观了一个很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公社,里面那些农民自己自足,还进行自发的艺术创作,他拍了很多照片。回到巴黎以后,他把这些照片用幻灯片的形式打到墙上来看,结果他忽然发现他当初拍的那些照片,这样打出来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拍的是一个很欢乐的农民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结果打出来以后那个脸忽然变成了饱经酷刑的年轻人的脸,或者是独裁者、警察这些形象,完全不是他当初拍的形象。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作为平行文本来参照《2666》,特别是《2666》第四部分的那些罪行描写,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关于文学的表现,文学面对恶的功用,甚至传统的模仿论,都有很多可以阐发的空间。
问题:为什么说《2666》超越了《百年孤独》?之前的讲到《2666》不再局限于原有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这应该算其中一点,但还有吗?
范晔:我试着简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并不是非常认同这种所谓的“超越”这样一个话语模式,有点像我小时候老跟小伙伴讨论剑齿虎厉害还是现在的狮子老虎厉害?这是个很有趣的讨论,但是可能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文坛确实存在着影响的研究,用布鲁姆的话说是“影响的焦虑”这样一种考察。
具体到波拉尼奥和爆炸一代包括马尔克斯他们之间的关联的,当然说大家可能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波拉尼奥对爆炸一代颇为不屑,这里面表现了文学上的弑父情节,因为必须要走出巨人的阴影才能建立自己的形象。但是你要真的认为波拉尼奥完全是这样一个很高傲的单薄形象,你就低估他了。他在不同时候也会有不同的强调。在很晚期的访谈里面,他就直接提出他对爆炸一代实际上是非常尊重的,他说略萨和马尔克斯的小说都有着千门万户的结构,在这种文学的等级里面他们永远是最高的,他说远远把我们这一代甩在了下面,这都是他自己的原话。更不用提他对同样是爆炸一代里的科塔萨尔是非常推崇的。当然他也提到,他有时候对略萨和马尔克斯有一些看法,他们都有公众人物的一面,所以在这方面波拉尼奥对他们的看法确实是有所保留的,他觉得略萨曾经竞选过总统,马尔克斯也是非常热切地喜欢跟权力者在一起,他对这些人的这些方面确实有所保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看轻文学前辈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就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一个完美的小说。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责任编辑:冯婧 PN04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