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分享会:来一场新新文化运动,新的鲁迅就会产生吗?
2015年09月29日 09:12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凤凰文化
有鲁迅的时代不只有鲁迅,这是鲁迅能够产生的前提。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鲁迅,更需要一场“新新文化运动”。若真如此,我们收获的将不止一个“新鲁迅”。
导语:“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去往何处?”9月26日,凤凰文化携新书《洞见》做客上海季风书园,与文化评论家朱大可、王晓渔、马小盐共同分享关于大众文化批评和当下思想文化现状的观察与思考。
马小盐认为中国人不接受真正的文化批评,一个是编辑的问题,一个是大众的问题。媒体人掌握话语权,知识分子退居二线,而媒体人的水平又良莠不齐。朱大可则认为大众的问题在于,年轻一代要求阅读解决他们的焦虑,所以宁可喜欢轻松的事物,喜欢于丹式的鸡汤,这样会觉得世界是美好的,生活是有希望的。而这种对正能量的全面追求,在王晓渔看来恰恰是一种负能量,反而没有希望。
提起批评,国人总会想到鲁迅。三人对此有一个共识:有鲁迅的时代不只有鲁迅,这是鲁迅能够产生的前提。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鲁迅,更需要一场“新新文化运动”。若真如此,我们收获的将不止一个“新鲁迅”。同时朱大可也强调,对于文化批评而言,鲁迅不应该成为一个样本,他只是一种独特的风格,但不是最好的、最值得追捧的风格。
以下为新书分享会完整实录,以供未能到场的朋友阅读讨论。
主持人:感谢到场的朋友。很巧合,昨天恰好是鲁迅先生的诞辰日,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谈论一个主题叫“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去往何处?”。首先我想就三位嘉宾的评论风格给大家介绍一下。

左起为主持人徐鹏远,嘉宾:朱大可、马小盐、王晓渔
大可老师是久负盛名,很多朋友都读过他的文字。我在朋友圈里对大可老师的评论有一个比喻,因为我也是本书的作者之一,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就把自己忝列其中了,“我等写评论好像操两把板斧,乱砍乱杀,大可老师则是挥一挥衣袖,耍一套黯然销魂掌,看似轻飘飘,但其实威力很大”。晓渔老师是在上海教学,之前也一直写评论,从事评论的研究。从晓渔老师的为人和文字笔锋来看,如果也用一个江湖人物来形容他,我觉得是令狐冲,笑傲江湖,追求自由。文化批评界有时候跟相声界一样,女性作者从事批评相对来讲数量还是少一些的。也用一个武侠人物来比喻小盐姐的话就是黄蓉,伶牙俐齿。当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觉得我比他们三个人都厉害,我是东方不败。
今天这个题目其实是依托于凤凰文化的同名栏目“洞见”,我们一直在做大众文化的批评,现在已经做到了200多期,这是我们一个阶段性精选的集结。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每个在公共平台都可以发声,每个人都是评论家,我们似乎不太像过去那么需要听到专业的批评,或者对某个现象的观点和阐述,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专业评论?同时,今天的专业评论也因为各种原因呈现了一种复杂的面相,我们曾经把鲁迅树为一个标杆,称之为是“匕首和投枪”。当然这种政治化的语言我们也可以考量。但毕竟鲁迅曾经树立在那,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又该去往何处?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另外一个鲁迅出现?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就请三位嘉宾与大家共同聊一聊这个话题。

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去往何处?
年轻一代要求文化产品解决焦虑
主持人:我之前看过小盐姐对我们新书的观点,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西方的大众文化批评领域里,从事批评的其实是一些学院知识分子,甚至是大哲学家。在中国,当然也不乏晓渔老师,大可老师这种学者,但是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媒体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无所不谈,但总归是缺乏雄厚知识框架的支撑。中国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是有没有可能出现西方的批评状况?
马小盐:西方文化批评,加拿大的多伦多派、德国的法兰克福派、法国后现代、意大利的阿甘本,四个派别都是哲学家。大家都知道萨特、福柯、巴尔特,现在的话朗西埃都是非常活跃的。像齐泽克把拉康的心理科学、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等哲学的理论都运用在批评里,福柯、巴尔特、鲍德里亚他都批评过。中国人不接受真正的文化批评,一个是编辑的问题,一个是大众的问题。像凤凰编辑还是水平很高的,他接受你这个东西,然后你的一部分才能进入大众的视野。普通的媒体编辑可能不懂专业文化批评的术语,或者是需要一种大众化,会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或者是大众觉得太深奥,齐泽克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但是读这个人的批评可能很少。齐泽克前段时间来中国演讲,到后边就是坐五六个人。媒体人认为话语权掌握在他们手里,知识分子退居二线,只有编辑,像凤凰文化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才能坐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很多东西是半桶子水,只抓住一句话就把整个理论推翻,说伯格、阿伦特根本不值得读。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哲学流派,任何人的理论都会有缺陷的,再大的哲学家也有漏洞,不能因为小漏洞就反对一个体系。我对中国的文化批评不太乐观,因为整体环境就是这么一个氛围,我在凤凰发的文章,骂的人是非常多的,而且往往是不懂的人在那儿骂得非常难看。
主持人:其实中国的当代的大众文化的一个批评,我想大可老师应该算是一个开启之人,就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进行大众文化的关注,并且写出了很多的,有的已经集结成书的一些评论的内容。刚才小盐姐已经说过的中国现在批评面临的一些现状,在您曾经刚开始进行批评的那个时期是怎么样的,您这么多年一直走过来有什么变化?

朱大可
朱大可:我的第一篇大众文化有两万字,叫做《甜蜜的行旅——论余秋雨现象》,结果被书香,百城改成了《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现在看来还比较性感,但当时就觉得不够严肃。那个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做大众文化批评的指标。后来季风出了我的《流氓的盛宴》,实际上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扩展本,应该算是当时比较早的文化批评的专著,这本书到现在是不可能再出来。那个时候媒体实际上不太关注大众文化,还是在精英的层面上来思考和观察。直到05年,中国大众文化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称之为中国大众文化元年,那一年出了两个伟大人物,一个叫李宇春,另外一个是芙蓉姐姐,一下子把这种大众文化以一个半民间的方式推到公共的视野。芙蓉姐姐出来以后,上海的《新闻午报》,冒天下之大不韪发了七个版的报道,我们看到全傻掉了。大众文化是一盘好菜,我们应该好好地去吃它。以前不吃是因为它太贱了,现在觉得真的是好菜,因为大众喜欢。
大众文化出来以后,大众文化批评才开始慢慢出现。中文系那些文学评论批评学者开始转型,文学系开研讨会谈论文学批评的转型和大众文化批评。文学评论家转向文化批评,老一辈的评论家认为你们是不务正业。我个人认为,文化批评最重要的队伍必须从文学转过来,否则很难转型,它没有扩充的配置。从哲学这条路径基本没有可能,到今天为止,中国所有的哲学系几乎都不会超过三个搞文化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转型,反而是文学这个领域做了一些转型,但是文学的工具是不对的,它还是运用文学批评的一些工具,如文学概论、美学,这种工具来做文化批评完全不对。实际上文化批评的背后是西方后现代哲学而不是文学理论,这是一个错乱。
第二个错乱就是媒体,媒体人用时评的方法来做文化批评。错得更远,时评是一些非常零碎的没有工具的分析,文化批评领域实际上是非常混乱的。我和晓渔所在的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就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以文化批评命名的研究机构,到今年正好10年,开始的时候势头很旺,最后衰败。而且这个衰败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言论的环境越来越缩紧,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媒体批评取代了原先更加批评原型的这种批评。一种主流的批评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比较正常的状态跟世界接轨的话,它就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包括《洞见》,严格来讲真正属于文化批评的非常少,大部分还是文化时评的出现,当然哪怕有文化时评我觉得也蛮好的。
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原因,80后和90后总体来讲更喜欢比较轻松的生活,更爱看《花千骨》和《煎饼侠》。《捉妖记》我觉得画面、视觉,包括它的情节处理都还不错,里面的动漫人物很萌,抓住人性本质性的东西,它有一种人类共同价值观在支撑着。从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到公众的趣味,一般人们不大喜欢我们这种人。年轻一代更喜欢轻松的事物,因为他们的生活很紧张,尤其是80后要处理各种家庭事务,他们认为文化产品最重要的阅读是解决他们焦虑的问题,你们搞得那么紧张,我本来很焦虑,你让我更焦虑。所以这种阅读对他们来讲是有障碍的,不是说看不懂,而是他不需要这种东西。他们宁可喜欢于丹式的鸡汤,让他们觉得世界是美好的,生活是有希望的。
主持人:我想追问一下,就刚才您谈到了这个中国从事文化批评的只能从文学系来进行转化,这是为什么?因为这在西方其实这是搞哲学的人干的事情。
朱大可:因为西方的学院派跟他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得非常好,你比如说苏哈·萨卡德对摄影、电影的评论。我们现在是哲学系学的那些方法和工具是没有办法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完全是一堆教条。他们掌握了很多的工具,但是他们认为工具就是教学资料,是一些枯燥乏味的东西,不知道如何转化。他们把海德格尔挂在嘴上,又不知道使用海德格尔的美学来分析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反而上海的诗人在做房地产文案的时候把海德格尔的名言用进去,叫“诗意地栖居”,后来被全国房地产夜疯狂抄袭。这不是哲学系人干的,这是一个诗人干的。哲学系真的没有办法进行转化,这跟我们学科体制有关系,我们的学术整个是一个教条化的僵死的体系。
中国学者对批评有大误解,鲁迅不该成为样板
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晓渔兄,就是同济大学的文化批评研究所05年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自媒体时代其实还没有充分地发展起来,后来有了微博,紧接着有了微信,越来越多发表观点、表达态度的平台。似乎吐槽就是大家各自从事的一种批评,而且这种吐槽里面不乏有才之人各种脑洞大开的调侃,语言好像显得也很犀利。那么您觉得这个能不能算是一种正确的批评?或者说在这样一个乐于表达的状况之下,专业批评它还有没有必要存在,如果有它存在的必要,那是什么呢?

王晓渔
王晓渔:专业批评我想应该一直有存在,不是存在什么时代就成了突然没了。说到网络的自媒体,我倒不认为是2005年以后的,其实网络时代就开启了自媒体时代。我最初上网是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往往是很多时候对思想化非常感兴趣的,每个人办一个网站,互相之间连接、交往,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自媒体。到了后面很快就进入到一个新时代,BBS时代,很难说是自媒体,但那时候是有公共空间的。2003年以前的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个人的自媒体,然后BBS构成公共空间,两方相对而言平衡得都很好,一方面可以有公共空间,一方面有自己的媒体表达。后来有博客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反而到了两微时代, 140个字所能表达的东西是有限的,与博客有非常大的差异。我个人挺喜欢博客时代,我就某本书写一些感想,而可以完全按照个人理念来写,不用考虑任何读者的。而且到了最后会发现,你完全不考虑读者的写作,反而会有很多读者看,读者会恰恰跟你的趣味非常接近的。绝对数量未必那么高,比如说我的文章如果在门户网站发表的话,那一般有的时候会有几万几十万看,但是在个人博客上面有可能仅仅是几千人看。但是我个人通常觉得那个几千甚至是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它的对象跟我们出就某本书的版本有非常深入的讨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可能对谈到自媒体时代,我是反而更加喜欢2005年,甚至2007,2008年以前的那么一个状态。
媒体刚刚几位其实都谈到了,媒体一个非常大的职业的要求是要求有时间,时效性。两年来给凤凰文化也只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文化批评跟时评确实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时评的运动模式确实是非常快的模式,我写作速度太慢,我经常那个时候是下午四五点钟收到电话,八点钟之前交,一篇一千四五百字的文章,我一般是用满两个小时的,很多时评的作者是可以半个小时写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时评往往是表达一个观点的立场,但是你没法来比较充分地来提供我为什么持这个理论。文化批评的“批评”不仅是说赞同或反对,可能我们特别认同的某个理论,当然有很多是批评的,但更多的是包含分歧的。文化评论,字数长一点的要稍微慢一点来写作,相对之下,凤凰文化可以容忍我们稍微慢一点来写作。但是这有一个内在的我们说的矛盾的地方,比如说大家在提到美国像桑塔格这些文化批评的,那时候没有网络,也未必是报纸,有的时候是一些杂志,但是相对而言他的空间很多,网络发展也非常好。
主持人:我们一听到批评总感觉很恐怖,好像一涉及到批评,一定就是一个不好的,否定的。当然批判就更让人毛骨悚然了。面对这样的历史语境,我们今天再从事批评时,我们往往就会想到鲁迅。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可老师,就是当我们探讨批评的时候会想到鲁迅,这到底准确不准确?就是鲁迅的写作是不是已经代表了中国白话文的批评体系里的唯一,还是说鲁迅只是其中一部分?鲁迅算不算一个大众的批评?
朱大可:我觉得对鲁迅要有一个更加综合的看法,既不要一味地褒扬,也不要一味的贬斥。现在互联网分两种态度,分裂得非常厉害,要么就把鲁迅从中学课文里删光,要么就是把鲁迅推到神座上。其实鲁迅就个人来讲有很多弱点。我把鲁迅的杂文分成两个时期,一个是《野草》时期,也就是北平时期,那个时候特别优秀。第二个时期是上海时期,即殖民地时期,带有很多的个人的情绪。所以我不太认为鲁迅应该成为文化批评的一个样本,他算是批评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但不是最好的、最值得的风格。其实我受他影响非常大,因为小时候没有其他的样本,从小学的就是鲁迅。以前有媒体采访我,我说鲁迅就是我的精神父亲,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会重新地看他,汲取他的那些优点,鲁迅的那种洞察力非常精彩,但是过于情绪化的我们要避免。现在我非常谨慎,写东西就是针对事情,尽量少针对人。
刚才那个标题,被改了以后就是对人家进行人格性攻击。我原来叫《甜蜜的旅行——论余秋雨现象》没问题,一改就出问题了。后面这些年,越来越警醒,不要把批评变成个人意气用事的工具。批评本身是什么,刚才你讲了批评的含义是研判、分析、解读、阐释,而不是政治概念里的攻击和否定。毛主席说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自己骂自己再骂别人,就会引到这种非常狭隘的界定中,而实际上它就是阐释。所以为什么西方哲学家它会直接走向批评这个道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障碍,而中国学者对批评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直到现在那些做时评的也会生产这个问题。
所以做文化批评,不仅是对当代文化,对大众文化,对古典文化为什么不能批评呢,就是古典研究。它实际上是一个可以广泛的领域,但现在我们把它狭隘化了,只谈《小时代》,只谈《花千骨》,只谈分歧,这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文化批评在认知上要调整的一个转变,第二个是要更广泛地扩展它的批评对象,这样它才会对整个中国文化50年,100年以后的复兴起一点微薄的作用。
主持人:谈到鲁迅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人,当然这个人是被捧出来的,所谓“可能成为下一个鲁迅”的韩寒。刚才晓渔兄提到了,在两微时代之前还有一个博客时代。他通过博客这个平台,写了很多个批评学的文字。我个人觉得他在那个时代可能引领了一股媒体上文化批评的面貌,甚至说一种行为的方式。小盐姐也写过韩寒和他另外一位说不清的同龄人的事情。那今天在现场可不可以说一下就是韩寒对文化批评起了一个什么作用,是让更多人对批评感兴趣,还是说其实是毁东西?

马小盐
马小盐:前几年是推动,韩寒的批评属于社会评论,也就是时评,他扮演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家喜欢他是因为他敢说真话,后边他拍电影去了,也就没有了。那几年整个博客上面是有他的功劳的,推动互联网全民的反思,他传播的基本就是常识。那个只是文化批评的一部分,社会现象的东西,那时候我还挺喜欢的,现在就不用多说了。
主持人:晓渔兄刚才提到网络时代的时期划分,大家对于自媒体的认知为什么在两微时代变得这么强烈,大家在熟人网络里发表观点,他可能觉得每一个观点都能受关注。但微博就是一个大很多的海洋,到了博客时代可能只有韩寒的博文会得到多少点击,我的博文就没人看。最早时候个人以外的网站,那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到的事,这涉及到参与的问题。专业评论给大家的观感就是什么呢,他是知识分子写作、媒体发表的,甚至是媒体人在做的东西,大家可能有一种被代言感,大家已经被代言得太久了,现在都在强调个性。那专业评论和读者受众这个矛盾您怎么看?
王晓渔:应该没矛盾吧。比如我要表达什么观点,所谓的知识分子要表达什么观点,公众要表达什么观点,在网络时代应该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不管我前面说的个人的网站时代,还是博客时代,还是BBS的时代,我们都可以举出他有可能此前是一无所知,但是因为他的言论被大家关注着。所以我认为网络希望更多的开放空间,而不再限制一个准入证。比如传统我们说的纸媒时代,纸媒时代确实是存在一个比较严格的机制,但我们说的网络几乎不存在这个范围。
正能量充斥也是一种负能量
主持人:但是现在大家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你行你上”,你觉得这种逻辑是正确的吗?
王晓渔:我倒是觉得应该区分开,公众的评论只要没什么违反法律的应该都可以,比如我的文章下面有各种奇怪的评论,我觉得都没有关系,这本身就是言论多样的一个呈现,我们不能希望一个所谓的言论开放是只有好的言论,没有坏的言论,如果只有好的言论,就不是言论开放,这是很明确的一点。
主持人:但是这种你行你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批评一个东西好像是等于是对它否定,那铺天盖地都是这些那谁还去干东西,你说这电影不好,你自己拍一个好的。这种逻辑的来源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大家求建设的心理所导致的呢?
王晓渔:批评与建设在我这儿同样也是问题,但不是一个操作性东西。我一向认为文化批评的价值就是参与社会建设。我觉得批评就是建设,两者之间很难区别,很多批评的东西经常很有正能量,全是正面的就很有负能量、没希望,如果大家都在批评那就还是很有希望的,说明大家有期待。如果说批评没有建设性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批评呢。
主持人:那小盐姐你怎么看?
马小盐:挨骂挺正常的,因为有的东西他不懂,中国人比较焦虑,现实生活不好,就在网络上发泄他的不满。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都要排泄,别的地也不能去。刚才说起鲁迅,中国人爱塑造偶像,完全是两极分化,要不这个人非常好,要不这个人就是坏蛋,就包括电影,要不就非常好,要不就是烂片。事实上批评是好的我点出来,坏的我也点出来,就阐释一下,整体拿这个哲学理论系统地阐释一下,走极端不是批评。
今天所说的常识有可能是反常识的
主持人:但是走极端会产生观点,这个时代大家好像患上了一种观点饥渴症。我不知道朱老师有没有被人这么饥渴的要求过?
朱大可:文化批评确实也有粉丝,好像我们成了他们内心的代言人。心理学上讲经验的投射,我个人对一个东西的喜爱,或者是对一个东西的不满,你说到我心坎上去了,这个他就喜欢,你说的越激烈,他就觉得你说得越好,很容易走到这个误区。80后曾经出过一个批评家,他模仿了《十作家评判书》,针对80后作家写了一个《十作家批评书》,骂得狗血淋头,那不是批评。他认为只要骂得越狠就越容易出名,结果这本书根本就没有出来,只是在互联网闪了一下,整个人就消失了。
不是说你越激烈就能够越博得众人的青睐,相反而是你越正确,真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说到点子上。如果不能说到点子上,谩骂一点意思都没有,沦为大众吐口水的状态。互联网上那种评论,我觉得只要不是谩骂都没问题。但如果涉及到人格侮辱就有问题了。我以前一篇文章里讲偷情,不行,后来改成通奸,OK。真正的秽语秽词反而不过滤,不仅不过滤,其实是一种助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互联网文明的制度化很简单,把过滤敏感词的精力转移到这上面来,中国互联网就一点问题就没有了。所以我不太赞同所有对你批评的批评都接受,凡是谩骂我的一概拉黑,但是你批评我,随便怎么你批评。这个里面有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如果什么时候中国的互联网建设成这样一种良好秩序的话,中国就非常有希望了,软实力就已经形成了。
主持人:我发现眼下的评论,包括很多个人公号的评论,从总体的面貌来讲,还是否定或者说调侃居多。除了大家要宣泄,是不是在操作性上这种评论的困难也会更少?
王晓渔:作为作者,每位作者一定都想到我的文章是不存在的。每个人写的东西都会有一个对象,像我的文化批评未必是写给公众看的,我还是写给受过基本训练的、和教育的对象来,因为如果反复讲给公众是非常低效率的。我今天抱了一本潘恩的选集,他的《常识》与我们日常所说的常识有很大的区别,潘恩所说的常识是经过大家反复讨论之后所形成的关于价值观的共体。那我们所说的常识是一个百科知识,比如说这个菜和另外一个菜之间会冲突。我们今天所说的常识有可能是反常识的。所以我们文化批评的对象,同样用常识这个词指的对象就会不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建立常识个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说的ABC是指的常识有很多冲突。我觉得没必要讨论基本的一加一是不是等于二,虽然现在好像有的时候经常说一加一等于三,我还是觉得讨论一加一等于二特没劲。
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源自反智传统

观众在认真记笔记
主持人:刚才谈到常识,这个时代最多常识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小盐姐举出了这么多的西方学者,其实他们都可以算作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他们在学院里边既教书又从事研究,另一方面们积极走出学院参与公共性话题。但是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堪的形象。我们在座的三位都不是被污名化的公知,应该算做旁观者清。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分别说一说。
朱大可:现在基本上,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已经不再成为知识分子的优势,恰恰相反,在很多大众看来你没事儿瞎掺和啥,又不是你的专业。当然也有一些公知确实比较随便,有时候会犯一些错。但是我觉得从整个世界的范围来讲,确实分两种知识分子,一种是私人知识分子,一种是公共知识分子。虽然知识分子严格来讲不能算是知识分子,只能说是知识人士。比如说他是一名教师,殷勤地教着他的学生,不在公共领域说话。西方讲的知识分子,它一般更完整的名词叫批判知识分子,就他一定是站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来说话的,这才叫知识分子。所以严格来讲只有中国才会把知识分子分成这两种,在西方知识分子只有一种,就是批判知识分子。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权利在一个更阔的公共空间有这个责任来发表他的看法,这是他的天然的责任,如果你不履行这个责任你就自己出去。但是中国还有另外一种“知识分子”是不发声的,那个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被污名化。
马小盐:我先接一下刚才影片没有好影评的,主要我觉得是影片已经到了文化领域了,文化批评肯定要有一部分后现代的哲学理念,就和手术刀一样,没有这个你就没法下手。好电影要涉及到哲学的东西,时间、空间,好多哲学理念影评人不懂,所以他只能看到坏影片骂,好影片挑刺,不知道该怎么分析。齐泽克的影评是非常漂亮的,心理学、时间、空间、镜头的移动、长镜头、短镜头,这些很专业的东西他们不懂,我感觉是他们不读书。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叫《都灵之马》,非常漂亮。但是中国互联网没有一篇出彩的评论。
然后我再说一下公知这个事,有一段时间还公知挺受欢迎的。但是到后边就养了一帮子人,故意的去比如说你批评一个社会现象,下边就会有人引导人说你是居心何在,你不爱国,就这样污名化了。污名化了以后,中国人就比较容易上当受骗,因为大部分人没有独立人格。当然有的公知也说朱老师的说法不负责任,但是我觉得任何人有说错话的权利,言论自由,不可能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我今天在这儿,肯定有的话今天也就说错了。
王晓渔:公共知识分子和公知好像变成两种情感含义完全不同的词。提到公共知识分子至少还是中性词,提到公知,基本上完全是否定的。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其实已经是一个同义反复了,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产生在19世纪后期做了一个区分,就是指要介入公共事务的人,否则我们已经有现成的名词叫专家,叫学者,那为什么还有一个词叫知识分子。
当然我们也知道20世纪的中国,到后面知识分子越来越无法介入公共事务,以至于我们在前面加一个公共,以表明知识分子似乎应该介入这么一个事务。但是把一个人称为分子的话,基本上这个人就比较糟了,所以不用知识分子这个词,称单个体为知识人或者知识者,群体的话叫知识阶层。在此之前的那个时代,从古代到现在的中间有一个词是过渡的,叫智士阶级或者叫知识阶级。我们要知道知识阶级和知识分子是非常不同的概念,知识阶级意味着知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你有自己的独立的价格观,不必任认同他的群体。
《常识》开篇这句话就很重要,有些作者把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它们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有不同的起源。他开篇第一句话就区分了社会与政治,那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的知识阶层,他主要做的其实是社会阶层的事情。文化批评主要是做社会建设,要有一个我们所说的社会的空间和大家经过讨论协商所形成的一种价值观,这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批评主要做的,或者我们广义而言是我们说知识人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对公知,批评人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在污名化,反智在我们的传统里是源远流长的。
有鲁迅的时代不只有鲁迅,还有胡适和陈独秀
主持人:除了知识人,学人也是海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个称呼方式。那我们回到题目,没有鲁迅的时代,批评去往何处?第一,没有鲁迅的时代,我们还需不需要鲁迅?第二,没有鲁迅的时代,是不是还有可能出现下一个鲁迅。第三,没有鲁迅的时代,在我们等待下一个鲁迅出现的这个期间,批评去往何处?
王晓渔:首先把有鲁迅的时代称作鲁迅的时代是有问题的,有鲁迅的时代不仅有鲁迅,还有胡适,还有钱穆还有太多太多人,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思想所产生的前提。我们是不是还需要鲁迅,当我们在讨论一朵花的时候,我们要讨论这朵花的土壤。我想这个时代不仅是需要鲁迅的,还需要所有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物,在任何一种思想观念上都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
朱大可:我觉得研究鲁迅的时代,要看他是从哪里长出来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什么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所以说鲁迅时代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没有新文化运动当然就没有鲁迅。1905年新青年诞生,那时候叫《青年杂志》,到现在正好100年。我们有没有可能出现“新新文化运动”,如果有,鲁迅就会诞生,还会诞生胡适,陈独秀,以及更多的各种流派学说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包括毛泽东。那个时代把这些人推到历史的前台,他们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这样的新兴文化运动产生的土壤,鲁迅是断然不会产生的。前几年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希望几年以后会出现新新文化运动,我们都在期待,但是我比较悲观。所以我对出现类似于鲁迅这样的人物表达悲观。

《洞见》签售现场
观众提问:我有一个问题一直在疑惑,很多批评家做评论已经很多年了,整个社会还是如此地浮躁、喧嚣,消费主义在横行,人文主义根本就没有。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变现状?好像我们一直在评论,公共知识分子有时候甚至是两派互相谩骂。在这个现状下,我们怎么引导公众去进行严肃的深刻的思考,怎么去改变整个社会非常浮躁的现象?
王晓渔:我觉得还是在观念,而不是具体行动的层面。一直以来好像对言论限制者都没有限制,我们自己都要怀疑言论界没有做成,经常觉得我们的言论没用,但是如果没用的话,为什么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很多的言论不停地被限制?限制者非常明白言论太重要了。这十几年,很多的观念在产生暗流一样的变化,它未必是完全自我呈现出来的样子。而且其实我很少想要改变别人,但至少我个人不要被别人改变了。当我们慢慢地觉得个人思想不重要的时候,那说明我们已经被现实情况改变了,迄今为止我依然觉得思想观念是极为重要的。
观众提问:朱老师前面说大众批评其实是一个后现代的文化。那么实际上中国现在究竟是一个在建立现代性的过程,还是现代性往后现代走?如果从现代性的视觉,能否重新解读鲁迅?
朱大可:首先你要讲清楚什么现代性,这个问题现在争议非常大,真的就没办法在这个地方讨论关于现代性,那个真的一塌糊涂。当年说实现小康,那小康算不算现代性呢,还是说按照这个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标准,这个真的就不好说。如果说现代性指个人健全独立的人格,甚至全独人格的形成,那么对不起,中国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如果只是说小康的话,我们可以说至少部分的小康已经实现了。鲁迅是具有现代性的,他始终保持了他相对的独立的人格,就这点他是特别值得我们尊重的,他身上所反映的思想品质就是现代性,就是这种独立人格的建构。如果没有鲁迅这样一种榜样,那么我们走上现代性的时候会感到很痛苦。虽然他有很多的弱点,但是无论如何来讲,他应该是我们走向现代性的很重要的标识。但是实际上今天我们从小学,幼儿园开始的教育是反现代性的。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实现,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困惑。
观众提问:我比较想问的是一个关于平台的问题。请问对于我们现在年轻一代来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批评的力量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王晓渔:我个人一直是为90后做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辩护。首先一个我觉得不能对90后下结论,因为最年长的现在25岁,未来还非常遥远。你刚才提到一个平台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90后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对80年代处在青春期的人而言,空间是相当之大的,当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几乎是这几十年最黄金的时代。在90年代处在青春期,92年的市场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自我表达空间。像我这个年龄段在06年左右正好做网络,网络对我而言是有太大的解放作用了。最近十年,我好像想不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网络这么开放的平台,现在好像流行创业,但是我好像不太清楚这个创业有没有提供这么一个自我表达的空间。
我前不久刚刚从拉萨回来,在西藏那边逛了很多寺庙,让我非常触动的藏传的佛教里面他们有一个传统。下午的两点钟三点钟他们和尚要辩经,我想我们所有的交流都应该有类似的东西,就是一个开放的,固定的,大家讨论的。公共辩论这么一个平台,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对我们个人的成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90后相对而言是有些匮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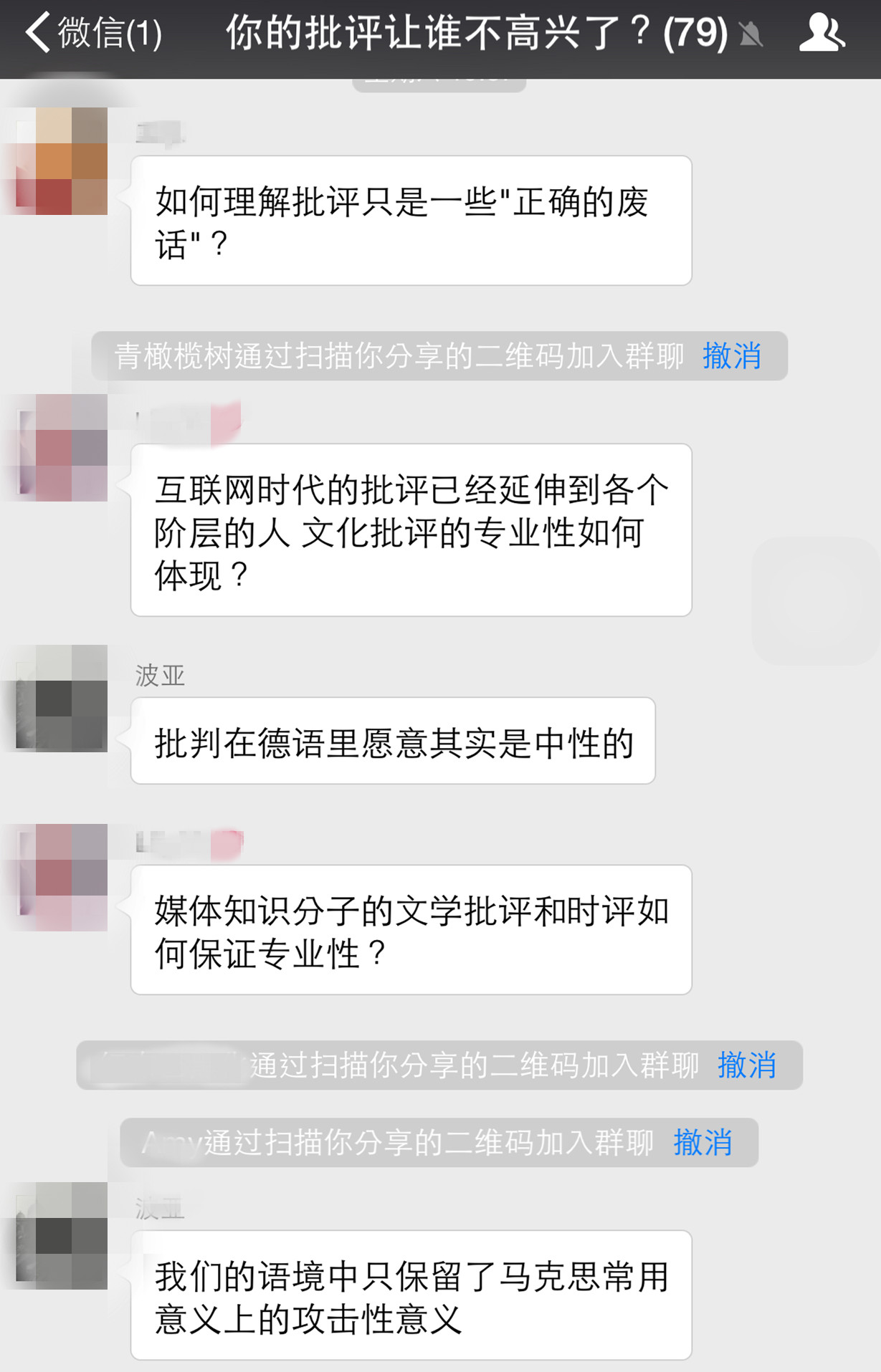
线上互动和提问
观众提问:如何区分所谓的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分子?
马小盐:媒体知识分子每天不间断地在搞评论,尤其是批评的时候,主要就是常识方面的,就是自由评论思想的,他踩着一定的线,敢写,主要是为了吸引大众。学院知识分子是有专业理论的。他像医生一样,有专门的手术刀,大的哲学家本身就是批评家,他是有自己的理论文化的,然后他对着一个具体的文化现状进行分析,他要治理这个疾病。
观众提问:文革到底对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宏观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影响是不是还在?
朱大可:文革实际上已经被符号化了,它是一个符号,里面有很多不便直接说出来的东西。对我个人来讲,首先它是一种生命经验。文革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我们从小受到它的伤害,童年充满着阴影。所以大家说这个暴力又来了,那不就是文革来了,它自己会做一个自然的联系。我算是50年代,这里在座有这么多90后非常幸运,我对90后非常看好,你们代表中国的希望,80后我觉得算了。因为80后有太多的负担,你们比他们更轻松一些,可能有更多的余力来完成我们未尽的理想,就是让我们不再生活在恐惧当中。
观众提问:之前学习过朱大可老师的《20世纪中国风尚学》,大可老师从20世纪开端,不断地根据时间顺序解读一些文化符号,包括我们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它象征着一个强大的孕育能力,每一个时期,包括那个陶瓷的缸子,包括红卫兵的袖章,就类似这些东西怎么是一些文化符号。那我想问的就是从文革之后30多年的时间,大可老师能不能阐释一下这段时间的代表性符号?
朱大可:1978年以后典型的文化符号,如果是大众文化的话那就是春晚。春晚是中国政治文化和大众文化极其重要的一次结合,从很大的程度上表达了或者是传递了中国大众的趣味,但是它的内部核心是国家价值的需求,当然它推出了大量的像赵本山这样的明星。那么最初有两个国家代言人,一个是赵忠祥,第二个是倪萍,他们是中国乡村美学的代表,到后来朱军就稍微现代一点了。包括歌星也出现了一些次生的符号,比如说像李谷一,这个符号是满月脸,曾经主宰中国漫长的大众文化。它是乡村美学的代言,因为满月脸是中国生殖能力的一个标记,跟牡丹花是一样的,长在人的头上的牡丹花。之后的脸就开始拉长了。从这些符号当中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发生的变化,所以我们研究符号目的不是说研究这个符号本身,而是看这个符号它跟这个社会发生怎么样的关系。

凤凰文化新书《洞见》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