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足球流氓?
2016年09月25日 18:52
来源:凤凰文化
作者:兰德尔·柯林斯
从在比赛中制造戏剧冲突发展为在场外制造戏剧冲突,就像从吵闹的节奏型音乐发展为狂舞区中半暴力的行为,最后可能比音乐本身还要吵闹。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产生更多制造兴奋的技术,虽然不一定会混合暴力。
编者按:在受动作片电影和畅销惊悚小说影响而产生的流行误解中,在社会科学家的常规解释中,暴力往往与贫困、种族或意识形态仇恨、家族疾病等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
但在《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作者兰德尔·柯林斯推翻了以往对暴力的认知:暴力是人类的野蛮本性,很容易发生,所以人类文明建立了一系列社会制度来阻止那些暴力的个体。
长期以来,我们对暴力的认知可能存在一个分类误区:暴力一定是坏的、不利于社会的、违反规则的;反之,如果暴力符合社会运转的需要与规则(尤其是由官方行使的暴力),或是以娱乐形式呈现出来,大部分时候都不会被认为是暴力,或是会被认为是“好”的暴力。这种一刀切的分类模糊了暴力的本质,更令我们对暴力和“暴力个体”形成了一种偏见。兰德尔·柯林斯为我们重新提出一种真实而令人不安的可能:人类的本性并不是触发暴力,而是在互动中逃避和弱化真正的暴力;因此,与其说社会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阻止暴力,倒不如说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为了鼓励暴力乃至将其制度化。这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警察与军队中的种种纪律;此外,个体表演型暴力(如拳击、跆拳道与击剑比赛等)和其他团体竞技体育(如冰球和橄榄球等)的规则,也有着保障暴力顺利发生的意味。
本文节选自《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第八章运动暴力,原题为《娱乐至上时代的观众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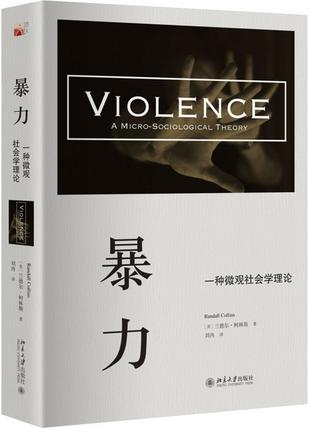

《暴力:一种微观社会学理论》,(美)兰德尔·柯林斯著,刘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
足球流氓的历史,就是塑造集体兴奋与欢腾的技术的发展史,而且这种兴奋可以与比赛本身无关。
足球比赛中的暴力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甚至更早。世界各地都曾出现过这种暴力,其中一些最暴力的骚乱发生在英国足球流氓不曾涉足的区域。例如,1982年在苏联,69人在一场骚乱中死亡;1964年在秘鲁利马,在一场对阿根廷队的比赛中,300人死亡,500人受伤(Dunning 1999:132)。1969年爆发了一场战争,洪都拉斯驱逐了数十万名在过去几十年里移民而来的萨尔瓦多农民;导火索是两国之间的一场足球赛,比赛引发了骚乱,进而引发了一场长达五天的战争,2000人死于其中(Kapuscinski 1992)。不过,我们分析的重点并不仅仅是伤亡人数,因为这并不能告诉我们究竟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模式。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之间的比赛并不是足球流氓暴力,而是我们在前一节讨论过的政治暴力;胜利与失败引发的骚乱是一种方便的动员机制,能够动员到比赛之外的社会冲突。这种骚乱(以及战争)也许在威权社会更容易发生,在那里,体育运动可能是唯一能够用来动员群众的舞台。反过来,我们在此处所讨论的则是民主社会中通过足球流氓团体等社会组织而动员起来的运动暴力;这些团体运用自己的技巧创造了"道德假期",按照需求制造独立于游戏之外的骚乱。大部分早期暴力都是我们曾经研究过的自发性球迷行为:闯入球场,或是将比赛中的情绪延伸为场外的胜利或失败骚乱。
英国足球联赛开始于1860年代,像其他运动一样,足球是中上阶级的领地。到1880年代末期,足球已经职业化,并获得了一批工人阶级球迷。球迷人数得到了增长,球迷暴力也随之增长。大部分此类事件都发生在场内(如体育场);由于观众区与球场之间并没有太多阻碍,所以也会发生许多闯入球场的行为。
也许正是英国体育场一个偶然形成的特点,导致其对球迷暴力格外具有吸引力。在传统足球暴力的时代,观众(特别是那些粗鲁的球迷)会挤在体育场的上层看台上。早期看台都是土坡,后来变成混凝土制的长椅。然而没人会老老实实坐着,这既因为传统观看方式是站着,也因为随着足球流氓的发展,警察会尽可能地将更多球迷塞进看台,并用铁链和其他障碍物将他们堵在里面。这一策略是为了把足球流氓(特别是客队球迷)与其他观众隔离开来,并在特定时刻允许他们出入场地,好让他们无法与当地球迷发生冲突。这一策略导致若干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限制了场内暴力,它反而促进了场外暴力策略的发展,而那些暴力则与比赛本身无关——这就是英国足球流氓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制造"道德假期"的技术创新。
另外一个后果则是增强了看台上球迷的团结感和情绪浸润。那些隔离带被称为"猪圈"或"地牢";里面的人们挤成一团,通过高度强化的互动仪式,按照同样的节奏摆动身体:
在任何运动中,观众都可能会作出在其他场合下不可能作出的表现:拥抱、呼喊、咒骂、亲吻、狂舞。最关键的是运动带来的兴奋;对这种兴奋的表达与目睹同样重要。但是,没有哪种运动能让观众体会到像在英国足球看台上一样的身体感受。你可以通过人群感受到比赛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而且无法拒绝这种感受……你能够体会到每一个进球。每一次进攻,观众都会屏住呼吸;每一次救球,观众都会同样夸张地松上一口气。每次我身旁的观众舒展身体,我都能看到他们的胸腔扩张,而我们则会被更紧密地推挤到一起。有时他们会紧张起来,手臂肌肉略略放松,身体则变得僵直;有时他们会向前伸长脖子,试图在夜晚古怪的无影灯光下看清楚球到底进了没有。你能够通过身体感受到双方球迷的期待。(Buford 1993:164-66)
并非所有高层看台上的球迷都是足球流氓。足球流氓是少数特别活跃的球迷,他们很可能人数并不多,特别是当他们前往客场(尤其是欧洲大陆客场)的时候。但是,正是高层看台的体验催生了群体团结感;与其他体育比赛的观看体验相比,这种体验不同寻常,并在1960年代发展成为场外一系列迂回而复杂的足球流氓技术。
我们几乎可以通过实验来证明这些独特的结构能够塑造观众的体验,只要观察这些结构发生改变时会发生什么就好了。1990年代,英国的体育馆改造成了美式座椅设计: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会尽可能安装独立的带有扶手的座椅(扶手也能将球迷的身体分开)。之前警察可能会匆匆忙忙地将球迷赶入场内,球迷可以借此逃过检票,或是在门口付现金但却拿不到特定座位的票据;现在,新的规定要求所有观众提前买票并拿到纸质的带有特定座位号码的球票。比赛也开始面向地位较高的家庭观众展开宣传(Buford 1993:250-52;Anthony King,2000年11月私人通信)。不过,粗糙的长椅式体育馆依然存在;金(King 2001)曾描述过马赛一家相当传统的带有笼式看台的体育场,座椅虽有编号,球迷却毫不在意,只是随意站着罢了。
这也是谜的一部分。英国体育场早期的特点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群体情绪,后来,这种情绪脱离了球场与比赛。1960年代发生了过渡的一步:警察开始将敌对的粉丝隔离在不同的高层看台,希望能减少他们在场内的暴力冲突。结果这些措施却在无意间以多种方式增加了暴力。第一,由于最疯狂的球迷被锁在了同一个高层看台里面,反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团结感。第二,这种结构创造了一种目标,使得球迷们能在比赛前或比赛中占领敌对球迷的地盘。如果说场上球员是"A队",球迷们就成了辅助性的"B队";球迷们也有自己攻击的目标,不是进球,而是用众人的身体来侵入对方的地盘,或是向其中投掷物品。第三,在更严格的规矩之下,太激动的球迷会被逐出场外。英国社会学家和其他研究者(Dunning et al. 1988;Van Limbergen et al. 1989)已经注意到,警察与球迷之间不断升级的战术,转变成了组织性更强的足球流氓暴力团伙。这与我之前提到的情况相类似:美国的保安们试图阻止场内的胜利庆祝,最后却导致更加暴力的场外庆祝。
在足球流氓的复杂技术中,还有一种发展自交通方式。20世纪初的早期足球暴力,大都涉及一起前去观看比赛的球迷,他们会集体租车,自称"刹车俱乐部"(Dunning et al. 1988:115,140,167-79)。类似现代足球流氓暴力的第一起事件,是1950年代球迷砸火车一事。球迷打架的主要地点一开始是火车站。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球迷的技术发展很快:轮滑;旨在躲避警察的旅行安排;事先散布传单宣布在特定比赛中会发生打斗等。随着警察注意到他们,并开始在相应的时间和地点派出人手,足球流氓们也开始愈来愈倾向于深入敌方地盘制造麻烦。此时,"地盘"的概念已经有所扩展,不再仅仅是入侵球场的另一端,而是要占据敌人老巢,入侵整座城镇,并四处追赶对手,将他们逼入不利境地。
英国足球流氓是一种社会技术,是为了将球场中产生的兴奋与比赛本身剥离开来。这种技术传播到了欧洲大陆(主要是荷兰与德国)和其他地方。比利时的硬派足球流氓在1980年代刻意引进了英国足球流氓的技术,他们甚至专门前往英国去观察和学习英国足球流氓最复杂的行为模式,并借用了英国的歌曲和口号(Van Limbergen et al. 1989)。
这些技术有两个目的:首先,现代运动制造了一种集体团结感和戏剧性的紧张与放松体验,而通过这些技术,球迷们能够将这些体验与比赛相剥离,让它们成为按需生产的情绪。其次,它们将球迷的地位抬高到与球员相同,甚至高于球员——足球队可能会输掉比赛或者表现不佳,但足球流氓团体却能"深入敌方老巢"攻击对方,创造出比球赛更夸张的叙事,并取而代之成为注意力的中心。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如果客观来看,球迷们的某些表现可谓猥琐,然而在这些条件和体验的共谋之下,他们就无法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他们面对运动员时卑躬屈膝,因为他们的情绪与注意力都取决于球员的表现;之前的照片显示,在球迷们最兴奋的时刻,他们全神贯注,毕恭毕敬,一心一意地崇拜着自己心目中神圣的对象。
足球流氓团体的社会技术解放了球迷。他们不仅重新获得了时间与空间中的自主权,更以一种深刻的方式获得了冲突中的荣耀感。沉浸在比赛体验中的球迷,其道德感已经退化到原始水平:他们毫无廉耻,以多欺少,在球场中以数万人的规模提高嗓门,摇摆身体,在虚拟的战争中对抗几十名客场球迷。相反,球员们则是英雄,因为他们参与的比赛是势均力敌的。足球流氓们从"球迷-球员"的阶级关系中解放了自己,建立了"英雄-帮派"之间的平等关系。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伪装与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只有在其人数占据绝对优势时才会挑起打斗,如果取胜机会各半,他们就会撤退或是拒绝对抗。然而,他们的叙事技巧隐藏了一切;在他们的主观视角中,他们自己就是英雄。B队取代了A队。
当然,这并不一定在各个方面都正确。足球流氓将戏剧冲突从比赛本身的事件与人物中解放出来——至少解放了他们自己的主体与情感参与。然而从时间和空间来看,他们并没有把自己从球队中解放出来。他们仍然需要围绕比赛时间表来组织活动;只有在与对手的比赛前后,他们才能入侵敌方领域或是守卫己方地盘。他们寄生在球队身上。这是无法逃避的,因为足球流氓团体本身的组织十分松散;这种组织形式让他们能够实施自己的战术,能够在躲避警察时假扮成普通人群。他们既不需要正式架构,也不需要永久的总部、财务、管理人员等;虽然就连最松散的政治运动组织也会需要这些,但足球流氓却能靠比赛时间表来提供最基本的合作可能。比赛时间表很方便地就将人群聚集起来,让他们能够实施自己的战术。
制造暴力的社会技术深植于历史情境中,因此有起有落。这些技术背后还有更加广泛的一系列技术,都属于现代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它们的终极目的不是寻求纯粹的肉体暴力,而是寻求一种集体兴奋感。现代运动正是一种不断发展的仪式技术,目的在于将涂尔干式的团结与场上情境混为一谈,只保留足够的悬念来保持高涨的兴奋感。体育流氓们进一步操控了社会注意力,让自己成为故事中的英雄。
在这里,我们也许会注意到本章与第七章的结论有相似之处。我在第七章指出:流行音乐会中的狂舞区是从乐队手中抢回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处于被动地位的观众从身为明星的表演者手中抢回了情感注意力空间的中心位置。这正是英国足球流氓用其社会技术所做到的:将比赛中的观众体验扩展到看台之外,进入自己能够控制的空间,将比赛中的戏剧时刻转变成按需生产的骚乱。
长期来看,狂舞者与足球流氓展示了同样的社会技术的发展。两者都是观众在大众商业娱乐时代的反抗。当然我并不是说它们就会以其目前形式一直持续下去。然而它们却与20世纪中叶的作家和导演们所描绘的未来"敌托邦"(dystopias)有所类似,例如《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发条橙》(Clockwork Orange)《太空英雌芭芭丽娜》(Barbarella)中那些寻求刺激的暴力团伙;他们都与赫胥黎等人对未来世界的恐惧一脉相承。这些想象意味着物质条件的进步无法带来社会和平;娱乐消遣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强大的娱乐经济,也令人们愈发重视如何制造属于自己的体验。
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复杂,思考得也更多,故也更能辨认出:在人工制造的现实中,行为如何互相嵌套。注意力一直是一种社会分层的形式;在过去50年里,情境性的分层变得越来越重要,并脱离了其他形式的经济、政治和长久以来的社会地位分层而存在。纯粹的情境地位变得与阶级和权力无关。但它们仍然未能脱离自己的社会基础:微观互动的组织条件,以及控制当下注意力空间的方法。音乐(特别是那些格外吵闹和节奏感强烈的音乐)、戏剧与体育已经成为吸引社会注意力的主要组织技术。站在聚光灯下,娱乐明星们(也包括运动员)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成为注意力的中心,从而控制整个情境。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崭新的地位分层出现之时,处于边缘的人们也发展出了新的社会技术;正是那些最狂热的粉丝发明了反击的方法,用来夺回注意力中心。这些表现可能是暂时的,但却指明了一个更加长远的趋势。
从在比赛中制造戏剧冲突发展为在场外制造戏剧冲突,就像从吵闹的节奏型音乐发展为狂舞区中半暴力的行为,最后可能比音乐本身还要吵闹。这意味着未来可能会产生更多制造兴奋的技术,虽然不一定会混合暴力。
这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好消息是:人们所争夺的并不是什么基本的东西。它们不是那些持久存在、深植于对抗性之中的社会身份,这些身份的力量来自在情境中生产它们的仪式技术。坏消息是:我们能制造出新的暴力源泉,无论它们有多么短暂。也许此处的一线希望正是我们在本书中一再看到的事实:大部分暴力都是虚张声势,不具备多少实在内涵。这些制造表演型暴力事件的社会技术看似可怕,但却也许能够阻止我们作出更可怕的事情。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责任编辑:魏冰心 PN070
- 0笑抽

- 0泪奔

- 1惊呆

- 0无聊

- 0气炸


凤凰文化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