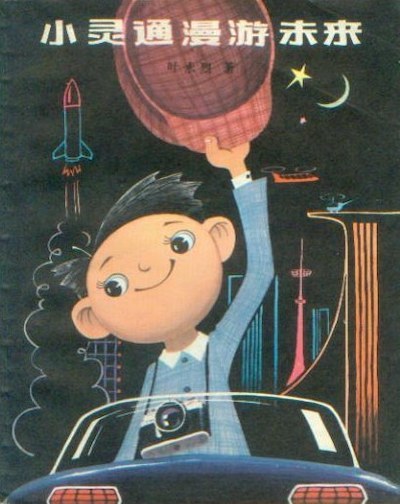科幻小说中的“漫游”


独家抢先看
在中国当代文化和技术语境中,“漫游”是一个多义且富有象征意义的词汇。在《辞海》中,它可以指随意的游玩,也可以指涉移动通信等中的技术现象。这个词在不同的叙事和历史背景中,承载了大量复杂的意义和文化寓意。通过追溯和分析“漫游”这一概念背后的古典义与现代义,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科幻小说。
首先,“漫游”具有古典义,其中特别强调无目的的跨界行走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象征性。这种无目的性并非真正的无目标,而是指向一种更高层次的合目的性。这种象征性旅程不仅在空间上跨越了不同的边界,还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实现了一种复杂的交换和联结。
其次,“漫游”的现代义则更多倾向于技术性语境,比如移动通信中的漫游。当一个人离开其注册服务区域,却依然能够保持与原服务区域的联结时,这种技术现象无疑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中的漫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这个语境下,漫游不仅指空间的移动,还涉及信息和通信的跨区域扩展与链接。
通过这两种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漫游”概念,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如何在科幻小说中得以呈现和表达。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描绘了一位小记者小灵通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跨越,进入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未来世界,这无疑是古典意义上的“漫游”在现代科幻文本中的延续和重释。而韩松《地铁·末班》中,向我们则通过主人公老王在地铁中的奇遇,描绘了一个在技术中走向未来的社会如何困在往日的噩梦之中,通过不同层次的空间的跨越和漫游,进一步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的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小灵通漫游未来》书封
叶永烈对于80、90后而言并不陌生,但对于更新一代的读者,他的作品就显得过于古早了。他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系列共写了三部,时间跨度很长,我在此关注的是他最早的一部,即《小灵通漫游未来》(1978)。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虽然是一部面向儿童的科幻作品,但仍然可以视作一个症候,从中透露着当时国人在无意识中如何理解未来的“科幻世界”。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小灵通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未来市”,见识到了许多关于未来世界的奇幻技术,并回到“现在”向读者宣传见闻。其中展示了一个科学乐观主义者眼中的未来世界。
在未来市的生活方式中,有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面,一个是对“人工性”的迷恋,一个是对“透明性”的迷恋。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各种人工制品替代自然物的乐观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人造器官、人造大米、人工控雨、塑料世界等充满乐观的浪漫想象;后者主要表现在对“人工太阳”、“天花板灯”等灯光技术的推崇之上。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见的,阴暗的或寒冷的,甚至南极都装上了人造太阳,那里冰雪融化、牧草茵茵。这种对“光明”的迷恋,与韩松《地铁·末班》中对漆黑长夜、地下世界、黑月亮的刻画形成对照。
《地铁》书封
在《小灵通漫游未来》所描绘的未来市中,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劳动,没有人想着去休闲娱乐,这是一种马克思式的理想: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韩松的《地铁·末班》(2011)中,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已经彻底不同。《地铁·末班》不是乌托邦,而更近乎恶托邦。这部作品中,单位临退休职员老王在一次乘末班地铁回家时,发现地铁中的人都成了透明人,而这些透明人后来被奇怪矮人抓走,“小矮人把乘客搬运出车厢后,就装进一口口的大玻璃瓶,瓶中盛满绿色溶液,每瓶仅容一人,由一个怪人吃力扛在肩上,另一个似若护持,成双结对,攀下站台,沿着铁轨,往隧道深处走去了。”地铁就成了一个虫洞,让老王“漫游”在当下(其实是2050年之后)与过往(梦游时代)。老王在惊恐之中,想去探寻真相,通过一张在地铁上捡到的身份证误入过往世界。在这个故事中,技术之变革,并没有带来光明未来,而是不断让人重新陷落回噩梦般的梦游时代。老王虽然试图去想救出那些被抓走的人,但结果是自己成了瓶中人。
与《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对人工性的迷恋不同,《地铁·末班》对于能够替代人工的技术态度悲观主义的质疑。这种态度体现在地铁的刻画之上,在大众的想象中,地铁是现代技术文明的象征,但在韩松笔下,地铁似乎就像处在卡夫卡式地下室中的物件,整个世界白天就像是一种掩盖,而漆黑长夜和天空中的黑月亮才是这个技术世界的本质。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梦游时代的阴影一直笼罩其上。如果没有人性的改变与对历史的反思,技术不会成为澄明的方式,而是遮蔽的方式。《地铁·末班》呈现的也完全是透明性的反面,技术光滑的表面带来的无尽的遮蔽。在地铁时代中,我们被遮蔽而遗忘了梦游时代,却又再度滑向梦游时代。
小灵通的“漫游”,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上理解。首先是从现在进入未来,这是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过程。其次,是小虎子带着他在未来市到处参观,就小灵通自己的角度而言,这种漫游是误入的、缺乏规划的,完全是被领着走。老王的漫游同样是穿越不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与地铁的梦幻世界,当下世界与过往时间,但他一开始并不是无目的的:他开始坐地铁是为了回家或去单位,或者是为了找到他捡到的身份证的主人。但意识到黑夜永寂,而人生无意之后,他就像迷失在丛林中的人一样。人生亦如此。我们知道工作或生活中每一件具体事情的目的,但不知道所有事情背后的目的:人生路走向哪里?在这部小说中,漫游不仅是两个时代之间的交叠与游走,梦游本就是一种变态形式的“漫游”,这个梦游就是在一种无知与狂热中的无意识的行动,当群体陷入这种梦游状态,他就带着政治的意味。
如同《小灵通漫游未来市》中所说,“未来市,不仅在现在的中国地图上找不到这座城市,就是在现在的宇宙地图上也没有这座城市。但是,在将来,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城市,而且在宇宙地图上也能找到这样的城市”。无论这个城市叫什么,这两本小说中的两个想象中的城市之间三十多年的差异才更值得我们关注。
小说在对待“人工性”和“透明性”上的不同背后,是政治维度的隐现。比如《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对理想社会的说明,已经揭示了其隐含的政治维度。其中无意间提到的月球上的环形山脉,以及中国海、李时珍山、鲁迅市等带有民族性的命名(完全可以用更技术性的语汇,比如H22海、S108山、C81市等编号来表达),也隐隐透露出民族国家的意识。如果和最近这段时间嫦娥六号在月球背面取得月壤之后带来的舆论狂欢比照,这种政治与科幻交融的意味就更明显了。
中国科幻小说自晚清开始,就与政治(尤其是救亡)联系在一起,裹挟在科学主义的浪潮之中。在始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科学派获得了明面上的胜利,科学所标榜的客观性使得人们在谈论科学时,不必言及政治(利益)。然而,当“科学”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观念,客观的科学同时也隐含了政治的宰制。同时,政治通过宣称自身的科学性来获得合法性。于是,科学与政治结成了同盟。
当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小灵通漫游未来》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它所展示的,对科学进步带来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已经自信到不言自明的地步。在小灵通漫游未来市时,没有人向他展示城市的政治建制,这隐喻性地表明,政治建制对他而言是自明的。而科学是实现这种形式的唯一方式,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然而,把理想政治的实现交托给科学,这本身忽视了政治的复杂性,甚至科技对政治之恶的放大,阿道司·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技术高度发达带来的就是恶托邦,人都成了标准化的工具,人性几乎丧失殆尽。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不清楚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究竟是因为在理想社会之中,所以科学才如此昌明,还是因为科学如此昌明,理想社会才得以实现。而在这个实现过程中,政治制度是如其所预设般自明,还是如其表象中那样,政治性可以被取消,这些都并不清晰。《小灵通漫游未来》正是由于在观察未来市时,有意无意地缺失对政治建制的观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罗尔斯式无知之幕问题:只要科学昌明,民众自然就可以组织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同体?
这是必然的吗?为何它没有走向《地铁·末班》的世界?就像乔纳森·克拉里在《焦土故事: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旅程》中描述的那样,在其自行发展中,互联网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盲目扩张下,带来的更可能是“焦土”,而不是解放。当科学成为城市建设的方式时,对政治性的忽视,并不会导致政治性的消失。缺乏自觉的反思意识,科学更有可能会走向恶托邦。当代科幻文学对广义政治维度的观照,正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地铁·末班》在人工性和透明性两个方面都给出了与《小灵通漫游未来》不同的回应。在一个由技术架构起来的媒介城市中,无反思地拥抱技术(人工性)带来的光明(透明性),由于忽视其中的政治性,我们可能会走向我们初心的反面。由此我们带出了更根本的问题:科幻文学中的漫游意味着观察真实的未来世界,但小灵通漫游之所以受限,正在于小灵通处于一个政治性空间中,但其观察世界的方式却缺乏政治性维度,因此所见证的是一个真诚的虚假世界。作为技术媒介城市中的媒介动物,我们并未超越古老的政治性。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