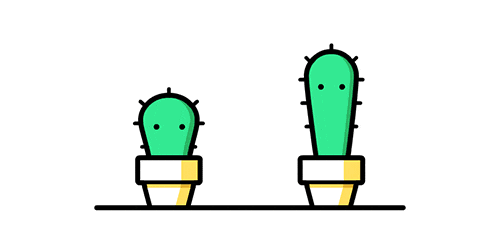伍尔夫传 | 如果生命有其根基,它便是记忆
我们都熟悉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她也是强健的步行爱好者,是“不知疲倦的探索者”,探索“人类处境的千奇百怪”。
传记作家林德尔·戈登通过伍尔夫的小说作品以及日记和书信还原出了这样一个伍尔夫。她书写的伍尔夫传记并非常规的线性传记叙事,而是在真实性所能允许的范围内,追踪记忆和想象在伍尔夫一生中的持续流动。
她同时也论证了这种传记方法正是伍尔夫的发明,这背后是一种全新的重视无名者的历史观。
本文摘编自林德尔·戈登《弗吉尼亚·伍尔夫传》,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发布。
01
亡灵的声音,
比活身边的人更为真实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如果生命有其根基”,它便是记忆。她作为一位作家的生命以两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为基础:北康沃尔海岸和她的父母。
清晨伊始,在夏日的圣艾夫斯,弗吉尼亚躺在家庭度假房的育儿室里,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一、二,一、二……在黄色的百叶窗后面”。躺在温暖的床榻上半梦半醒之际,她听到了海浪的节奏,风把窗帘吹开,她看到一瞬间的光亮,感受到“能想象到的最纯粹的狂喜”。
多年过后,她想让海浪的节奏贯穿于她最好的作品——《到灯塔去》和《海浪》之中。潮汐的翻涌与破碎代表了存在与终结的最多的可能性。
弗吉尼亚·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生于1882年,本名是阿德琳·弗吉尼亚·斯蒂芬,她是朱莉娅和莱斯利·斯蒂芬这两位非同寻常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第三个孩子,弗吉尼亚自己也很难说清父母二人谁更杰出。对海浪的记忆一定很早就有了,而对父母的记忆却具有不同性质,它并非一种感官记忆,而是源自理性分析。
弗吉尼亚八到十岁时,父母成为她关注的焦点。她的父亲是个古怪的登山爱好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他对待知识的诚实态度很折磨人,这种态度既让孩子们害怕,又使他们头脑活跃。她的母亲以照料贫病之人为业,这是个耗费心血的工作,但她拥有实用的智慧和细腻的同情心。
在一张拍摄于1894年左右的模糊旧照上,朱莉娅·斯蒂芬正在和她年幼的四个孩子一起读书。弗吉尼亚神色羞怯,脸型因为过长而显得不够协调,她的体型瘦削纤弱,眼神敏锐,双目下缘像梨子一样浑圆。孩子们聚精会神,照片呈现出极其宁静的气氛。
三十多年过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描绘了一个相似的场景。作为母亲的拉姆齐夫人大声朗读,她看着儿子漆黑的瞳仁,看着女儿被富有想象力的文字吸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们再也不会比现在更幸福了。”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试图重建并保存的维多利亚时代里,朱莉娅·斯蒂芬是最不容忽视的人。
朱莉娅死于1895年,紧接着,她与前夫的女儿斯黛拉在1897年去世,此后便是1904年莱斯利·斯蒂芬的死和1906年儿子托比的离世。十年间接踵而至的死亡封存了弗吉尼亚的青春时代,将其与她的余生割裂。
“生命的一切恐惧都在眼前逼近。”死去的人在她的想象世界里萦回环绕,直到五十岁她还在日记里写道:“……鬼魂在我脑海中古怪地变化着;就像活着的人,随着你对他们的听闻而改变。”
作为一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紧抓着往昔和亡灵们日渐清晰的说话声,或许对她来说,他们比活在她身边的人更加真实。当亡灵的声音催促她走向空中楼阁时,它们会把她逼疯,而这些声音一旦得到控制就成为小说的素材。
每经历一次死亡,她对过去的感受就愈发强烈。她的小说都是对这些已逝之人的回应。“……过去是美好的,”她说,“因为人不可能在当下就意识到某种情感。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延展,因此,我们只能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最完整的情感。”
逝者在记忆中日渐丰满,呈现出最终的形态;而活着的人却是混沌的,就像她自己一样仍在形成中,但这并不能阻碍她在想象中塑造他们。她把自己挚爱的人——父母、兄弟、姐姐、朋友、丈夫——转化为拥有固定观念的角色,使他们超越时代,永不消逝。
在盛年之时,她并不希望详述死亡本身,而是渴望描绘出流芳百世的人物肖像。这些肖像并不像照片那般写实:她会让对象变形,从而使个人的记忆符合某种历史的或普遍的模式。
无私的拉姆齐夫人就是弗吉尼亚根据印象中的母亲来写的,但她被转化成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人物,当她带着孩子们读书时,又成了母性的典范。通过这种方式,弗吉尼亚·伍尔夫让死者复活,把他们定格在书页上,就像《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把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永远定格在画布上一样。
02
没有一个作家的生命
被这样完整记录过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弗吉尼亚·伍尔夫留给公众的印象是一种鲜明的现代性,而到六十年代,这个形象朝着另一种片面的事实转变:一个支持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
尽管从她的所有作品(包括草稿)出发,这些形象我们都能看到,但很明确的是,她作为现代小说大祭司的阶段非常短暂,而她的女权主义论辩也只是尝试改写而非摒弃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典范。
她回望过去寻找角色的原型,她的写作生涯一部分是被记忆、被对过去的强烈感觉,尤其是被与十九世纪的种种联系所决定的,而另一部分或许与她对“匿名”的渴望相关,这份渴望在她写作生涯的末期愈发明显,这意味着她抛弃了现代派作家那种自知自觉的优越感,转而关注无名大众,尤其是女性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她寻求与强权和“头戴金色茶壶的帝王”的历史截然不同的“反历史”。
艺术是重要的,女性的命运也是,但她的美学实验和政治论辩只是探索未知事物的副产品。
“我的体内似乎有个坐立难安的探索者”,她曾在日记里写道。正是这种探索精神促使她开始写作。叶芝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某个场景,某种冒险……这就是代表他隐秘生命的意象”。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伍尔夫心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是一段探索的远航,或是藏在海浪中的某个潜伏形态的鳍。“为什么生命中没有这样一次探索呢?”她继续写道,“人们可以伸手触碰它,并说:‘是它吗?’……我强烈又惊讶地感觉到那里有某种东西……”每天下午她会外出散步很长时间,伦敦就像一片“未被开垦的土地”一样召唤着她。
她并没有漂浮在自我沉醉的意识流之上;她是一个好奇的探险家,追随着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家或者,比如说,达尔文的脚步,渴望了解她所说的“人类处境的千奇百怪”。
弗吉尼亚·伍尔夫塑造并捍卫了现代小说。她留下将近四千封信件,四百篇文章,还有三十卷日记。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生命被这样完整地记录过。
然而,这位女作家依然神秘难解——当然,情况也必定如此,因为对任何生命的理解都永无止境。作为布鲁姆斯伯里先锋艺术集团的领军人物和一位热爱写信的作家,她会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现出不同的面目。
“多奇怪啊,”她承认,“我竟然有这么多个自我。”然而,她总是掩藏起那个作为小说家的自我。她曾对一位友人说:“为了写作,我必须是私人的、隐秘的,我要尽可能地隐姓埋名,潜藏自己。”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布鲁姆斯伯里引人瞩目的生活、她为人称道的奇思怪谈、她身患疾病时的离群索居,以及关于一位病弱的淑女、一副冷淡的肉体和一个远离真实世界又矫揉造作的唯美主义者的种种传说,被世人不断重复着。
然而,以下才是塑造了她的作品的隐秘事件:童年的记忆、零散的教育、火山爆发般的疯疾、不同寻常的婚姻。
将这些丰富的记忆拼凑起来,就是为她的隐秘人生寻找无可辩驳的证据,与她广为人知的公众生活相比,这种隐秘生活截然不同却又并行不悖。当她自己在《海浪》的草稿里解读一位作家的人生时,她写道,在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之间——在“外部和内在之间”——“存在某种不可避免的裂隙”。
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说,只有写作才能构成“我生命的整体”。
大约三十五年里,她每天都坚持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包括笔记、草稿、未完成的短文、早期的日记,甚至是阅读计划—都被保存了下来,但为了准确定义她的写作事业的性质,我们必须把这些文献和正式作品结合起来看。
她逃脱了惯常的分类,正因如此,大众媒体倾向于给她贴上“疯女人”或“自命不凡”这样的方便标签而忽视她的作品。我的目的并不是介绍她的每部作品,而是去展现她的写作事业的整体轮廓。为了看到其中的连贯脉络,我将追踪潜藏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的生命观。
她在小说中反复指出,生命的重要时刻并非像出生、婚姻与死亡这类传统观念中的节点,而是一些隐藏在普通日子里的普通事件。她曾在1921年的日记里回忆起1890年8月的一个普通夏日,回忆起海浪的声音和花园里的孩子们,她认定,自己的生命正是“扎根于此、被此渗透:究竟程度有多深,我永远也无法说清”。
叶芝曾谈起作家通过艺术获得的成长,他将其称为“新人种的诞生”,这也适用于作为新女性的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曾对一位朋友说,自己被“训练得沉默寡言”。后来,尽管她以自由和智慧的言论主导了当时的伦敦知识界,她仍为小说保留了属于自己的一面。
《远航》里那个性格古怪又渴望探索的雷切尔之死,《达洛维夫人》中那位疯狂的、沉湎于过去的塞普蒂默斯的自杀,都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这部分自我在虚构作品中的呈现—它富有创造潜力,但也可能会被扭曲,并且总是面临毁灭的威胁。她的自我抑制使公开出版作品变成极度痛苦之事。
03
写作是女性容易进入的活动,
但仍未得到完全的赞许
记忆的“根基”、“存在的瞬间”、女性的沉默:这些线索将我们引向弗吉尼亚·伍尔夫独一无二的写作生涯。不过,她也受到上个时代的陈旧习俗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她所说的“隐形存在”,她的传记理论也将是不完整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肯辛顿、主流的理想女性形象、教养良好的男人们隐藏的性欲、只为她的兄弟们保留的教育特权:弗吉尼亚在反抗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也被它们塑造着。
她最大的抗争是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女性形象的抗争,那种固化的形象一直纠缠着她,或许比同时代的其他女人更为长久。在她五十多岁时,有一次邓肯·格兰特因为区区风寒而感到难受,她懊恼地发现自己和姐姐正无意识地扮演“慈悲天使”的角色。
1931年,在一次面向职业女性的演讲中,她说道:
“你们这些更年轻、更幸福的一代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家中的天使’。她极富同情心,极具魅力,毫无私心……几乎每个体面的维多利亚时代家庭都有这样一个天使。当我开始写作时……她羽翼的影子落在我的纸页上,我听见她的裙子在屋里沙沙作响。但这个物种……从没有真实的生命。她—这是更难对付的—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幻影,一个虚构的实体。她是一个梦魇,一个幽灵……”
这个天使在初次撰写评论文章的年轻女孩耳边窃窃私语,告诉她,如果她想成功就必须服从。“我转向这位天使,扼住她的喉咙。我用尽全力杀死了她……如果我不杀她,她就会杀了我—作为作家的我。”
另一种抗争针对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女孩们的封闭生活,她反抗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禁锢和束缚,更是那种被引导的愚昧无知和情感上的惯性压抑。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
斯蒂芬一家人住在肯辛顿海德公园门22号,他们的房子朝向一个死胡同,那里安静而乏味,他们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通向肯辛顿公园的马路上遥远的车轮声和马厩里的马蹄声。她们向外望去,只能看到坐在轮椅上的老雷德格雷夫夫人,她看起来就像博物馆里装了轮子的文物展柜。
当然,与这种封闭生活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体面观念,它使得弗吉尼亚和姐姐瓦妮莎的反抗如此持久又如此沉默。
弗吉尼亚十五岁的时候,曾在一天晚上听到一个老头下流的呓语,第二天早上却被告知那只是一只猫。她一生都很厌恶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这是对他们被压抑的性欲的一种合理反应。
弗吉尼亚大约六岁时,她已成年的异父哥哥杰拉尔德·达克沃斯曾把她抱到桌子上,触碰她的私处。她被迫参与了这次偷偷摸摸的行动,她感到很困惑,但她也本能地知道,这是件过于可耻、不能说出来的事。“当我想起这件事时,依然羞耻地发抖,”她在1941年对一位友人坦白。
在《往事札记》里,弗吉尼亚·伍尔夫回忆起自己和姐姐是如何被教育要“安静地坐着,看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们表演钻聪明才智的马戏铁圈”。
《到灯塔去》以一种滑稽又冷淡的态度对待大英帝国的行政人员和高校教职人员,而这些职位恰恰是她的中上阶层家庭所赞许的追求。昆汀·贝尔解释说,他们家族的男人总是以工作谋生,但绝不是那种使用双手的劳作。他们不属于有闲阶级或世袭统治阶级,也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他们是“专家”。
他们的子孙都受到严格的教育,因为成功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努力。这个家族在上世纪贡献了许多专业人才,弗吉尼亚母亲的家族培养了不少东印度公司的官员,而斯蒂芬家族那边有律师、法官、中学和大学校长。弗吉尼亚气恼又不乏嫉妒地观察着只留给家里的男孩们的“钻铁圈”游戏,而他们似乎无一例外地擅长此类游戏。
她写道:“我所有的男亲戚都很善于玩这个游戏,他们了解游戏规则,并为规则赋予重要意义。父亲特别重视校长报告、奖学金、荣誉学位考试和学院职位这类东西。费希尔家族的男孩子们几乎拿到了所有的奖励、荣誉和学位。”
阻止女性受教育的言论“像树根一样坚固,又像海雾一样无形”。接受严苛教育的男人们渴望拥有少女般单纯、甜蜜、忠贞又温柔的家庭之花。如果让女人学习拉丁语或希腊语,这些花朵可能会枯萎。
曾有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母亲,她同意送女儿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读书的条件是:她必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那样”回到家中。
在各类文艺活动中,写作是女性最容易进入的,但仍未得到完全的赞许。范妮·伯妮烧毁了“大量”早期作品,这是出于她自己的羞耻感—而非(弗吉尼亚认为的)继母的强迫。
“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女人一生的事业”,罗伯特·骚塞曾在给夏洛蒂·勃朗特的信中写道。勃朗特向他保证说,她作为一个家庭女教师,每日的工作量让她“没有一丁点儿时间去做梦”。
她继续写道:“我承认,我的确常常在夜晚沉思,但我从不用我的想法去打扰别人。我小心翼翼地藏起自己心事重重或古怪反常的样子,以免生活在一起的人发现我的爱好……我不仅要用心履行一个女人应尽的一切义务,还得努力对它们感兴趣。我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因为,当我在教书或做针线活的时候,我更想读书或写作;但我试着克制自己……”
04
这些零散的记忆,
构成《到灯塔去》的根基
不管弗吉尼亚如何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她依然很怀恋那时的人们的举止风度。
在《夜与日》里,当凯瑟琳和她的母亲希尔伯里夫人一起翻看家庭相册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和自己这代人做了对比。希尔伯里夫人的原型是萨克雷的女儿安妮·里奇—莱斯利·斯蒂芬第一任妻子的姐姐。
希尔伯里夫人翻看故人的照片,对她而言,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就像船,像壮丽的船,不停地向前进,不争先恐后,不像我们一样总是被琐碎的事困扰。她们像鼓着白帆的船,走自己的路”。
而在《岁月》中,佩吉——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理想破灭的医生——唯一崇拜的人就是她维多利亚时代的老姑母,她赞赏她语言中的力量,“仿佛她仍然满怀激情地相信—她,老埃莉诺—人类已经毁掉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一代人,她想。有信仰的人……”
弗吉尼亚年轻时曾听过老斯特雷奇夫人高声朗读剧本。她只有一只眼睛好用,却可以一口气读两个半小时,扮演剧中每一个角色。
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多才多艺、精力旺盛、富于探索精神、思想先进”——深深吸引着弗吉尼亚:她顽强地对抗岁月与灾祸,热情洋溢又充满活力地追求高尚与诗意。对弗吉尼亚来说,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的行为举止充满美感,这种美建立在自制、同情、无私—一切文明素养的基础之上。
她自己的母亲也完美地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气质:所有男人都很崇拜她,她也毫无疑问是个无私的女人。在美丽和俏皮的外表下,她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护士;在慷慨付出情感的表象背后,她有着严格的判断标准。她的步态显露出果决与胆识。
她笔直地撑着她的黑伞,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充满期待的神色”靠近你,她的头微微抬起,以便双眼能够直视你。对她丈夫来说,她就是华兹华斯的理想的化身,是一个带着高尚的意图去提醒、安慰、指导别人的女人。
弗吉尼亚记得,每天晚上,她的母亲都会写信为别人提供忠告和警示,对他们表达同情,“她眉宇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目光深邃如炬……她历经世事,饱尝风霜,但是憔悴的脸上却看不出悲伤的痕迹”。她的努力有的放矢,几乎从不白费。正因如此,她留在别人心中的印迹是“无法抹除的,就像是打上烙印一般”。
从某种意义上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人称道的“现代性”——那种努力逃离过去、创造当代新形式的努力——是站不住脚的。
十九世纪深深地影响了她彬彬有礼的风度举止、她的沉默寡言、她对教育和自由的渴望、对鲜为人知的人的关注(像华兹华斯和哈代一样),以及最重要的,影响了她对于崇高瞬间的强调,正是这一点让她与浪漫主义诗人产生了联系。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
童年时代在圣艾夫斯的夏日时光是永失的乐园,铭刻在她的记忆中。海浪、散步、海边的花园唤醒了“崇高的感觉”。康沃尔带给弗吉尼亚的就像湖区带给华兹华斯的一样,是一种自然中的情感现实,在往后的生命中,没有任何体验可以超越。
1882年春天,弗吉尼亚刚刚出生后,莱斯利·斯蒂芬像往常一样在康沃尔漫步,他偶然走过一段“能够想象到的最美的路程”。他看到缓缓倾斜的原野上长满荆豆,中间夹杂着成片的报春花和风铃草,远处可以望见圣艾夫斯海湾和沙丘。清甜的微风吹过广阔的原野,他描述说,空气柔软如丝绸,带着“新挤的牛奶般的鲜甜味”。
一时冲动,他去查看了正在招租的塔兰德屋。
这栋房子是大西部铁路公司在十九世纪四十或五十年代修建的,不过,铁路在八十年代初期才延伸至圣艾夫斯。当时,这个四四方方的大房子就坐落在城外的一座山丘上,楼上的房间还没有家具,自来水管道也没有安装,不过,这里视野极好,对面就是海湾和戈德雷伊灯塔。
莱斯利·斯蒂芬在这里度过一晚,他告诉妻子,他拉开窗帘躺在床上,只为能“看到海滩上嬉戏的孩子们”。有一条平坦的小路正通向下方的沙湾,“孩子们很容易就能走下去”,他写道。
于是,每年七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斯蒂芬一家会搬到这里住一段时间。那时的圣艾夫斯尚未遭到破坏,仍然保持着十六世纪的风貌:房屋像一大堆贝类、牡蛎和海蚌,杂乱地覆在陡峭的山坡上。为了抵御海浪和大风的侵蚀,这些白色花岗岩石屋的墙壁都建得很厚。圣艾夫斯是一个地势崎岖、多风、街巷狭窄的渔村—一个远离他们单调而憋闷的伦敦居所的自然世界,在一年中的另外十个月,他们都难见天日。
每当弗吉尼亚回忆起塔兰德屋时,她总会想起花园里的孩子们。
这个占地一两英亩的花园由十几个被灌木树篱分隔开的小草坪组成,它们沿着斜坡向大海延伸。每个角落、每片草坪都有自己的名字:咖啡园、板球场、厨房菜园、池塘。这里有能让孩子们滑滑梯的斜坡、缠结的醋栗灌木丛、泉水、远处的马铃薯和豌豆苗床,还有各类夏季果实:草莓、葡萄、桃子。
“总之,”莱斯利·斯蒂芬在1884年写道,“这里就是一个小天堂……”
每天,孩子们都能吃到一大碟撒着焦糖的康沃尔奶油茶点。他们每周日都跟父亲一起步行到特伦克罗姆山。从山上可以看到康沃尔两侧的海岸,一侧是圣迈克尔山,另一侧是圣艾夫斯海湾。通往山顶的小路藏在欧石楠花丛中。“爬山的时候,我们的腿被刮伤了;荆豆花黄灿灿的,有香甜的坚果味。”
正是这些零散的记忆而非正式的事件构成了《到灯塔去》的“根基”。
弗吉尼亚无法忘记1892年9月到戈德雷伊灯塔的旅程,以及弟弟如何因为不能前行而垂头丧气,这些都记录在了孩子们自创的报刊《海德公园门新闻报》里。
《到灯塔去》留下了弗吉尼亚对朱莉娅·斯蒂芬的记忆:炎热的午后,她坐在走廊里看着孩子们玩板球。弗吉尼亚还记得塔兰德屋是多么脏乱破旧,客人们又是如何熙熙攘攘:有烟瘾的沃斯滕霍姆先生坐在蜂巢椅上,他是《到灯塔去》中那位独立诗人卡迈克尔先生的原型;还有基蒂·勒欣顿——保守的明塔·多伊尔的原型。基蒂听从斯蒂芬夫人的劝告,在铁线莲花丛下接受了另一个客人的求婚,孩子们立即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爱情角”。
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些本地居民:爱丽丝·科诺提着满满的洗衣篮,歪着身子,脚步沉重地走在车道上;珍妮·贝里曼打扫了房间—她们都在这个孩子牢固的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她的小说中延续生命。
塔兰德屋那田园诗般的生活持续了十年,直到1893年的夏天,屋子前面建起了一座“地狱般的宾馆”,斯蒂芬一家人也因此预见了圣艾夫斯的商业化。
“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让我如此魂牵梦萦,”莱斯利·斯蒂芬给妻子写信说,“看着那儿的板球场,想着曾坐在那儿的所有人,对我而言几乎是痛苦的……”又过了一个夏天,他们还是放弃了这栋房子。
十一年过后,弗吉尼亚的父母都已过世,兄弟姐妹重返故地,看到许多坚固的白色建筑拔地而起,在1894年的时候,那里只有一片欧石楠花丛,而曾经只有一条步行小径的荒野旁边也铺设了宽大的公路。
对弗吉尼亚来说,1905年重返圣艾夫斯的旅程无异于一场朝圣(这个词经常出现在她的康沃尔日记里)。8月11日的日记有意写成挽诗体,它记录了兄弟姐妹四人坐上大西部铁路火车时内心如何充满了希望。
在英格兰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我们会找到被封存的过去,仿佛在这段时间里它一直被悉心守护和珍藏,只等待着我们回去,回到那一天……啊,这种感觉多么奇妙,看着熟悉的陆地和海洋的轮廓再次在眼前呈现……那些无声无息却可以触摸到的轮廓,十多年来只能在梦里,或在清醒之时的幻象中出现”。他们再一次看到悬崖上的褐色岩石如瀑布一般倾泻入海;海湾的曲线“似乎环绕着一大片流质的雾”;在那里,海岛的岬角发出簇簇光芒。
黄昏时分,他们乘着铁路支线到达海边,走出火车站时,他们想象自己只是结束了出门在外的漫长一天,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等他们到达塔兰德屋时,会猛地推开门,看到自己置身于熟悉的场景中。
他们穿过马车道,登上坑坑洼洼的台阶,从灌木丛的缝隙向里窥视:“我们看到了那栋房子……石瓮紧靠着高高的花丛;我们目前看到的一切就好像是今天早上才刚离开这里。但我们也很清楚,不可能再往前走了;如果再前进一步,魔咒就会打破。那些灯光不是我们的灯光,声音也是陌生人的声音。”
他们在此逗留,幻想还能走近客厅的窗户——《到灯塔去》第一部分的情景框架——但他们不得不保持距离。“我们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树篱的阴影中,直到听到脚步声,我们转身离开了。”
多年后,弗吉尼亚·伍尔夫又一次回到这里。1936年5月,当她因为《岁月》而濒临崩溃时,又悄悄回到塔兰德屋的花园。黄昏中,这个五十四岁的女人透过一楼的窗户向屋内窥望,想重新找回那个早已逝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夏天。
本文摘编自
《弗吉尼亚·伍尔夫传》
作者: [英] 林德尔·戈登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艺文志eons
副标题:作家的一生
译者: 谢雅卿
出版年: 2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