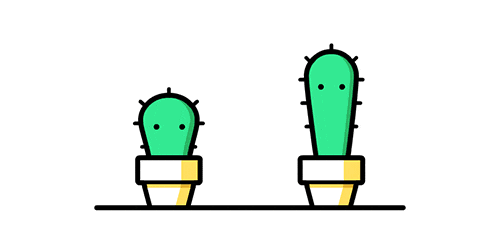到大觉寺看孔雀| 星期天文学·叶昕昀
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补缀、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26辑,嘉宾是青年作家叶昕昀。《最小的海》是她的首部小说集。余华在为此书所做的序言中评价叶昕昀:“每次阅读她的新作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我不知道她接下去的写作里还能爆炸出什么能量。”
下文节选书中第一篇文章《孔雀》,此文首发于2021-4《收获》,称得上是叶昕昀的成名之作。文中,一个瘸腿的女人与一个独眼的男人,因为被介绍相亲而相逢,关于他们的一些往事的真相逐渐在约会的日常中抵达……
叶昕昀在此文的创作谈中如此写道,“他们不只是我小说中的人物……我们是孤独者的相遇。他们的孤独,就是我的孤独。”
叶昕昀,1992年出生,云南曲靖人。本科毕业后进入国企从事行政工作,三年后辞职。2018年开始小说创作,2021年取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与批评方向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最小的海》是她的首部小说集。
孔雀(节选)
她约张凡到大觉寺看孔雀那天是六月十九。到寺庙上香的人很多,流通处厢房买香烛和文疏的人几乎没有间断。她那天脑子昏得很,人家说要一把香,她递两把,说要三道文疏,她递五道,昏头昏脑地到下午三四点,几乎忘了看孔雀的事。四点寺庙关门,人渐渐散去,她一样一样清点货品,发现柜台里的绿松石手串少了一个,不算贵,二十来块钱,买去图个吉利的,但少了要她补上,多少觉得亏损,只能怪自己不留神,再一想,又怪老刘今天没来,她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大概就是埋怨到老刘头上的时候,张凡到了。他们此前没有见过面,是经常来寺里做事的周孃从中牵线,说让两人见个面,算是没有明说的相亲。她没有拒绝。
他从外面探头进来,大热天还穿一个皮夹克,个子挺高,皮肤是云贵高原紫外线塑造的黝黑。他问,杨非在吗?她点点头,说,在呢,你面前。他一下子就笑了。她看他,你是张凡吧。他说,是,我是张凡。
她注意到他挺拔的身躯和稳重的步伐,然后低下头去,说,你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一会儿,我还有事没做完。她习惯点两遍货品,算是某种强迫症,现在还差一遍。张凡问,这里忙吗?她低着头,说,看日子,香客多的时候一刻也不得闲,你待会儿再跟我讲话,我现在忙不过来。
张凡便不说话,坐在椅子上看院子里的三角梅,他的右眼视力好,看得清相隔二十米对面佛殿牌匾上不大的字,是地藏殿,他想问地藏殿供的是哪个菩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往地藏殿旁边看,佛殿的匾额被一棵贝叶棕遮住了,他将目光收回来,看厢房门口浮着睡莲的青褐色石缸,里面有几尾金鱼,天气太热,一直往外吐气泡。他盯了很久,听到杨非说话,你定力挺好。他回过头去,杨非又说,走吧,去看孔雀。
她把柜台的隔板抬起来,张凡过去扶住,让她出来。她解下身上的墨蓝色罩衫,把身后那条长长的黑发拨到胸前,平视的视线只能达到他的腰际。他系着一条黑色皮革的腰带,印着老虎头的金属闪着光。她说,要劳烦你。张凡就走过来,站在她的身后,微微蹲下,两只手托起她轮椅两侧的把手,缓慢地抬起来。她比他预想中轻很多,即使加上轮椅的重量也还是很轻,跟他儿子的重量差不多。他感觉到她的双手紧握,后背往下靠,他尽量使自己的步子平稳。他抬着她的轮椅跨过厢房的门槛,到了台阶,那里有专门的木板搭成的小坡,可以让轮椅下去,他没有放下,直接将她抬下台阶,然后安稳、缓慢地让她落地。
杨非对他说谢谢,声音很轻。张凡假装没有听见,预备推着她往前走,杨非用手卡住轮子,说,不用,我自己来。张凡就撤开手。
寺庙的路都是石子铺成,她划动得有些吃力,张凡放慢步子,跟在她后面。她在石子路最里面的禅房门前停下,说,里面的木桶里有玉米粒,你用碗装一点,碗在木桶旁边。他走进去,禅房的案桌上立着一幅观音送子的画像,香已经燃尽。他绕过案桌,在角落里看到木桶,旁边放着一个不锈钢碗,他从桶里舀起一碗玉米。
她看见他走出来,说,把门带上。他回过身去关门,转头时她已经往前走了。他跟着杨非,绕过大雄宝殿,来到寺庙的后院,远远就望见那只被一片铁丝网围起来的孔雀。
孔雀站在罗汉松旁一动不动,杨非划着轮椅过去,将扣住铁丝网的钩子移开,然后回头看张凡,说,放里面吧。
食物就在面前,孔雀仍站在原地不动。张凡蹲下,将碗往里面推了推,孔雀警惕地扬起脑袋,头上的冠羽轻轻地晃动。张凡这才注意到孔雀蜷缩着一条腿,准确来说不是蜷缩,而是萎缩,它只凭一条腿立在那里。张凡突然想知道它怎么走路,于是又往前走一点。孔雀意识到入侵,往后退,它萎缩的右腿落在地上,右半边身子大幅倾斜,左腿立即向后迈一步,将身子稳住。
张凡觉察到这样有些残忍,他于是向后退去,直到走出它的领地,关上那片铁丝网,与它保持最初的距离。
张凡到杨非身旁,孔雀还是待在退后的位置,没再往前。张凡说,它挺怕生。杨非说,分人。张凡点头,我确实吓人,别人都这么说。杨非说,这挺好,没人敢欺负。张凡笑,它怎么不吃。杨非划着轮椅退后,说,人走了它才吃。张凡说,还挺有个性,养了多少年了。杨非想了想,说,二〇〇八年老马从版纳带回来的,也有十来年了。张凡问,谁是老马?杨非说,以前经常给寺庙捐钱的富源煤老板,后来煤矿倒了,就没再来过。张凡点点头,那也挺老了。杨非问,谁?张凡说,孔雀。杨非没说话。张凡往左边跨了一步,说,这是绿孔雀吧。杨非说,不知道,我不懂。张凡说,这是绿孔雀,我当兵的时候在怒江集训,见过这种孔雀,现在是濒危动物了。你们养得不好,毛色都变了。杨非问,你在怒江当的兵?张凡说,算是吧,滇西那片都待过。杨非问,怎么样,那边。张凡说,不好在,不如东边。杨非没再说话。
张凡退到杨非身后,他们站在松树下面。一片云彩飘到太阳底下遮住光,天微暗下来,吹来一阵风,张凡觉得凉快,又觉得有些恍惚。空气中有从前院寺庙飘过来的檀香气味,在此刻短暂的静止中,他心里生出一种久违的隐秘和平静。
从后院出来,她觉得饿,提议去寺外的清真街吃凉粉。张凡说好,他们便往外走。张凡说,我推你吧。她说,不用,走到千佛塔的时候,又说,好吧。他走过来扶住她的轮椅。她抬手指着千佛塔,说,上学的时候来参观过吗?他说,没有。她问,那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建的吗?他说不知道。她告诉他,是元代。他说,没谱气,历史没学好。她说,有六七百年了。他说,噢,是古物。她身子往后靠了靠,说,我刚来寺庙的时候,每天就在塔下面看,看到太阳刺得眼睛睁不开才回屋,后来视力就降了,总是看不清楚。他说,那你配个眼镜。她说,不用,能看清人就行。他说,人你看不清。她岔开话去,问他,你知道这塔有多少龛佛吗?他说,千佛塔千佛塔,上千吧。她笑,你回去查查。他点点头,好,塔尖的两只鸟是什么。她随着他抬起头来,一齐看那座二十米高的佛塔,她笑,那是鸡,金鸡。他说,我看着倒挺像后院那只孔雀,你看,它也蜷着腿。
他们在凉粉店外坐下来。有几个人在里屋,杨非说热,他们就在外面坐下。杨非是熟客,老板娘笑问,今天吃什么?她说,两碗凉粉,我那碗不要米线,你呢,她转过头去问张凡。张凡说,我要多一点米线。杨非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张凡答,司机,给领导开车,之前跑长途货运。杨非点点头,介绍人没跟我仔细说你的情况。张凡看着她,你想知道什么,随便问。杨非摇摇头,现在不用了。张凡说,我离过婚,有个儿子,跟了他妈。杨非没说话。张凡又说,我爸死得早,家里有个老母亲,现在城里住的房子是我大伯的,我前些年在开发区买了套电梯房,还有辆二手车,大众的。杨非说,吃东西吧。
和张凡分开的那天夜里,杨非发起了高烧。房间里很闷热,她想也许是明天要下雨,然后想起张凡眼睛上的那颗痣,又想起洒在地上的玉米粒和落在泥土里的月季花瓣。她渐渐魇在清醒的梦里,小腹传来的疼痛没有减弱过,从子宫右侧的某个点开始,呈放射状地蔓延着疼痛,它不是持续的,大概隔几秒加剧,躯体的痛楚将梦境变成一堆破碎的画面。她有时听见开门声,有时听见有人在耳边低语,有时看见灰褐色的水泥广场和漫长的延伸到铁轨的马路,然后那个男人模糊的身影又开始出现,慢慢靠近,她感觉到自己在坠落,然后是奔跑,似乎有风从她耳边穿过,又拂过她的小腹,她摸到自己的双腿,突然从梦魇中清醒,像是沉溺在海底又浮出水面的一瞬间,那种熟悉而恒久的绝望。
一丝光从蓝色的窗帘透进来,她盯着窗帘上跃动的斑点,很久以后,那种梦境带来的无法言说的感受仍在持续,那种针刺般的、小小的欲望从她腿骨的一处开始蔓延。天渐渐亮起来,光充满空荡的房间,充满她内心某块凄清的空白。
她终于听见父亲起床的声音,她轻轻喊着,但嗓子几乎发不出声音来,她张着嘴吐出无声的语言,然后抬起右手,从空中降落,捶击在床沿,只是发出轻微的响声。过了很久,她听见父亲推开她的门,说,起床了。她没有回应他,他于是走过来,看她暴露出青筋的脸庞和手臂,以及肿胀的眼睛。他摸了摸她的头,说,我去买针水。她感觉到内心突然滋生起来的与悲伤相掺杂的怒火如同落在床上的拳头一样,软绵地四散开来,散布到身体的每一处。
那天她没到寺庙去,第二天也没去。第三天的时候,张凡找上门来。下午三点,父亲刚下中班回来,他在附近的小区当保安,三班倒。她坐在阳台上吹风,父亲走到她背后,说,你有朋友来了。她转头,短暂的诧异之后,她看见张凡的脸。透过窗户的光照在他的脸上,印出三道长长的条纹。
张凡走过来,把手里的水果放在茶几上,父亲咳嗽了两声,走进房间,关上门,将她和他隔绝于那间落满斜纹光影的客厅。张凡站在客厅中央,说,我去寺庙找过你。她没有说话。张凡又讲,阳台上晒,要不要我推你进来。她自己把轮椅退回来,摇到茶几旁边。
她请张凡坐,要给他倒杯水,张凡拦住她,说,我自己来。他在她面前站起来,身体挡住她面前的光,她注意到他今天换了一条腰带,棕色皮质。他握着杯子在她面前坐下来,说,我想了想,觉得我们能处。杨非说,怎么处。张凡转动着杯子,说,你看我的眼睛。杨非看着他。他说,左眼。她就看他的左眼。他说,你仔细看。杨非说,怎么弄的。张凡说,在勐海的时候,抓捕一个毒贩,他拿刀朝我眼睛捅过来,我没来得及躲。她问,勐海在哪里?张凡说,在版纳,对面就是缅甸。她说,挺狠毒的。张凡抬起手摸了摸左眼,说,他没下狠手,他本来可以朝我脖子捅,我肯定死。两人沉默,她又看他,说,这眼睛挺逼真,是马眼睛吗?小时候丝厂大院里有个男孩,被鞭炮炸掉了眼睛,在眼眶里装了一只马眼睛。张凡摇头,不是,是玻璃的。杨非点点头,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张凡问,你们以前住在丝厂?
杨非摇着轮椅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水,说,以前我爸在丝厂缫丝车间,做到车间主任,我们就住在生活区,十平米的房子,没有厕所,整栋楼都是尿腥味。后来丝厂倒闭,我们就搬了出来。张凡站起来,在屋子里四处转着,说,丝厂是二○○○年左右倒的吧。杨非说,好像是,想了想,又说,是,那年我初三。
张凡在电视柜的几张照片旁边停下来,他仔细看了很久,转过头问杨非,你小时候跳舞?杨非说,是,从小就学,拿过县里挺多奖。张凡说,真厉害,学过舞气质不一样。杨非没接话。张凡又说,你应该开个舞蹈班,教孩子跳跳舞。杨非说,我这样子怎么教。见张凡有些尴尬,她又说,我不喜欢小孩子。
张凡感觉到杨非兴致不高,他在那些照片旁边停了很久,说,要不然今天出去,你喜欢看电影吗?一中对面的商业中心新开了一家电影院,环境不错。杨非说,我不方便。张凡笑,有什么不方便。杨非说,我不爱出门。张凡说,要适当出去走一走,外面都大变样了,我带你去看看。
杨非没有拒绝。
她这几年相了很多亲,要遵从彼此匹配的原则,所以对方都缺胳膊少腿,像是照镜子,相互看见都觉得尴尬。她与张凡的第一次会面却不尴尬,这是她少有的体验。另一个觉得不尴尬的是一个乡镇中学的语文老师,右腿车祸截肢,爱读史铁生和路遥,眼镜总是滑到脸中央,笑起来眉头就皱在一起。他们那时几乎快成了,后来男方家里又嫌她工作不好,要她陪嫁一套房子,父亲几乎要妥协,她找到语文老师,说我们还是算了,残缺的地方不一样,彼此补不起来。
张凡是第一个以四肢健全的姿态站在她面前的男人,她观察他,想要发现他的残缺,最后得到的却是他的无比健全,她竟觉得恐惧。她早发现他的眼睛问题,可这种残缺和她的残缺并不对等,和她比起来,他仍旧是健全的。她厌恶他的健全,却又贪恋他的健全。
张凡开来一辆吉普,是单位的车。他将杨非推到院子里,上车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但这种犹豫没有持续太久。他说,我抱你上去,轮椅放在后面。杨非同样地犹疑,她看着张凡的腰带到达她的眼睛,突然觉得有些滑稽,她点了点头,双手从扶手抬起来,张凡蹲下来,轻轻咳嗽了一声,靠近她的身体,将她的双手搭在自己肩上,抄手绕过她的双腿,扶住她的后背,轻轻地,将她抱了起来。她轻轻贴着他的胸膛,大脑里有一瞬间的空白,除了父亲,这些年来,她再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靠近过一个男人,他的军绿色衬衫上有着炙热的汗味,带着腥气,她的体内突然又升起那小小的刺痛感。
张凡将她轻轻放在副驾,她的重量在他手上消失的时候,他的衣衫上沾湿了一片汗渍。他关上车门,在炙热的空气里轻轻呼出一口气,提起地上的轮椅,放进后备箱。他记得那天热得出奇。
她坐在副驾,看着放置在她前面的车辆通行证,下面印着一个大大的政府红章。她轻轻吐出一口气,一种陌生的未知在她面前展现。
张凡上车,侧脸看了看杨非,说,系一下安全带,最近查得严。她拉过背后那条长长的黑色带子,始终找不到能够扣住的地方,她的脸憋得通红。他终于伸过手来,拉住她的安全带,轻轻扣进去。她没觉得得救,而是更重的沉溺。
一路上,他们没有说话。他推着她从地下车库走进电梯的时候,她尽量使自己不低下头去。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一个穿黑色裙子的女人跑进来,眼神在杨非身上停了很久,她与他们并排站立,毫无掩饰地表达出对于他们的好奇。从地下二层到一楼,电梯的空间始终呈现一种密闭而窒息的状态,从电梯出来,她再次感受到那种从海面浮起来的感觉。
他去买票,她在后面等。后来让她回忆,她完全记不得那天看的到底是什么电影。工作日下午看电影的人很少,售票小姐的声音在空荡的大厅里听得很清楚,售票小姐说,两张是吗?张凡说是,售票小姐问,是后面那位女士吗?张凡说是。售票小姐微笑着说,凭借残疾证可以半价。张凡说,不用,两张全票。售票小姐说,好的,请稍等。
她突然想立刻逃回去,逃回那间此刻已经落满日光的房间,一个人藏在被子里,睡上漫长的一觉,等到黄昏来临的时候,去感受房间空荡的凄清。但她终究待在原地,像她人生中所面临的所有选择。她看见他朝她走过来,她一时分不清他哪只眼睛是真的。他看着她,说,我们走吧。
她在梦境里再次沉溺,在梦境那片荒凉的废墟里,那种只属于她的昏黄色调的梦境里,她始终有一种不想再醒来的愿望。
那天从电影院出来,他说,你喜欢看飞机吗?她问,什么?张凡说,城外的军用机场,附近有一个很高的水坝,小的时候我经常去那里看飞机。
小城是云南最大的坝子,抗战时期在县城西南边建了军用机场,驻扎美国空军部队,建国后成了空军训练基地。张凡小时候跟爷爷住,就在机场旁边的村子,每天听见飞机在头上轰隆轰隆地飞过。他问爷爷,是不是要打仗了?爷爷抱着水烟筒,你想不想打仗?他说,想,电视里演的可刺激了。爷爷摇摇头,不说话。老家的墙上现在还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美国大兵,搂着一个小男孩的肩膀,男孩裸着身子,骨瘦如柴,瞪着眼睛看镜头。那个男孩就是爷爷,爷爷的父亲曾经是修建机场的民工,每天都要拉着巨大的石碾压碾机场跑道。有一次爷爷跑去机场给父亲送饭,美国人给他拍了一张照,后来洗出来送给他,爷爷一直视为珍宝。那个大兵,是开战斗机的嘞,爷爷说。张凡说,那我以后也要开战斗机。
他们最后去了盘江河边。盘江属珠江水系,绕县城四十余公里,这是距城最近的一段。河边新建了一片别墅区,修了宽大的柏油路和河滨公园。杨非小时候来过,那时候这里还只是一条长长的泥土路,在土堆里能找到大大小小的海蛳螺。那些童年的海蛳螺使她相信课堂上老师所说,这里原来是一片海洋,后来海水退去,成了一片平原,一片在云贵高原中低洼处的显眼坝子。
那时太阳已经落下去一点,没有建筑的阻挡,阳光恣意地、大片地照耀着柏油路大道,他推着她沿树荫走。他原本想沿台阶下到河边,但台阶很高,没有适合轮椅下去的坡道,他就放弃了。他感觉她有些累了,便在一片树荫下的石凳坐下来,旁边是一棵炮仗花树,长出来的花红得像一串串鞭炮。在路的对面,一排排空着的商铺贴着招商广告,中间有一家突兀的小超市,他说,我去给你买瓶水。
她坐在炙热的大地里,转过轮子,去看河水。已是汛期,河水涨了上来,河流裹挟着从上游漂流下来的松木枝和各种垃圾。河岸的斜坡上间杂地长着各色矮牵牛,偶尔有羊群从公路穿过,不听话的几只就跑下来,咬几口岸边的花,再留下一堆小小细细的粪蛋,等赶羊人长长地喊一声,它们又跃跑着追上羊群。
等她转过身来的时候,他已经给她拧开了瓶盖。他指着河对面那片红墙建筑说,我初中就在那个中学。她点点头,九中。他说,你在一中吧。她说是。他喝了一口水,看来学习好。她笑,学习不好,小升初是舞蹈比赛保送。他便惊叹起来,真是厉害。她突然愿意谈论这个话题,说,我读书读不好。他说,我更老火,看见字头就疼,天天想着能开飞机。她笑,你想当飞行员?他说,从小就想,但我连高中都没考上。她说,你当兵了,也算是接近。他说,不一样的。他扎你眼睛的时候你疼吗,她突然问。
张凡看着河流上的大桥,那桥算是一个城乡分界线,驶过那座五十多米长的大桥,便算出了城。从前那只是一座不到三米宽的小石桥,每天晚上下自习,他就骑着自行车穿越那座小桥,去大伯家里。他借住在那里,留给他的是一个三平方米的小房间,之前是他的奶奶住,最后奶奶死在这个小房间里。大伯和父亲将奶奶从房间里抬出来,她睡得很安详,那对陪伴她大半辈子的、长长的玉石耳坠将她的耳朵坠到了底。小时候他曾问奶奶,你什么时候死?奶奶摸着耳朵,说,等我这个洞坠到底,就死了。他被那把尖刀戳穿眼球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就想到奶奶那只坠到了底的耳洞,他觉得自己的眼睛也坠到了底。
他说,当时没有感觉,后来才觉得疼,觉得自己会死。她看着他的眼睛,说,后来呢,那个毒贩。张凡拍了拍自己的胳膊,抬起手来,臂膀上印着一只虫子的尸体。被战友击毙了,一枪穿破了脑袋,他说,就倒在我面前。
杨非不再说话。
张凡帮她赶了赶面前的飞虫,问,你以前跳什么舞?她看了看他,似乎自己也有点疑惑,顿了一会儿,才说,学的民族舞,老师说我跳孔雀舞好看,后来就一直跳孔雀舞。杨丽萍你知道吗?张凡点头,知道,我妈喜欢吃的那个糕点,包装上印着她。杨非说,当时老师天天让我看她的录像带,我还逼着我爸买了台VCD。张凡说,你爸对你真好。杨非沉默下来。
读书的时候追你的人很多吧,张凡突然问。杨非说,还行。张凡笑,看样子很多,有谈朋友的吗?
杨非说,有一个。张凡问,什么样的?杨非说,长得还行,就是有点胖,都叫他胖子。他爸是县里的官,有钱,每天都给我送早点,买礼物。张凡点头,是,男友有钱就魅力大增。杨非没搭话。张凡说,我能抽根烟吗?杨非说,你抽。张凡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点了火,嘴里含着烟说,电视里都这么演,男人没钱,女人就要跑。杨非看着他,你觉得我是贪你的钱么?张凡说,我不知道,我也没钱,但我觉得你贪别的。杨非望着他,什么?张凡不说话。杨非说,麻烦烟借我一支。张凡看她,没说话,拿食指敲出一支烟,把自己的烟头凑近,点燃,递给她。张凡说,你会抽烟。胖子教的,杨非说。后来呢,张凡问,你和胖子。
太阳又落下去一点,杨非往树荫下挪了挪,后来我出事了,休学,没再联系过。张凡说,现实。杨非两只手叠在一起,望着对岸。
两人聊到天已有些擦黑,那时晚饭后到河边散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张凡说,我们走吧。他推着杨非向路边的车走去,打开门,轻轻抱起她,放到副驾驶座上,他碰到她的双腿,觉得异常冰凉,他看了看她,她只是抿着嘴不说话。
她到家的时候,父亲坐在桌边。她叫,爸。父亲点点头,吃饭吧。她扒拉了几口,说吃饱了。父亲说,在外面吃了?她答,没吃,就是吃不下。父亲动了动嘴,没说话。
她回到房间,去抽屉里翻相册。门锁坏了,她就推着轮椅背靠着抵住门,一面听着外面父亲洗碗的声音,一面一张一张地翻照片。照片右下角印着的暗红色的日期在提醒她,在某个时刻,她曾在某个地方对着镜头笑过。与张凡聊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似乎陷入一种失忆之中,记忆并非她想象中连贯的线条,而变成一些细小的、随时可以丢弃的碎片,这使她感到一种被记忆背叛的恐惧。这是第一次,她涌出一种强烈的、回忆过去的渴望,那些回忆曾被她强制压在脑子某一处黑暗的角落。
她突然听见父亲向她房间走来的脚步声,她左手抵住门,右手将相册往床底下滑过去,留出一个边角,她没来得及过去塞起来,父亲就推门而入。
父亲端着菠萝水进来,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个,用冰糖煮菠萝,放凉以后搁到冰箱里,冷透了再拿出来吃。以前没有冰箱,父亲总是煮好一锅,笑嘻嘻地去楼下的小卖部,放在小卖部的冰柜里,晚上去拿,给小卖部舀了大半,剩下的半锅端回来。
她接过菠萝水,问,今天不上夜班吗?父亲说,待会儿就去。父亲站在她面前,看她吃完几块菠萝,说,今天那个男的就是你周孃介绍的?她说,是。父亲说,还是找个真心实意的好。杨非说,他挺真心实意。父亲递纸给她,让她擦嘴。还是条件相当一些的好,父亲说。杨非吃下最后一块菠萝,菠萝卡在她的喉咙,等她吞咽下去,喉管里却始终残留着一段可感的空隙。父亲接过她手里的碗,转身出去,轻轻关上门。
她把纸巾捏在右手手心,用左手划动轮椅到床边,用轮子推了推那本相册,她低下身子去,没有够到相册,她再弯下去一点,还是够不到。她的身子趴在自己的腿上,随即缓缓抬起,她扬起手,重重地捶在腿上,没有一点知觉。
张凡和杨非开始定期见面。一般是一周一次,张凡空下来,就去找杨非,他在寺庙外一条巷子等她,开车去河边,或者是公园。他们第一次亲吻是在月亮湾公园。那是一个废弃很久的公园,荒草长得老高,池里暗绿色的水发出阵阵臭味。是她提议去的,说是小时候去过公园里跳蹦蹦床,五毛钱两个小时,她很喜欢那种腾空的感觉,比跳舞时的那种腾空要精彩得多。那边,她指了指公园东北角,以前蹦蹦床就在那片空地上。张凡朝她指的方向看过去,现在堆满了一层层破碎的石棉瓦和几个废旧的皮沙发,越过围墙,旁边是一片居民区,居民楼窗户里漏出的光照在那片废墟上,能看见灰尘的颗粒在黄色的光晕里流动。
他们选择了一片草比较浅的石凳,他挨着凳子的边沿,扶着她的轮椅。她说,给我讲讲你当兵时候的故事吧,我爱听。她喜欢他那些与此刻不同时空的故事,带着残酷的荒蛮和猎奇。她也喜欢他讲故事时的神态,眼睛微微眯起来,仿佛与这个世界隔着一层主动的疏离,然而她却能穿过那层疏离,轻易地走进他的世界。
他说,我入伍的时候,跟的是李哥,就是我跟你说过,用枪打破毒贩脑袋的那个。他跟我是同乡,比我早几年入伍。李哥带我们去边防站查检,是个半夜,我记得挺清楚,刚下过暴雨,看得见蓝色的天空和白云。我们上一辆卧铺车检查,大部分人还在睡觉,各种奇怪的味道混在一起,我的脑子猛地清醒起来。几个男人坐了起来,抱怨一趟车要检查多少次,李哥低吼了一声,车里立刻安静下来。我跟在李哥后面,车门处的卧铺坐起来一个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头发黄黄的,看上去像发育不良。李哥挨个查身份证,让我搜他们的随身行李,其他几个战友搜车厢里的大件物品。那女孩低着头看我,嘴唇发白。她移动身子从床上下来,我在她卧铺上翻找,李哥提醒,床铺什么的都要翻,我一一照做,最后是她的包,一个黑色皮革的背包,表面的皮革剥落,我让她把包里的东西倒在床上,仔细查看每一件物品。然后第二个人。我们没有发现什么,我松了一口气,有点像以前看考试卷子上的分数,明明知道结果,还是会心惊。我和李哥走到车门边的时候,李哥停留了一下,随即我们下车,就在下车的时候,那个女孩一下子扑倒在地上,嘴里吐着白沫,李哥看过去,说,他妈的。
杨非问,她藏毒?
他说,是,塞到下体的毒品破了,我们的女兵从她阴道里掏出几百克海洛因。我现在还记得那女孩的样子。后来没抢救过来。
杨非问,她为什么?张凡点上一支烟,开始沉默。不知怎么,他突然想起,曾有一次,他也这样问过李哥。在李哥退伍的前一年,那时候他的眼睛也还没坏,李哥给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李哥说,那时队里接到一条情报,派他去中缅接壤的一个村子里和毒贩接头。那个村子里原先有十几户人家,全部吸毒或者贩毒,后来死的死,逃的逃,成了一座空村。他就躲在村里一间土基房旁的石头后面,听见毒贩在外面开枪,他听到是手枪,但不能分辨型号,不知道对方子弹打完没有。等对方的枪声停止,他拿那把步枪抵着毒贩脑袋的时候,才看清楚,那人是曾带过他的一个老兵。那时张凡问李哥,他为什么?李哥摇摇头,过一会儿,突然问他,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张凡说,我会开枪。李哥又问,如果你拿枪指着脑袋的那个人是我呢?
想什么呢,他的回忆里闯进杨非的声音。烟灰落到裤子上了,杨非说着,伸手过来帮他拍了拍裤子上的烟灰。他笑了笑,突然说,我以前不抽烟的。她抬起头,说,是吗?他说,当了兵以后才学会。她点点头。他说,那时候我们要整夜整夜地守着山头,全靠烟撑着。他抬起手里的烟,说,李哥那时候教我,在烟屁股上涂万金油,然后深深吸进去,整个肺都凉透了,脑子才清醒起来。那时候我们还开玩笑,说这么抽一口,跟吸毒没什么两样。
你尝过吗,毒品,杨非问。她的眸子望着他,似乎要从那只玻璃眼珠里发现些什么。
张凡没有直视她,说,不能算尝,有时候需要用牙床验毒,尤其是海洛因,纯度越高,味道就越酸越涩。张凡再点起一根烟,他的烟盒里已经没剩下几支了。越了解那东西,越知道不能碰,张凡说,以前我们队里一个老兵,缉毒的时候被灌了毒品,现在还在戒毒所。戒了又吸,吸了又戒,那东西根本不可能戒得了。
夜色深了下来,张凡听着那栋老旧的居民楼传来电视剧的声音,似乎是一对夫妻在吵架,在停火的间隙,他听见杨非问他,你杀过人吗?张凡吐出烟圈,烟雾随着气流缓缓上升,融合,然后消失。他说,杀过。
张凡第一次出任务,去山上伏击毒贩,李哥让他负责射击。对方是支土枪,估计是个新手,听见动静后虚空放了一枪,张凡没多想,朝着枪声的地方开了几枪,开完枪的手还不停颤抖着。李哥给他点了烟,接过他手里的枪,走到毒贩旁边,还没死透,又朝毒贩开了一枪,说,不要命的孙子。
那之后整整三个月,我天天梦见他,满身是血地看着我。张凡说完,低下头去,听见风吹过草丛的声音,他把烟蒂按在椅子上,烟灰随着风吹到一旁的草丛里,未熄灭的火星子闪了几下。然后他抬头,看见杨非的眼睛。她握住他的手,手心里全是汗珠,湿腻腻的,他就低下头去亲她的嘴唇。他听见她加大的喘息,闻着她脖颈里淡淡的香气。轮椅朝一旁摇了摇。他握住轮椅,将她放到面前来,用双腿固定住她的轮椅,他看见她脸上渗出的汗珠。
她从他的手臂里挣脱出来,觉得身体里的东西炙热得可怕。他稳定了自己的情绪,握着她的手。
她问他,后来为什么退伍,是不是因为怕死?他说,不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是。她看他,他说,不是怕自己死,是怕别人死。他说完,低下头去含住烟。她不说话,只是移过去,把头搭在他的肩膀上,一仰头,就看见稀疏的星星。
他们去河边约会的一个晚上,他送她回家,在路灯投入车内影影绰绰的光影中,他说,今晚别回去了吧。
张凡把车停在城边的一间旅馆,老式的招待所样式。张凡拿身份证去开房,杨非坐在车里等他。她看着旅馆闪着红灯的招牌,“鸿瑞宾馆”,在心里默念出声。“鸿”字的三点水掉了一个,“馆”字的颜色比其他三个字亮一些,应该是新焊接上去的。在心里默念的时候,宾馆两个字背后确切的含义慢慢在她脑海里显现,她的心脏开始加速跳动。她看见张凡走出来,站在“宾”字下面,随着闪烁的灯光点起一支烟,他厚厚的下唇兜住烟雾,再轻轻吐出来,她的目光和烟雾一起上升,停留在他那只玻璃眼珠前面,随着他轻轻的咳嗽,烟雾散去,她看见他那只在夜晚格外明亮的眼睛。她身体里小小的炙热升腾起来。
(未完)
本文摘选自
《最小的海》
作者:叶昕昀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品方:新经典文化
出版年: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