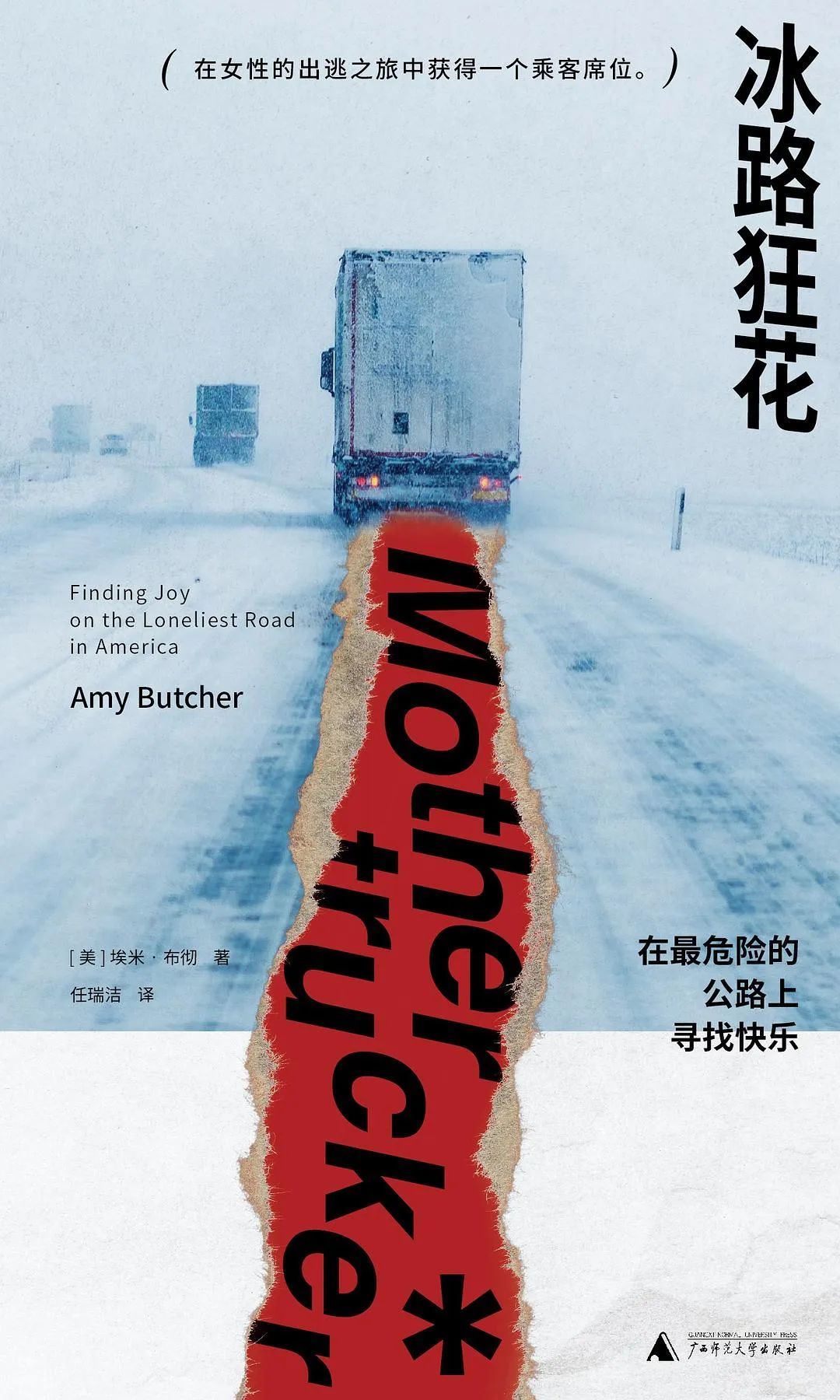穿越极寒之地,她是“死亡公路”上唯一的女卡车司机
“我(埃米)是一名女作家,也是沉默的家暴受害者。她(乔伊)是一名卡车司机,在美国最危险的公路上跑运输。”
在某次被家暴后,埃米决定“出逃”,前往阿拉斯加,与乔伊见面。
两位女性一起穿越666千米的致命冰路,在属于自己的车里,她们无须解释与证明什么,也不用再寻求他人的肯定。
在道尔顿公路,在北极荒野的狼群与驯鹿前,在乔伊的大卡车上,两位女性互相倾诉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埃米开始明白,她所钦佩的乔伊的勇气和韧性,来自于她所熟悉的痛苦。
“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书,关于我们的守望相助,以及死亡也无法阻隔的情谊。”在诉说与倾听中,她们相互依靠,彼此慰藉。
这本书记录了两位女性真实的重建自我之旅。我们从中节选了两段真实的对话记录,两个困惑又果敢的灵魂,在荒原放肆地笑,自在地哭,轻轻触碰彼此的伤痕。
下文摘自《冰路狂花》,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乔伊·维贝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道尔顿公路上驾驶重型卡车,这条路被评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公路”,乔伊是这条路上唯一一位女性卡车司机。图为乔伊和她的萨摩耶
01
这便是示警、保护
并最终拯救彼此的意义
距离北方的普拉德霍湾还有 30 英里,狂风席卷,卡车被吹得左摇右晃。车窗外能见度仅 4 英尺,眼前的一切都是白蒙蒙的。夜幕终于降临,乔伊用摇篮曲迎接它,随着节奏轻点制动踏板,想必过去的十三年她都深受这旋律的熏陶。
“情况还好,不是很严重。”她说。她掰开一盒有机草莓,一口口咬下去,草莓只剩下梗。从她咬着下唇的样子,我能看出情况并不好,她很紧张。这是乔伊第一次露出恐惧的神色。她用两指夹出一颗草莓,车轮一步一滑,拖着这台机械沉重的身躯,踉跄前行。
“没那么糟啦,”她补充道,“刚到能让你长记性的程度。”
她的意思是记住要小心,要稳住,要知道死亡是有可能的。她紧握方向盘,每根手指都攥成一个小拳头,仿佛每多一点努力就能让我们离最坏的可能远一点。乔伊解释说:“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所谓的‘冰雾’。”
冰雾像幽灵一样绕着我们的车盘旋,车窗结上了霜,我们看不清路。乔伊伸手擦拭玻璃。当太阳下山,热气蒸腾,能见度迅速降低时,空气冷到足以使雾结成冰,冰雾就会出现。她用指甲刮着玻璃,划开雾气在车窗内凝成的冰晶。
“我不喜欢这声音。”我说。
“我也不喜欢。”乔伊说。
仪表盘显示当前温度为零下 16 摄氏度,接着又跳到了零下 19 摄氏度。雪花像白色的厚墙一样被推到我们面前,沿路积雪迅速地越堆越高,民用无线电台里传来混着杂音的男声,提醒我们前方路况更为严峻。
“收到,”乔伊说,然后她看向我,“我们不是真的这样说话的,但有时候我会假装这么说。”她接着对无线电说道,“谢谢你,哥们!很感谢。”
这就是卡车司机会为彼此做的事,是里奇、唐纳德等人边吃蘸汁薯条边谈论的事,也是为什么人们会在餐券上写下救命恩人的传说。
这便是示警、保护并最终拯救彼此的意义。
“也许附近并没有人,但你还是会朝暗处呼喊,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些话会有什么用,”乔伊说,“我的心态是,要么你已经掉进了沟里,要么就在掉进沟里的路上。所以,必须时刻保持警醒。”
“不用。”那位卡车司机回话说。
我的手指紧绷着,脚死死踩住汽车地板。车子滑向一堵冰墙,乔伊再次抓起对讲机。
“你说的是真的!”她对着话筒,“这太糟糕了!”
02
她从未像现在这么美,
卸下防备,无所畏惧。
我尽量在位子上坐好。我能感到风在撞击车窗,它呼号着,仿佛一头猛兽。
“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讲给你听,但你不能——不能把它写进书里!除非我死了!等我死了你才能讲出这个故事!”
“好的。”我应允道。
她终于褪去了强悍的卡车司机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我一直期待她讲出的故事,她对公路生活本来面貌的如实描述。
我不相信乔伊没有一个故事来讲述这条路如何让她变得坚强,或者至少试图磨炼她的心志。
狂风继续撞击驾驶室,我准备开始一场真诚的对话,关于她所忍受的种种破事和来自其他卡车司机的刻薄言语,关于路上的男人们怎样的粗鄙,这些都令她感到独力难支,似乎这条路上没有她的立足之地。
乔伊开口说:“有一次……”
我竖起耳朵。
“我实在忍不住要拉屎了。”
事情是这样的:可想而知,这儿没有休息站,没有盥洗室,移动厕所也很少,且很难遇到。
“而且说实话,移动厕所更难办。”她告诉我。
我会意一笑。
“那天风很大,但我真的,真的憋!不!住!了!”
她找到一个路面变宽的地方,决定把车停在冻原上,然后下车在货物背后解决问题。
“ 我当时拖的是 …… 我也记不清了, 可能是钢管?……反正是又大又重的东西。就这样,你懂的。想着我至少该隐蔽一下,万一有别的车路过呢。”
于是,她蹲下,拉屎,然后就看到一辆卡车白亮的大灯照了过来。
“当时我想赶快完事,”她笑着说,“可是这大便啊,在这大风天,你知道压力多大吗?我有点怯场了,根本拉不出来。”
“怯场?!”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没错!”她说,“就好像得了拉屎恐惧症!我慌忙着打算站起来,想把脱到脚踝的裤子提起来,遮住我的小三角裤,可那辆卡车、那位司机,不停地朝我开过来。他肯定能发现是我,首先他会来查看,因为担心我遇到了麻烦。然后他再看看驾驶室和车身颜色,就会知道那正在拉屎的屁股,是我的。”
乔伊在座位上扭动屁股,重现当时的场景。我笑得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开始扭来扭去,”她接着说,“终于把屎拉了出来,提上裤子,可那坨屎!它……”
她笑得前仰后合。
“我的那坨屎,被风卷了起来,开始翻滚,边滚边结冻,就像动画片《结霜的雪人》似的。接着,它滚……到……了……马……路……上……就在他的卡车前!”
“大便风滚草!”我笑得太厉害,甚至笑出了眼泪,
乔伊也边笑边冒泪花。
“没错!太对了!”她说。
她用力喘着气,泪水大颗大颗地顺着脸颊流下。
“我从没提过这件事,”她说,“但好家伙,他看到了,我的超大坨大便风滚草。”
她看着我,咧嘴一笑,泪水沿着两颊的皱纹奔流。她从未像现在这么美,卸下防备,无所畏惧。
“他看到了,而且他知道,他完全知道那是啥。”
03
有些夜里,
她甚至感觉自己要死了。
她说:“让我再讲个故事。”
她抹掉眼泪,“这个故事你可以分享。”
她指向一个英里标志,但车速太快,我看不清上面的数字。
“就在这个地方,一个黑漆漆的冬天,冷得要死,我遇上了一场风暴,我是说,一场大暴风雪。”
我从座位上直起身子,试图看清前面的路。雨刮器结上了冰晶,每当我们开过坑洼或开上斜坡,我都能感到厚重的积雪摩擦着车轮,前轮毂盖几欲脱落。
“跟这会儿不一样,”乔伊察觉到我的焦虑,对我说,“现在,就像我说过的,辣妹,虽然恶劣但不算太糟,只是冰雾而已。但我要说的那一次——那次我真的吓到了。什么都看不见,前面什么都看不见,左边看不见,右边也看不见。”
我们撞上了一个坑,车打滑,但乔伊稳稳地握住方向盘。
“现在的卡车司机培训会教你,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应该沿路肩行驶,因为你看不见有什么车朝你开过来。要知道,开过来的都是巨大的卡车,而且开得很快。
但路肩也是个问题,因为它们是阿拉斯加州政府建的。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北部,路面比冻原高出 8 到 10 英尺,因为萨加瓦纳克托克河——我们叫它‘大水沟’——经常发洪水,发洪水的时候,路面被淹,谁都过不去,有时能耽搁好几天。你只能干等着,在车里看电影。公路变得像一个大露营地,我们走出车,互相问候,分享零食之类的。但你也要知道,堵在路上的每一天都会造成几百万美金的损失。”
“我有读到过。”我表示。
“没错,所以他们把路加高了,这也没什么,只是这下就没有护栏了。本该装上金属指示标,就是那种粗大的金属杆,告诉你路在哪里。但它们在暴风雨中被冲倒了,也可能一开始就没装好。本来每 15 英尺就该有一个,但有些地方大概 100 英尺才有一个,如果是为了省钱,这实在是个烂法子。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就在路上,开着车,瞎开,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她摇了摇头。
“我看不到路的边界在哪里,哪里开始是冻原,所以我决定在路中间慢慢开,放松点,努力适应前方路况。幸运的是,那天我想和萨曼莎多待一会儿,所以比平时出门要晚。我觉得就是出门晚救了我的命,因为路上除了我就没有别人了。”
“所以你孤身一人在路上,遇到了你曾见过的最大的风暴。”我说。
“是的,天很黑,天气很坏,很恐怖。”
乔伊告诉我,有些夜里,她甚至感觉自己要死了。北极的某些夜晚格外寂寥,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一片坚硬、黑暗的穹顶,这会让人不禁怀疑自己命不久矣。那些夜晚,你会救赎一切,原谅所有人。你会简短祷告,因为你知道该祷告了。
你在等待最后的时刻,你认为这是上帝的考验。你把自己卑微的灵魂臣服在这蕴藏着无数灵魂的宇宙面前,你的痛苦与他人的别无二致,你遇到的问题亦然。
她所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夜晚。
“我以为我要死了,内心的紧张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停下车,举起双手呼唤上帝。就在那时,我看到了它。”
04
所有东西都想活下来
“上帝吗?”
“不是,不是,是一只小狐狸,白色的小北极狐。它就在我前面大概 10 英尺远的位置,被三匹白狼追赶。”
她说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一只身披雪花的小狐狸,奔逃留下的小脚印消失在它身后,可是这只童话中的小狐狸全身是血。
“血到处都是,”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很同情那个小家伙,它显然受伤了,而且敌人数量比它多。”
乔伊看着它们,想着给它做个见证。当它走到她的卡车前时,突然转身,站在车灯下一动不动。风在它四周呼呼作响。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告诉我,显然她正在目睹一只动物的最后时刻,“它已经累坏了,完全没力气了,可是除了继续跑,没有别的办法。”然后它消失在她的车灯下。
“它可能在说再见吧。”我猜测。
“不,”乔伊说,“不是这样。我想那只狐狸内心深处是知道的,那些狼最终会抓住它。所以它穿过我所在的那条路,想着卡车的噪声也许能为它争取一点点时间——狼是怕噪声的。这就是它的用意吧,想在地球上再多活一会儿。”
我感到我的心脏仿佛要跳出胸膛。
最后我问:“那些狼,它们抓到它了吗?”
乔伊看着我没有说话,面色惆怅。
“我不得不开走了,”她说,“谁又说得准呢,这里的生命就是这样。那只狐狸,它的状况实在不乐观。”
我的头靠着窗户,皮肤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乔伊说:“山上的世界——当然山下也是,有时是极为冷漠的。”
从后视镜中,我看到我们的尾灯在雾中闪烁。
“所有东西都想活下来,”乔伊似乎察觉到我的不适,对我说,“在这里开车,这种事见多了,无比常见,大家都想活着。像我之前说的,那些可怕的开夜车经历。你以为自己要死了,所以你原谅了所有辜负你的人,忘记了伤害和挑剔,放下了所有世俗的怨恨,向上帝臣服。你变得更适宜去爱,于是祂决定让你活下去。”她向我伸出手,柔软的手掌搭在我的手肘上。
“这条路能让你改头换面,”她重复道,“这条路就是活着的一种方式。”
接着,就像得到提示似的,电台传来裹着电流的声音:“前方有一头死驯鹿,尸体仍在雪中流血,引来一群狼觅食。”
“情况不简单,”司机补充道,“33 英里处,附近的人,如果你正往北开的话,它就在你左手边。”
“留意它,”乔伊说,“或者别被它分了心?我也不知道。”
我瞥向窗外,黑暗中阴影涌动,我几乎看不见前方道路,更不用说远方有什么东西在环伺。我们静悄悄地缓缓驶过 35 英里和 34 英里处,乔伊轻踩刹车,终于我们看到了那头驯鹿,距离公路不到 30 英尺。
狼群倏然抬头。
“看!”乔伊说,“就在那儿,这并不是常见的事。其实就连我也是第一次见。它们肯定是引诱小驯鹿,使它脱离鹿群。这样的恶劣天气,是顿美餐。”
“可怜的驯鹿……”我说。
“只是你这样觉得。”她说。
她向狼群打了个招呼。
狼群继续低头进食,她对我说:“我们都想活下来,辣妹,这个世界不过是我们所有人为了活得久一点而奋斗,有些人得到了,有些人没有。而决定谁有谁没有,是上帝的工作。”
本文节选自
《冰路狂花——在最危险的公路上寻找快乐》
作者: [美] 埃米·布彻
译者:任瑞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