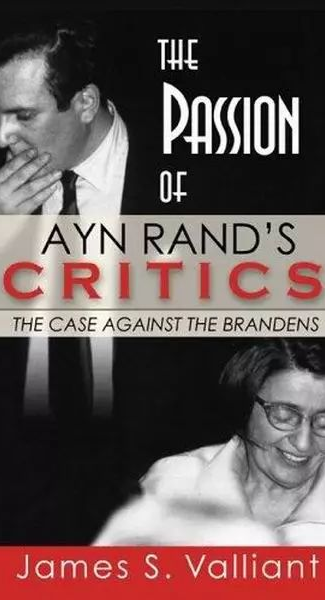影响费翔一生的作家安·兰德,曾被误解为庸俗价值观的捍卫者
“在一般的采访中我提到安·兰德,没有人会认得,只有你会认得,我特别高兴。”在《十三邀》对费翔访谈中,初代偶像费翔和许知远谈到对他影响最深的一位作家,他说:“安·兰德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作家,我看了她所有的书,不止一遍。”
美国作家安·兰德曾写下《源泉》《阿特拉斯耸耸肩》等数本畅销的小说,她的哲学和小说里提倡理性与个人主义,认为理想社会应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
在节目中,费翔讲到安·兰德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强调,但同时也提出了他的怀疑。“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尽职尽责,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但是这个社会怎么办呢,社群是会瓦解的,”费翔说,“这是现在世界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安·兰德为什么饱受争议?作为一个推崇自由资本主义的人,安·兰德如何看待金钱?安·兰德的婚外恋最终走向了彻底的悲剧,这一切为何会发生?
下文是中央民族大学田方萌老师的文章《安·兰德是思想家中的荡妇吗》,作者指出,将安·兰德视为贪婪者的教母,无疑是一种误读。
安·兰德(Ayn Rand,1905—1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期从苏联流亡至美国,以其小说作品和哲学思想闻名于世。她崇尚理性与个人主义,认为理想社会应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代表作有《源泉》(1943 )、《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后者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累计销售超过 8000 万册。
安·兰德是思想家中的荡妇吗
作者|田方萌
2017年2月底,《上海书评》刊发了香港作家林行止的文章《特朗普内阁均为兰德信徒》。林行止先生在主题之外,还点到美国思想家安·兰德的风流韵事:“……这本小书(《自私的美德》)由她(兰德)和她的‘上床弟子’弥敦-布兰登合撰。布兰登与乃师从‘入室’到‘上床’,令其妻芭芭拉下堂;后来,芭芭拉将这段灵肉交缠的‘欲史’写成《兰德的激情》,1999年拍成同名三级电影。”读者也许听说过德国哲人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的师生恋,以及法国作家萨特和波伏娃的多角爱恋,两者都不如兰德师徒的情色故事耸人听闻。
死后曝光的不伦之恋
安·兰德原名阿丽莎·罗森鲍姆(Alissa Rosenbaum),1905年生于俄国圣彼德堡,曾就读于彼得格勒大学。由于家庭受到苏联政府迫害,她年轻时就移民美国。兰德善于通过戏剧和小说表达自己的思想,晚年也写过评论文章和哲学论著,成为二十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
2009年,美国作家海勒(Anne Heller)出版了《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Ayn Rand and the World She Made),中译本也由启蒙编译所于2016年推出。海勒主要根据访谈资料和俄国档案写成此书,这部研究性质的兰德传记较为客观和全面地反映了传主的生平。主要依据这本传记,我将兰德的罗曼史简述如下。
《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
兰德一生有过三段恋情。上大学期间,她有了第一个恋爱对象列夫(Lev Bekkerman)。列夫长得英俊帅气,政治理念也与兰德相投,让她一见倾心。兰德五十五岁时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被他的英俊吓了一跳。……他让我最喜欢的品质是傲慢。”可是,列夫并不喜欢主动强势的女性,几周后他就不再与兰德约会了。移民美国后,兰德一度混迹好莱坞担任编剧,其间她结识了自己的终生伴侣奥康纳(Frank O’Connor)。奥康纳也是位美男子,他参演过几部美国影片。兰德第一次见到他的罗马士兵扮相,便决定追求他。两人三观一致,谈了两年多就登记结婚了。
兰德与奥康纳的婚姻堪称恩爱,两人相依为伴,走过一生。时至1949年,兰德已是美国文坛颇有名气的作家。某日她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写信人是纳撒·布兰登(Nathaniel Branden,Nathaniel在香港译为弥敦),一个年方十九的迷惘青年。纳撒对兰德崇拜有加,自称将兰德的小说《源泉》读了四十遍,能背诵其中很多段落。女作家被粉丝的热诚打动了,她邀请这位年轻读者到加州家中做客。两人由此相识,头回见面就畅谈了九个半小时。第二年,纳撒又将女友芭芭拉(Barbara Branden)介绍给兰德,两人一起拜她为精神导师。
兰德与纳撒认识后就开始频繁通话,有时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芭芭拉和奥康纳偶尔觉得他们在调情。1951年春,纳撒和芭芭拉因求学来到纽约,兰德夫妇也于当年秋天迁居曼哈顿。据一位好友推测,兰德迁居纽约只是为了接近“那两个孩子”。纳撒和芭芭拉于1953年1月结婚,兰德夫妇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并担任了伴娘和伴郎。以纽约的住所为据点,她身边形成了一个信奉自己思想的小圈子。每周六晚上,作为“教主”的兰德会召见一干弟子,为他们面授教义。纳撒是当仁不让的大师兄,他与老师的关系变得亲密,渐渐超越了师生关系。
1954年秋,兰德夫妇带着纳撒夫妇前往加拿大旅行。回家路上,兰德与纳撒低声细语,让芭芭拉有所察觉,并向丈夫大声抱怨。尽管纳撒否认他与兰德有任何私情,回到纽约不久,兰德就约纳撒一诉衷肠,纳撒也因精神导师向自己表白而自鸣得意。两人随后向奥康纳和芭芭拉公开恋情,并表示不会影响到他们对各自伴侣的感情。两对夫妇达成了君子协议:兰德一周可与纳撒会面两次,以此维持着脆弱的情感平衡。
1955年初,兰德和纳撒开始了同居生活。纳撒后来谈道,他成了兰德理想的“情妇”,温顺的奥康纳则是理想的“妻子”。可是,纳撒心中感到不安,既为他扮演的角色,也为他身处的四角关系。兰德对情人的要求也让他感到压抑。尽管如此,畏于教主权威,他还是选择了隐忍,并投入推广兰德学说的工作之中。这项工作为纳撒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他也乐于以兰德代言人的形象自居。可在私人生活中,他自称患有间歇性的性欲不振,这让兰德很不高兴,她有段时间还染上了抑郁症。两人的性爱关系在五十年代末便终止了,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
1963年,兰德提出与纳撒恢复情人关系。为了避免关系紧张,也害怕失去地位,纳撒只得答应,两对夫妇先后搬入了同一座公寓。这年年底,纳撒爱上了时装模特帕翠亚(Patricia Gullison)。帕翠亚充满了年轻女性的活力,她和丈夫都是客观主义班上的学生。她借婚姻问题找纳撒咨询,并表露了对他的钦佩之意,两人很快发生了恋情。纳撒爱美人,也爱江山,他不得不瞒着兰德偷欢。
然而,纸里包不住火。1965年,芭芭拉首先发现了老公的外遇,两人感情破裂,准备离婚。不明真相的兰德还对纳撒说:“亲爱的,也许我们现在有机会重新恋爱了。”纳撒找了些借口推托,他将帕翠亚介绍给兰德,希望让她能够渐渐接受两人的关系。然而他们的来往让兰德心烦意乱,为此与纳撒多次争吵。真相就在那里,可她不愿承认。
过了不久,纳撒夫妇和帕翠亚夫妇先后离婚。兰德感到纳撒在离婚后言行不一,向她隐瞒了一些事情。有一次她甚至指名道姓地说:“帕翠亚之类的人要从我的头脑、抱负和成果中揩油,你想也别想。……(你)无权和低劣的女人上床。”1968年7月初,纳撒面交兰德一封长信,表示他不能与兰德恢复情人关系,只希望保持友谊。兰德感到被抛弃了,她看了几页就破口大骂,要求纳撒和帕翠亚断绝往来。胆怯的纳撒同意了。
一个多月后,兰德通过芭芭拉知晓了全部真相,包括纳撒对她的长期欺骗。兰德向纳撒大吼:“你敢拒绝我?我是你的最高价值,你说过你的生命中不能没有我,你说过我是你梦寐以求却在现实中不抱希望能遇到的女人!”她狠狠打了纳撒几耳光,然后向他发出恶毒的诅咒:“如果你还有点良知,心理还算健康的话,接下来二十年就该阳痿!”兰德随后向学员们发出公告,称她与纳撒和芭芭拉永绝一切关系。两人离开了纽约,纳撒与帕翠亚正式结婚,迁往洛杉矶居住。兰德则回到了丈夫奥康纳的怀抱。
兰德生前和众弟子们维护着自己的一代宗师形象,私生活并不怎么为人所知。纳撒和芭芭拉也守口如瓶,只跟几个人透露过真相。兰德于1982年去世,四年后芭芭拉出版了《兰德的激情》(Passion of Ayn Rand)一书。又过了三年,纳撒也公开了自己的回忆录《审判日——我与安·兰德度过的岁月》(Judgment Day: My Years with Ayn Rand)。这两本传记批露了兰德等人的多角恋情,出版后引起舆论哗然。2005年,瓦利恩特(James S. Valliant)根据兰德的日志出版了《安·兰德批评者的激情》(The Passion of Ayn Rand's Critics),反驳了布兰登夫妇对她的一些负面描述。这样的故事总会有罗生门式的多重版本,不过枝节上的争议并不妨碍本文下面的分析。
左起:《兰德的激情》《审判日——我与安·兰德度过的岁月》《安·兰德批评者的激情》
安·兰德的性爱观
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兰德与纳撒的恋情具有三重不伦的意味。一是不守妇道,背叛丈夫奥康纳,与其他男子寻欢作乐;二是不循师道,与门徒发生了肉体关系;三是不具长者之风,用兰德自己的话来说,她成了“一个追逐小白脸的老女人”。持有这些价值观的人完全可以给兰德贴上“荡妇”的标签。兰德的情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想必会遭遇更可怕的舆论攻势——想想当年杨振宁和翁帆的婚姻在网上引起多少嘲讽和谩骂吧。然而,兰德的不伦之恋不仅符合其人生哲学,也体现出她保守的审美倾向。
在一本全球女哲学家的传记集中,兰德的作者海尔(Jenny Heyl)这样评价道:“……她(兰德)的文艺仿效了她的人生,她的人生也效仿了她的文艺。”有些作家说一套做一套,兰德却实践了知行合一的原则。她将自己的思想称为“客观主义”。就本体论和认识论而言,客观主义接近我们熟悉的唯物主义哲学。她的伦理学则极力批判利他主义,张扬个人主义。兰德小说《源泉》中的主人公洛克就体现了这种哲学的典型人格。他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质,既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他,洛克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
以自我为中心的客观主义哲学也体现在兰德的性爱观中。十九世纪以前的西方哲人大都不屑于谈论床笫之事,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首先承认了性爱之于人类精神的关键意义。他将性活动视为意志的集中体现,性欲不满是痛苦的根源,满足则是无聊的开始。尽管兰德的哲学也重视性爱,她的立场更接近尼采,将性爱看作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阿特拉斯耸耸肩》被公认为兰德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其中的人物弗朗西斯科曾说:“那些自轻自贱的人竟然想通过性冒险赢回自己的自信——这真是南辕北辙,因为性并不是前因,而是后果,是一个人自然价值感的一种表现……”
兰德相信,性爱绝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求,还是全部人格的精神体现。她鄙视将性视为动物本能的观念,甚至借弗朗西斯科之口宣称:“只要跟我说一个人性兴趣的指向,我就能告诉你他整个的人生哲学。”在她看来,性爱追求必然是自私的,没有人会出于无私的理由投入这种活动。对男人来说,一位女子越能反映出他深刻的自我形象,就越能吸引他。因此,“一个对自己的价值有无限自豪的确信的男人,总会希望得到他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女人,他所渴慕的女人,最强最难征服的女人——因为只有拥有了一位女英雄,他才会得到一种成就感……”我们只要将这句话中的“男人”和“女人”互换,就可以知道兰德本人的性爱观。
在兰德的伦理体系里,性爱活动具有强烈的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并非基于人际关系,也不受限于社会规范,而在于是否忠实自我。兰德与奥康纳成婚时,几位友人曾说兰德的签证快到期了,她需要找个办法让自己留在美国。这实在小看了兰德。她也许会借助婚姻获得绿卡,但她不可能为此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子。除了与纳撒的婚外情,兰德与奥康纳的婚姻生活相当稳定,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直到奥康纳死在她怀里。
兰德的性别观念也很传统,她既觉得同性恋者“恶心”,也认为女性不该当总统,因为每个女人都应找到可以仰视的男人,而女总统无法仰视任何男人。她本人自视甚高,常有鹤立鸡群之感,只欣赏有阳刚之气的男性精英,而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有些学员曾向她暗表爱慕之意,她一概置之不理。兰德很少遇到心仪的男性,可爱情之神还是在年近半百时眷顾了她。海勒这样评价她与纳撒的婚外情:“对他们来说,相爱在哲学上是不可避免的,是浪漫的,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同时这也意味着,纳撒与帕翠亚偷情,不只是在肉体上背叛了兰德;更可怕的是,这是一次针对客观主义的叛教行为。既然性爱体现了一个人精神上最高层次的追求,而只有她和纳撒达到了这种境界,两人在对方身上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纳撒是不应当去寻找其他女人的。然而,他却爱上了帕翠亚,这正是兰德最鄙视的那种男性——“他绝望地狂呼,因为他对他尊敬的女人毫无感觉,却发现自己受缚于对阴沟里的荡妇的不可遏止的激情中。” 她于是激烈地指责纳撒是个“对卖唱姑娘的肉体产生性冲动”而抛弃了自己最高价值的男人。
安·兰德的批评者提到她的师生恋,不仅想说她在情感上是放纵的,还要借此讽刺她在精神上也是贪婪的。林行止先生称兰德坚信“自私自利和贪婪是资本主义社会前行的原动力”,“贪婪在兰德词典中有正面意义,她的不少著述遂被暴发的‘新钱’们视为贪婪的福音(The Gospel of Greed)。”在《特朗普灵魂中的女人》一文中,许纪霖教授也说:“她对个人主义(确切地说是精英主义)所具有的狂热,与清教徒的审慎与谦卑格格不入,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贪婪和骄傲也缺乏起码的警惕。”其实,兰德恰恰是个反对贪婪和拜金的思想家。
兰德笔下的弗朗西斯科曾这样批判“实用主义者”:“(他)轻视原则、抽象观念、艺术、哲学和他自己的灵魂。他把获取物质的客体视为存在的惟一目标——他嘲笑考虑它们的目的或是源头的需要。他期望它们给他提供乐趣——他搞不懂为什么他得到的越多,他感觉到的反而越少。他是那种将时间花在追逐女人上的人。……他告诉自己他追求的一切不过是肉体的快感……在征服一具没有灵魂可言的肉体中又会有什么光荣可言?”能写出这样一段文字的人,怎么可能贪得无厌?
兰德本人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精神追求,她书中的主人公在精神上也是自足的。将她视为贪婪者的教母,是对她的严重误读。兰德理想中的社会建立在出于自愿的贸易基础上,金钱只是这个社会的“工具与符号”——不仅是“自由国家的货币符号”,也是“自由思想的符号”。“它(金钱)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但它不会取代你成为驾驭者。它会赋予你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但它不会赋予你欲望。”也就是说,兰德认为金钱只有工具性的价值,不应成为人类追求的根本目的。
安·兰德
理性自负的悲剧
安·兰德的婚外恋最终走向了彻底的悲剧。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在他编译的《安兰德传》一书中,独立学者刘仲敬写道:“兰德圈却产生了东方式宫廷政治,最终把‘大维齐’布兰登(纳撒)都牺牲了。”如果我们仅仅将这段故事看成一部贪欲导致的宫斗剧,就不可能理解它真正的悲剧意味。
就情感生活来说,兰德的信念是高贵的,行动是勇毅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她的人生哲学没有问题,与纳撒的婚外恋暴露了客观主义的重大缺陷。正如许纪霖和刘仲敬曾指出的,兰德的哲学有着理性主义的明显特征。像其他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激进主义一样,她的哲学也指向一种乌托邦,区别在于它是以绝对个人主义为导向的。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兰德必然要求改造人性,塑造以客观主义为指南的“新人”。作为教内大弟子,纳撒被她视为最成功的实验品,两人的爱情正是这一改造的果实。
在婚外情被各自的配偶知晓后,兰德也试图通过理性,说服奥康纳和芭芭拉接受她和纳撒的情人关系:“你们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也知道纳撒是怎样的人……就我们的全部逻辑,就性爱含义的全部逻辑而论,我们必须爱彼此。……无论你们俩感受如何,我相信你们的智力,我知道你们能够体认我们对彼此感受的理性,而你们将理性置于一切之上。”“如果我们四人的境界不够高,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兰德成功地说服奥康纳和芭芭拉,却未能阻止纳撒移情别恋。当两人的师生恋开始,她像以往一样追求灵肉结合的高贵爱情,渴望得到一个能够征服自己的男子。不同的是,她已不再年轻。兰德曾是个美丽自信的女性,不难赢得奥康纳的忠心。可她认识纳撒时已有四十五岁,比他大了二十五岁。初次见面时,纳撒就发现兰德比他想象的要矮和胖。芭芭拉回忆说,兰德有双迷人的黑眼睛,但“无论如何”不算美丽。两人还注意到兰德不修边幅:她的长袜常常是破损的,裙子也褪了色,有时还不梳洗头发。
1959年2月,美国著名主持人华莱士邀请兰德上电视接受访谈。兰德在镜头中的表现虽不如多年后的一位中国长者那样谈笑风生,却也显示出睿智和理性的成熟风采。不过,她毕竟不是青春靓丽的少女了。她对纳撒的吸引力,更多来自拥有的话语权力,而非自身的女性魅力。兰德也曾问过纳撒,他是否嫌她上了年纪,纳撒则胆怯地矢口否认。与帕翠娅偷情的时候,他还欺骗兰德说:“你会一直拥有性魅力,任何年纪,你都是无人能比的。”
兰德对纳撒的感情在精神和情欲层面是一致的,纳撒对她却非如此。她相信纳撒和她一样,以理性作为感情的基石。可纳撒的内心不得不承认,年轻貌美的帕翠亚比徐娘半老的兰德更有吸引力,虽然后者才是他的精神支柱。兰德的理论听上去很迷惑人,可它为性爱赋予了过多的精神内涵,仿佛性爱可以摆脱基本的生物规律,仅凭理性便能激发出荷尔蒙。与纳撒的矛盾爆发后,兰德完全不承认年龄差距是根本问题,依然自欺欺人地活在“理性”的世界里。在1989年的一次演讲中,纳撒则痛苦地忏悔道:“我把孤独、夫妻间的失望、对兰德难以置信的钦慕、英雄崇拜与爱情混在一起了。”
兰德将纳撒视为“精神继承人”,她曾说:“纳撒对我永远代表了未来,而未来就存在于现实中……”他的叛教行为之于兰德,相于林*事件对毛 泽 东的打击。读到纳撒长信的那个夜晚,兰德低声自语:“我的生命结束了。他将我连根拔起。”客观主义的信奉者也因纳撒事件而深感疑惑,甚至引发了激烈争论。兰德指定的接班人以最戏剧性的方式与她决裂,在美国西岸“另立中央”,开始传授一套强调感情因素的“修正主义”心理学。
在一次访谈中,芭芭拉说她写作《兰德的激情》,部分是为了“让兰德从自我神化的需要中摆脱出来……她只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单就情感生活而言,兰德不如与她同时代的法国女思想家波伏娃成熟。尽管波伏娃在很大程度上也相信人性可以改造——所谓“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建构的”,她对男性的了解比兰德更接近现实。她与萨特都有过其他情人,两人都为此产生过醋意,但毕竟没有闹到彻底绝裂。波伏娃也曾与比她小十七岁的朗兹曼有过一段恋情。持续六年后,在波伏娃五十岁的年纪,朗兹曼同她分手,她平静地接受这一切。
兰德毕生宣扬“理性”,致力于改造“人性”。她曾观看美国宇航飞船升空,称赞它代表理性的光辉,代表勇气和诚实等美德。然而,就男女情事而论,其本质就是“感情用事”的,这里“人性”必然胜过“理性”。兰德和纳撒都因客观主义而成名,也都陷入了这种哲学错误的性爱理论而难以脱身,这导致了他们的情感悲剧。诚如兰德所言,人类的感情自有其原因,这原因却不在理性的世界中。
今天,安·兰德被冠以“市场女神”的名号,她的大名变成了商业人士的护身符,而她理论中的道德性则被剥离了。在兰德生前,有份美国报纸就嘲笑说:“兰德小姐堪称自由企业的圣女贞德,只是用美元代替了十字架。”在她死后,林行止先生写道:“宣扬这种(自私)哲学,在新经济潮流中成功的弄潮儿和官商勾结有道的财主从此有了精神寄托,理直气壮地牟取暴利,并心安理得地享受飞来横财!”一位追求高贵的尼采式思想家,就这样被误解为庸俗价值观的捍卫者,这恐怕是兰德人生最大的悲剧。
最后说一句,《兰德的激情》虽是部三级片,有些性爱场面,但并不低俗露骨。兰德一角由英国著名女演员米伦(Helen Mirren)主演,她曾当过戛纳和奥斯卡影后,也因此片获得了艾美奖的最佳女主角。读者不妨找来看看,相信一定会从中得到艺术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