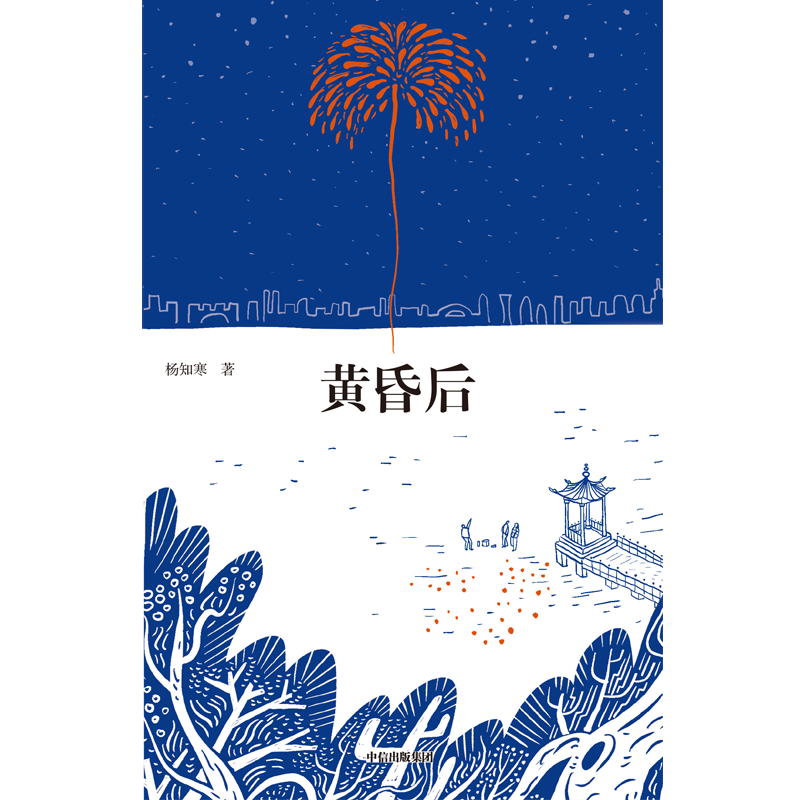以后也许见不到面了,现在是我们人生最接近的日子 | 星期天文学·杨知寒
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补缀、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22辑,嘉宾是青年作家杨知寒。她的最新小说集《黄昏后》收录了10个发生在东北小城的故事,创造出戏谑之下充满厚重感的文学世界。她善于捕捉人物的“内心秘密”和“高光时刻”,用犀利的目光观察着一个个在生活中摸爬滚打的小人物。
《海山游泳馆》一篇是关于游泳的故事,也是关于友谊与情感、关于伤痛与失去、关于信任和自我袒露的故事。当我们在泳池中漂浮,那些嫉妒和骄傲,那些伪装和勇气,也像鱼饵一样在水里浮游着……
杨知寒,1994年生,成长于黑龙江齐齐哈尔。小说见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等,已出版小说集《一团坚冰》。获萧红青年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新人奖、丁玲文学奖等。
海山游泳馆
文 | 杨知寒
一
我妈总是鼓动我,该培养一项持之以恒的运动,没事出出汗,解解乏,关键对身体好。一旦熟练掌握了,是伴随一生的技能。
人在运动中忘乎烦恼,何乐不为?
我思来想去,也就游泳还有点儿意思,湛蓝的水波里,和海龟一样浮游向前,不想动的时候静止也行,也是漂浮的状态,女孩子泡在蓝水里,会显得脸白。
市里游泳馆不多,我小学的时候,除了工人文化宫前的大游泳馆,只知道一家海山游泳馆。它就开在我家对街,一条小巷子里,门对门是一所培智学校,巷子里暴土扬长,过的都是三轮。
牌子上写的是游泳馆,但你跟司机报地名,得说去海山浴池,因为去那儿基本都是洗浴的,游泳有点贵,搓澡合算些。
我家住的是老楼,取暖困难,一到冬天三口人洗澡,是件麻烦事,花洒是后安的,得一直用手举着,关键是水不热,屋里室温也不高,洗澡伴有感冒的风险,除了我爸害羞,死不在人前脱衣,我和我妈都渐渐更愿意去外面洗,不遭罪。
我们当然要去海山游泳馆,去了两次,前台忽悠我妈说,不如办张卡,游泳洗澡搓澡一条龙,比纯洗浴合适。看你这姑娘,多适合培养游泳。
我不知道她是咋看出来我适合的,我那时不白,也许该多在水里泡一会儿。
我妈和我一样兴致盎然,当天我们就去百花园,那个小批发市场,一人置办一身泳装,两个游泳镜,我还要了个打水板。
卖货的也忽悠我们,你买游泳圈,孩子一辈子学不会游泳,老箍着能行吗?得把腿在水里抻开扑腾,孩儿,你抱着打水板。我抱着了,他扔掉手上泡在塑料袋里的麻辣烫,现场指导我,孩儿,到水里你也这么抱着,想象你遇难了,这就是船上掉下来的甲板。
我妈有点不爱听,我倒是入了情境,听他继续说,想象后头有鲨鱼追你,大浪赶你,眼前不远就是沙滩。抱着它冲,冲上岸时,压着它就跟压着床垫似的,多喧腾。
我妈说,撑死十块钱,不跟你讲了。他顿时不给我讲了,我意犹未尽。
回家后我缠磨我妈,什么时候真去游泳啊?开始计划挺好,说明天下班带你去。到明天下班我妈没回来,有酒局,后天、大后天也一样。
等她醉眼迷离,踩响我家楼道里的声控灯,用脱下来的跟鞋大晚上砸门时,我爸还没怎么着,我火了。
她看见我卧室床上放着那块打水板,自己飘飘然压上去,嘀咕说,挺硬啊,不咋喧腾。姑娘?姑娘离妈近点儿。我问她怎么不穿鞋。她说回来路上把脚割了,没看见地上有块儿碎玻璃。
我凑近看她的右脚,大脚趾附近的确有道鲜红的口子,我爸默不作声,去拿酒精棉。
我走到他俩面前,低着头,双拳攥得死死的,酝酿要说的话,呼吸加剧,胸腔鼓胀。我妈终于注意到我,说,姑娘,妈压了你的打水板了。我问她,什么时候去游泳?你说个准日子。她笑嘻嘻的,你定。我说,明天周六,你不上班,明天必须去。
他俩对视一眼,我妈说,姑娘,妈脚坏了,下不了水。我说,前天你脚不坏,昨天你脚不坏。我看你是故意的。
我爸没替她说话,他看戏呢,但道理渐渐在沉默中归向了我妈,她的伤千真万确,冲澡都费劲,在洒满消毒水的泳池里泡几个小时,的确不合适。可我当时心里只有不服气。她提议说,让你爸带你去。我爸立刻说不,在泳池边上展示他的大白膀子,他不愿意,我也不愿意。
我又把头低下了,眼泪照计划行事,滴答下来不少。她一定还没醒酒,不然也不会答应我,我妈喝醉的时候,我俩不论辈分,能论点儿道理。她把我两手攥到身前,抓我去碰碰她的脚,我没碰。她叹息说,非得去吗?
我爸说她惯我,他不管了,周六是他铁打不动的游戏之日,基本一天,从早饭到晚饭,都在电脑桌前解决。
我妈在她受伤的脚趾上套了一块塑料布,用皮筋扎紧。我们过条马路,拎着全副装备,到了海山游泳馆。
虽说来过两次,可两次都是来洗澡,不往里面走,今天往最里面走了,就有种高人一等的感觉,尤其在更衣室里换泳衣时,旁边的小女孩紧着瞧我,问她妈妈,她凭什么穿这个?
我把那件新买的,像我小时候学跳舞用的练功服一样的裙子,从柜里拿出,慢慢给自己套上。腰上有圈裙边,胸口画着小黄鸭子,泳衣整体是深蓝色的。
有点儿买大了,带子总是从肩膀上往下掉,我得刻意挺着腰板,像个芭蕾舞演员一样走路,戴着我同样深蓝色的泳帽,露出宽阔的脑门儿。
我妈还在研究她的脚趾,皮筋扎得太紧,脚趾不过血,有些发白了。我俩走过热气腾腾的浴室,穿过没开灯的休息大厅,沿一条狭长的走廊,一直到尽头,视野开始白茫茫。
一个中年妇女穿短袖短裤,坐在板凳上把守关卡,看了我和我妈的手牌,说,今天来游的不多。先过消毒池,泳池转弯就是。
我茫然地点头,脚终于离了拖鞋,踩在白瓷片上的感觉让我兴奋。我妈在前头走,蹚过了深到脚腕的消毒池。我搀着她,眼瞅着有水漫进了她脚上的塑料膜里。
中年妇女眼尖,问,咋的,脚不行啊?我妈巴不得有人问,让我脸红。听她说了原委,我脸果然红了,中年妇女却说,来都来了,顺孩子意吧。是啊,再没人过来游,她家就得黄摊子。
我妈领我拐过弯来,蓝色世界豁然出现,水是平静的。
我抱着打水板,踩梯子下水,我妈先下去,在底下接我。可她早晚得放开我,一放开,我就开始叫唤,那时我身高一米三左右,踮脚勉强能把头露出来,脚一旦放平,水从四面八方涌来,钻进我的鼻子、耳朵,打水板没有屁用。
我妈托着我起浮了几次,我就像只陆地上的树懒,挂在她水中的躯干上,感到冰凉和恐惧,再看远处的深水区,简直如汪洋。上半身精瘦,露出两片排骨的救生员站在沿上,盯我俩半天,说,大姐,你这孩子容易呛水。
我妈说,你不是管救的吗?我寻思先让她感受感受。救生员说,别感受了,我怕来不及。
我妈下了水,就开始享受水,她好久没游了,想游个痛快,此刻她脚上的伤仿佛转移给了我,我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有伤,和水不相容。
他说,可以让孩子自己去上边小池子游,上边水浅。我俩挺惊喜,早说有儿童游泳池啊。
我爬上梯子,冻得打哆嗦,我妈在水里则像个黄棕色的泥鳅,一会儿西游,一会儿东游,绽放出少女的笑容来,远着跟我招手,说,你自己上去,先学学。都不会游呢,净耽误我。
二楼是个不完全的平层,面积不到一楼一半,有两个小池子。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那是泡澡的浴池,水也不蓝,像温泉,热乎乎的,有浑浊的砂砾。我钻进小池子,站起来,水刚到小腿。
我试着用打水板练习,让自己在水上漂起来,可池底的瓷砖轻易就能贴着我的腿,不用打水板,想淹死也实属费劲。
我一人练习着,一楼逐渐来了几个人,能听见我妈和别人聊天时的笑声,有男有女,他们似乎约好了,要从泳池一头一起游到另一头,竞赛正要开始。救生员在底下喊,开始!他似乎在掐表。小浴池里越来越陌生和安静。
我试着踢了两下水,水声泛起来还好,水声一停,身后没鲨鱼没打浪头,像人原本就在沙滩上,怎么游,都搁浅。
我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往下瞧,宽阔的蓝泳池里出现了个伶俐的身形,蝌蚪一样,被人安放进水里,就能自由自在摆动两脚,腿并在一处,如灵活的尾巴。
我妈和几个大人都游在她身后的水浪里,她游到头,没多逗留,立即折返,等她游回到浅水区,我妈他们还在返程的中段。
我看见那个救生员把一条白色的大浴巾递给她,她一蹿坐上池边,披着浴巾,两只细白的脚在水里无聊地打着。
我妈摩挲一把脸上的水,泳镜卡到脑门上,问她,姑娘几岁呀?她说十一,说阿姨我认识您。我和李芜是同学,上次您不是来我们学校演讲吗?有印象。
我妈和她并排坐着,说太巧了。我姑娘也来了,应该让她和你学游泳。你叫什么?她说,我叫杨洋。我还没来得及躲,我妈抬手就指上了我,像盲打的一枪,我在楼上人没动地方,但有些部分,已应声倒地。
她说,李芜完蛋。在浅水池游呢。你去找她?我在楼上对杨洋僵硬地招着手。杨洋在楼下仰头看我,她穿着一身黑色的连体泳衣,已有少女的曲线,站起时,从两腿的肌肉上水珠直往下滚。
她白皙的圆脸上也有水在滑,滑下她圆翘的鼻头,像打了个滑梯。她扑哧一笑,眼仁黑黝黝的,连着两道浓眉,比在学校时更好看,像个异族少女,似乎游泳是她与生俱来的本领,除此外,她还掌握剑术和狩猎。
她又在岸边做了几个训练动作,和我妈告了别。穿好棉服,我和我妈走出海山游泳馆时,她紧着往我脖子上缠围巾,连我的嘴也缠上,我说话呜呜的。
我妈说,你抱着块打水板,在楼上站着,两边肩带都滑下来了,你不知道?看见同学也不说话,就知道傻笑,跟对面培智学校孩子放出来了似的。
我矢口否认,我没傻笑,那是冷笑。我妈问我,为啥冷笑?我想了半天,都快到家门口了,呜呜地说,幸亏她没上来。我冷笑,把她震慑住了。
我妈看了我一眼,才想起问,上面啥样?水好不?我把围巾拉下,呼了半天气,里面已经湿漉漉的,带冰碴儿了。说,还是深,幸亏带了打水板。那啥,漂我已经学会了。
二
从海山游泳馆回来第二天,我妈脚上的伤发炎了,肿得很厉害。她总想以此责备我,每次都被我一句话顶回去,那你还在水里紧着游呢。
我俩好些天互不搭理,我对游泳不再惦记,失去了幻想中的兴趣,倒是穿泳衣的杨洋,她身体曲线的样子还常在我眼前出现。
在学校里我早注意过她,市里有个春苗艺术学校,每年都去几个小学里,招培养的苗子。校长是个方脸的年轻人,常戴副墨镜,进门也不摘,走几步皮鞋站定,像在舞台上亮了相,总是睥睨众生般看着我们这帮孩子。
我被选去的那次,站在第一排,肩膀向后挺得生疼,墨镜男走到我面前时,我还笑了笑,露出没长好的门牙。
他眉毛挑了下,视线很快掠过我。后来很长时间我都后悔自己不该笑,该冷峻点儿。
可杨洋也笑了,她就站在我后头,从镜子里我能看见,她笑的时候嘴角轻扬,混血儿般的大眼睛里放出星芒,跟有蝴蝶飞过去似的。他久久看着她,我也是,听见他怀着颤抖的喜悦说,姑娘,让我培养你吧。
我哭了一场,我妈在家养伤,一直睡到下午。
下午她醒来时,我已经在家了,对着包铜的老式窗框,不住把眼泪往上边抹,一擦一道痕。她问我怎么回事,我把事情讲给她,我妈很快就回答了我困惑的问题,说落选是因为我体态不好。
我问,什么是体态?她在床上坐起来,厚实的上半身昂首挺胸,目视前方,带着规整的笑意说,看妈妈。
我看看她,说杨洋不是她这样,她挺自然的。我妈问,杨洋?游泳那姑娘吧。我说是。我坐到床边,靠着她的腿,把头倚上去,不想说话了。
我选在下一个周六,独自去海山。
我妈给我把包装好了,在我棉服口袋里塞了个她不用的小灵通,叮嘱我,到了来电话。她给我三小时,三小时内我必须回到家。我爸试图讲价,两个点儿吧,两个点儿够她游的。他还想送我过去呢,我和我妈都没让,最后勉强同意,他可以在三小时后,到海山游泳馆接我。
那个在游泳池前把守的中年妇女看见我一个人时,则没那么不放心。她眼前一亮,说,孩儿,来了?你妈脚咋样?好像她是我一个失散多年的大姨,问候得亲切又坦然。
我说,好多了。差点儿跟着说,家里都挺好的。
她亲热地替我把鬓边掉出来的头发往泳帽里掖好,问我是不是和小伙伴约着来的,说她早来了。我心里一颤,下意识想溜。杨洋不能算我的小伙伴。
她一人游呢吗?我问阿姨,她似乎乐得有人跟她聊一会儿,哪怕是小孩儿也不耽误。我在浅浅的消毒池里一直站着听她讲,毒消了好一会儿,知道原来杨洋每周六都会来游泳。
原来那个救生员就是教她的老师。她现在不用人教了,作为一门爱好,她掌握得已相当熟练。救生员总是怂恿她,可以往专业上发展,杨洋的父母不同意。
我想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同意,所有知道杨洋在泳池外一样有光芒的人都不会同意,太多大人争着培养她,感觉选择多了,也是种困扰。
拐弯我就看见, 那的确是杨洋。
她正兀自在蓝海里浮游,救生员今天不在,整个场馆里就她一个人,屋内高高的举架,消毒水肃杀的气味和她在水里画着线的影子,都让我觉得孤单。我没叫她,还是抱着打水板,上了二楼。
我在小浴池里一声不响地泡着,听楼下的水花。我像能看见自己五六岁时,和妈妈第一次去澡堂里,遥远的雾气中的脸。
小小的我在水流里站着,妇女们谈话,传来的每一句回音都让我如置梦中,那是任何人不会懂的感受,感到人人都在无尽的蒸汽里,暂时逃离了世界。
有人突然叫我,李芜。我看见杨洋就在我面前的楼梯上,正踩完最后一级台阶,我哗啦一下从水里站起来,温度从全身降到了小腿,水位也只到那里。
杨洋瞧瞧地面上她自己的脚,瞧瞧我说,怎么来了不游呢?我问,你知道我在?她说她知道。
她下到我的小池子里,脚在里面暖和着,人坐在池沿,令我顿觉这池子或许就是拿来泡脚的。
我一言不发,她又看了我一阵,问我为什么不下去游一会儿。总在这儿泡着,你永远也学不会。我说,不爱学。她说,那你还抱着打水板。我急于结束对话,搪塞说,你下去好好游吧。我再泡一会儿就走了。我其实是来洗澡的。
说完我就后悔了,圆谎比撒谎更费事。我何必再加一句解释,谁会抱打水板来洗澡?培智学校的孩子也都不至于。她果然想想就笑了。
我从最简单的开始教你,怎么样?杨洋歪头看我。我说,不学。她问我是不是打算一直在这儿泡脚,毕竟来游一次也不便宜。我转头时,杨洋偷偷把我的打水板抱进了怀里。
身后传来她一溜小跑的噼啪声,人很快跳入了下面的泳池。我追过去,在岸上掐腰,往水里喊,干吗呀你。杨洋在水里吐出一口水,笑嘻嘻地说,下来,你的板儿也在下头呢,过来拿。
我看着那块淡粉色的塑料板正在她手边漂浮,要是我能像那块板子一样,轻易漂起来就好了。我连漂还没学会,我和杨洋的距离,分明是差出十万八千里,还有富余。
她没要我的打水板,兀自游到我脚边,双手扒住池沿,憋了一口气,头埋下去。我看着她修长的身体在水面上完全铺展开,从水下漂到了水面,手臂和双腿都能接触到空气,感觉整个人是比板子还轻盈。
她漂了一会儿,双腿一蹬,头钻出来,说,很简单,你一定能学会。下来试试。
我转过身体,开始下梯子,脚后跟最先感到了冰凉,感觉有人在碰我的小腿,指尖也是冰凉的,杨洋在水中抱着我的腰,我又紧着想扑腾,听她安抚我,说,想象你周围是空气,水一样的空气。
我既想挣开她,又不敢。
她比我高一个头,能在水里站住,透气不困难。我不行,可我又不能像盘着我妈一样,盘着她。我后悔自己为什么要下水,水里的我连冷笑这种基础防御都做不出,不龇牙咧嘴就不错了,想喊救命的冲动在嗓子眼儿里一直跳着,都跳累了。
杨洋将我引到池边,简直是命令我,把手搭上,搭沿儿上,松开。我说,松开沉底儿了。
她突然消失,我扑腾来扑腾去,抓不着她的身体,一口水呛进来,人却在往高走,有人在水下托着我的腰,将我硬生生举出了水面,我腾出来的两只手立刻抓上了,她希望我抓住的池沿儿。
杨洋呼哧带喘,下另一个指令,把腿离开地面。我说了,你是在像水一样的空气里。把腿抬起来,你不会倒,只会漂浮。如果你不能漂浮,你觉得刚才我是怎么把你举起来的?
杨洋就在我身后,我感觉到她,见不到她,我在她说的水一样的空气里,感到近乎失去知觉的自由。
腿一旦离开地面,像再不属于自己,它飘着,属于其他的太空,好像我也正在另一太空,顶着防护头盔,知道只要闭上眼睛,什么也无法与我成联结。
杨洋对我说,李芜,你漂起来了。我张不了口,张口还得进水,但我能听见她说什么,也能感觉到,自己的确轻盈得前所未有。我把腿蜷缩起来,脚尖掂到了瓷砖上。
她问我,刚才漂的时候,你想啥呢?我说,想让更多人看见。
她坐到了梯子上的一级,没说话,只朝我笑着。我问,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儿笨?她说,你不是笨。是放不开。游泳最能让人放得开,所以我总来游。只有游泳的时候,四肢都伸展了,才像我自己。
我说,反正你在哪儿都有光彩。即便你不像你,也总有人喜欢你。我不一样,我总得训练自己,要么挺直腰板,要么挤个笑。连我妈都说,我体态不好,和你天差地别。
她目不转睛看着我,仿佛我说的是她不懂的语言,良久,她又笑了。李芜,你看看我。
我怎么不是目不转睛看着她,看她的腿在水里变形了,像两根插在水杯里的吸管,位移出不同的层次。她腿上有模糊的花刀,我揉揉眼睛,怕自己看错,她配合地把腿扬起来,说,我腿上着过火。
前年,五福小区着火,我自己在家,往楼道里跑的时候,没跑及时,腿被燎了,人也倒在楼里。送我到医院时,腿还不如现在呢。我说,那你可挺勇敢,还敢往出露。
她说,藏不住,总得露出来。在水里还好一点儿,别人只能看见从我腿里打出去的水花,水花总是漂亮的。我说,你是漂亮的。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
杨洋愣了会儿神,突然又跳进水里,我们面对面站着,如果她不这样做,我都没留意我已经能在水里站住了。她试图拥抱我,借助水的浮力,我们靠近彼此时,若有似无,像梦中的接触。
我爸准时来接我,杨洋没跟我出来,我几乎是依依不舍,看她在泳池里继续来回着,独自去浴室冲洗身上的消毒水。
见着我爸时,我已经全副武装,在路上他问我,游泳入门了没有。我说入了,还想来,想每周每天都来。他挺诧异,穿着红色羽绒服的笨重身体在我前面走,提着我带的粉色洗浴兜,一言不发。
我追着他,俩人没再交谈,等进了家门,我妈还在床上看电视。
她把音量调小,亲吻我走过去时仍红扑扑的脸蛋,说,姑娘你运动运动,就见好看。
三
后来我路过春苗艺术学校,看见杨洋的照片在门脸上挂过一阵子。很快那张她穿着紫纱裙的艺术照又不见了,像一种幻觉似的,我好像总能在城市里发现杨洋的身影。
和我妈聊起这些,她都会问我,杨洋是谁?直到她脚伤完全养好了,也没再陪我去过一次海山游泳。
我说,杨洋是游泳馆里游泳的女孩儿,上次你们游比赛,她把你们都赢了。她还被选上了春苗艺术学校,要当小明星。
我妈说,没觉得你俩关系多好,你怎么总提她?我说,我俩是朋友。只不过在学校里不打招呼,见面笑一下。在游泳馆里,我俩如影相随,我到哪儿她都跟着。
我妈说,那挺好,还怕你总一人去游,孤单呢。我说,杨洋也这么说,过去她每周六一人去游的时候,是孤单。现在我也去了,她教我游泳,我给她做伴,我俩各取所需。
我妈说,最近你话又密了,还爱蹦成语。我说,人生苦短,知音难求。我妈给我脑袋一下,说,当着我,别说人生苦短。我比你还短,没知音不活了?
我们这里夏天过得快,秋天就更快,只有冬季无比漫长,眼下树又开始掉叶子了,海山游泳馆门前的土路上,积水有封冻的迹象。
我和杨洋每周六风雨无阻,在泳池里相会,游泳我学得不怎么样,她渐渐也不怎么锻炼我,两人更多时候只在水里浮着,漂着,说漫无边际的话。
杨洋今天来得晚。她从门里进来时,我正把脑袋埋水里练憋气,试了好几回怎么在水下不戴泳镜,也能睁开眼睛,我看到杨洋是这么做的,她这么做眼睛一点儿也不疼,我不行,眼睛睁开了,幻想更多,恐惧也跟着来。
杨洋在我头顶附近站着,没叫我,估计怕把我吓着。我喘一口气,从水里露出脸,瞧见她蹲着看我,问,折磨自己个儿呢?我说,你怎么才来。
她说,本来不让我来了。我爸带着我妈,忙活搬家呢。我说,等我上来跟你说。她说不用,扑通跳下,溅我一脸水。我看见了一个和往常略有出入的杨洋,她背靠着池沿,平静地站在那儿,两道眉上每根眉毛都清晰可见,脸色苍白。
一手摘了泳帽后,露出新剪的男孩一般的短发,十分利落,她用水湿的手捋了下额前的头发,那些发丝立马分开来,跟上了发胶似的定了型,垂下单薄的几绺。
我问她,你头发呢?咋剪成这样了?她问,不好看?我说,好看是好看,你很难不好看。就是不知道你怎么想的,留得好好的长头发。
她说,嗯,我要去哈尔滨了。
杨洋一动不动地瞧着我,眼神和她打开的肩膀一样,一览无余,十分坦荡。我想了想说,去吧,大城市好玩儿得多。
她说,你怎么总惦记玩儿。城市大了,泳池多了,很难再像现在这样,我和你霸占一个大泳池,想怎么游怎么游,想怎么待怎么待。
我咽了几口唾沫,刚才憋气没憋好,鼻子里进了水,现在已到达喉咙,没拦住,仍在往下滑。
她低下头说,我再教你点儿啥吧。她朝我游过来,说,自由式你会了,学蛙泳?我说,啥也没学会,憋气都不会。她笑了笑说,是她没教好。她说我已经入门了,会漂,我们一起在水上漂的时候,她在水下偷着瞧,我漂得很好。
我忽然发现,杨洋耳朵下面有块凸起的形状,和她小腿上的伤痕接近,一块红一块白的,红白交织着,像被打混了的两样粥,凝结在皮肤上。感觉自己该说点儿什么,如果此刻不说,以后很难再找到能开口的时刻。
我说,你比我想象的更勇敢点儿。她说,还行吧。说着用手碰了碰耳朵后的疤痕,说,大火也烧到了这儿,我一直用头发盖着。
要到新环境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想总藏着掖着的。我妈说我是小精神病,你觉得呢?
我问她,还烧着哪里没有?她说,有,往后一点点往外露。说完她又笑了,和那天我在排练室镜子里看到的笑容一模一样,我不知道杨洋为什么愿意和我讲这些,就像不知道为什么她在一开始就选择亲近我。
她说,李芜,我们以后也许见不到面了。我们会念初中、高中,然后是大学,现在是我们人生最接近的日子。你把手给我吧,我们一起漂一会儿。
我把手伸出去,握着她,她就是我的池沿,我的陆地。我们互相借助彼此的力量,在寂寞的泳池里安静漂浮,我紧闭双眼,察觉到她水下的视线,鱼儿一样游过我的面前。
三小时很快要到了,我俩还站在浴室的水龙头下面,脱去了泳衣,任水流浇着头顶。
杨洋在唱歌,她已经唱了有一会儿了,我一直听不清,也不想去听,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在浴室的蒸汽里,像睡梦中的伴奏带,加深告别的痕迹。她关掉自己头上的花洒,替我收拾带来的沐浴露和浴花,跟我妈一样,有条不紊,装进我的浴兜里。
她并没走,挤进我的花洒底下,碰着我的手臂。她的皮肤温热而光滑,反而是我的,浇了这么久,还凉丝丝的。
我看着她的脸,水流划过她的脸,杨洋面带微笑,我不敢去看她身上其他地方,从来我们游完泳,在一起冲澡,总是各洗各的,加上雾气缭绕,只闻声不见人,从没认真注意过。
她的眼神像鼓励我去看,去发现,我却说,你走开。她说,李芜,你不要哭。我说我没哭。
她说,那把你的花洒也关了,看你脸上还有没有水。我说,你走了,我再也不来这儿游泳。谁求我,我也不来。她说,反正这儿也快黄了。我说,赶紧黄。我不像你,有更好的地方去。我这辈子也不游泳了,再好再大的泳池我都不游了,我看见泳池里的水,就犯恶心。我回头把花洒拧紧,拿上自己的浴兜。
她跟着我出来,有点儿打晃,不知道是不是在浴室里站久了,人缺氧,我们都有点儿打晃。
从各自的柜子里拿好衣服,一件件套上,她戴着顶鹅黄色的毛线帽,搭配同样颜色的长围巾,我俩装束好,面对面站着看,想起一年前在此相识的画面。
我兜里的小灵通不停在震动,一定是我爸在外面等着急了,他又进不来,现在应该很急躁。杨洋把我嘴上的围巾拉下来,说,你再跟我说句话。
我说,别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往后我每次游泳,都会想起你,什么时候你也想我了,就去游泳吧。水就是空气,我们泡在一样的水里,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距离不远。
我说,知道了。我还是先走,我不知道杨洋每次是在我走后,过了多久才离开。我爸在游泳馆门口抽着烟,看见我,把烟头一甩,气得磕巴了。你,你,你怎么回事你?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儿。
杨洋走了以后,我再没去过海山游泳馆,也不再和我妈提到那些怀疑在哪儿见到她的想法,杨洋和海山游泳馆似乎命运共通,当我不再念着它时,它静悄悄地在城市里消失,人们再打车过去,只说去培智学校对面。
那里如今的地方,是一家私人妇产科医院。偏僻的位置就适合开这么一家医院,毕竟,谁又能想到在条黄土道里,曾藏有一片寂寞的海。
我面前的咖啡已经凉透了,关于杨洋和游泳的回忆似乎只能到此为止,我当然还见过她,但那已经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范畴,它属于现实的狗尾续貂,如果可以,我真想抹去它。
再见到杨洋,是在哈尔滨一家商场里,我和我妈因为来哈尔滨办事,逗留了几晚。
当时我们正在一楼的鞋架间漫无目的地挑选,说有一搭没一搭的事儿,杨洋一直走到我面前,按理说,我应该对她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讶,我们却都很平静。
她说,李芜?我说,杨洋?大家各自笑了笑。她说,你来逛街呀?我说,你也来啊?她自己来的,也许在等人,看了眼手表急匆匆地和我道别,我盯着她的背影看,我妈正在试鞋,瞥我一眼,问,碰上同学了?
我说是杨洋。她没听清,也是不在意,紧着让柜员再给她换一双,这双小了,挤脚。
杨洋的背影完全走了形,很难让人信服,她学过游泳,还游得很好;她是个明星,起码在我们都灰头土脸的年纪里,公主似的光彩夺目。
我一下子想起她在换衣间最后和我说的那些话,如果以后想念彼此了,就各自去游泳。看来她没怎么游,起码没坚持。我不能责备她,因为我也没再下过水。
长大成人后,我习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回避他人的注视,说话三思而谨慎,愿意将自己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放好了,稳当不摇晃。
我妈说,人得掌握一门运动,为了能在生活里喘口气,也为了能在紧张的环境里,暴露自己的本真。人能暴露自己的时刻,总是太稀少。
现在我胡思乱想,如果和杨洋重回到水里去,我们能一起游多远。海山游泳馆不复存在,很多事都不复存在,但水里该有我俩的痕迹在。
当四面无人,空旷的游泳馆里水声都消弭了,只有少女的笑声,说起恐龙和宇宙,嫉妒和骄傲,那些话和鱼饵一样在水里浮游着,钓出一个又一个美好的约定。我们看着打水板逐渐漂远了,再不需要它。
那一年,我们是彼此的陆地和海洋,山川总有改换,可山川始终都存在。
本文摘选自
《黄昏后》
作者: 杨知寒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品方: 中信·乘风
出版年: 2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