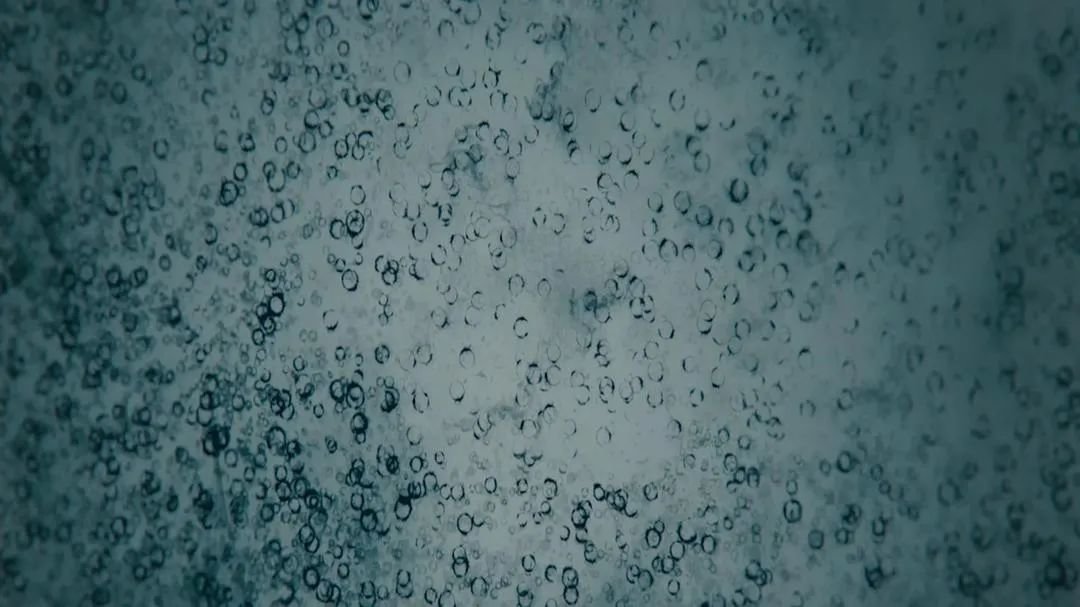和父亲无话可说的第四年,我决定…… | 星期天文学·薛超伟
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补缀、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16辑,嘉宾是青年作家薛超伟。其首部小说集《隐语》收录了九篇风格各异的小说,有的观照都市中合作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有的将乡村叙事的传统焦点转投注到富裕农村的生活状态。而不同风格的小说并不完全孤立,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互文的关系,比如下文的书籍同名短篇《隐语》中的“谜语”以互文的方式在另一篇《化鹤》中呈现“谜底”,两者又都可独立成章。
在短篇《隐语》中,薛超伟通过“古代谜语”这个中介,结构起一对父女之间的关系——父亲希望通过为“谜语”找到“谜底”,走进女儿的世界;女儿则专注于寻找“谜语”的过程,试图找回并重构失落的时间。虽然父女两人追寻着“谜语”的不同侧面,最终却殊途同归。
薛超伟,1988年生于浙江温州,毕业于复旦大学MFA创意写作班,毕业作品《水鬼》受到金宇澄激赏。作品散见文学期刊,现居杭州。
隐语
一
远处有铛铛声,我想象那声音是一种饰物,悬挂在古城上空。古城终日在翻建,每日都比前一日新些,但又在某些方面尽力做旧,像一场无用功,又像跟时间做抗阻运动。
我坐在灯谜馆的前台,等待可能的访客。林亭在后面的房间,守着贵重展品。没人的时候,我们会互相喊话。她说得最多的话是:“简秋榕,我好无聊啊。”她总说想换工作,但又怀疑找不到更好的。我可以理解她的烦恼,但不太懂无聊是一种什么状态,面对那些空白的时间段落,人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来填充它。它们那样空着就好,很自在。
下午外面刮大风,一会儿下起了雨。路人在街上跑动,有几个躲到馆里来。我让那些人在访客表上登记。他们本不是来参观的,登记完,也自然而然地参观。
展馆很小,一共三间屋子,馆内挂着很多灯笼,四方或八角的宫灯,里面是灯泡,晴天的时候也亮着,雨天格外明亮,映着灯谜。玻璃展柜里摆着一些古代留下的谜书,布展或维护时,我会借机翻一翻。林亭待的后屋有块大端砚,一人高,砚中有数块小砚,小砚里外包罗万象,有山水,有楼阁,有人物。似乎专为引起人的惊叹,它立在那里,无用而庄重。他们都与它合影。
他们参观完,雨还没停,便来回踱步,看看雨幕,又走回去。我坐在那里,暗自偷笑。与阑风长雨对峙的时候,人会争胜,于是,就很难取胜了。
雨渐渐停了。跟很多事一样,它们开始占据你的时候,就会停下来,这是它们的善意。避雨的人陆续离开,馆内又变安静了。天亮起来一点,又正式黑下去。
檐漏滴答,放晴了,檐头还下着残雨。我望着,想到“漏卮”(渗漏用的酒器)这个词,这个词后来被一名古人制成了谜,在《诗经》里找到了对应的谜底:“不可以挹酒浆。”《诗经》里本义说的是北斗。从酒具到星斗,路途遥远,借诸谜语,倏忽间也就到了。我从窗户探出头,在天上找,能看见几颗星星。我分不清星宿,不知道哪几颗算北斗,但假装都看见了,可不是,它们肯定都在那。
“简秋榕,下班了。”林亭把我喊回来。我同她清查展品,锁好馆门。在路上,她说:“我有种感觉,有时候你站在那里,其实并不在。”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哎,我也不知道,就是这种感觉。”我们走下一条长长的坡道,坡道底下有小菜园,几个小孩拿着铲子在挖雨后的泥土,一只黄狗在旁边兴奋地绕圈。我凶他们:“这么晚了,囡仔还不转厝(闽南语,意为回家),在这迌(闽南语,意为玩耍)。”他们回嘴:“要你管!”林亭跟我哈哈笑。到十字路口我们分开走。我家在文庙前大广场的东巷里,属于景观的一部分,所以门户被改造得很漂亮,每次走到家门口,看着路灯晕染的淡淡红砖墙,我总是开心。
听到我回来,我爸把事先备好的食材下锅,开始做菜。以前他不等人,自顾自先吃完,我回来只能一个人对着墙壁吃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变了性子。林亭说男人老了都这样,开始想对家人好了。她阿公,使唤了一辈子她阿嬷,有一天突然帮忙收拾了。如果是这样,那我宁愿我爸不要变。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跟他离了婚,两人都没怎么管过我,是我阿嬷把我养大的。他和阿嬷也吵架,跟那些在古城只有一面之缘的游人倒是处得不错,喜欢和他们聊天,五湖四海的方言都学一点。有一天,我爸说他这是在挑女婿。他说:“会有人因为跟岳父聊得来而娶他的女儿吧?”
我忍不住笑,说:“你这话有逻辑问题。”
“会有吧?”他说。
他总是别别扭扭的,喜欢拐着弯邀功。本来,他跟年轻人聊天,帮我留意潜在对象,这两者都没什么问题,但非要联系在一起,就叫人不舒服。但我知道他一直是那种人,也很难怪他。吃饭的时候,他又提起这个话题。
我说:“我不是没人要。”
“我知道,你得积极一点。”
“我也没有坚持什么不婚理念。只是现在还不想。”
“所以你要想,而不是不想。一年又一年,到最后就没得挑了,你姨婆当初……”
“嫁到山里去了,过得很苦。”我接过话。
“我知道,你忙,你研究谜语。以前有个人,天上在下炮弹,他躲在家里研究谜语。你们这些人,世界上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总是拣最不重要的去做。”
“那个人后来呢?”
“你看。”
“后来怎样了?”
“还能怎样,被炸死了。”
“他结过婚吗?”我绕回来问,避重就轻。
我爸不说话了。
晚饭后我回到房间,坐在靠窗的书桌前。很多个夜晚,我这样坐着,翻开桌上的本子,上面抄写着我从谜书上记下的谜语。展馆的线装谜书中,有一本《嗜痂记》,此书记载作者平生与谜友会集,猜射为戏的旧事。作者叫“味辛老人”。馆里收藏的是手抄稿,根据专家判定,是清人纸墨。誊抄人只留了个“揭云居”的称号。所以我知道揭云居是清人,味辛老人是他同代或更早之前的人,除此之外,对他们生平一无所知。这书倒是寻常,但是我在末几页发现了疑似不属于正文的内容,我猜是揭云居抄完书后自己写下的。他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说的是,某天他在书斋闲读前人高隐的笔记,这位叫高隐的古人在野外发现了一只小动物,它只有狸奴大小,周身豹纹,头似圆盘,乌睛白眉,四肢若骏犬般有力。它在草丛里跑跳,停下时发出“厌厌”的叫声。他悄然接近,那小东西一下就窜远了,不知所踪。高隐猜那是古人说的驺虞,但回去翻书,书上说驺虞大若虎,肯定不是他看到的那般小。他凭记忆把它画下来给友人看,友人们都说不认识。他带人去荒地里找,搜寻几日不得见。想到它那天厌厌有声,就名之为“厌厌”,记载下来,待后人探究。揭云居在文章里感慨,天下只有高隐一人见过厌厌,实为遗憾,现在他不知道厌厌是什么,耳畔却能听到它的叫声,仿佛那厌厌就藏在眼前的书页中,只是常人看不到其形貌。四时变迁,万物都会陨谢,但总有一些方式可以将它们保存下来。揭云居受到启发,于是自制谜语游戏,用一物去镌记另一物,以慰忧物之心。
此后,他闲暇时,就写下一些事物的名称作为谜面,慢慢找谜底。谜底须有典故做支撑,不然猜谜就没有难度可言。这种制谜方式有些特殊,一般是先发现二者有勾连之处,再去探究有无成谜的可能,而他却是任意写下谜面,随缘去寻谜底,自己是自己的出谜人。他在书卷中读到“罗敷”二字,觉得念来很有韵律,便随手记下作为谜面。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友人们踏秋,在黄栌下设宴,饮清茗赏花叶,诵“秋”之赋之诗之词,以助秋兴。一友人吟诵欧阳修的《秋声赋》,到“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揭云居拊掌笑,众人惊异。揭云居解释,他猜到了一个谜的谜底,“罗敷”射“夫秋”正好,因为罗敷的丈夫叫秋胡,有李白的《陌上桑》为证。
靠类似方法,他造了一些谜语,比如“江南省”射“宁俭”(《论语》),“雅音”射“乌号”(《淮南子》)。有些谜难解,他在文章中也没有解释。比如,“皋”,射“接余”,我想不明白。后来我查了《诗经》,有毛公作注:荇,接余也。皋荇,大概是“高兴”的谐音?这竟也可以。那天想到这个谜,揭云居肯定很高兴。
手稿上还有些谜,未写下谜底,就那么空在那里了。可能是揭云居还没想出谜底,也可能是他刻意空着,留给后世像我这样的闲人去猜射。那么,如果我想到了谜底,就不仅是物与物相随,彼此镌记了,而是我与他也产生了联系。我记下他的几个谜。其中“裂素”这个谜面是我最喜欢的,我时时揣摩。“裂素”出自李白思念儿女时写下的诗句“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谜底须用典,也就是说谜底在所有的古书里。那可能要找一辈子,也可能像他找“罗敷”的谜底一样,与友聚会即可偶得。无论如何,我不着急,只是闲暇时随意地找一些书看。我虽然喜欢谜,但对谜的悟性很低,也没有足够的知识量。但,谜底总能找到的吧,找不到也没关系。
二
在阿嬷的店里,我接过她递来的面,自己加卤菜,用剪刀剪一小截猪大肠和一小段猪软骨,多加了些素菜,自家的店,更要节制。我找自己的小桌坐下,吃着面,跟阿嬷说话。跟阿嬷说话就是,阿嬷的话我可以不接,我的话阿嬷也可以听不见,没有人急着追问,没有人觉得不快。
店面位置偏僻,在古城副街的街尾。街尾有街尾的人来吃,多是老食客。常常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进的门,悄无声息,发现时,就已经坐那了,他们不专门点单,等待一会儿,阿嬷就把干拌面端上来,要加什么料,加多少,很少出错。错了也将就。他们有称呼,但缺少名字。比如附近食杂店的阿伯,我多年来都喊他阿丘伯。有一天阿嬷告诉我,那人不叫阿丘,阿丘是他阿公的名字,阿丘早不在了。这明明不是什么叫人开心的事,但阿嬷说话时的语气,让我觉得很好玩,我就一直笑。阿嬷瞪我:“查某囡仔,没礼貌哦!”我问:“那他叫什么?”阿嬷歪头想了一阵,发现自己也不知道,我又忍不住笑。这次遇到,我依旧喊他阿丘伯,他依旧应着。总有一些东西延宕下来,拖着旧时虚影,恒久存在着,连名字也是。
门口的木麻黄树长得毛躁,树底下停着一辆摩托车,车身银钢色,车座红黑拼接,伏在街边。我不懂车,也觉得好看。车是阿嬷的,阿嬷六十多岁突然买了摩托车,引街坊诧异,为此我爸还跟阿嬷吵过。我记得我爸问:“哪个老阿嬷会骑一辆这么凶悍的摩托车?”
“山里头的老阿嬷人手一辆摩托车。”阿嬷说。
“这里又不是山里头。”
“行远路,早做准备。”
没见阿嬷行过远路。我曾想过,阿嬷是不是要骑着摩托到处走走,比方说环游世界。但几年过去了,阿嬷始终没有启程,那辆摩托,也只是拿来代步。
把面碗端到厨房,我看着阿嬷。阿嬷曾是个粗壮的女人,但再粗壮,老了后,也像烧了一半的纸,蜷起来,身上腾起一缕叹息。我抱抱阿嬷,说我要走了。阿嬷说:“去吧去吧,多大了还撒娇。”
我没跟阿嬷说过,我或许见过真正的阿丘伯。不仅是阿丘伯,我见过很多遗落在过去的人。他们影影绰绰,在古城的面馆、茶楼里,在某个不惹眼的角落,甚至在大街上。我出生长大的这个小城,跟谜语是相合的。那些人那些物的本义消解,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依然存在。阿福家的四果汤还是那个味道,换了店铺,从城南来到了有竞争力的前街。小时候从自家门前抬头就能看到的女儿墙不见了,现在在文庙周围建了一圈带女儿墙的小楼,会有人倚着三楼栏杆,跟底下的游客互相窥看。文庙里的千年古柏,在二十多年的短暂时间里,只是把南枝往前伸了一些,并于去年拥有了一个新修的树围。路过,我就会去文庙里拜拜,我看过的谜里,有太多他老人家(指庙中供奉的孔子)的语录,常受教诲。更早,与老人家不熟的时候,我就来玩的,只当他是一个更高大的尊像,与那些故居里的、牌坊上的人像无异。在被管理员训斥之前,爬过几次基座,摸摸老人家的袖子。
那个时候我顽皮,为了消耗过剩的精力,一个人瞎热闹,不然会胡思乱想,想念爸爸妈妈。记得爬过闲谭巷的围墙。有一段挨着一户人家的阳台,那户人家经常有麻将局。我爬上去,站在上面,想着妈妈是不是在那个阳台后头,能不能偷看一眼。她跟爸爸离婚后,我很久没见过她。结果走两步就摔下去了,幸好被一个大人接住。我吓得扯住他衣领,眼前是白头发,往下看,是白胡茬,是一个阿公。他把我放下来。我等着,以为他会训斥我。结果他没有,有点奇怪,不像别的大人。我说:“阿公,以后我不乱爬了。”我记得他说:“没关系,囡仔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但别太入迷了,玩的时候,要留一部分神,照看好自己。”我用力点头,仰头看他,他很亲切,长得像我们家的人。但我们家的男老人都不在了。他捏捏我的脸,笑一笑,转身走了。以后就再也没见过他。好像他就专门出现那么一下,就为了接住我。会是我的一个祖先吗?
在灯谜馆,我问林亭有没有见过自己的祖先。她说我头壳坏去了。我说:“某一个时间,你一定见过,只是你不知道。”她见我讲认真的,想了想,走过来跟我说:“还真是,我小时候看着我太公的照片,能听到他讲话。后来才知道,照片挂在墙上的人是不会讲话的。”我说:“那你怎么知道那就是你太公的声音?”林亭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想。”我说:“你见过你太公吗?”她说:“出生的时候见过,但我不记得了。他不久就过世了,我有时候会想念他。想念一个没讲过话的人,奇怪吧?”我说:“不奇怪。”
三
我爸退休后,把攒下的积蓄和老厝的拆迁补偿款拿去给中间人放贷,每年收一些利息,也够家里的生活费。他在家待了两年,突然跟我说想要做点投资。他说:“做个好业人,女儿才能嫁好人家。”他又以我的名义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但追究起来,那话里也有一些真。他的投资理念一直保守,拿了钱只想存银行,能拿去做借贷,也是被人劝的。他现在肯定是真的想挣点钱。
我说:“爸,老实说,我目前的状况,就是只能养活自己。你一定要做投资,我也支持你。万一亏了,还有我呢,我换个赚钱的工作就是。所以,你想做什么,就做吧。”
我爸笑着,说好。
过几天,他跟几个外地来的朋友见面,聊合作的事。之后还要去蜜柚园考察,看值不值得投资。我也跟着去饭局,给他壮壮声势。酒桌上的几个人给我爸讲现在蜜柚的销路好,在原来的蜜柚基地边上,又开辟新的种植园,还要做对应配套项目,比如农家乐,很有前景。他们拿出蜜柚园的照片满桌传看。我爸听得兴奋,频频敬酒,也被敬酒,喝了很多。我帮他挡了几杯,他们说,我干了,你是女孩子,少喝一点。我在很多场合听过这话,但第一次在我爸的饭局上听到。我几乎没跟我爸一起参加过饭局。
投资的事聊完了,他们开始聊些这边的风俗名物,聊得很杂。有人说起闽南方言里“有”的发音像普通话里的“无”,觉得这一现象很有意思,比如“只有你”音似“肌无力”。接着谈到“酒干倘卖无”这句歌词,一般正常的说法,是“酒干倘有卖”。还有“水有饮勿会完”,不直接说“水饮不完”,要先加个“有”。以有说无,以无说有,很有闽南人闲适的性格。我听出很多错误,忍不住插话:“闽南话‘有’跟普通话‘无’发音相似是巧合,在语音流变过程中,两者发音偶然碰撞在一起,并没有那么多门道。”被反驳的人似乎想接话,看看我,又犹豫起来,只是笑。爸爸打圆场:“喝酒,喝酒。”他们说:“你女儿厉害的哟。”
吃完饭,他们搂搂抱抱,告别话讲了很久。我问好他们的目的地,分别给他们叫了车。坐在车里,我问我爸,刚才直接呛他们是不是不好,会不会不礼貌。他说:“没有,你是女孩子,不会怪你的。”我想了想,虽然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但如果真有这样的好处,好像也挺不错,至少在这个场合,我没有牵累我爸。我跟我爸分析了他们的个性,从他们的言谈举止,能看出一些东西。但如果一定要说他们不懂语言学就也不懂投资,在这处夸夸其谈就会在那处大吹大擂,也不公平。
“总之,再观察吧,做个参考。”我说。
“对,要多方观察。放心吧,借出的钱拿回来也要一段时间,爸不会这么快被骗的。”我爸说。
“那缓缓被骗?”
他笑得很大声。
洗完澡,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书。吃一顿饭几乎掏空了我的能量,我的能量来自静物。比如一只小狗很可爱,我会远远看着它,如果它向我跑来,那种可爱马上会变成负担。
对面有几扇窗开了一半,不下雨,有些人家就把窗彻夜敞着,接纳夜风和飞虫,也借窗外的景。路灯下,剥了漆的门不再被修缮,委灰中显出一点轻轻的红。
爸爸敲了敲我的房门,问可以进来吗。我打开门,让他坐。他闻了闻房间里的气味,可能是香水味,似乎想到应该与成年的女儿保持距离,说:“要不要到外面聊聊?乘个凉。”我心想,乘什么凉。从阿嬷的老厝搬来跟爸爸一起住,四年了,我们还是没学会,父女间应该怎么相处。我说:“就这里吧,咱俩也很久没聊了。”除了嫁人的话题,我想。他在房间里走动,看我的书架,又翻翻我桌上的书,说:“这书好看吗?”
“也不是好看才看的。”我说。
“啊?不好看为什么要看?”
“我找谜底。”
“谜底在书里?还要找?谜不是猜出来的吗?”我爸带着酒意问我,有点像吵架。
“是的,我猜的那些谜,谜底都要有出处,有典故。”
“为什么要有出处?”
“要有个目的地。”
我爸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问我:“现在在研究什么谜语?”
我觉得再跟我爸相处四年,他也猜不出谜底,但又不能不告诉他。以为父辈什么都不懂,嫌烦,拒绝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矛盾就是这么开始的。
我说:“谜面是‘裂素’两字,谜底在古籍里,指的是所有的古籍。”
我爸说:“所有的古籍。”
我点点头。
我爸说:“我都没看过几本。”
“所以咯,很难的。”
“你要一本一本看,看完历史上所有的书吗?”
“也不是,就是给自己一个看书的借口。谜底找不到也没关系,我头脑不算好。反正有很多时间。”
我爸说:“谁说的,我囡仔头脑好着呢。”
我爸又跟我讨论了很多问题。我发现我也很乐意解答。我们聊到了往事,妈妈,阿嬷,我们的老厝,这座古城,他小时候古城的模样。我还知道,他年轻时候也算是个文化人,做过报社印刷工人,钱少,后来才去的汽配城。
临出房门,他找我要纸和笔,让我把谜面写下来。我给他写上“裂素”二字,想了想,又在下面作了备注:谜底须用典故,典故在古籍中找。
四
我跟阿嬷说:“爸爸变得比以前好,会照顾人了。”阿嬷说:“你爸找你了?没有烦你吧。”我说:“没有,他还挺好玩的。”
我看着门外的木麻黄树,阳光抚过它的毛躁,使之显得温和。摩托车也温和,它不动的时候,像一只被染发的小狗。
“你有个骑士阿嬷,好酷哦,她会在夜里炸街吗?”以前,朋友这么跟我说过。当时我哭笑不得。
我从阿嬷手里接过面碗,又送回去,我说:“我要阿嬷帮我打卤菜,好吃的,大块的。”
阿嬷笑着摇头,说:“囡仔小时候可是很懂事的,现在怎么越来越娇惯了。”
我嘿嘿一笑。因为过得开心,才能娇惯。因为面对的是阿嬷。因为在这间小店,无事发生,世上所有的痛苦都隔绝掉了。在这里,时间也不再流逝。
小时候,天还没亮,阿嬷就起床去备菜了。我也要起,阿嬷让我好好睡,囡仔缺觉。我问阿嬷怎么不缺觉。她说,人老了就这样,老天爷会匀一点时间给你。我说,那越老就匀得越多,以后阿嬷一百岁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时间。
我吃着面,想起来,我几乎问过阿嬷所有的问题,聊过所有的话,有一个还没问。我说:“阿嬷,姨婆是什么样的人?”
“怎么突然问起你姨婆,你都没见过吧?”阿嬷说。
“对啊,你们不来往。她可能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我。但不知为什么,我会想起她,会想她。”
阿嬷跟我讲了姨婆的故事。
姨婆爱玩。这个“爱玩”,是旁人的描述,姨婆本人并不认可。几十年前,她交了一个男朋友,经常跟着他在外面溜达,玩到夜里才回来。阿嬷这个做姐姐的,看在眼里,很心急。她叫了一伙人堵他,打到半死。
“幸好没打死,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阿嬷说。
之后姨婆还是跟那个男人好,在床边照顾他。但他是怎么都不敢要她了,等清醒能说话的时候,就让她走。我姨婆说:“你如果愿意继续跟我好,我们就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过日子。你如果更喜欢这里,我也跟你留在这里。如果再出现伤害你的人,我会杀了他。”他说:“我只希望你走,求求你。”
我姨婆走了。
姨婆后来负气,嫁了个山里人。男人是诏全的,虽然归属同一个市,实际相隔六百里。家里人都反对,那里不只条件艰苦,还落后,女人进不了宗祠。姨婆还是坚持嫁给她。阿嬷说:“你可以嫁过去,我们从此不要再联系。”
姨婆不吭声,点了头。
阿嬷讲完,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时间太快,很多事都不一样了。故事里,姨婆是单方面受苦的那个人。但其实,回到那时候,阿嬷也有那么做的理由。
我走到阿嬷身边,轻声对她说:“阿嬷,你是好人。妈妈跟爸爸第一次闹离婚,你还偷偷给妈妈出钱了。你以为她要远走,想着,查某上路还是要带些钱的。”
“囡仔怎么知道?我没跟人讲过。”阿嬷说。
“你上一次跟我说了。”我没跟阿嬷说,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
我走出阿嬷的店,走在路上。古城到处都在翻建。在建的新楼,都是记忆里的老样式。旧时南洋带回的五脚基建筑,被摆在主街。常有女孩子站在红砖柱子前,定定地看着前方,忧郁或浅笑,闪光灯过后,从失神里醒转,重新欢悦起来。二楼往上又是传统的窗与槛。木质窗扇,与外墙红成一色,又与砖柱区别开来,两扇向外开,常与风合谋,吱吱呀呀,调戏过路的鸟。窗槅是一块块菱形的空,连缀在一起,或许就是李渔说的欹斜格。谜里也有格,梨花格、卷帘格、解铃格之类,仿佛跟窗槅是一件事。若与人说,这是梨花格的窗,谁能听出破绽呢?
中西合璧的建筑,让我想到一个同样中西合璧的谜,谜面是“谭”字,谜底是“西言曰十”,不仅把“谭”拆分得恰到好处,而且还扣合了西语中“十”的发音“ten”。我每次想到这个谜,就会笑。因这个“谭”字,我就常往闲谭巷走。宁愿多拐些弯,也要穿巷。走在巷子里,麻将声无缘由地漏下来,如不细究,那声音是叫人安心的,从小听惯。旧城改造以后,收租的人多了,终日打麻将的人也多了。我妈就在其中。
她跟我爸离婚后,嫁了一个,又嫁了一个。要论优点,都比我爸好。但没我爸滑稽。都是些得意洋洋的男人,我爸也得意,收着得意。我妈喜欢跟我讲我爸的坏话,说在我小时候,他对我多么不在意,曾经把还不会走路的我,独自放在高高的灶台上,他自己溜达到不知哪里去了,任我手脚乱抓,险些掉下去。这个故事,我妈讲了七八遍。起初我奇怪,多年过去了,还这么恨着吗?后来想明白了,她跟我已经没有话题了,她就是想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会坐在一座工地对面,看着缓慢生长中的建筑,把它盯到羞涩,等将来它落成了,可以跟它说,你是我看着长大的。工人大多是中年人,有几个年轻的。年轻人跟年轻人一起玩,或蹲或坐,在一起看手机。我跟其中一个年轻工人搭上话。他说他家在菜场附近,旧城改造时没拆到,那一带仍像过去一样脏乱,家里也改不了民宿。我问他为什么要干工地。他说,你这话问的,挣钱么,难道是爱好啊。他说他有很多想做的事,这头一件,就是让母亲过上每天打麻将的生活。她每天睁开目睭,发愁的事情,就是牌路。
“那不是很空虚?”我说。想到林亭,她总喊着无聊。
“空虚好啊。比方说,空心砖,都用在不承重的部分。做空心砖,多快乐。”
我心里高兴,被一个小年轻说服了,突然觉得妈妈那样过一辈子,也挺好的。开心总比不开心好。
走在路上,麻将声听着也悦耳了。我在谜书上看到过一个谜,“雀戏”射“载弄之瓦”。大概因为麻将也称为“麻将瓦”,而古时又将这类娱乐场所称为“瓦市”。有了这层联想,我觉得麻将声里也添了古意。不过我更喜欢另一个谜,“棋声丁丁”射“子路有闻”。不只棋声丁,雀声也丁的。
五
我坐在灯谜馆,外面又下雨了。
新闻上说,诏全山区发洪水,板凳、家禽,就连摩托车都被水冲走。新闻说,山区里,人们的重要代步工具就是摩托车。
我想,原来,阿嬷买摩托,是要驶去诏全的。她坐在那辆红黑车座的摩托上面,双手搭住车把,银发扬起,行驶六百里,中间加了一次油,最后歪歪扭扭地在泥泞山路上骑着,目的地是姨婆的家。她把摩托停在姨婆的院子里,不用说什么,姨婆就明白。姨婆会说:“阿姐,你来了。我等了你五十年。”
然后,那么那么多年的嫌隙,就此消解。
但阿嬷始终没有启程。
我问阿嬷为什么不去,心心念念的,为什么不去看一看。
阿嬷说:“刚开始想去,后来拖着拖着,就算了,还是不要去打扰她。想着,是不是太轻易了。如果轻易被原谅,就糟糕了。”
我不懂阿嬷的意思。
阿嬷说:“人这一生,总会有一些不好,怎么会事事尽好呢?活得问心无愧,对我来说不敢想,甚至有点可怕。”
我听了,有些想哭。我抱着阿嬷,把脸埋在她衣襟里。我跟她诉说这些年的歉意。我没有做的事,我做了的事,因为她不在了,每一件事都是遗憾。
阿嬷说:“囡仔,不用道歉。人啊,怎么活都可以,顺你的意就行。可以听爸爸的话去结婚,也可以不听他的话。怎么选都会有遗憾,那就可以忘记遗憾。”
我摇头:“不能不结婚。如果阿嬷当初不结婚,就没有爸爸,也没有我了。被生下来,存在着,真的很好。”
“会有的,都会有,只不过从别的地方长出来,不叫阿华,不叫秋榕。叫个别的。”
我点点头,作为这一个简秋榕,这唯一一个,唤着阿嬷,一声接一声,直到最细声时,丰盈的拥抱变成虚无。
我希望所有人都永远存在。永远存在下去。
我回到灯谜馆,一直掉眼泪。林亭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梦到阿嬷了。”她给我递纸巾,轻轻拍我的背说:“你去后面展馆吧,我来接待。我会插上耳机,你如果想哭,就继续哭,如果需要我,就叫我。”我向她道谢,交换了座位。
古城慢慢暗下来。
晚上回到家里,爸爸看我。我别过头,用长发遮住,他又拐着弯看我。
“囡仔,怎么哭了?”
我说我没有,又说:“看了一本感人的书。”
“你哪会在上班时间看书?你宁愿坐那发呆。”
“嗯?你怎么知道。”
“我会路过。”
我没多问。
他说:“给你讲件高兴的事,爸爸猜出谜底了。”
“谜底,什么谜底?”
“裂素的谜底。”
“这么快?怎么可能,这才过了几天?”
爸爸拿出上次那张纸,摊开来给我开。他看看字,又看看我,小心地问:“这个谜底,你觉得对不对?”
裂素,陈玄。
良久,我问:“爸,这‘陈玄’两个字,是出自古书吗?”
“是,唐代韩愈的《毛颖传》。”
我想起来了,那是篇简单的古文,上学时还学过。陈玄是墨水的意思。“裂素”著文,需要用墨水,也需要在绢纸上列出玄色的字。且不论是不是真的谜底,是不是揭云居所想的谜底,这两个词作为谜面和谜底,总归是和融的。我说:“爸,这是对的,你猜对了。这是正确的谜底。”爸爸的眼神一下子亮了。
我问:“爸,你怎么知道谜底在这篇文章里?”
“你馆里有块砚台,我经常去看的,解说词上说,砚台也被称为‘陶泓’。我就想知道这说法哪里来的,去找,就看到了。”
“你还去参观过,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可多。”
我笑了。他见我笑,伸手捏捏我的脸。我轻轻拍开他的手。我说:“哪个爸爸会捏自家老姑娘的脸啊?”
他笑笑,看着纸上的谜语,说:“裂素,陈玄。白色裂开了,陈列出黑色。意思是,拔断白头发,现出的是黑头发。”
“才不是这个意思!”我笑着说。
“这谜挺好的,好像时光会倒转。”爸爸说。
我看着爸爸,看着他的模样,头发白了一半,胡子也白了。曾经,我们家的男老人都没了,都变成照片挂在了墙上。现在,又有个男老人慢慢长成。
我突然知道他是谁了。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的爸爸,以后会变成谁了。
“爸,原来你老了长那样。”我说。
“嗯?”他说。
不知道爸爸找过我几次。在那同一天。不过,他为什么要找我呢?找那时的我。
我知道了。跟我找阿嬷的理由是一样的。
原来,时间没我想象中那么多。
晚饭后,爸爸又要去广场,去找他那些年轻的远方的朋友,会那一面之缘。我跟着他去,这是我第一次同他一起来到夜晚的广场。家门口就是景,但我没跟他一起散过步。星星全部落在广场中央的水池里。我跟爸爸讲起我第二喜欢的那个谜语。
只要我愿意,我可以直达星斗。但此刻我哪里都不想去,这里就是我需要存在的地方。
本文节选自
《隐语》
作者: 薛超伟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