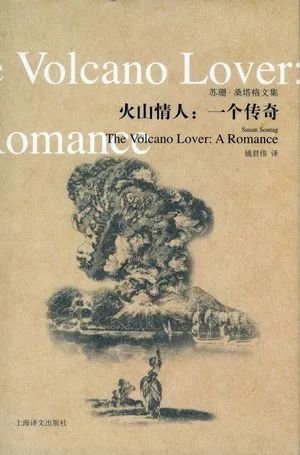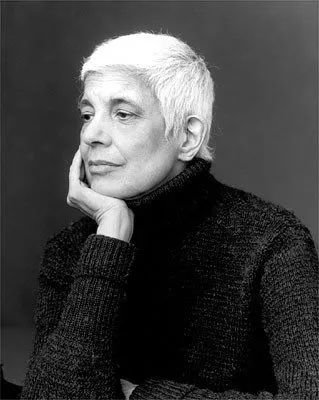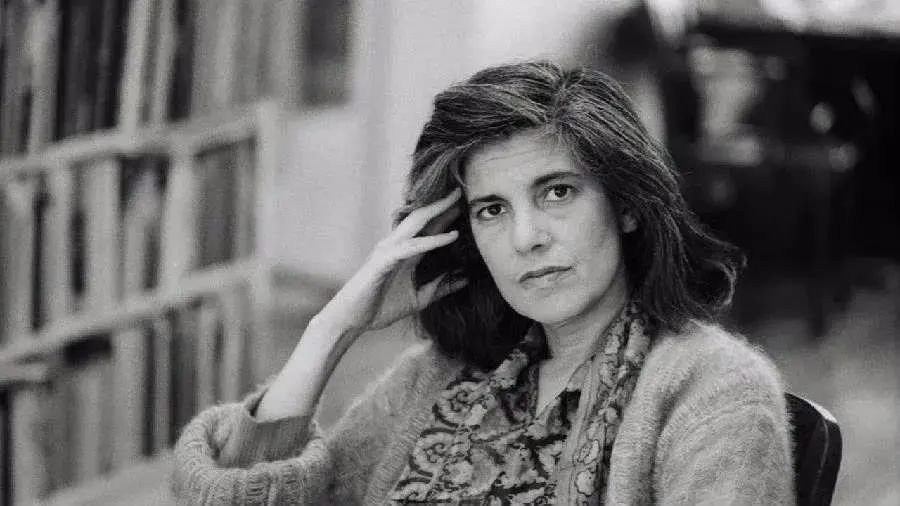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丨苏珊·桑塔格
《反对阐释》《疾病的隐喻》《论摄影》《关于他人的痛苦》……这些书你或许没有读过,但一定有所耳闻,它们均出自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女权主义者,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今天是桑塔格的诞辰。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生于美国纽约,开启了她作为“天才少女”的一生。“她的功成名就确实令人惊叹:那完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路表演下来的。”在《桑塔格传·人生与作品》中,作者如此感叹,“一个年纪轻轻的美女,学识渊博得令人生畏。”
然而,相比桑塔格的思想和行动,美貌于她,或许正应了那句俗语,是“最不值一提的优点”。德语作家卡内蒂曾写道,当代杰出的作家“是具有独创性的;他总结他的时代;他对抗他的时代”。桑塔格的一生即是如此,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超越了其他任何一位杰出的公共思想家,以一种在她之前或之后的知识分子都从未采用过的方式,为文化辩论定下了基调。
“文化是值得为之献身的。”这是桑塔格毕生的信念。
在诞辰之日,我们摘编了《巴黎评论》编辑部对桑塔格的采访。交谈中,桑塔格陈述了她的成长和求学经历、写作习惯、女性主义视角、以及她对文学的态度。对读者而言,这或许是初步了解桑塔格的一次尝试。
经出版社授权推送,有删减。
01
我真正想要的是
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
《巴黎评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苏珊·桑塔格:我也不确定。但我记得,大概在我九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尝试自己印刷。我尝试着从印一份四页的月报开始,用胶版印刷的方法(一种很原始的复印方法)印制了大概二十份报纸,然后以每张五美分的价格卖给了邻居们。而后的几年,我一直坚持办那份报纸。
《巴黎评论》:你一直以来就想当个作家吗?
桑塔格:在我大概六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居里夫人的女儿艾芙·居里写的《居里夫人传》,所以最初,我立志成为化学家。后来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又想成为物理学家。最后让我不能自拔的是文学。我真正想要的是将每一种生活都过一遍,一个作家的生活似乎最具包容性。
《巴黎评论》:你有崇拜的作家吗?
桑塔格:当然,我曾把自己看作是《小妇人》中的乔,但我不想写乔所写的东西。而后,在《马丁·伊登》里,我发现了身为作家的主角,而且我对他的写作有种认同感。所以我又想成为马丁·伊登。不过杰克·伦敦把他写得很凄惨,这我可不想要。我把自己视作(我猜是这样的)是一个英雄式的自学者。我期待写作生涯中的搏斗。我认为每个作家都会具有一种英雄主义的禀性。
《巴黎评论》:你还有其他偶像吗?
桑塔格:后来,在我十三岁的时候读了安德烈·纪德的札记,它展现了一种有巨大优越感和不懈渴望的生活。
《巴黎评论》:你记得你是何时开始阅读的吗?
桑塔格:别人告诉我,我在三岁的时候就开始读书了。不过我记得,我在六岁左右才开始阅读真正的书籍——传记和游记等等。而后,我迷上了爱伦·坡、莎士比亚、狄更斯、勃朗蒂姐妹、维克多·雨果、叔本华和佩特等人的作品。我的整个童年时代是在对文学自得的谵妄中度过的。
《巴黎评论》:你一定和别的孩子相当不同。
桑塔格:是吗?但我也很擅长掩饰。我不太关心自己是个怎样的人,但我会高兴地去向往成为别的更好的人。同时我也想置身于别的地方。阅读本身营造了一种愉悦的、确凿的疏离感。多阅读、多听音乐是如今世人越来越不在乎的,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正是我所追求的。我一度觉得自己来自别的星球,这个幻觉来自当时令我着迷的纯真漫画书。
当然我无从知道别人怎么看我。实际上,我觉得别人完全不会想到我。我只记得四岁时在公园里,听到我的爱尔兰保姆告诉另一位穿着上过浆的白色制服的大人说:“苏珊的弦绷得很紧,她非常敏感。”我当时想,这是个有意思的说法,对吧?
《巴黎评论》:跟我说说你的教育背景。
桑塔格:我上的都是公立学校,但一个比一个糟糕。不过我运气不错,在儿童心理学家的时代尚未到来之前就开始上学了。因为既能读又能写,我立刻就被安排到三年级的班里,不久我又跳过了一个学期,所以从北好莱坞高中毕业时,我才十五岁。
之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接受了一段很好的教育,然后又到了芝加哥大学所谓的赫钦斯学院读书。我的研究生是在哈佛和牛津读的,主修哲学。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读书,从我的每一位老师那里都学到了东西。
但在我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则是芝加哥大学,不仅那里的老师们让我敬仰,我还尤其要感谢我的三位老师:肯尼思·伯克、理查德·麦克科恩和列奥·斯特劳斯,他们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黎评论》:你十八岁便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当时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作家?
桑塔格:有,但我还是去了研究生院。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能靠写作谋生。我是个知恩图报但又好勇善战的学生。我自以为会以教学为乐,不过也的确如此。我小心翼翼地做了充足的准备,当然不是教文学,而是教哲学和宗教史。
《巴黎评论》:不过你只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教过书,后来拒绝了要你返回大学教书的无数邀请。这是不是因为你逐渐感到学术生涯和创作生涯之间不能兼容?
桑塔格:比不能兼容更糟。我曾经目睹学术生涯如何毁掉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
02
写作就是一种生活
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有多顺畅?
桑塔格:《恩主》我写得很快,一点都不费力,我花了周末的时间在两个夏天之间完成了(我当时在哥伦比亚学院的宗教系教书)。我觉得我讲了一个愉快而又阴险的故事,它描绘了某个叫做“诺斯替教”的异教观念是如何交上好运的。早期的文章写得也很顺手。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写得越多并不代表会越写越顺手,而是恰恰相反。
《巴黎评论》:你的写作一开始是如何下笔的?
桑塔格:我的下笔始于句子和短语,然后我知道有些东西开始发生转变。通常都是开篇的那一句,但有时,一开始我就知道结尾的那句会是什么样的。
《巴黎评论》:你实际上是怎么写的呢?
桑塔格:我用毡头墨水笔,有时用铅笔,在黄色或白色的标准横格纸上,像美国作家惯常的那样写作。我喜欢用笔写作时那种特有的缓慢之感。然后我把它们打出来,再在上面涂改。之后我再不断重打,有时在手稿上修改,有时则在打字机上直接修改,直到自己觉得已经写到最好为止。我一直用这种方式写作,直到五年前我有了电脑。现在,在第二或第三稿之后,我将它们输入电脑,然后我就不需要再重新输入整本原稿了。不过,在电脑上改完之后,我会继续手写修改。
《巴黎评论》: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帮你下笔?
桑塔格:阅读,不过通常它与我正在写或希望写的东西无关。我大量地阅读艺术史、建筑史、音乐学及主题各异的学术论著。当然还有诗歌。磨蹭也是准备开始的一部分,阅读和听音乐就是我的磨蹭方式。听音乐既让我精力更旺盛,同时也让我心神不定,让我对不写作产生愧疚感。
《巴黎评论》:你每天都写吗?
桑塔格:不,思路如泉涌时我才写。当压力在内部叠加,某些东西在意识里开始成熟,而我又有足够的信心将它们写下来时,我就不得不开始落笔。当写作真的有了进展,我就不干别的事了。我不出门,常常忘记吃东西,睡得也很少。这种非常缺乏规律的工作方式,使我不会多产。再者,我的兴趣太广泛。
《巴黎评论》:叶芝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和工作之间做出选择。”你是这样认为的吗?
桑塔格:实际上,他所说的是,一个人必须在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工作之间做出选择。写作就是一种生活,一种非常特殊的生活。当然,如果你说的生活是指与他人相处的那种,叶芝当然讲得对。写作要求大量的独处时间。我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写作,这样就可以减缓这种二选一的残酷无情。
我喜欢出门,喜欢旅行。在旅途中我不能写作。我喜欢谈话,喜欢聆听,喜欢去看,去观察。我或许有一种“注意力过剩症”。对我而言,世上最易之事莫过于去关注。
《巴黎评论》:你是边写边改,还是整个写完之后才修改?
桑塔格:我边写边改。这是很愉快的事。我不会因此失去耐心,我愿意一遍又一遍地改动,直到能流畅地往下写为止。万事开头难。开始下笔时,总有恐惧和战栗的感觉伴随着我。尼采说过,开始写作就好像你心意已决,要跳入一个冰冷湖里。只有在写作进行到大约三分之一时,我才能知道它是不是够出色。此时我手里才真正有牌,可以玩上一手。
《巴黎评论》:你是否按照顺序来写小说?
桑塔格:是的。我一章一章地写,这一章不完稿我就不会开始写下一章。一开始,这种写法令我感到十分沮丧,因为从一开始下笔我就知道,我要这些角色在结尾的独白里所说的话。但我害怕的是,如果我过早写下结尾,可能就没办法回到小说的中间部分。我也担心等我写到结尾部分时,会忘记当初的某些想法或者不能再体会到一些感受。第一章大概有十四张打字纸的篇幅,花了我四个月的写作时间。最后五章大约有一百页的篇幅,才花了我两个星期。
03
《火山情人》:女人,愤怒的女人
《巴黎评论》:你在开始写作之前,书的内容有多少已在你心中成形?
桑塔格:一般先有书名。除非我已经想好了书名,否则我无法开展写作。我有了献辞,我知道这本书将献给我的儿子,我有了“女人皆如此”的题词。当然我也有了故事的概貌和书的跨度。最有帮助的是,我对结构也有了很棒的想法。
《巴黎评论》:似乎在开始写之前,你已经知道了很多。
桑塔格:是的,尽管知道了这么多,但我仍然不清楚该如何呈现所有这些。于是我开始思索,《火山情人》这个故事应当属于主人公威廉·汉密尔顿,这位火山的情人,在书中我把他称为“那个骑士”。他是主角,整个小说以他为中心。诚如各位所知的那样,我以牺牲第二位太太的故事为代价,来展开描写汉密尔顿的第一任太太凯瑟琳的内敛性格。我知道凯瑟琳的故事,她和尼尔森的关系必须在小说里呈现,但我希望将之置于背景中来交代。
三重序幕和第一部分,其忧郁(我们或称其为沮丧)的主旋律的各种变奏:收藏家的忧郁,那种从忧郁中升华出来的狂喜,都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着。第一部分一直围绕着主角威廉·汉密尔顿,但我开始写第二部分时,爱玛就占据了主导地位。爱玛生性活泼,从精力充沛、活力四射到为那不勒斯革命抛洒鲜血的过程,是一个血的主题变奏。这一点使得小说转入到更强烈的叙事方式和对正义、战争和残酷的探讨之中(小说的章节也由此变得越来越长)。由第三人称所作的主要叙述就此完成,小说的其余部分由第一人称继续进行叙述。
第三部分非常短:主人公威廉·汉密尔顿精神错乱,“冷静”的主题通过文字的方式,演绎了他的死亡,其过程完全如我想象。接着,我又回到了以主角威廉·汉密尔顿为轴心的第一部分。我在写第四部分的独白——“火爆”时,发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女人,愤怒的女人,从冥界发出声音。
上海译文出版社丨2012-3丨译者: 姚君伟
《巴黎评论》:这些人是不是都非得是女性?
桑塔格:那是肯定的。我一直知道这本书将以女性的声音来结束,书中的一些女性角色的声音,她们最终都会有自己的话语权。
《巴黎评论》:你是借此来表述女性的观点。
桑塔格:当然,这是因为你假定世上确实存在着女人或女性的观点,但我没有。你的问题提醒了我。从文化构建角度来看,无论世上有多少女性,她们总被认为是少数群体。正因为女性被视为少数群体,所以我们将女人只会有单一的观点这个论断强加在她们身上。“上帝啊,女人想要什么?”等等就是一个实例。
如果我的小说通过四个男人的话语来结束,就不会有人觉得我提出了男性的观点,这四种话语之间的不同将会过于显著。这些女性角色性格各异,正如我可能选择的四个男性角色一样。她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观点重述了一遍已为读者所知的故事(或部分的故事),每个人都想说出真相。
《巴黎评论》:她们有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桑塔格:当然。她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知道,这个世界被男人所操控。所以,对于那些触及她们生活的重大事件,她们代表了被剥夺话语权的弱势群体的声音。但她们也不止于对重大事件发表意见。
《巴黎评论》:为什么要把小说的场景设定在过去?
桑塔格:为了摆脱与感觉相关的限制,比如我的现代意识,我对如今我们生活、感受和思想的方式是如何日益退化、变得一文不值的意识。过去高于现在。当然,现在就是当下,总会存在。
在《火山情人》中,叙事的声调是属于二十世纪晚期的,是由二十世纪晚期的各种关注所引发的。我从来不会想到去写“你就在那里”类型的历史小说,即便我能将小说中的历史内涵写得既紧凑又准确,进而受到赞扬,甚至还能感受到更大的空间感。我正在写一本小说《在美国》,决定再给自己一次在往事中嬉戏的机会,但我没有把握这次是否还能有一样的效果。
《巴黎评论》:你是否把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
桑塔格:这是少数几个我愿意接受的标签之一。尽管如此……这难道不是一个名词吗?对此我表示怀疑。
《巴黎评论》:哪些女性作家对你来说意义非凡?
桑塔格:有很多。清少纳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迪金森、伍尔夫、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伊丽莎白·毕肖普、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等等,当然还不止这些。因为从文化意义上讲,女性属于少数群体。当我把自己归为少数群体中的一员,我庆幸能看到这些女作家的成就;当我把自己归为作家中的一员,我庆幸能崇拜任何作家,女性作家的数量并不比男性作家少。
《巴黎评论》:你是否介意被称作为知识分子?
桑塔格:被扣上帽子以后,一个人总是会不高兴的。对我来说,与其说“知识分子”是个名词,倒不如说它是个形容词,这样更易理解。即便是这样,我仍旧觉得,人们把知识分子视为一群蛮狠的怪物,如果这个对象是女人就更糟了。这使我更坚定地抵制那些主流的反知识分子的陈词滥调,比如心灵与头脑之争,情感与理智之争等等。
04
我写作是因为世上有文学
《巴黎评论》:文学的目的在于教育是不是一种过时的想法?
桑塔格:文学确实教育了我们关于人生的种种。如果不是因为某些书的话,我不会成为今天的我,也不会有现在的理解力。此刻,我想到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一个伟大命题: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一篇值得阅读的小说对心灵是一种教诲,它能扩大我们对人类可能性、人类的本性及世上所发生之事的感知,它也是灵性的创造者。
《巴黎评论》:文学会让人迷狂吗?
桑塔格:当然,但不如音乐或舞蹈那般可靠。文学使人痴狂更多地表现在思想上。一个人要以严格的标准来选书。一本值得一读的书的定义是:我只想读那些我觉得值得再读一遍的内容。
《巴黎评论》:那你会回过去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桑塔格:除了核对译文以外,我肯定不会重读,绝对不会。对已经成形的作品,我既不好奇,也不依恋。另外,大概是因为我不想见到它们还是原来的样子。也许我总是不愿意去重读十多年以前自己写的作品,因为我怕它们会毁掉我在写作上不断有新起点的幻觉。这是我身上最美国化的地方,我总觉得下一部作品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巴黎评论》:你的作品总是各有特色。
桑塔格:作品应当具有多样性。
当然,其中也应存在某些气质和令人全神贯注的东西的统一:某些困境,某些诸如热情或忧郁的情感的再现,以及对人性中的残忍所抱的执著关注,无论这种残忍表现在个人关系里还是在战争中。
《巴黎评论》:你是否认为你最好的作品尚未问世?
桑塔格:我希望是,也许……是的。
《巴黎评论》:你会考虑你的读者的感受吗?
桑塔格:我不敢,也不想。但无论如何,我写作不是因为世上有读者,我写作是因为世上有文学。
本文节选自
作者: 《巴黎评论》编辑部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品方: 99读书人
译者: 仲召明 等
出版年: 201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