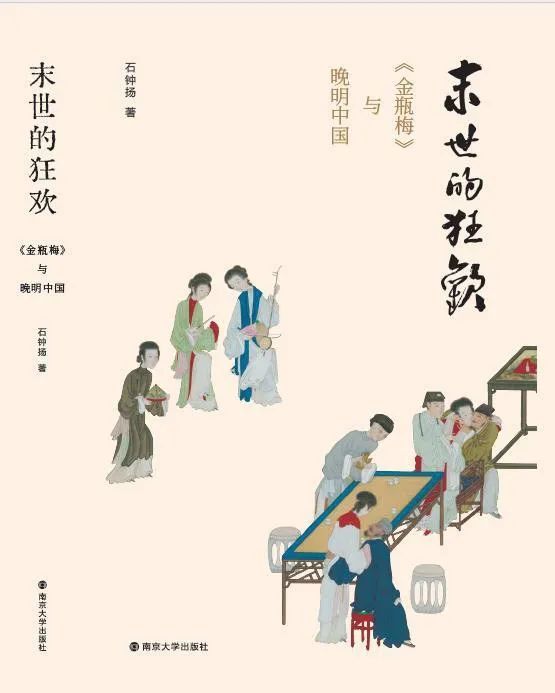潘金莲被“污名化”了吗?
《金瓶梅》锐利清晰,于大千世界无所不包、无所不见,更把人生之鲜血淋漓、丑恶可怕之处一一揭示给人看。学者田晓菲曾评价《金瓶梅》:“《金瓶梅》这部书自己,简直就好像一般人眼里的潘金莲,她的魅力不可抵挡,她的诱惑是致命的。”
然而,在历代批评家那里,作为《金瓶梅》中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潘金莲一直以来都被冠以“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在下文作者石钟扬看来,有一千个读者就该有一千个潘金莲,对于“潘金莲”这样一个复杂而成功的艺术形象,“以骂代评”似乎过于简单了。
《金瓶梅》里的几个主要女性角色,年龄都在二十岁以上,比如潘金莲初遇西门庆时25岁……在以十五岁为女子成年期的古中国,她可算是半老徐娘。然而潘金莲并不甘于自己的身份:“金莲的可爱与可悲处,就在于她既不得不承认作为小妾的地位,而又决不安于那小妾的地位;身为下贱,而心比天高……”
下文摘选自《末世狂欢》,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一、换副眼光看金莲
潘金莲与西门庆无疑是《金瓶梅》中的两大主角,也是全书写得最成功最灵动的艺术形象。要写《潘金莲论》,我提起笔来,却颇为茫然,不知从何下手。因为潘金莲早就以“天下第一淫妇”的骂名被钉在耻辱柱上,供人詈骂数百年:
金莲不是人。(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载于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3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潘金莲者,专于吸人骨髓之妖精也。若潘金莲者,则可杀而不可留者也。赋以美貌,正所谓倾城倾国并可倾家,杀身杀人亦可杀子孙。(文龙《金瓶梅》第二十八、四十一回批语,载于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601、611页)
这是清代人的评论。张、文于《金瓶梅》多有卓见,但对潘金莲的评说却终未摆脱“红颜祸水”的封建男权主义观念。鲁迅不止一次清算这种谬见,先有《女人未必多说谎》,再有《阿金》,皆有高见。仅引后文: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以来,虽说时代不同,而评论《金瓶梅》,尤其是评论潘金莲的男权主义观点,非但没有根本改变,反而似乎是有增无减,甚至愈演愈烈,这也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化领域的一大奇观:“淫妇”“恶毒妇”“妇女中的魔鬼”“西门庆家的女恶霸”“天下第一淫妇”“第一可恶可憎之女人”“催命榜上第一人”“罪恶之花、戕身之斧”……无所不用其极,以至说潘金莲是“一个最淫荡、最自私、最阴险毒辣、最刻薄无情的人”。
国内学者如此固不可原谅,最不可理喻的是美籍华裔著名学者夏志清浓烈的男权主义观念。无可非议,夏氏对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都有精到的研究,以至被国人奉为“经典”。但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第五章《金瓶梅》(单篇译文被冠名为《金瓶梅新论》)中,夏氏将潘金莲定性为“一个非常狡猾和残酷的人物,一个为满足其性欲无所不为的占有性色情狂”,西门庆反倒“是一个做事鬼鬼祟祟,为自己辩解的丈夫,而潘金莲则是个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的妻子”,“她依然保持着对她们公有的丈夫的绝对控制权”,“西门庆是她取乐的工具”,西门庆之死实际上给人的印象是:“他被一个无情无义而永远不知满足的女性色情狂谋杀了。”(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胡益民等译,第194、214-216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版)仿佛从西门庆的死到西门府败落的责任都要潘金莲来承担,已将“红颜祸水”论推到了极致。这令我深为惊诧。
如果没有鬼才魏明伦以“荒诞川剧”《潘金莲》抒发他的异端之见,如果没有美籍华裔女学者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瓶梅》发表了对潘金莲极为慈悲的评说,我真怀疑历史在这里停止了它前进的脚步。或许是“红颜祸水”论裹住了中国男士前进的脚步,因为自明至今,中国“金学”的基本队伍是由男性支撑的。男人们对潘金莲骂声不绝,而《金瓶梅》又曾久禁不止,有学者指出,不少男性在玩弄一种自欺欺人的解读游戏:睁开眼骂潘金莲,闭上眼想潘金莲。虽有些刻薄,却似乎不无昭示意义。
骂不妨骂之,想不妨想之,那是别人的自由。但我认为,对于一个复杂而成功的艺术形象,“以骂代评”似乎简单了一点。骂固然也是一种评论,而且可解一时之恨,却终究替代不了入情入理的审美解读。鲁迅所论《红楼梦》的“读者学”观点,对谈《金瓶梅》人物也有意义。他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全集》第八卷第145页)
可见,读者自身的眼光是何等重要。有道是: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理,有一千个读者就该有一千个潘金莲。而我却希望读者诸君不妨先撇开成见,搁起感情,换一副眼光,心平气和地读读文本,以一颗平常心看看这位潘女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然后再作分解。在了解中同情,在同情中了解,方能持平。
二、当潘金莲来到西门府上
潘金莲一无娘家势力撑腰(如吴月娘为千户之女),二无丰厚的嫁妆(如李瓶儿、孟玉楼皆为富寡妇,即使是李娇儿也从妓院中带来了一笔财富),三无儿子来巩固其家庭地位(如李瓶儿有官哥儿,吴月娘有孝哥儿)。她所有的只是另类的美貌、另类的激情、另类的风月。她是个唯性、唯欲、唯情主义者,舍此种种,别无所有。她以性为命,为梦而生。
世间男女相逢皆讲个缘分。无缘无分不谈,有缘无分,无缘有分,有缘有分,各有千秋,人间多少悲喜剧皆源自这缘分二字。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潘金莲与西门庆本来有缘有分,但金莲却嫌不足,她追求全缘全分,让西门庆成为她的“唯一”,她的“最爱”。这就派生出种种矛盾与危机。这就有许多事故与故事在等待着她。
“奴今日与你百依百随,是必过后休忘了奴家。”——这是金莲与西门庆偷情期间的悄悄话。
“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这是金莲的恋歌《绵搭絮》中的关键句。二者结合,堪称金莲的性爱宣言。
正是在这性爱宣言的鼓动下,金莲不顾生命与声誉,以协杀亲夫为代价换得自由之身,七月三十早晨接到武松的家书,八月初六烧了武大灵床,八月初八即匆匆嫁给西门庆。
聂绀弩曾以杂文笔调写足了封建社会女子出嫁的狼狈情景:
“在过去,一个女人,在三从四德贤妻良母主义之类的教育或熏陶中长大,和一个漠不相识的人订婚,然后离开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像关云长单刀赴会一样,像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一样,像陈丽卿空手入白刃一样,嫁到一陌生的人家,以别人的父母为父母,以别人的兄弟姊妹为兄弟姊妹,这空气首先就令人窒息。
如果母亲家没有势力,随身没有妆奁,自己没有姿色,婚后没有儿女,往往上受公婆折磨,下受小姑刁唆,中受老公嫌弃,一家人站在一条线上与自己为敌,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不能帮助,乡党邻里不能干涉,无异陷身人间地狱,任有天大本事,也离不开,拔不出,摆不脱,丢不掉!这种场合,怕老公还来不及,怕老公一家人还来不及,怎谈得上使老公怕呢?这种老婆,真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聂绀弩《论怕老婆》,《蛇与塔》第7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1月版)
这当中仅两点与潘金莲的情景不同:
其一,西门庆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金莲却并非无姿色;
其二,金莲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并不怎么怕老公。这样,她从武大那简陋的窝巢进入西门庆这深门大院,并无多少陌生感,她很快就融入西门庆的妻妾群落,并成为其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第十五回写到西门府上第一个元宵节,在“佳人笑赏玩灯楼”中,金莲是何等天真烂漫:
吴月娘看了一回,见楼下人乱,就和李娇儿各归席上,吃酒去了。惟有潘金莲、孟玉楼同两个唱的,只顾搭伏着楼窗子,往下观看。
那潘金莲一径把白绫袄袖子儿搂着,显他那遍地金袄袖儿;露出那十指春葱来,带着六个金马镫戒指儿,探着半截身子,口中嗑瓜子儿,把嗑的瓜子皮儿都吐落在人身上,和玉楼两个嘻笑不止……
引惹的那楼下看灯的人,挨肩擦背,仰望上瞧,通挤匝不开,都压儿……
更令金莲欣慰的是,她与西门庆“二人女貌郎才,正在妙年之际,凡事如胶似漆,百依百随,淫欲之事,无日无之”(第九回)。为了西门庆的欢快,金莲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痛快痛快,先痛后快,不痛不快,为快不惜其痛——这或许是金莲获得性爱快感的轨道。
她不辞用樱唇品箫,以香腮偎玉,甚至替西门庆咽溺(第七十二回),或装丫头市爱(第四十回),因听得西门庆在翡翠轩夸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欲夺其宠”(第二十九回)。
每见西门庆到自己房里来,金莲“如拾金宝”(第三十三回),或如“天上落下来的一般”的欢欣。在床笫上金莲每每“恨不的钻入他腹中,在枕畔千般贴恋,万种牢笼,泪揾鲛绡,语言温顺,实指望买住汉子心”(第三十九回)。
“潘金莲醉闹葡萄架”,“险不丧了奴的性命”——虽备受西门庆淫具所带来的皮肉之痛,但回到房中金莲仍“云鬟斜亸,酥胸半露,娇眼乜斜,犹如沉醉杨妃一般”,令西门庆“淫思益炽,复与妇人交接”,“二人淫乐为之无度”(第二十八回)。
这里的“淫乐”或许应读为欢乐。因为在《金瓶梅》中“淫”并非全为贬义,至少西门庆每每笑骂金莲等“淫妇”“小淫妇”“贼小淫妇”“怪小淫妇”,多为特定情境中的昵称,非谩骂;潘金莲称西门庆“怪行货子”“贼强盗”也多属此类。潘金莲堪称“新新人类”,她超前地用身体,乃至用下半身书写着她生命的进行曲与交响曲。
三、“强人之妾”的爱情难题
然而,无论金莲如何全身心投入,对西门庆做爱的奉献与性的满足,她都被置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境之中。
与当初在武家比,如今金莲所面对的是一个强悍的男人,不像武大那么懦弱;她在西门府上是妾,而且是排名第五位的妾(故称“五娘”)。尽管她当初身为一个懦夫之妻很不开心,但如今身为一个强人之妾也更有许多想象不到的难题……
西门庆妻妾队伍中或许只有金莲,不仅“整个身心地奉献”给她心爱的男人,同时奢望全额地获得对方爱与情与性的回报。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在丽春院半月不归:
丢的家中这些妇人都闲静了。别人犹可,惟有潘金莲这妇人,青春未及三十岁,欲火难禁一丈高。每日打扮的粉妆玉琢,皓齿朱唇,无日不在大门首倚门而望,(按,词话本为“每日与孟玉楼两个……”此本去孟玉楼更显其为“唯一”也。)只等到黄昏。到晚来归入房中,单枕孤帏,凤台无伴。睡不着,走来花园中,款步花苔。看见那月漾水底,便疑西门庆情性难拿;偶遇着玳瑁猫儿交欢,越引逗的他芳心迷乱。
此情此景,是何等动人。谁说《金瓶梅》是一片污秽,其实它每写到金莲几乎都有锦绣文章好读,就怕你无耐心欣赏,只是走马观花,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对其间的花——锦绣文章视而不见,那也只得徒呼奈何。
言归正传,生活是何等作弄人,金莲当初配武大则浩叹命运不公,而今跟了个“白马王子”——用金莲的话说是“俊冤家”,又不免管他不住,处处潜伏着危机。
其实就在搞定武大问题的当天,金莲就急切地对西门庆说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到后来‘网巾圈儿打靠后’。”西门庆道:“这个何须你费心。”金莲仍不放心地问:“你若负了心,怎的说?”西门庆道:“我若负了心,就是武大一般。”(第五回)
多不吉利的话,但此时他们已别无选择。从此,担心男人负心成了金莲生命的焦点。他们尚在恋爱期,就因西门庆的失约,让金莲痛苦不堪,既有热望,又有咒誓:“你若负了奴的恩情,人不为仇天降灾”,“你如今另有知心,海神庙里和你把状投”(第八回)。进入西门府后,金莲不屈不挠地为获得专爱而继续斗争。
第三十八回“潘金莲雪夜弄琵琶”,前文我是将之作为金莲才艺来写的,而这实则是一支失恋者之歌,其关键词是多段反复吟唱的:“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张竹坡说:“潘金莲琵琶,写得怨恨之至。真是舞殿冷袖,风雨凄凄。”我则认为这首失恋者之歌,是一种生命的呼唤,写得哀婉动人,岂是“怨恨”二字所能表达。
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剧虽千姿百态,大抵有两大类:或由父母之命造成的悲剧,或由男儿负心造成的悲剧。金莲屈嫁武大,是父母之命造成的悲剧的变种。进入西门府后,金莲却时刻担心陷入男儿负心的悲剧。平心而论,西门庆也并非彻底的负心男儿,他虽有官场、商场、交际场上诸多事儿要应付,仅就情爱而言,他与金莲之间的缠绵已够充分了。
如意儿作为权威性的旁观者,曾说:“我见爹常在五娘身边,没见爹往别的房里去。”(第七十四回)西门庆自己也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
即使到了别的房里,西门庆也往往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有次金莲与月娘口角,难以平衡,西门庆只得两处都不留宿,去了李娇儿房中,事后他向金莲解释:“昨日要来看你,他(吴月娘)说我来与你陪不是,不放我来。我往李娇儿处睡了一夜。虽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第七十六回)“乖乖儿,谁似你这般疼我?”(第七十二回)“我的儿,你会这般解趣,怎教我不爱你!”(第十回)
西门庆的此类赞词,只献给潘金莲,其他妻妾从未获得他如此之激赏。
因为“金莲也是唯一对西门庆有激情的。她和西门庆的关系,打闹归打闹,似乎相互之间有某种默契,只有她一个人和西门庆亲密到开玩笑、斗口(不是吵架)的地步。时而骂他,时而哄他,时而羞他,时而刺他,西门庆也只在她面前才谈论与其他女人的风月事。她是西门庆的知己(唯有奴知道你的心,你知道奴的意),论其聪明泼辣,也堪称西门庆真正的‘另一半’”。(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第40页)
四、《金瓶梅》:写妾的书
旁观者都认为西门庆将金莲宠得发狂,而金莲却是“情重愈斟情”。她无杨贵妃之命,却有杨贵妃之志:“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西门庆虽无三千佳丽,却也是妻妾成群。金莲几乎无视成群的妻妾,而欲西门庆专宠于她,不许肥水流入他人田。这样她势必与西门庆、与其他妻妾都会构成矛盾。
就西门庆而言,他虽爱金莲,却性趣广泛,还有广阔田野等待着他去灌溉,岂能专宠金莲;就其他妻妾而言,都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去夺取西门庆的“力比多”,又岂容他专宠金莲?
以往的评论多责备潘金莲好淫,其实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有二:
其一是封建家庭的封闭状态。即使是武大家也要关门闭户,窗上悬帘,以防户内春光泄露。西门庆成群的妻妾更是被圈养在庭院之内,偶尔有个元宵看灯、清明秋千、喜庆赴宴就是天大喜事,众妻妾在家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除了打牌、闲唠、斗口之外,则无所事事。诚如聂绀弩所云:
“家庭的天地是窄狭的。长期生活在那窄狭的天地里的妇女,眼光或器量都不能不是窄狭的。家庭里的妇女,往往只作为男性的性的对象而存在。她们自己也俨然以作为男性的性的对象为统一的职业,性生活几乎就是她们的生活的全部,这样的妇女是有时会玩出种种花样来的。”(聂绀弩《贤妻良母论》,《蛇与塔》第61-62页)
其二是一夫多妻制,准确地说是妾媵制度下的家庭结构。对于封建社会的妾媵制度,就我的视野所及,数舒芜的《〈红楼梦〉里的妾媵制度》讲得透彻而形象……
在“妾”的范畴内又分几等,最高的一等是“二房”,第二等的是“姨娘”,最低的是“通房丫头”。“通房丫头”完全没有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只需主人“收用”,不用任何仪式。作为妾的女奴隶,其主要任务毕竟已经不是一般的服役伺候,而是对男主人作性的服役了。
这样丈夫方面,事实上还是多妻,既可以无限地纵欲,尽量地繁殖,还可以仗着妻与妾之间被规定的“嫡庶”关系亦即主奴关系的制度来限制和调节她们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借以使自己摆脱或减轻困境。
妻子方面,其地位和权利既得到一些保证,她也就必须对丈夫以及丈夫的宗族负担一系列的义务,首先是必须容许丈夫纳妾,同丈夫的妾搞好关系,以及主动积极地替丈夫纳妾,特别是在做妻子的不能替丈夫生儿子的时候,赶快替丈夫纳妾更是天经地义。
(舒芜《哀妇人》第649-66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舒芜是以《红楼梦》为形象资源来分析清代妾媵制度的。清承明制,以清推明,大致不差。
由此可见,其一,金莲在众妾队伍中排行第四,只能属于“姨娘”之列,若“姨娘”一律平等,那她于妾辈地位在李娇儿(其为二房)之下,春梅之上(其为通房丫头,准妾,相当于《红楼梦》里贾琏房中的平儿,宝玉房中的袭人);若“姨娘”也要排座次,那她的地位还得下降到三房孟玉楼、四房孙雪娥之下。所有妾都是西门府上的女奴隶,金莲也不例外。
其二,吴月娘对西门庆纳妾几乎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说“几乎”是指她对西门庆娶李瓶儿有些疑惑:
第一,她孝服不满;
第二,你当初和他男子汉相交;
第三,你又和他老婆有连手,买了他房子,收着他寄放的许多东西。(第十六回)总之怕有官司牵连。
西门府内妻妾的分工也是等级森严的:“家中虽是吴月娘居大,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来往。出入银钱,都在李娇儿手里。孙雪娥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譬如西门庆在那房里宿歇,或吃酒或吃饭,选甚汤水,俱经雪娥手中整理,那房里丫头自往厨下去拿。”(第十一回)
李娇儿因房中丫鬟偷盗而卸职,继任的孟玉楼因避嫌而辞职,这才轮到金莲权管些时日。但真正重头钱财还掌握在吴月娘手中,如亲家陈洪与李瓶儿转移过来的大宗财物都始终收藏在吴月娘房中。众妾固然属于西门庆,又都是正房吴月娘的奴隶,所以金莲曾对吴月娘说:“娘是个天,俺每是个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秃扠着心里。”
由此既能看清金莲与吴月娘关系的实质,也能知道为什么西门庆死后吴月娘有权将妾们卖的卖、嫁的嫁。
其三,西门庆对妻妾的态度有本质的差异。西门庆对吴月娘虽不怎么爱却不失起码的尊重;西门庆对众妾尤其是金莲虽“爱”,却并不怎么尊重。西门庆曾与“红灯区小姐”李桂姐夸耀:“你还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这几个老婆丫头,但打起来也不善,着紧二三十马鞭子还打不下来。好不好还把头发都剪了。”(第十二回)这里的“俺家房下”指吴月娘,“老婆丫头”指几位妾妇。她们的地位高下已说得很清楚了。
有次金莲与玉楼正在下棋解闷,西门庆从外面归来,见她俩打扮得“粉妆玉琢”,不觉满面堆笑,戏道:“好似一对粉头也,值百十两银子!”以妓女(粉头)的价格为标志来夸奖自己的小妾,何其不伦不类!这正暴露出西门庆在心灵深处对爱妾的评价不过尔耳。因而惹得敏感的金莲反唇相讥:“俺们倒不是粉头。”
有时家中议事,金莲在旁发表点与众不同的意见,不中西门庆的意,西门庆不去评论她的意见本身有什么不对,而是从根本上剥夺她的发言权:“贼淫妇,还不过去!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甚么说处?”(第四十一回)西门庆与吴月娘亲热也好,闹矛盾也好,从无此等言行。
即使在床笫,西门庆与吴月娘的行为从来就是“规范”的,虽乏激情,却不荒唐。至于淫具与春药也少见用之于上房正室,而在上房正室之外却大发淫威。在作者看来,金莲对西门庆无所不用其极的爱的奉献与性的投入,实为妾妇之道……
近代怪杰辜鸿铭晚年既有小脚娇妻姑淑,又有日籍美妾吉田贞子。他曾无遮无掩地炫耀说:“吾妻姑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贞子,乃是我的‘安眠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适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第341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2月版)
就功能而言,金莲对于西门庆来说或许既是兴奋剂,又是安眠药。而西门庆所谓爱金莲,充其量也只能到达这个分上。辜鸿铭只一妻一妾似易和平共处,西门庆一妻五妾就难处得多。金莲的可爱与可悲处,就在于她既不得不承认作为小妾的地位,而又决不安于那小妾的地位;身为下贱,而心比天高,岂能相安无事?
《金瓶梅》是天下第一部写妾妇生活的长篇小说……其实妾的生态、妾的心态、妾的命运与妾的挣扎等,所构成的妾文化,其影响未必仅见之于妾。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的历史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往复循环而已。奴隶与妾有何区别呢?如此说来,妾的生态、妾的心态与妾的挣扎难道就不见于须眉男子之身吗?有些大老爷若落到“妾”的地位,其形象未必比金莲们见佳!
男人世界,人有十等;女人世界,也是人有十等。鲁迅有云:“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鲁迅《灯下漫笔》,邓珂云编《鲁迅手册》第151、152页,上海:博览书局1946年10月版)
本文节选自
《末世狂欢:〈金瓶梅〉与晚明中国》
作者:石钟扬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