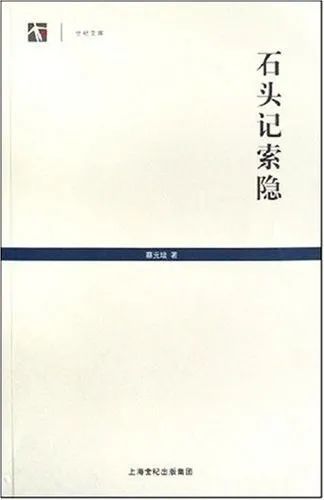不必读懂李商隐,也不必读懂现代诗
李商隐的诗歌以文辞晦涩、意韵深微著称,比如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锦瑟》,其内容美丽、深切、缠绵、深沉、隐秘……但除了这些朦胧暧昧的情绪,我们可能依然不知道这首诗到底在写什么。
在作家张炜看来,“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在表达方式上离得最近的,可能就是李商隐。”我们读不懂李商隐的《锦瑟》,恰如我们读不懂许多现代诗。不过我们也根本不必追求读懂它们:“诗无解,则以心化之,自我消化”。
下文摘选自《唐代五诗人》,经出版社授权推送。
“《锦瑟》已成为李商隐的代名词”
《锦瑟》是李商隐最有名的一首诗了,而它又是如此晦涩;但它最终从文学专业人士到一般社会文化层面,渐次洇染并广泛流传开来。不过即便是这样,市井与乡间仍旧少有人知,可见至今没有抵达俚俗。艺术的产生与传播关系之有趣,既难有定规又似乎遵循某种常理。在一部分人这里,《锦瑟》已成为李商隐的代名词,一想到“锦瑟”二字,马上在脑海里出现一个相对固定的诗人形象:或风流倜傥,或英俊潇洒,或柔弱腼腆,是这样诱人的想象。实在一点说,文学成就与社会层面的影响,一般来说不仅没有等值关系,甚至许多时候还恰好相反。深刻难解的文学与思想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表现出超常的复杂性,它需要相当多的条件与机缘才能与大众沟通。
就李商隐来说,即便是文化人,虽然普遍知道他的名字,但大多数人仍然不太知晓他的艺术,不能进入更具体的内容,深入领略其特质。这正是因为他的深邃,原本正常。他为文化人所知晓和关注的主要因缘,往往还是因为这首《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都说读不懂。但是看上去真好。局部的意思是懂的,连缀起来就“惘然”了。现代自由诗也常有这种情形,意象转换频繁而恍惚,想要弄个一清二楚是不可能的。这有点像欣赏交响乐,要将声音旋律切换为具体的视觉目标和思想意义,总是困难的。这样的文字有可能是高级的艺术,也有可能不是。但《锦瑟》显然是高级的,为什么?因为直觉告诉我们,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因为它让我们入迷,千百年来吸引了无数的人,大家深深地喜欢它。
它是如此美丽、端庄、深切、诚恳、缠绵、深沉、隐秘,以至于伤感。就其组合的字词本身而言,已经是足够华丽了,如锦绣绘满琴体,弦柱锃然挺立,丝弦交织;蝴蝶和春心,珠泪和玉烟;一个睹物追思之人,一个万千话语无从说起之人;沧海月明,蚌在深处,珠泪晶莹;蓝田氤氲,玉烟袅袅;涟涟如珠耀,朦朦似玉晕。诗无解,则以心化之,自我消化。
宫妓调琴图 周昉(仿) 唐代 绢本
这首诗不仅是千余年之后的现代人,即便是古人,那些领悟力极强的天才们也似乎不能确指。比如宋代诗人黄庭坚读此诗不晓其意,请教苏东坡,对方解释说:
“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宋·黄朝英《缃素杂记》)
这里是否为东坡之原话原意,已无可考。但就记载来看,此解反而通向了更幽深处,使它越发玄妙而难于言传。其“适、怨、清、和”四字,需要多么细微的感受才会获得。这里边需要审美者具备的条件实在是太多,除了人生深度、生活阅历之类的相助之外,还需要写作学和诗学方面的知识来参与化解。实际上,像领会音乐一样读诗是必要的。这种无解其实正是一种大理解。
宋代刘邠的《中山诗话》说:“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这就有点过度、过于具体地诠释,反而使诗意变得狭窄。还有人将其批点为失恋诗、悼亡诗、政治诗,或者是情感追忆,或者是哀叹落拓的命运。总而言之,各种各样的想象与评说都有,难成共识。这恰是此诗意象奇妙、幽境迷离的魅力,甚至是其价值之所在。
高逸图全卷 孙位 唐代 绢
如果像一部分人那样通过索隐、考证获取所谓确指,而且言之凿凿,就变得可怕了。最可怕的是追究作者身世遭遇,具体地对号入座,一切也就全完了。诗不是这样的,艺术往往不是这样的。艺术固然有使用性、工具性,但它是归向心性和灵魂的,不是一般的世俗的使用。有些作品的缘起也许来自具体的社会物事,但是创作者由此开端起步,抵达了一定速度之后就开始飞翔。那个时候他的能指就变得高阔了,与起始之时的具体目标拉开了不知多么遥远的距离,甚至于从创作者最初的具象铺展到连他个人都感到陌生而繁复的领域。它的多义性、费解性缘此而生,其深度和晦涩度纠缠一体,一件艺术杰作的高妙清绝,由此开始达成。
有人在分析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时候,曾经给予了极实在和极具体的成因解释:将音乐开始的旋律,即所谓命运之神的敲门声,解释为艺术家面对上门索要欠款的讨债人的烦躁敲门而做出的回应。把音乐充分生活化世俗化,而且讨债人还有名有姓,佐证确凿。但这又能说明什么?这真的能诠释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之实际?能说明他关于命运的沉湎、联想和探究?能让这首雄浑壮美的旋律变得浅显易解?完全不能。声音的洪流,思绪的洪流,想象的洪流,席卷而去,由一个斗室涌向街头,涌出德意志,涌向了一个未知的时空。未来仍然需要继续这场盛大的演奏,一再重复的迎候、接受、聆听,有仪式,有众多的参与。它达成共识的时间还非常遥远,这个时候它的发端就显得完全不重要了。
李商隐的大量诗文有各种色彩与意义指向,尽可以欣赏和揣摩。但其最突出的光泽就如这首代表作一样:华丽。抓住了华丽就抓住了重要特征,这既是表象又是本质,然后再论其他。有人可能更注重其“伟大的社会意义”,比如揭示和记录,还有反抗和呼吁等等。这可能都是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人们普遍喜爱他并引用他、记住他、得益于他的,仍旧是什么、主要是什么,大概不言自明。清代陆次云在《五朝诗善鸣集》中说得至为精彩:
“义山晚唐佳手,佳莫佳于此矣。意致迷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于初盛诸家中得未曾有。三楚精神,笔端独得。”
永乐宫壁画 佚名 唐代
“李商隐的诗歌最接近‘纯诗’”
纵观唐宋元明清以来,文学,特别是诗的走向,大致还是通向了“现代”。这个“现代”不是一般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艺术划分的概念。有人会认为现代汉语的自由诗直接就是从外国诗翻译而来,是伴随着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一起走入东方,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是白话文运动的结果。这样说原本不错。但我们也不能否认,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多少还是支持了现代自由诗的,多多少少应该是这样的。这需要我们于静处默默倾听,于文字间仔细体味。如果说现代诗歌艺术中传统全无,这怎么可能?如果说古代诗章对现代散文乃至于小说发展起到了作用,而唯独越过了现代自由诗本身,这恐怕也说不过去。于情于理,皆未能合。
实际上古诗之意象表达,音乐性,通俗性,或它的反面即晦涩性,已经在时间里不断发酵,早就被现代自由诗作为营养吸收了。当我们对这个过程进入具体分析,探究汉语诗史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人对此做出了最大贡献,他就是晚唐的李商隐。他想象自由如李白,却又比李白晦涩了许多。在意境营造上,他如李贺一样冷艳诡异,但又比李贺温润明媚。他真是自我之极,对诗对心,对灵魂,对生命的快意和隐秘,极端专注,许多时候并不在意向外的传达。有些诗作连朋友也不给看,只是为了记个心绪,记个感觉,记个隐情,没有说处。当然许多古诗产生之机缘、产生之状态,也都如此。李商隐在这方面做到了极处,他的诗作从诞生缘起到去向归处,与许多人仍有不同,在数量和程度上,都具有某种指标意义。它们并非总是歌时代之欣、吟时代之痛,而是指向个人,指向自己内心,恍兮惚兮,窈兮冥兮。这也拿他没有办法。人早就不在了,责备他也没有用。所以还是要直面文本,学习其好的方面,汲取营养。
“紫府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碧城三首·一》)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无题二首·二》)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一》)
这些诗句如何作解?它们实在是迷离杳渺,不过还是那两个字:华丽。清代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中说:“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冯浩对李商隐多有诠释,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文字。他认为“实有寄托者多”,而“直作艳情者少”,所以也就做出了许多社会政治方面的解释,有时未免极端化,仍然属于过度诠释。偏向社会物事和偏向艳情,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过于直接、狭窄和具体。他们忽视了文字的实际功能与艺术神秘的飞扬想象之间的区别,有时二者之间相距遥远。
京畿瑞雪图 李思训 唐代
诗性是酿造而来,而酿造是一种复杂的转化,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其最终结果不可以逆向还原。这里的晦涩多解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呈现。当然晦涩也是各不相同的,故弄玄虚非牛非马,感觉落不到实处的,那不是真的晦涩,或者说这种晦涩廉价而无聊。而当一个人要表达的内容意蕴与思想情愫极为微妙难言,非直白形式可以抵达者,写出来也就费解了。这种难解是朴素和诚实的结果,这个结果才会是有意义的。我们会在心理体验中感悟,在无以言表的情感与经验中抵达,欣赏和喜爱。对李商隐的许多好诗,我们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认可,才推崇。
他的一些无题诗真是棒极了。没有这些“无题”,就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李商隐,研究唐代文学史也就不会为他开专章,因为人们会少一些兴趣。兴趣于艺术非常重要,这在古代和现代都一样。一些具有“伟大社会意义”的作家,一旦离开了具体的“社会”需要,人们也就不再感兴趣。众所周知,一旦事不关己,也就高高挂起。
一般来说朦胧不是优点。如果朦胧来自诚恳和朴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来源。陈寅恪曾说,李商隐的诗歌是最接近西方所谓的“纯诗”。此言一语中的。这里的“纯诗”,是指任何其他文字表述形式都不能取代的那种极微妙的生命情愫。而中国大量的古诗,包括那些万口传诵的所谓名篇佳句,有些并不属于这种“纯诗”。它们是非常实在的说理与记述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写作方式所取代。我们所感受到的不可诠释的唯美的情致、意蕴、韵味,即所谓意境,那种“不隔”,那种豁然诉诸感觉的气息、温度、色泽,皆来自诗中那些极为纯粹的表达。这是诗的特质。我们离开诗的特质去谈诗的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而我们一部中国古诗的诠释史、赏读史、评述史,其中有许多“隔”,是语无伦次,漫无方向,无涉要害的分析和鉴赏。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在此可以不论。
说到古代朦胧诗人,人们马上会想到李商隐,可见这正是他的重要价值。这种朦胧不仅是美,也不仅是谜,更有深刻在,包括艺术的、思想的、社会的、人性的诸多方面。这种朦胧包含得太多,信息量太大,所以就有了更大的价值。
现代诗人与古代诗人,在表达方式上离得最近的,可能就是李商隐。
宫女浴孩图卷 周昉 唐代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强力索隐,不仅荒谬,而且无聊”
读商隐诗,自古至今存在一种“大方法”,就是要从根上将它的奥秘拆解,让谜语一点点化解。时间离诗人越来越远,难度也就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工作也就越有难度;而越有难度,诗人的魅力也就越是增加。这种研究工作似乎变得更复杂了,用鲁迅的话说,即“战斗正未有穷期”。
可是奥秘当有多种,既可以是艺术本身,也可以是艺术之外。有人说艺术总是内外关联,搞懂其外,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内。比如把一首诗的创作背景搞明白就非常重要,由此可以得知诗人的创作初衷,即到底为什么要写这首诗。此种想法貌似有理,能够说得通,但仔细想一下,实在是过于天真,甚至还有点可怕,非常令人担心。
从过去到现在,在我们文学艺术的研究传统中,考证派和索隐派实在是太多,所以就有了太多的可怕。虽然不能完全否认它们的作用和效果,但大抵上要有足够的警戒。比如对李商隐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些人为了猎奇,在考证无题诗或内容晦涩之作时,竟然编织出大量荒唐离奇的三角恋和风情故事,还有人竟然挖空心思地推理出诗人的四种恋爱对象,即女道士、宫女妃嫔、妻子王氏、官家歌妓和女眷。比如诗集中有许多涉及玉阳山学道的诗篇,便从中考证出有一位道士是诗人的情敌,甚至从李商隐近六百首诗作中考证出二百七十首“恋妃诗”,而所恋者竟是唐文宗的歌舞嫔妃飞鸾、轻凤姊妹等。这真是荒唐至极,令人怀疑一个为学术者之用心。
这让我们想到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些公案和事端。有人对鲁迅就不乏这种刻薄,或者说用此类褊狭和低劣的用心加以中伤诋毁。这些文字离我们更近,展读之下令人厌恶。二者何其相似乃尔。艺术、学术当然不可以过于道德化,但作为一个从事者,其文字必然会留下供人评说的道德空间,走入这样的不堪之处,实在可惜可怜。
索隐不是没有用处,完全抹杀索隐之功是不对的。比如《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代表人物蔡元培,他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明确提出:
“《红楼梦》中所有种种之人物、种种之境遇,必本于作者之经验,则雕刻与绘画家之写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
“苟如美术之大有造于人生,而《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其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
这里所说的艺术审美之“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后可”,综合了想象力与创作者人生阅历、作品缘起之间的关系,这种论说自有其价值,也贴近实情。类似索隐,从目的到结果都有一定价值,所谓知人论世,是论艺术不可偏废之功。
《石头记索隐》蔡元培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 2008
在哪个方向和方面使用索隐功法,是问题的要害。如果只抓住文字中的某些局部,如只言片语、某个人名地名,某段微细的表述、某件器物、某首诗词等,将其与历史人物对号入座,类似猜谜般从中捕捉,这种考证方法实际上必然要牵强附会,有百害而无一利。从“红学”研究诞生之初至今,索隐派红学家们抛出了多少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是兴味未减。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索隐,从曹植的《洛神赋》到李商隐的“无题诗”,从《红楼梦》到《金瓶梅》,从诗歌到散文小说,皆是如此。不仅荒谬,而且无聊;不仅无聊,而且对一代又一代的赏读者,对那些享用艺术者,产生严重的干扰和误导。离题万里,言不及义,所害甚大。
一些貌似曲折严谨却不乏窥视癖的学术达人,所谓“术业有专攻”者,实在是非文学的帮闲人士。强力索隐,对号入座,不仅在特殊年代里可以将作者置于死地,而且还有其他大弊。在平和时期,索隐也许对作者的日常生活无大害,却能将其艺术置于死地。在这种索隐之下,那些光华四射的天才想象会成为机械的操作与编织。他们索隐考证,推敲不已,顺藤摸瓜,似乎有理有据,其实完全不得要领。语言艺术在这些人手中变成了僵死之物,化为密码和符号。它们通向的不是无限的诗境,而是具体的社会环节、人物事件和个人隐秘。如果文学艺术是如此简单,那根本就不需要审美,不需要审美的感悟力。那些难言之趣、之意、之美,原来靠机械的量化、靠换算即可完成。那么在网络数字时代,在电子计算技术空前繁荣、未来不可预期的前景之下,审美也就彻底死亡了。
所以说,对艺术作品的强索隐,其实大可休矣。索隐对于艺术家和作品而言,还是粗略一些为好,掌握一个度,适可而止。只有这样,才能客观深入地欣赏,才能够进入真正的艺术之境。如果总是挂记作者因何事而喜而怒而悲,就将力气用歪了。如果艺术作品那么直接而裸露,即不需要艺术,直接写颂扬书、呼吁书、揭发信或检举信即可。有人说艺术品之所以曲折,或因为作者胆子小之故,于是才会产生各种谜团:需要运用各种曲折之笔来遮掩真实意图,通过比兴、隐喻、象征、寓言等手法,来完成表达。那么既然如此曲折、隐晦,曲折隐晦到什么程度,也就只好由诠释者来鉴定了。这样的鉴定者越是权威越是可怕,如果他们指鹿为马、化虚为实、别有用心,如果他们完全为了满足一己之私,那结果又会如何?
真正的艺术哪里会是强力索隐者所能理解。这是一个飞翔的精灵所为,只有一个相应的精灵,才有资格伴飞。
是的,审美的过程就是一次又一次的伴飞。强索隐,是面对极其复杂的艺术审美,表现出的无能和胆怯。艺术是粮食酿成的酒,索隐者一定要把酒再变回粮食,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审美力的缺失,最后的尴尬就是在艺术之外格外用力。按部就班地逐一对号入座,会对艺术造成极大伤害,并误导许多初入门径者。
丧失了诗性的感悟力,再多的窥视和强拉硬扯,也只能走到艺术的反面。
本文节选自
《唐代五诗人》
作者:张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