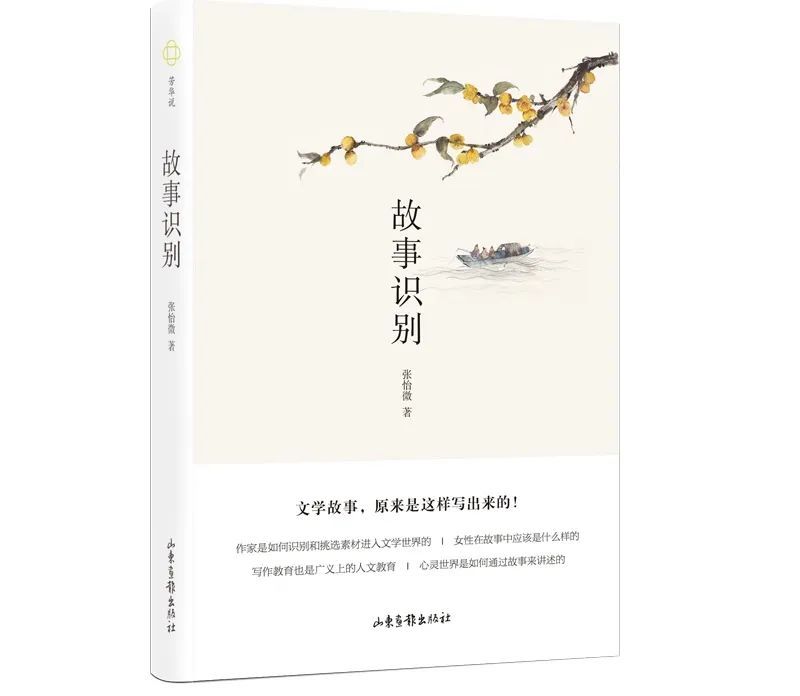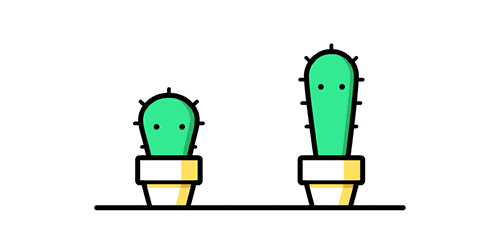“后来我再也没有交过像我12岁时那样好的朋友了”
经典文艺作品中,总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友谊线。如《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又如《古惑仔》里的洪兴五人帮,抑或《鹿鼎记》中的君与臣……《教父》中有一句台词,“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谊”,这句话的正确性我们不得而知,但的确,男人之间的友谊似乎更轰烈,更有团体感,更显江湖义气。
张怡微在《凝聚的渴望》一文中,就十余部经典文学、影视作品对于男女友谊塑造的差异,以探讨女性友谊的独特性,比如“女性友谊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再向闺蜜发出共同受难的邀约”,“人们一直认为女人的交谈无足轻重或是自我放纵……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我们的力量之一,而非弱点之一”,并且期待在生活与文学中,都找到能使女性产生“凝聚的渴望”的关键力量,因为“好的友谊,一定会使人共同成长、共担风雨,也能共享福乐”。
下文摘选自张怡微新书《故事识别》,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凝 聚 的 渴 望
——论女性友谊的书写
一
女性友谊的诞生
在近三年的写作教学观察中,涌现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青年写作者似乎总说不好友情故事,又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学员都是女性,女性友谊的呈现成了一个创作难点。有几方面的原因可能形成了讲好友谊故事的阻碍:
1.家族有姐妹,一般而言血缘关系比非血缘关系牢固,打发时间的需求可以满足;
2.利益平衡/争夺是任何关系的试金石,年轻创作者缺乏参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实际经验;
3.消费主义对身份认同焦虑的影响。
许多学生反映,友谊故事很难写。尽管“结交最好的朋友”是青春前期儿童同辈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童年自觉“争取”友谊的努力在写作中却很少发挥出良好的情节功能和叙事潜力。在大部分故事里,友谊的言说方式既没有发挥以儿童之眼看世界的优势,也没有展示性别差异的叙事功能。
要在中国故事中寻找一些友谊书写的范例,最容易联想到的依然是经典名著《红楼梦》,因为《红楼梦》里人多、女性多。然而,仔细研判后我们会发现“富贵场”“温柔乡”几乎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家族身份的认同更体现为“人在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大观园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体系,少男少女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参与到的,是借由身份进入的阻力最小的路。
欧丽娟教授提醒我们,在《红楼梦》的神女谱系中,警幻给男性的帮助是“启悟与解脱”,在点化过程中她还会积极介入给予帮助,试图改变他们的命运,但小说不断暗示着读者,“女性”,即使是优秀女性,所面对的都是悲剧的命运,其中没有人为努力的空间,也就没有扭转命运的机会 。
《红楼梦》中的女性群像
在当代文学中,作家苏童也写了不少女性(友谊)故事。王宏图教授曾经和苏童做过一个访谈,问苏童“怎么看待女性命运?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的困境是男人和男人的文化造成的;但也有人出来反驳这种观点,他们认为男人也是某种社会体制和结构的受害者,他们拼命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女人的欢心,女人也沾了男人的光,间接的得益匪浅。你对女人的基本看法是什么?”这当然是非常学院派的问法,苏童回应说,
“我从小便觉得女人命苦,这主要是外婆留给我的印象……我的作品中女性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她们受到了伤害。如果问到底是什么伤害了她们,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国家机器,或者传统的文化。然而,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我认为关照女性在小说中的功能时,我要凸显她作为女人本身的这个问题,这是文学应该关注的问题。”
作为映照可以看到男性视角在女性关系书写中的潜在意图,即女性命运的悲剧性在小说里是如何呈现的——呈现为,“帮不了”。作家看到了她们的聪明、美丽,也看到了她们挣扎、损害,可惜的是,“没有扭转命运的机会”。这可看作是一类女性故事书写的潜意识。本文无意讨论文学研究中的性别议题,相反性别在此将会是一个较为棘手的分别方式,因为它并不会解决青年写作者为什么写不好友谊故事的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写作的困难本质上反映了创作者对于“友谊”命名的困难。说起来很稀奇,因为我们想当然认为每个人都有朋友,女性日常社交的朋友数量会比男性更多,但要说清楚友谊形成的过程却比较麻烦。“有朋友”却不一定有完整的友谊故事,日常友谊的延续不是以故事的完整性作为支撑的。生活中的友情可以是没有情节可言的,但小说里的友情却少不了要有情节的需求。这是写作的难点,也是创造的乐趣。
它对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于友谊故事来说,什么是“关键情节”。在这一点上,男性友谊的论述非常值得参考。如河合隼雄在《大人的友情》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颇为小说化的指标:
“所谓朋友,就是半夜12点开车来,后备厢里装着一具尸体,问你该怎么办时,都会二话不说地帮忙想办法的人。”
河合隼雄认为,这一具体例子可以化为平常说的,“不管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情”“不管你做了多么恶劣的事情”“二话不说”“帮忙想办法”……这意味着彼此拥有深厚的信赖关系。又如小说《围城》,方鸿渐与赵辛楣的友谊起源于他们同时喜欢上了苏文纨但都追求失败,这也会结成深厚的男性友谊。其他事件如借钱、托孤、为别人坐牢等指标化的情节虽然通俗,却十分具有说服力,会让读者相信忠诚、团结、信任是有价值、有力量的。然而在女性友谊故事书写中,这样的例子就很稀缺。因为“耐心倾听陪伴”这样日常生活中女性友谊的建构方式,很难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有效推动故事的展开。本文关切的问题在于,能否通过理性爬梳“友谊”故事建构的过程中,发现更多的复杂欲望,并照亮一些新的写作契机,和女性写作的优势。
二
“友谊”的命名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中曾定义“友爱”,他认为
“(友爱)是一种德行或包含一种德行。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因为,即使享有所有其他的善,也没有人愿意过没有朋友的生活……关于友爱本身的性质,人们有许多不同意见。有的人认为,友爱在于相似。另一方面,有的人则说,相似的人就如陶工和陶工是冤家。”
他将友爱提升至公正、共同道德、共同体同样的高度,让“共同”这一关键词在友爱关系中成为核心。我们的四大名著中,有两部男性故事表现了类似的友谊观念,《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对于“共同利益”的描绘就很精彩。让我们确认了关于中国式“友谊”的大众常识,即“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诺千金。以至关羽在曹操手下时,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情义至深,曹操只能表示敬佩。
《三国演义》中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
作为映照,我们却很难用一句话说明《红楼梦》或《红粉》中的女孩们的共同利益到底是什么,她们互相教育的诉求又是什么,想要发现新的“友谊”故事的叙事空间,当务之急是找到新的“共同”使命,或持续的“共同利益”。“结盟”是需要社会动机和符合社会条件的。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中讨论“友爱”,我们不太说“善”,而更喜欢说“义”。“义气指同道中人之互相撑腰,是朋党之间的忠诚而已……讲义气的目的是求取相互保护以增加生存的机会;再进一步言之,所有自觉在危险中斗争的人群,也罕有不讲究分辨敌友的小圈子道德的。”孙述宇认为,“义”字背后有迫害感和边缘性,“聚义”代表了同做危险的勾当,“义胆”表示在法外行径上与同道合作的勇气。这种文化心理甚至超越了国界,被一再搬演。
如最明确表达要对“友谊”这个词语的内涵进行重新命名的作品,是马里奥·普佐的畅销小说《教父》。老教父唐·柯里昂经常谈起“友谊”。小说开篇就说,
“人人向唐·柯里昂求助,希望也从不落空。他不许空头支票,不找借口掩饰懦弱,说什么世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束缚他的双手。他不必是你的朋友,连你有没有能力报答也无关紧要。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你本人,要承认你对他的友谊”。
他暗黑的权力大厦似乎非常需要一个柔软的包装,而他选择了命名“友谊”。故事的起点出现了六个需要唐·柯里昂帮助的人,西西里人在女儿结婚的那天有不能拒绝别人要求的风俗。老柯里昂将这些人曾经、或未来寄存的所谓“人情”以预支的方式加以兑现。他执意为这种明确的“交易”命名为“友谊”,小说之外的我们,却很容易就能感觉到这种“友谊”不过是一种优雅的说辞。好像老教父总是彬彬有礼地表示“我会提出一个他不会拒绝的要求”,最后却用枪顶着别人的脑袋一样。
《教父》中的老教父唐·柯里昂
《教父》中“友谊”的建构不断加固着老考利昂的权力体系。他并没有依靠威胁,甚至不透过购买,而是依靠权力本身的“吸引力”(庇护作用)获得人间“友谊”,获得的方式是“交换”。读者都知道,这是法外交易,而且惩罚规则完全由教父本人制定。他拒绝帮助殡仪馆老板的时候说,
“你践踏我们的友情,唯恐欠我的债……你生意兴隆,过得不错,以为这世界是个无忧无虑的地方,你可以随心所欲享受快乐。你不用真正的朋友武装自己,因为有警察保护你……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我不会把友谊硬塞给并不需要的人,尤其是那些看不起我的人。”
而且他认为“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谊”。我们很难揣测作者本人为什么选择“友谊”这个名词来形塑老教父的人格,在教训别人的时候,老教父问了和亚里士多德一样的问题,“幸福的人需要朋友吗?” 让“友谊”的问题回归到了伦理学的拷问中。实际上,对于这部通俗小说而言,“友谊”只是一个虚拟的象征。从“麦克”的角度来看,《教父》有很强的成长小说的味道,说的是一个在父权阴影下曾经善良、叛逆的翩翩少年,如何一步一步成了“真正的西西里人”的故事。家族亲情的不死不弃,基因力量的顽强,要远远胜过所谓呈现“友谊”价值的企图。
不仅男性友谊书写受限于这种边缘性的牵绊,好读的女性友谊故事也多是风尘中的结义(如小说《红粉》),抑或是因故被社会边缘而结伴共同生活的情谊(如电影《自梳》)。“好人好朋友”这样的叙事因缺乏冲突,是青年创作者面临的困窘。“江湖义气是亡命汉的商标”,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亡命的经验。友谊除了“义”之外,还有些什么搬演的路径呢?友谊的舞台很可能转移到了虚拟世界。技术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社交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中间当然包括了年轻的文学创作者。当机器(手机、电脑、互联网)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史和情感史的重要载体,“友谊”将如何重新命名。它会不会受到古典时代对于“友谊”书写的规范,又会不会打破那些规范,这都是非常有趣的话题,有待未来的写作者来开拓。简而言之,小说的责任是发现“友谊”在虚构的世界里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将问题的焦点更集中一些,女性的友谊在小说里应该是什么样的。
《自梳》中的意欢(杨采妮饰)与玉环(刘嘉玲饰)
三
“当两人结伴时”
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男性友谊的呈现更多表现为两人以上的团体(如《美国往事》、史蒂芬·金《尸体》),而女性友谊的呈现则表现为“当两人结伴时”,这几乎已经成为窠臼。这种故事类型被演绎的非常多,近期比较畅销的小说如《我的天才女友》《摇摆时光》《萤火虫小巷》《对岸的她》等都表现了两个女孩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历程,在游戏、或学艺的过程中,她们会讨论到身体的变化、外在相貌的差异、自我表现和异性关系等内容,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程度或许会决定故事的深度。
如扎迪·史密斯本人对公共议题(“种族、阶级、女性”)的参与度就很高,《摇摆时光》将“友谊”当作观摩外部世界丰富面向的媒介;埃莱娜·费兰特则揭露了那不勒斯女性生存和女性教育的残酷境况,莉拉和埃莱娜可以看作是同一类女性的不同命运,实现了“what if”虚拟叙述的意图,这也是文艺作品描绘女性友谊的常见套路(如电影《七月与安生》)。
两个女孩的叙事模式或成了两种命运的可能性,或互为镜像(“世界上的另一个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表现为内部竞争,甚至是相互嫉妒。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的天才女友》和《我是纱有美》都提道了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说《小妇人》,虽然《小妇人》描写的亲姐妹的故事,但对女性自我教育而言是一部一再被创作者致敬的经典(“如果你觉得你的价值只在当装饰品,恐怕有一天你会相信,你真的只是这样。时间会腐蚀所有表面的美,时间无法消灭的是,你心灵美好的运作,你的幽默,你的仁慈,以及你的道德勇气”)。《小妇人》中男性的缺席并不是她们主观造成的,而是南北战争的外部原因。女性结盟的方式也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
《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莉拉和爱莲娜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中曾提道“女人间的友谊其实是用芥蒂结成的,越是有芥蒂,友情越是深。她们两人有时是不欢而散,可下一日又聚在了一处,比上一日更知心。”既是描述,也是评议小说主人公王琦瑶和她人生不同阶段女性好友的关系。此外,王安忆有两篇纪念散文同样塑造了女性友谊在文学呈现上的特征,追忆陆星儿的《今夜星光灿烂》与追忆程乃珊的《她多么爱生活,爱得太多太多》。
在《她多么爱生活,爱得太多太多》一文中,王安忆借用越剧《红楼梦》黛玉焚稿的唱词:“这诗稿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望它高山流水遇知音”,揭示了长久以来女性写作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功名,也没有途径求取功名,而是为了求知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女性能写的事情不多,女性没有资格写作所有的事。在有限中寻找意在言外的心灵价值,成了女性书写精神性的指标。
在《今夜星光灿烂》一文中,王安忆提道了“随着交往渐深、渐久,我们的话题也辐射开去,覆盖彼此之后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写作,却始终贯穿其中,是一个基本的线索……我们在许多事情上会发生严重的分歧,可我依然十分惊讶她的感受是如此不同。”文章反复提道“谈不拢”的气馁,但谈不拢并非是因为不想谈拢,恰恰是“止不住地还要谈” 。“交到最好的朋友之后,对他的和最好朋友的行为抱有更高的期望,这些期望往往导致异议或争论” 是《今夜星光灿烂》一文真正的动人之处。一样是少年时期开始热爱写作的文字生涯中人,三位女作家(另一个是王周生)通过写作生活凝聚到了一起,拥有了共同的理想和使命。
在西方小说里,女性友谊呈现的类型不少,主要表现为女性对“友谊”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和女性主义的意见紧密相连的,如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谢莉》,是有意识书写女性结盟的作品。我们在中学里阅读《简·爱》,经常把它当作一部女性如何成就自身的范本来阅读。即使知道简·爱具有许多珍贵的品格,她的形象依然像一个永远在愤怒的人一般难以亲近。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看,简·爱这种天然的个性特质,与其说是反抗特征,不如说是她拒绝向世界提供某种奖赏价值。
电影《简·爱》中的童年简·爱
劳渥德学校的桥段巨细靡遗地描述了一个十岁时失去双亲的女孩子所经历的家变、瘟疫、饮食及所能获得的有限的教育等等。这似乎是一所黑幕重重的学校,有非常多的暴力、霸凌、凌辱和饥饿,“揭露”的勇气是需要一个强动力支撑的,作者胸中有怒。这种怒火不是针对疾病本身,而是针对道貌岸然的管理者,针对少女命运的不服从。在这一团怒火中,简·爱在学校也完成一段非常正常的、陪伴型、精神性的女性友谊的确立。
简·爱的童年好友海伦·彭斯是一个天使般的女孩子,受的苦也比简·爱多,但她却对简·爱说,“你把她(里德太太)对你所说所做的一切记得多么详细啊…… ”记录详细的,还有劳渥德学校的体罚、恶劣的伙食和不被及时治疗的儿童伤寒。这个因伤寒早逝的女孩还对简·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她说“你把人的爱看得太重了……” 与简·爱相比,海伦·彭斯要平和很多。这令人相信,作者能够辨析公正与偏见。作者之所以保留偏见,一定是有所意图。
此外,《简·爱》对“友谊”是有一些独特的描述的。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小说,会发现与《教父》类似的关系建构,她执着于命名关系。继承遗产后的简·爱以一万五千英镑确立了与圣·约翰一家的亲情。简·爱对圣·约翰说,“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有一个家和几个亲戚……部分地报答深厚恩情,给自己赢得终身朋友的乐趣……而你却根本想象不到我多么渴望兄弟姐妹的爱。” 稍微理性一点的圣·约翰表示质疑,“简,你所渴望的家庭联系和天伦之乐,除了用你考虑的方式之外,你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获得啊;你可以结婚。”但简·爱固执己见,不耐烦地拒绝了。所以简·爱也在试图命名关系,她要以自己的方式定义“亲情”和“友谊”,而不是服从社会约定俗成的惯例。这与创作者想要在小说中重新命名“关系”的企图是相似的。
电影《勃朗特三姐妹》剧照
在写作《简·爱》之后,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部作品《谢莉》同样描写了女性之间、母女之间的友谊、同盟,她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女性之间的对话,反复肯定了女性友谊的价值,这反映了19世纪女性面对的种种社会偏见,并非针对性别,而是针对“关系”。如“男人眼中易变善妒的女性之间能否产生真正的友谊”“女人之间的关系可否健康”、因为男女的社会地位不同“你也许同一个男人有友谊,而在他看来,却没有什么重大的看法和兴趣是同你有关联的 ”等等。卡罗琳与谢莉之间的友谊具有精神性的排他功能,且作者认为,婚姻会破坏女性友谊的排他性,而且女性能够互相给予的东西,父兄及丈夫都无法给予,她们却渴望那种东西。《谢莉》的写作意图有其更为独特的时代背景,19世纪英国女性人口的极大过剩导致了多30%的女人终身不嫁,这些独身女性如何自主自立成为一个全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谢莉》应被看作是作为一个要自谋生路的女作家对当时的社会焦点的自觉回应 。
“婚恋”与女性友谊的关系有别于男性友谊书写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订盟,订的那么勤又那么急,可见背后迫切的生存愿望。女子结婚却不可能集体草率。回到亚里士多德所言,虽然寻求利己是个考虑,友谊会带来互惠,但互惠是最脆弱、最经不起考验的。我们说的情谊,不管是兄弟的、亲人的、夫妇的,都在描述一种关系,一种使人与人凝聚起来的力量。友谊,当然属于那样一种力量。人愿意与自身以外的人在一起,产生凝聚的意愿非常重要。而如果意愿接近到渴望的程度,就必定会产生交往,遭遇磨合的风险。好的友谊,一定会使人共同成长、共担风雨,也能共享福乐。
四
“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谊”?
“男人比女人更理解友谊”这话来自《教父》,作为文本之间的交际,夏洛蒂·勃朗特的回应,能使女性产生“凝聚的渴望”的力量显然是要战胜这种偏见。因为无论是厌女的硬汉故事类型,还是擅长世情书写的男性作家,很少有看好女性友谊的范例。
蒙田在《论友谊》一文中就认为,
“以女人寻常的能力来说,她们难以胜任维系这个神圣纽带所需要的交流和沟通;她们的灵魂不够坚强,不能承受如此沉重而持久的关系” 。
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也写过友情。短篇小说《友谊》表面上围绕着女性婚姻与友谊不相容的主题,实际上还是在表达对女性友谊不可靠的嘲讽。不可否认的是,女性婚姻与友谊的矛盾是存在的,男性婚姻与友谊的矛盾则显得微乎其微。这是在小说中作为变量的“婚姻”对于男女成长的不同影响所造成的。
夏洛蒂·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1816年4月21日~1855年3月31日),英国女作家,她与两个妹妹艾米莉·勃朗特和安妮·勃朗特,在英国文学史上有“勃朗特三姐妹”之称。
夏洛蒂·勃朗特写作《谢莉》的故事也非个案,金雯教授曾细读英国小说家理查逊的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提道小说里“克拉丽莎唯一感受到的纯粹友谊来自安娜小姐,在她受勒夫莱斯诱骗离家出逃陷入困境时,安娜不仅提供金钱支援,还提出和她一起去伦敦。正因为如此,她与安娜小姐的关系在小说里成了克拉丽莎唯一认可的亲密关系,被赋予了崇高的类似婚姻的含义。她多次称安娜小姐为爱人,并把自己的戒指作为遗产赠送给这位唯一的朋友” 。她指出,克拉丽莎的选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十八世纪早期的女性思潮相吻合,且在小说里就受到了男性父兄的蔑视。但“婚姻是友谊的最高形式”,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话题。《克拉丽莎》中单身女性及女性之间友谊的刻画方式,有和男性友谊书写相似之处,如救援之力的呈现,也有差别,如信物或遗物的托付。金雯最后提出,“女性间的友谊是《克拉丽莎》开拓出来的一个新的文学母题,体现了这种情感对于异性婚姻的重要补充作用,也显示出其脆弱和艰难”。
古今中外,在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女性的生存处境决定了女性在文学中的处境,这暗示着女性命运与悲剧创作的亲密联结。女性通过观察母亲、模仿母亲获得女性经验,通过友谊、创伤等经历完成自我启蒙,女性友谊又会受到异性婚姻的考验。归根结底,一个女性在社会上闯荡总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性会彰显规训的作用,例如在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女性终究会选择丈夫和后代,而不是女性盟友和真相。韩剧《我亲爱的朋友们》中有一句台词,一位女主人公对她的好友哭诉道:“你为什么每天都活得那么苦,让我没办法完全依靠你”,暗示女性不是不想讲义气,而是女人因为自己受苦,才看得见朋友的苦。她们都是没有办法从苦海中脱身的人。回应了本文开篇所引苏童所言,“我从小便觉得女人命苦”,可见女性友谊的特征之一就是不再向闺蜜发出共同受难的邀约。
“你为什么每天都活得那么苦,让我没办法完全依靠你”《我亲爱的朋友们》
另一方,面对于小说写作而言,风险未必是一件坏事,还可能是一种叙事契机。许多女性精英在小说里完成自我蜕变,结果不一定是悲剧。如德莱塞笔下的“嘉莉妹妹”,从一个面粉厂工人的女儿逐步攀登,终于成了芝加哥尤物。可惜我们很难对“嘉莉妹妹”发问,她是不是需要一个帮助她的女性朋友,因为帮助她的男性已经很多了。又如爱丽丝·门罗,同样写作了大量的女性,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身份,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她们可能是女儿、妻子、情人、继母、祖母……她们各自经历的内心生活与命运波澜。作为个体的她们甚至会被女性同盟所共同轻蔑(如《恨,友谊,追求,爱情,婚姻》)。所以,共同讨厌一个人似乎也能结成女性的同盟,这种同性的迫害之力,从另一层面上居然也能帮助小说主人公完成命运的突围。
本文开篇曾经提道有几方面的原因可能形成了讲好友谊故事的阻碍,第三点是“消费主义对身份认同焦虑的影响”,只能在此略做补充。在近期青年写作的题材方面,出现了“追星”与“微商”的内容,那显然也是符合“凝聚的渴望”特征的,且与消费、与机器的联结非常紧密。它不再拘泥于同性、异性友谊关系的习套,且涉及金钱、时间、冲突等多重通俗性的要素,还相当具有女性特征。可惜的是,这虽是年轻人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却并没有出现特别有心灵价值的作品,有待于未来的研究者和创作者继续观察实践。
五
余论
至此可见,想要理顺一些习以为常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关系并非易事。西方有其得天独厚的文化路径,例如从打破基督教父权的庇护或要求直接与上帝对话等方式 ,重塑“凝聚的渴望”,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有玛丽莲·罗宾逊的《管家》,小说的诉求非常明确,通过露西尔和姨妈希尔薇的结盟,重塑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性的关系)。
如果能去性别化地看待“友谊”的写作母题,“友谊”故事并不一定非要独立成为创作题目,而是灵活隐藏于童年书写或成长小说中的。围绕这个主题,大部分优秀作品,都会写到青春的逝去与友情的落幕。这并非是女性写作独创。如宫本辉的《泥水河》,表面上写的是童年友谊,实际上写的是战后心灵创伤对孩童命运的影响。史蒂芬·金的小说《尸体》很好诠释了友谊、死亡与失去。
“后来我再也没有交过像我12岁时那样好的朋友了”《伴我同行》
《尸体》在1986年被改编成电影《伴我同行》,故事的主题被凝练为“后来我再也没有交过像我12岁时那样好的朋友了”。而这段深刻的友情故事,缘起于寻找一具尸体的游戏。小说里写到“最重要的事情往往也最难以启齿”,
“这种事随处可见,有没有注意到,朋友在你生命中进进出出,好像餐厅中的侍者来来去去一样。可是每当我想起那场梦、想到那两具尸体正用力拖我下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也好。有的人会沉沦,如此而已,并不公平,但世事就是这样,有的人会沉沦下去。”
回应到欧丽娟认为《红楼梦》传递出的悲剧主题,表现为女性的命运没有人为努力的空间,也就没有扭转命运的机会……其实在新的时代,年轻男性也未必有扭转命运的好运。“友谊”问题不是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边界,但友谊书写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为创作者所利用观看外部世界的变迁。这是可以被一再书写、一再挖掘的母题。
本文讨论了为女性写作“友谊”重新命名的文学可能性,期待一种打破“两人结伴”的俗套模式,照亮生活史和情感史的缝隙,创作前景广阔。从世情角度而言,重组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中就存在有类似亲戚的“友爱”关系。从机器与传播角度而言,如今的游戏、阅读App大多带有社交功能,虚拟交往和情感依恋未必存在于现实世界,其中一定有发现新故事的可能性。从女性角度而言,有非常多的前沿研究发现,
“女性之间的友谊,可以提供学习成为自我的最佳条件。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女人的交谈无足轻重或是自我放纵。女性的亚文化以交谈为中心:我们应该把它视为我们的力量之一,而非弱点之一。”
文学化的“交谈”与交际,可能成为青年写作者探索世界的协作工具。女性的友谊,虽然从未成为人类关系的典范,却正因没有答案、没有结论的现状,为青年写作创造了写作条件。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能使女性产生“凝聚的渴望”的关键力量。无论是在文学内部,还是在文学以外。
本文节选自
《故事识别》
作者:张怡微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出版年:2021-9
编辑 | 仿生斯派克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