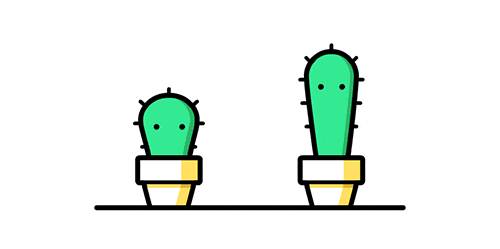他们看我开的车,以为我是富人|星期天文学·郑在欢
周五好,这里是「星期天文学」。也许有读者还记得这个名字,它初创于2016年,是凤凰网读书最早的文学专栏之一。这几年,我们与网络环境相伴共生,有感于其自由开放,也意识到文字载体的不易,和文学共同体的珍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星期天文学」将以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为纯文学爱好者设宴。这里推荐的小说家,年轻而富有才华,是新文学的旗手,他们持续而毫不功利的写作,值得我们多花一点时间,也填补、延展了我们的时间。
「星期天文学」第3辑,嘉宾是作家郑在欢。以下推荐的《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收录于他的新书《今夜通宵杀敌》,主角是刚回老家的年轻人,他给发小打电话,求他重讲小时候那些“破故事”……没什么原因。“我想到闲人更多的地方去,和闲人聊天,不抱任何目的,最初的快乐就是这么来的。”
找快乐,也是找自我,找失落的少年世界。正如评论家李壮所言,把一桩正剧性、悲剧性的事情,用喜剧性、闹剧性的策略来写,甚至以“不谈”的方式来“谈”,郑在欢是此中高手。
郑在欢,1990年生于河南驻马店,长居北京。著有《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今夜通宵杀敌》《团圆总在离散前》等作品。标志的幽默语言,多变的故事素材,让他的小说好笑又好哭,并且极其好玩。
《还记得那个故事吗》
作者:郑在欢
下午没事儿,我给光明打电话,我们从没有打过电话。我从他妹妹那里要来的号码,他妹妹是城里的中学老师,他姐姐是高中老师,他是一个空调装机员——有时候也卖空调。我找他不是为了买空调。
光明,是我,我是李青。
李青啊,咋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有事吗?
我想问你个事。
啥事?
你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还记得吗?
什么故事?噢,你说“小三放牛”啊。(小三放牛是光明常讲的故事,不过不是小三放牛。)
不是小三放牛,是另一个故事。你还记得吗?有一年夏天,在你家院子里,你妹妹在,你姐也在。我们四个在玩牌,你讲了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什么故事?
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忘。洗牌的时候,你讲了这个故事,把我们都吓坏了。
什么故事?你提个醒。
你妹妹第二天去打了耳洞,还有印象吗?打耳洞之前,她说了你们邻居的事。那个女孩睡在豆子上,睡得太久了,耳朵硌在豆子上,硌出了一个洞。听到这个我们都深吸了一口气,你还记得吗?后来那个女孩在豆子硌出来的耳洞里戴上了耳环。你妹妹很羡慕,所以决定去打耳洞,你还记得吗?
好像是有这么一天,豆子把耳朵硌穿,我们当时都觉得疼,都大口吸气,我记起来了,还是我给的五毛钱,让小娟去打耳洞。
对,就是那一天。
她叫乔乔,我记得这回事。
不是这个故事,是你讲的故事。你妹妹说完乔乔的事,你给了她五毛钱之后,你又给我们讲了个故事。你再想想。
不要一口一个你妹妹你妹妹的,她叫小娟,你不认识她吗?你平常都叫她什么?
我还能叫她什么,我叫她小娟。
那就叫她小娟啊。
好,我叫她小娟。
你们现在怎么样?你和小娟,你们什么时候能结婚?
你别打岔。我现在不想说小娟的事,我就怕你问小娟的事才说的你妹妹。我找你不是说小娟的事,我想让你给我讲讲那个故事。
什么故事?你和小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出事,没出任何事,我和小娟很好,你能别提小娟了吗。
没出事为什么不让提?我跟你说,小娟可是个好姑娘,她都没有谈过恋爱。
我知道,我知道小娟是好姑娘,我很喜欢她,你尽可以放心。现在你能跟我说说那个故事吗?
什么故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怎么会呢,我一直都记得。是你讲的故事,你当时还比我大三岁,你怎么会不记得?
你记得?那你跟我讲讲不就完了。
我以为我记得,我一直都以为我记得。我经常突然想起来,我们在葡萄架子下面打牌,先是小娟说了耳洞的事,我们都觉得疼,然后你说了那个故事,把我们都吓坏了。每次我想起来,都以为记得那个故事,我没有细想,我以为那个故事就在我脑子里。前几天我又想起来这事儿,本来可以像以前一样想一下就过去了,就去干别的事了。那天我太闲了,我在车上,我想把整个故事都想一遍,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想不起来了。
想不起来就算了吧,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不是闲着没事嘛。这种感觉你肯定也有过,越想越想不起来,很难受,你肯定有过这感觉。
你就是太闲了,为什么非要想起来?想起来有什么用?你找工作了吗?没有工作你怎么结婚?小娟是个好女孩,你不要让她吃苦。
怎么又扯到小娟了!光明,故事可是你讲的。你能不能放松点,像小时候一样,就像小时候你跟我们讲故事一样。你讲“小三放牛”的时候提过小娟吗?
现在不是小时候了。再说,小时候你也没跟小娟谈恋爱啊。
我要求你——我请求你,我求你,就当现在是小时候,能不能跟我聊聊那个故事。就聊那个故事,别的什么都不要说。你要是再说小娟,我现在就打电话跟她分手。
好,你别激动,你就爱激动,我不说小娟了,好吧。
谢谢你。我是有点激动,我先挂了,平静五分钟再给你打,你趁这会儿好好想想。
想什么?
想想那个故事!
我挂了电话。我又有点控制不住了。这两年不知怎么回事,我跟他们说话特别容易生气。这里的他们包括所有人。在北京的时候,我跟人说话从不生气,只是单纯地觉得没意思。在小酒吧和路边的饭馆里,我可以和任何一个朋友聊任何算不上事儿的事儿。我们可以聊一晚上,不管聊什么都能聊得津津有味。随便一个话题我们都能像对待哲学问题一样全神贯注。我们随着话题的深入而感到兴奋,好像已经触摸到思维的娇蕊。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没意思,我意识到这个让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好像在聊一件事,其实我们在聊八件事,那七件我们根本不想聊的事情伪装成我们想聊的那一件事情,搞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聊什么了。所有聊天都是这么结束的,我们突然忘了原来在聊什么。我们偷偷地看对方一眼,觉出尴尬,并迅速道别。
从北京回来,我没有别的考虑,仅仅是想换换心情。我想到闲人更多的地方去,和闲人聊天,不抱任何目的,最初的快乐就是这么来的。他们看我开的车,以为我是富人,其实我就这么一辆车,还是朋友给的。刚回来那阵确实快乐,我开着车四处游逛,看到个闲人就去跟他聊。大爷,钓鱼呢?这有鱼吗?然后我就开始听大爷给我讲鱼,鲫鱼是怎么从土里生出来的,泥鳅为什么也吃钩。作为回报,我告诉大爷在美国,他们都钓鳟鱼。鳟鱼个头很大,有十多斤,要钓鳟鱼,得用好线。大爷不服气,跟我讲他年轻时候钓的草鱼,足足十七斤六两。年轻人,你可知道,猪大三百斤,鱼大无秤称。再大的鱼,我都不稀奇。这样的谈话让我快乐,猪大三百斤,鱼大无秤称,我第一次听到这话。我听到,并感到稀奇,再一想,觉得有理。
我找人聊天,不分对象,只是饶有兴趣地聊天。两个月后,我谈起恋爱,这是个意外。我跟小娟,得有八年没见过了吧,第一眼,我没有认出她来。姑娘,听歌呢?能给我听听吗?在北京,我绝对没有这种胆子,我从没有搭讪过女孩。那些天我到处找人说话,胆子确实大了不少。在傍晚的人工湖边,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亭子里听耳机,我突然想到,还没找女孩说过话呢。我找大爷说话,找大叔说话,找大妈说话,就是没找大姑娘说过话。敏感的男女问题约束了我的热情。就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找她聊聊,就像跟大爷大妈们聊天一样自然。那时候我怎么会想到,这次聊天还是造成了男女问题。她抬起头,看着我笑,并把一只耳机递给我,然后我听到了中学的英语: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你在学英语?她还是笑,我是英语老师,我在备课。我跟她说起我们小时候学英语的方法,给单词下面写上汉字,按汉字的发音念。go是狗,to是兔,go to school 是狗兔死过去,去用括号括住,老师抽查的时候只念狗兔死过。我说话的时候,她一直笑着看我,看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她不算美,不过笑起来很好看,嘴里像含着糖,不像别的女孩,都是抿着嘴笑。你真的认不出我了?我是小娟啊。我这才知道她那种笑,是故人相逢的笑。我们从故人再度成为熟人,她就不那么笑了。
《站台》
光明,怎么样,想起来没?
没有,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怎么会呢,你到底有没有想。你是不是干别的去了。
我在算账。
你算什么帐。
空调的帐啊,我在算提成。
你能不能把工作放一放,先想想故事。
我真想不起来了。
你没想怎么说想不起来,你想想啊。
我想了,现在我就在想,我想不起来。
我真服了。你讲的故事你都想不起来,小三放牛你想得起来吗。
那还用想吗,小三放牛我熟得很。
小三放牛这样的破故事你都记得,为什么想不起来那个?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骗你干嘛,就是小三放牛我也好久没讲了。我现在不讲故事了,我给我儿子都不讲。
你都在干嘛,你连故事都不讲了,连你自己的儿子都不讲。那时候你讲故事,可不管是谁在听。现在你儿子到了听故事的年纪,你都不讲了?
有电视,讲故事干嘛,看电视多好。
那能一样吗?故事可是你亲口讲的,就像这个故事,要不是你讲,我怎么会记那么久。
……
我给你提个醒,这是个古代的故事,记起来了吗?故事说得是儿子吃太多包子了,当爹的一巴掌把儿子的脑袋拍下来了。这么惊险的情节你会不记得?
我哩个娘!这是什么故事?我怎么会说这种故事,这太恐怖了。
就是你说的,小娟说了耳洞的事之后,你讲的。
好,我讲的,我忘了还不行吗。
现在呢,记起来了吗?
为什么非要我记起来,你记得不就行了。
我就记得这么多,我忘了前因后果,儿子什么要吃那么多包子?当爹的为什么要打他?他的头为什么一拍就下来了?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吃包子,他饿呗,饿就吃呗。
对!肯定是他饿,他饿才会吃包子。
你吓我一跳。这有什么稀奇的,饿就吃嘛。
你觉得这不稀奇?你太久没讲故事了。这很重要,他饿,所以他吃,所以我们知道了,他饿肚子,而且是长时间饿肚子。
是,古代人经常饿肚子。
他为什么饿肚子呢?
他是穷人呗。
你又说对了,他肯定是穷人,这是个穷人的故事。
穷人都会乱吃东西。
对!天呐,你还说你不讲故事了,你简直就是讲故事天才,你一语中的。他肯定乱吃东西了,这就接近故事的真相了,他乱吃东西,所以头一打就掉。
你在熊我吧,什么讲故事天才,我讲的故事都是书上看来的。
我熊你干什么,我在认真跟你聊这事儿。你能不能也认真点,像装空调一样认真地讲故事。
你也知道我装空调,我装空调有钱拿,不认真能行?讲故事有什么用,讲故事要拧紧螺丝吗?你这种想法,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知道轻重缓急,你有这时间怎么不把房子装修装修?我爸就这么一个要求,让你装装房子,你怎么不知道着急呢?小娟都多大了,她可等不起了……
我把电话扔了出去。这是惯性使然,以前,和女友吵架的时候,为了让她闭嘴,我会扔手头的东西。在小娟面前我还没扔过东西,我不确定是她脾气好还是我们没到那一步。我正努力发现她的优点,好下定决心跟她结婚。我不是装修不起房子,也不是不想装,我只是故意拖延。光明的意见就是从这来的,他一定是觉得我散漫惯了,他怕小娟跟着我受苦。我也怕小娟受苦。有多少看起来无比合拍的结合,到最后不欢而散。我和小娟还算不上合怕,我一直在北京,她一直在老家;我心里隐约还有点梦想,妄图通过写作闻达于世;她对生活大体满意,习惯了攒钱和评职称……我喜欢她,但不确定这种喜欢能支撑多久。我得尽可能多地从她身上找到让我离不开的地方,以防日后变心。反之,我觉得小娟也应该考察考察我。但我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就显得很鸡贼,好像我没有那么爱她。我爱她,毫无顾虑地爱,我爱她,所以顾虑越来越多。这种话跟光明怎么说呢,他现在连故事都不讲了。手机掉在书桌与墙的夹缝里,他的声音从那里面钻出来。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别一说这事儿你就打马虎眼。
光明,能别说这事儿了吗?
那你说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和小娟的事,怎么办?
照你说的办,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挂了电话我就办。
那好,就这么办,我挂了。
窗外传来孩子声,他们在花园里追逐打闹。他们的笑和惊叫特别大声,能这么叫一定很痛快。这世界对他们来说太新了。快要被抓住的人大叫,抓住了人的大笑,他们玩什么都那么专注,听故事也是。世界对他们太新了。我还保持着打电话的姿势。我只是想重温一个老故事,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屈辱。像光明这样的人,我宁愿一辈子不和他说话。我站在窗前看了好久的孩子,直到他们跑出视线。他们跑到远处的树影,消失了。我又站了一会儿,等寂静再度完整地降临,我第三次打给光明。
光明,跟我聊聊好不好,算我求你。
瞧你说的,还求我,咱们什么关系。
那我们好好聊聊行不。
好啊,聊什么?
聊聊那个故事。
好,你说吧。
我们刚刚说到哪了,我想想……
乱吃东西,我说穷人就会乱吃东西。
对,你说得很对,穷人就会乱吃东西。现在我们要想想,他为什么乱吃东西?
这还用想吗,他穷呗。
我知道,光明,我们不要那么急着下结论,我们要多想几种可能,穷肯定是一方面,除了穷呢?要知道,天下的穷人多了,为什么这一个穷人被讲成故事了呢?这里面一定有它的特殊性。
能有什么特殊的,饿了就吃,这不是天经地义吗。
是,是天经地义,但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是个孩子,一般来说,孩子吃东西都是跟着大人,为什么大人没事小孩就有事了呢?
抵抗力强呗,大人的身体肯定比小孩棒。
这也是一种解释,不过这个解释不构成故事,大人比小孩身体棒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天经地义的原因不是故事的原因。
那什么是故事的原因,有人给小孩下药了?这是故事的原因?
这是故事的原因,不过这个原因又太强了,这么强的原因肯定不是好故事。你当时讲得可是个好故事,不然我怎么会记那么久。
小三放牛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你不是说那是个破故事吗,怎么也记那么久。
……
你真行,光明,你把我问住了,你抬起杠来倒是有一套。我收回那句话,小三放牛不是破故事,只是我听得太多了。你那时候总讲小三放牛小三放牛,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怨我吗?是你们老追着我让我讲的。
不怨你,我还要感谢你,你讲故事很棒,真的。
这有什么好感谢的,你现在说话怎么都是酸溜溜的。
一点都不酸,我是认真的,你不要怀疑我的诚意好不好。你想想,那时候为什么我们一帮孩子都愿意跟着你玩,因为你会讲故事。
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大吗?小孩都爱跟着大点的小孩玩。
大点的小孩多了,为什么跟着你——好了,别说这个了,我们回到正题,我再问你一遍,他为什么乱吃东西?
我怎么知道,我说什么你都不满意。
你只管说,我不是对你不满意,我们在讨论问题,我是对答案不满意。你再想想,答案肯定不止一个。
好,我想,他为什么乱吃东西?他是穷人家的孩子所以他乱吃东西,他跟着他爸乱吃东西,他爸没事他有事,那他应该不是和他爸一起吃的东西,他肯定是在家里吃不饱才跑出去乱吃东西,他爸不给他做饭吃吗,他爸是不是工作很忙……
停,停,你提醒我了,他妈呢?
我怎么知道,你也没说过他妈的事啊。
这里面就有文章,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说这一对父子,完全没有提过孩子他妈,他妈去哪里了呢?
他妈死了?
对!这就是故事了。他妈死了,这很关键。
怎么关键了?
你想啊,故事一开始,就有一个人死了,这就是故事,有多少故事一开头就死了人,尤其是死了亲人。这个女人对于爸爸来说,是妻子,对于儿子来说,是母亲,她死了,对这两个人肯定是一件大事。
这倒是,不管是死了老婆还是死了妈,对人都是重大的打击,说是天塌下来了也不为过。
是啊,天塌下来了。这个孩子还小,可能还不太伤心,对于爸爸来说,肯定是伤心死了。他英年丧偶,要一个人抚养孩子,以前不会做的事,都得学着去做,他去做妻子做的那些事的时候,怎么能不想到她。他肯定想到她了,想到她有多好,多勤劳,她永远都回不来了,他能不伤心吗。
是啊,他肯定伤心死了。
人在伤心的情况下,是提不起精神的。他每天昏昏沉沉的,干什么都没心思,工作估计都没法干了,说不定还会借酒浇愁,又伤心又喝酒,哪还顾得了孩子……
对!对!他借酒浇愁,我想起来了。他借酒浇愁。
你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真想起来了?
我真想起来了。
我就说你肯定忘不了。
我确实是忘了,是你说借酒浇愁,我想起来了。他在河边借酒浇愁,当时我还担心,怕他掉水里淹死,八贤王不就有一次喝多了掉到沟里去了吗。八贤王是天生爱喝酒,他是借酒浇愁,我记得这个词儿。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成语,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他终日地借酒浇愁”,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终日地借酒浇愁。终日我也不太明白,还查了词典。
我就说,我就说你忘不了。
我也没想到还能记起来,我那时候喜欢记成语嘛。我床头还贴着一张成语接龙你记得不。
我记得,你还教我成语。
对,我那时候喜欢成语,我还有一本成语小故事呢,我跟你们讲的故事就有从那上面看到的。
我知道,你讲过“掩耳盗铃”。
对,对,掩耳盗铃,那个太好笑了。
我们都笑惨了,其实我们一开始没觉得好笑,你又给我们比划了一遍我们才笑。
对,是的,太好笑了。
好了先别笑了,你赶紧给我讲讲,别又忘了。
讲什么?掩耳盗铃吗?
什么掩耳盗铃,我说那个故事,借酒浇愁,你不是记起来了吗?
我是记起来了,你说完我才记起来的。
那你给我讲讲啊。
讲什么?
借酒浇愁啊。
这有什么好讲的,不是你先说的吗,借酒浇愁。
你不是说想起来了吗?你想起什么了,给我讲讲啊。
不是借酒浇愁吗?你说完我才想起来,借酒浇愁,那个男人死了老婆,他借酒浇愁。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就不知道了。
你这叫想起来?你就想起来这一个成语?你再想想。
我真想不起来了。
你肯定能想起来,你都想起借酒浇愁了。顺着这个往下想啊,他死了老婆,他伤心得要死,他借酒浇愁,他不管孩子,然后呢?
然后……然后他不能再这样了,再这样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记起来了,有个人跟他说,你不能再这样了。
你又记起来了?
我记起来了,他的邻居,是个老头,跟他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啊,你还有小孩。对,一个老头说动了他。他幡然醒悟,这又是一个成语,因为他老喝酒嘛,所以是这个词儿,幡然醒悟,有一种酒醒了的感觉。人的酒一醒,就注意到以前喝酒的时候有多邋遢了,他也就注意到自己的儿子有多饿了。所以他带着儿子到街上,给他买吃的。他儿子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喝酒的时候,他儿子都没饭吃,天天叫饿,叫得烦了他就骂他,可能还打过他,我不记得了。反正他儿子可怕他了,再也不敢去烦他,饿了就自己出去找吃的。那一天,他幡然醒悟,又恢复了理智,带着儿子去街上买吃的。那孩子可高兴了,他爹又开始疼他了,别看他饿,他走路都带风。他恨不得让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看看,他是跟着他爹出来的,他爹带他买吃的。他们来到包子铺,是那种马路边的包子铺,桌子摆在外面,我记得清楚,书上有一幅插画,画得就是他们在路边的包子铺吃包子。他们来到包子铺,爸爸对儿子说,想吃多少吃多少。儿子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又饿又高兴,他特别想表现给他爹看,看看他有多能吃。他们吃得是南方那种灌汤包,包子里面都是热汤,刚出锅可烫嘴了。那孩子狼吞虎咽的,吃了一个又一个,都是囫囵个吃进去的。旁边的人看了都觉得奇怪,奇怪他为什么不觉得烫。他爸也看不下去了,觉得他吃得太急了,给自己丢脸了。他让他慢点吃,别烫着。儿子说一边吃一边说,一点儿都不烫,一点儿都不烫。他爸还琢磨,是不是老板卖给他们剩包子,怎么一点儿都不烫。他也学着儿子那样大口吃了一个,结果烫得吐出来了,他觉得儿子在蒙自己,明明就很烫却说一点都不烫。他一巴掌打过去,骂他骗自己,没想到这一巴掌下去,把儿子的头给打掉了。
是的,就是这个故事。光明,我服你了,你总算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就是这个故事,太好了,这个故事太好了,太神秘了,还很悲伤,是不是。
我也没想到还能记起来。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古怪。这个故事很古怪,也很悲伤。
可还是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那个孩子的头,为什么一打就掉?
是啊,为什么一打就掉呢?是不是为了突出他们的惨,旧社会的穷人都惨。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要是这样,这个故事就太高级了。你那时候还看不到这么高级的故事。其实我也记起来了,你讲完这个故事,我们都吓坏了,我们问你,他的头为什么一打就掉?这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人问,他的头为什么一打就掉?你还记得当时是怎么说的吗?
不记得了。
你说,因为孩子吃得太急了,他连碟子都吃到嘴里去了。碟子硌在他的脖子上,就像豆子硌在那个女孩的耳朵上一样,所以他爸爸一巴掌拍下去,他的头就掉了。
是吧,我好像是这么说的,因为小娟讲了耳洞的事嘛。
当时我们都信了,那时候小嘛,讲故事的人怎么说就怎么信。现在我才知道,又听你讲了这一遍我才知道,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把碟子都吃进去,太牵强了。
什么牵强?
就是勉强,把碟子都吃进去,这说不通,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原因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吗,你说给我听啊。
好,我跟你说,他的头为什么一打就掉,因为他吃了太多的生东西了。他爸不给他做饭,他只能去外面找吃的,他们是渔民,他很自然地去河边找吃的,又因为他是个小孩,他不会捕鱼,他只能找到河蚌、田螺、蛤蜊这些东西,他也不会做熟了吃,都生吃了。这些东西身上都有很多寄生虫,日久天长,这些寄生虫就寄生到了这个孩子的喉咙里,这就是为什么他吃灌汤包不会觉得烫。因为长期被寄生虫寄生,他的脖子已经空了,所以一打就掉。
妙啊,这就说得通了,就是这样,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这样,这就是这个故事成立的原因,看起来很有科学依据。虽然深究起来这也很牵强,不过一般人不会注意这个,水里的东西,谁能搞得明白呢。
是的,听起来很新奇,也很可怕,可不敢乱吃生的了。不过我也想问问你,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渔民。
我猜出来的。
猜出来的?怎么猜出来的?你怎么知道你猜得是对的?
这么说也不对,不是我猜出来的,是你讲出来的。
讲出来的?我没有讲渔民啊。
你讲了,你说他们吃灌汤包,这是南方的食物,你说他在河边借酒浇愁,你为什么提到河,因为河很重要,他们以河为生,所以,这个死了老婆的男人,他是一个南方的渔夫。
厉害啊你,头头是道的。我记起来了,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这么说的,一个渔夫,他的老婆死了。
这就连起来了。真是个不错的故事,你应该记住它。
是不错,不过也没有什么好记的,我现在不讲故事了。
再讲一次吧,光明,再给我讲一次小三放牛吧。
创 作 谈
“说”的悖论,或“有效的莫名其妙”
——关于郑在欢《还记得那个故事吗?》及其他
作者:李壮
那是2020年春天的一个中午,郑在欢把他刚完成的一篇小说初稿微信发给我看。我当时正坐在麦当劳里嗑麦旋风冰激凌,本来只打算先看个开头,没想到一口气细细读到了底。小说看完,麦旋风已经化成了奥利奥奶盖,黑色的饼干碎屑漂浮在乳白色冰凉的液体上,就那么暗幽幽地闪耀着,像话语从内部解体后、散落在经验之河上的残片——借用小说原文里的一种描述,这实在“很古怪,也很悲伤”。
我端起这杯完全融化掉的冰激凌一饮而尽,用方言给郑在欢敲去了一句脏话。原文是:“我□□□□(此处省略四个字),写得好哇!”
小说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题目,叫《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一年多后的此刻,我正试图严肃地谈论它。事实上,不仅题目,整篇小说都很莫名其妙。说的好听点,这篇小说的风格叫“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得放肆点,那就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整篇小说的精髓就在于“说的悖论”:人物(包括作者)在其中所说的几乎全部的话,都与他真正想说的话没有直接关系。他一直在说,说得甚至非常有趣、让人极其想听,但实际上却似乎从未张口。这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力量,乃至揭示了某种荒谬的必然。小说赋予“沉默”一种喧哗的形式,或者说,给“沉默”打造了一具叙事的、语言的肉身。
由此言之,这篇小说与前一阵莫名火起来的“废话文学”——“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七日不见,如隔一周”云云——似乎有血缘之亲。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呈现为喜剧的悲剧性“无语”,并将其打造为把玩、审美的对象。然而实际上,这篇小说的问世时间,可要比“废话文学”(当然,我在此指的是网络世界的新潮“话风”、而不是文学史上那个以“废话”为名的实体流派)成为青年群体“话语时尚”要早得多。谁说文学跟时代生活脱节了?有些时候,文学对时代生活隐秘气息的感受和捕捉,甚至比流行文化更早,只不过我们未必注意到了而已。
因此,“莫名其妙”当然不是贬义。在今天,有太多太多的“情真意重”,都只能通过“莫名其妙”才能表达出来。这并不是故弄玄虚。在这个经验繁冗、情感膨胀、“信息过载”与“信息茧房”并行不悖的时代,“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固然是事实,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也同样是实话。“表达”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地磨损了、透支了,以致我们很难再以古典性的方式,走着台步、甚至踢着正步,便穿透经验的厚重脂肪、刺中充满疑问的意识本质。
就拿《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来说吧!它当然有一枚“正经”的、本质化的内核。这篇小说要讲的,其实是人世的“变”、人心的“隔”,讲的是一位青春将尽的年轻人,对理所当然的、“正常”而“正确”的人生未来的恐惧。甚至说得再直白一点,这篇小说讲的,其实就是一位敏感青年的孤独内心、及其“恐婚”故事。这当然是很重大、也很有时代典型性的主题。但问题是,如果就单看上面这段“干货总结”,如果作者就这么端起范儿来直愣愣扛上去写,反正我自己是一点也不想读这篇小说的。
这是文学面对着的巨大悖论:一方面,有些主题确乎值得我们一谈再谈,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容易一动笔就把事情谈滥谈糟、谈成“套路”、谈出一股太过熟悉的酸味儿来。况且,这一切本也不是什么新奇的经验,“远行者有故事”,但我们的读者乃至我们自己,都不是“远行者”而是“沉溺者”“受困者”。近景魔术最难演。
怎么办?一种有效的方案,便是“劳师袭远”“欲擒故纵”。把一桩正剧性、悲剧性的事情,用喜剧性、闹剧性的策略来写,甚至以“不谈”的方式来“谈”。我想郑在欢是此中高手。《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便是很好的样本:这个故事在不断地“跑偏”“掉线”、但又始终隐隐地围绕着某个不可见的力学中心,在偏离中求抵达、于沉默里求发声。小说的题目里提到了“那个”故事,单数。但这篇小说本身显然是一个复数的故事,三层不同的故事之间相互嵌套,相互遮蔽,相互呈现:
——首先,就是字面上的“那个故事”。这是最直观的第一层。“我”忽然联系发小光明,想再听他讲一遍“小孩吃包子”的故事。对这个故事的回忆、讲述,构成了小说的绝大部分内容。“小孩吃包子”这个故事很荒唐、甚至有点恐怖(具体情节我在此就不再复述了)。比故事本事更荒唐的是,多年过去,故事原本的讲述者光明,早已经把故事给忘了;但“我”居然不依不饶,不仅强迫光明回忆这个故事、甚至拉着他一起推测故事的逻辑、补充故事的细节……谢天谢地,故事最后总归是被完整地回忆起来(你甚至干脆可以说“创造出来”)了。然后,小说也结束了。
——其次,是“失乐园/复乐园”的故事。在第一层故事中,存在着一对明显的对抗性关系。“我”一定要推动叙事(努力回忆那个故事),光明则一再地阻滞叙事(没兴趣回忆那个故事)。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小说故事的第二层:“我”与光明、或者说与失落掉的少年世界间的故事。一个成年人缠着另一个成年人要听故事,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换言之,此事背后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便是,“我”对自己身处的成人世界产生了巨大的不认同。在“追讨故事”的缝隙里,“我”已经透露了自己在现实中遭遇的困境:生活仿佛索然无味,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
“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没意思,我意识到这个让人沮丧的事实:我们好像在聊一件事,其实我们在聊八件事,那七件我们根本不想聊的事情伪装成我们想聊的那一件事情,搞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聊什么了。所有聊天都是这么结束的,我们突然忘了原来在聊什么。我们偷偷地看对方一眼,觉出尴尬,并迅速道别。”
这是一条隐藏着的故事线:“我”从北京回到了老家,因为“我”成了一个被无聊而虚伪的成人世界“开除”的人。在形式上,“我”回来是为了“换换心情”、为了“和闲人聊天”;而在本质上,主人公乃是试图找回那已然沉没在水面之下的少年世界。“小孩吃包子”的故事,便是覆盖在少年世界之上的那一道水。“我”要找到这水,要像摩西分开红海一样分开这水面、穿过它抵达记忆中的黄金国度。这层故事,建基于当下现实经验背景(虽然相关元素并不浓重),同时又相当古老、带有某种母题性的色彩。
——最后,是一个哈姆雷特式自我怀疑的故事。与“我”不同,光明显然不想跟“少年黄金国”较劲。并且,光明是希望“我”长大的:“你就是太闲了,为什么非要想起来?想起来有什么用?你找工作了吗?没有工作你怎么结婚?小娟是个好女孩,你不要让她吃苦。”小娟是光明的妹妹,是“我”的女朋友。终于,我们来到了小说最核心的、却也是幽灵一般最飘忽的第三层故事。“我”不想结婚。“我”对生活、对人、对爱,似乎都是没有信心的。他不信任别人告诉他理应信任的一切,或许这在本质上是因为他不信任自己:他对自己可预见的未来、乃至“自我”本身,藏着一份根本性的怀疑。他“不确定”,故而“没想好”,并因此“说不出”。“我正努力发现她的优点,好下定决心跟她结婚。我不是装修不起房子,也不是不想装,我只是故意拖延。光明的意见就是从这来的……我喜欢她,但不确定这种喜欢能支撑多久……我爱她,毫无顾虑地爱,我爱她,所以顾虑越来越多。这种话跟光明怎么说呢,他现在连故事都不讲了。”
是啊,这样的话,怎么好跟别人讲呢?于是没有办法,只能去讲那些不相干的话,去讲那些徒劳的、无意义的、故意延宕的话。只能去追讨和回忆一个故事,而对“那个故事”的追讨,完整地构成了郑在欢笔下的“这个故事”——并且,在其中藏匿了更多更重要的故事。
这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但它是一种“有效的莫名其妙”:通过近乎通篇的“无效的说”,郑在欢把一些“不好说”甚至“不可说”的东西说了出来;甚至对于生活、对于围绕着生活的种种表述(“表述”的背后当然是“认知”),这篇小说还构成了对其无效性的充满悲哀的反讽。
因此,化用一下前面的“干货总结”:这篇小说,其实是把“变”与“隔”直接转化成了叙述的形式,在自我表达的可能性被不断耗尽的巨大焦虑中,完成了对理所当然的、“正常”而“正确”的故事形态的超越。这背后,是郑在欢小说世界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甚至形式:话语理性的大量丧失——即话语的失控现象——本身,恰恰承担着强大的叙事功能;它为作品提供了特殊的动力逻辑、表达形式,并直接指向小说的精神题旨。
本期推荐书目
《今夜通宵杀敌》
作者:郑在欢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1-11
编辑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