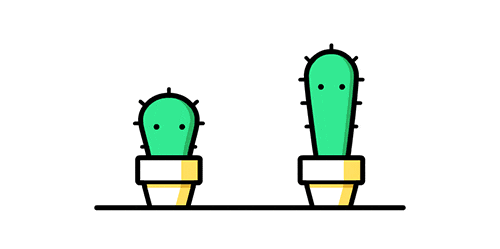顾城:我是一个放猪的孩子
1969年,13岁的顾城随父母下放到山东的一座小渔村火道村。在火道村,顾城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跟随下放的诗人父亲顾工一起喂猪放羊、割草拾柴……对于一家从京城来到乡间、爱好文学的人家来说,这正是诗意栖居,而这份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给顾城诗歌创作带来最初的启蒙与灵感。
诗人路也探访顾城青少年时期居住的火道村,寻找顾城的诗歌启蒙,在她看来,“顾城比很多人都幸运,命运给顾城送过一个叫做‘火道村’的大礼包。”下文摘选自路也新书《未了之青》,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顾城的渤海村庄》
01
循着少年顾城的足迹走一走
我抵达火道村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清晨。
这个大清早,村头不见人影。太阳渐渐升起,照耀着四处飘荡的云雾,“它们飘到了火道,/ 变成一个个空想。”村庄及村外的原野上,万物都在“肃静中呆立。/ 只有一颗新生的露珠,/ 在把阳光,大胆地分析。”夏天已经过去,曾经,就在不久之前,在这村庄附近,在潍河草滩上,在渤海的莱州湾滩涂上,“太阳烘着地球,/ 像烤一块面包。”而今时令进入深秋,抬头望见天空中一排大雁正往南飞,它们将“告诉慈爱的春天,/ 不要忘记这里的渔村。”
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我来此地,是想“在马齿苋 / 肿痛的土路上”循着大约半个世纪前某个少年的足迹走一走,寻找“像遗失的纽扣”那样星星点点地撒着的野花。
顾城1970年秋摄于山东火道村
就在刚才,在乘出租车开往这火道村的途中,那个本地司机,不断地向我介绍附近的地理及其变迁:车窗外,道路两旁,那些方形的蓝色水塘,是用来晒盐的盐池。此处是盐碱地,抽上来的地下水,都是浸进海水的卤水,这里离海太近了,难以打出淡水。这周围曾经都是渔村,后来,大约二十年前吧,北边填海造地,导致海水倒退了很多,建成农田和镇子。原本保留下来的不少盐池也正在逐渐减少,一些造纸厂化纤厂等污染企业都从市区搬了过来,另外,还有一些圈起来没来得及使用的荒地……车窗外不断掠过的那些大货车基本上都是拉盐的车,也有一些油罐车,动不动就拉上百吨,路面原本很好,刚修了没几年,就被压得坑坑洼洼了。
沿途的盐碱地上,很少见到大树,而以荆条为主的灌木居多,都变成了棕红色,倒是蛮好看的,还有一些就是矮细的小树了。途中经过白浪河和潍河,这两条河相距不远,在大地上平行着,都从这里入海,河汊子与海汊子相连在了一起,淡水渐变成咸水。经过一座桥时,看见潍河静静地仰躺在蓝蓝的天空下,火道村马上就要到了。往北拐之后,越接近大海,村子越少,火道村差不多算是最北边的村子了,恰好位于潍河入海口的一个海汊子上。
从这里再往北,就是码头和海边了。
村子及其周边地区,地势低平,明显有些空旷。想必在过去年代,建筑物少时,更加显得荒凉和旷远吧。就像那个曾经客居此地的少年所讲的:“从这个村子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最原始的天和地,正像中国古人说的:天如盖,地如盘,大地和天空都是圆的,你看不见其他任何人造的东西……你就永远站在这个天地中间,独自接受太阳的照耀。”那个少年就这样从“布满齿轮的城市”忽然来到了这僻远之地,独自站立在天地之间的荒野上,而荒野,有生长的力量,有繁殖的力量,有原创的力量,有孤独的力量,有异于平均主义的个性的力量。
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来火种。燧人氏钻木取火。唐太宗东征“道中取火”的村子被赐名“火道村”,也就是说当年唐王在此练兵,周边荒凉,找不到火来用,直到进入这个村子才发现了火。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前期,一个从京城来的少年又从这个村子里撷取了他的诗歌火种,由此以后,他的诗歌燃出了火花,并最终成为一场盛大的生命的篝火。1969年初冬,在离京临行前,在奔赴山东半岛的车上,在为抵达这个渤海村庄而迁徙辗转的半路上,这个刚满十三岁的少年一直在写着诗,他就那样一路写了过来。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写的每一首诗里几乎都出现了“火”的意象,他知道他即将抵达的那个村庄的名字里,镶嵌着一个“火”字。
这个少年,名叫顾城。
顾城一家四口在1969年—1974年从京城下放山东五年,恰是顾城进入青春期的十三岁至十八岁期间。据我的并不确切的统计,他在山东写下了差不多有二百首诗歌。其中除了跟随父亲顾工进入济南军区政治部在济南生活过一年并写过类似“路路连千佛 / 泉泉汇大明”之类的旧体诗之外,他的其他“山东时间”则均生活在潍坊昌邑县东冢公社火道村,即现在的昌邑市下营镇火道村。此处位于昌邑最北部,偶尔被简称为“昌北”,附近渤海之中那段莱州湾,有时也被称为北海,古时这一带曾设北海郡。
少年顾城在这个渤海边村庄里灵感四射,根据我的也是并不确切的统计,他在这里写下了包括《生命幻想曲》在内的至少一百二十首诗作。在每首诗的后面都标注了写作年代、写作地点甚至有的还约略注上了写作背景,比如:“1969,火道村”、“1970,潍河下游”、“1970.11.10,火道村”、“1970年元月,火道村”、“1970,火道,茅屋中”、“1970,下营村外”、“1970年东冢公社火道村”、“1970年二连,和爸爸煮猪食”、“1970,昌北农场”、“1971年夏,自潍河归来”、“1971年5月,火道,割草路上”、“1971中秋夜,火道小院”、“1971,火道,水塘边”、“1971年,牛车上”、 “1971年夏,火道村,草滩上”、“1972年2月,火道—农场路上”、“1972,割麦”……他几乎是在用诗歌来写日记,有时干脆以现代诗的形式从火道村给远方的长辈们写信。
顾城一家
我走进安静的村子。也许是为躲避海风之故,这里的房子与山东其他地域的高瓦明屋相比,明显盖得都矮了一些。村里的道路旁置放着很多当季收获的金灿灿的玉米,玉米堆成了圆柱形的堡垒状,外面还用丝网给罩了起来。村道两旁的白粉墙上画着彩色宣传画,有“盐村—火道”字样,看来这里也是晒盐产盐之地。忽然我发现墙上竟有一张彩色画像,看上去应该就是顾城,画得不是很像,但通过那顶头戴的牛仔布裤腿做成的筒状高帽,还是能辨认出是顾城,而不会是别人。看来这个村子里的人并没有忘记那个在这里生活过的少年,当然顾城也没有忘记这个点燃了他诗歌之火的村子,他后来经常提及火道村,并且说:“我是一个放猪的孩子”、“我是一个在盐碱滩上长大的孩子”。他在国外接受访谈时,一遍又一遍地谈及他少时在山东养猪放猪的经历,有一次采访完毕,最后一个提问是:“你觉得还有谁会同意你这些观点?”他回答:“我的猪会同意。”
并不夸张地说,顾城是在火道村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跟随下放的诗人父亲顾工在这里喂猪放猪,还养羊、养狗、养兔子、割草、拾柴火,同时写出了留待后来发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正式开启了诗人生涯。
02
“其实,顾城可不如你幸福!”
可能我来得太早了,村委会的小院里没有人,村委办会室上着锁,隔壁那间“火道村知青馆”,同时挂着“潍坊市青少年红色文化教育基地”的牌子,也上了锁。
我得找至少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人,才可能认识并且了解顾城。毕竟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十年了。遇到一个扫街的中年妇女,我打听顾城,她直摇头。这时有一个中年男人出来倒垃圾,我问及顾城,他说他什么也不知道,但他愿意领我去王校长家,认为王校长应该知道一些情况。
于是我见到了从火道村完小退休的王庭祥校长。王校长方形脸盘,高大健硕,看上去顶多六十岁,太年轻了,对于将近五十年前的事情,能知道多少?正在我有些疑虑时,王校长却说自己快七十岁了。哦?我一下子觉得有希望了。他又告诉我,顾城一家在火道村住过三处房子,住的第一处正是他家院里的一幢闲屋。哦?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觉得有戏。
王校长刚洗刷完毕,还没有来得及吃早饭,就被我缠上了。我们坐在他家堂屋沙发上聊起来。王校长记忆力很好,他开始了属于他的回忆:他与顾城的姐姐顾乡是高中同学,顾乡比他小一岁,属马的,今年该67岁了吧?顾乡一直在这里读完高中,而顾城在这里没上过学,辍学在家。他们上的那个高中叫昌邑县东冢中学。当时他在一班,顾乡在二班。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的,他记得很清楚,1969年12月8日开学,1972年1月18日毕业——那时的学期起始日期与现在也不一样——顾乡整个高中时代都在这里就读,她也爱写作。
顾城一家四口,刚来时,就住在王庭祥家。顾家住在东面两间房,王家住在西面两间房,还有一间是两家共用的。后来,顾家搬到了紧挨着王庭祥家对门另一家去住了,也是王家本家的一户人家,住在东厢房的偏房里。记得顾城母亲个子矮,人很和善,常常跟王庭祥的母亲聊天。他们一家到来的具体日期,已经不记得了,大约是1969年秋冬之交吧。
摄于火道村
火道村旁边,当时有一个6094部队昌邑农场,顾工下放到那里喂猪,一家四口则住在村子里,但其实他们既不属于部队上的人员,也不属于村民。跟顾城住在一个院子里,当时听到顾城说话的声音,声带已经变声了,想必应该进入了青春期,但顾城很少说话,出来进去的,基本上都不吭声。很久很久以后,等到已经出事了,才知道顾城后来所有那些事情的,还有朦胧诗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前两年,新西兰来过一个人,访问顾城住过的这个村子,当时录了一段录音,王校长在里面对着顾乡说了一段话,来人说带回去给顾乡听,但后来一直没有消息,也不知道捎信捎到了没有。
接下来,王校长一遍又一遍地问我:你能联系上顾乡吗?我回答他,我没有联系方式,但是愿意通过一些渠道间接地帮他打听一下。看得出,他迫切地想联系老同学。他遗憾地告诉我:“高中同学每次聚会,顾乡都没有来过。”
我想去看看顾城住过的老房子。在他们到来后新安置的家中,“忽然惊醒的火跳出了炉口 /吓跑了门缝中守望的星星”,他曾经“在昌北狭小的茅屋里,/ 蒸煮着粗粟黄米”,那小小的茅屋在夜晚“成了月宫的邻居。/去喝一杯桂花茶吧! /顺便问问户口问题。”
接下来,王校长自动提出来我去看看当年顾城住过的他家的那处老房子原址,以及住过的第二家房子原址,如今村子重新规划过了,顾城一家住过的老房子早已不在了,种上了树。我们往村外走去,过去的老房子的原址如今竟已经变成了村外。村子重新规划之后,过去的痕迹已经很少了,现在村子的主干路是东西走向的,路两旁是农家院落。
当年顾城一家四口住过的前两处的房子的原址,如今已经是一大片树林子了,旁边有石头碑刻,上写“知青林”。林子里种了些杂树,都长得不高,在这样的深秋,黄绿相间,大致有槐树,柳树、杨树、女贞、白蜡什么的、还有冬青月季等更矮的灌木。林子中间有一条窄小的甬路,把林子分成了两部分。王校长指着甬路的右边说,那曾经是他自家老宅,而隔着甬路的对面,紧挨着的那片林子,就是顾城他们住过的第二家的原址。树林子旁边竖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长方形红色铁框架,王校长指着那架子告诉我,这里本来是一块宣传牌,上面有对于顾城的介绍,结果风太大了,给吹跑了,只剩下了空的金属架框。
王校长领我沿着林子中间的小路,继续往村外田野方向走,可以看到空旷田野了,有一些已经掰了玉米棒子之后,没有被砍掉的玉米秸秆,枯干了,还成排地挺立在风中,迎接冬天。王校长说要带我去看一下不远处的干沟河,我们走到了一个很小的桥坝上,那下面是裸露着石块水泥的沟底,已经完全干涸了。王校长说,顾城在村里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个桥坝的,桥坝是后来修的,那时直接用扁担铁桶到这里来挑水,担回去吃,那时还没有自来水。他还告诉我:干沟河水来自峡山水库,河水很清澈,这条河的东边就是大片稻田,这里产的大米很好吃。我忽然想起那个少年描写村野之夜时的句子“星星混着烛火 / 银河连着水渠”,诗中的水渠,指的一定就是家门口这条有着来自峡山水库的清清水流的干沟河吧。
王校长告诉我,顾城一家下放来时,没有硬性任务,相比成天为口粮发愁的本村农人,他们基本上过着悠闲的生活。
大海、滩涂,一条又一条河流、草滩,蓝天、稻田、空旷四野、高天远地……想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前期,这个小村多么美啊,对于一户从京城来到这里客居同时没有太大生存压力的爱好文学的人家来说,正是诗意栖居啊。
顾城画作《计谋》
正说着,一个汉子带着一个女子,骑摩托车过来了,摩托车上还横放着农具。王校长拦住他们,简单地为我们相互介绍彼此,说,真巧了,这就是顾城住的那第二家的人了,也姓王,是本家,当时我们两家住对门。然后又对摩托车上的来人说:“记得你们家大哥那时候常到这不远处的干沟河里给顾工一家挑水。”摩托车上的人叫王维湖,比顾城小七岁,顾家住在他家时,王维湖也就六七岁的样子,已经记事了。王维湖现在应该有五十六七岁了,但看上去顶多五十出头。夫妇俩刚刚大清早从田里干农活回来,摩托车上横放着锄具,后座上坐着媳妇,二人就坐在停下来的那辆摩托车上,跟我们说话。女人穿了红毛衣,不吭声,只用手扶靠着丈夫的后背,坐在后面座上。王维湖的童年遇到了顾城的少年,在一个庭院里度过。王维湖也提到,顾城不爱讲话,他们家人跟村民交流都不多。接着又说,在他的童年印象里,顾城的父亲常常在家读书写作,同时教顾城念书。他想了想,又提及,有一次顾城的父亲从部队带回家一只刚出生不久的黑色的小狼狗,顾城就跟那只狗一起玩。王维湖提到狗,让我想起顾城后来确实专门写文章回忆起在火道村养过的几只小狗的故事。
看得出王维湖不是爱说话的人,但关于顾城的说题,他还是挺愿意跟我交流的。我问他:“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顾城是个诗人并且关于他后来的故事的?”他说:“也就是近十来年吧,有人来访,才知道的,市电视台为了拍片来采访过我母亲。”
接下来,我问了一个很庸俗的问题:“顾城一家当年住村民的房子,付租金吗?”王维湖微微露着笑意说:“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们不会去想这种问题,谁家有空闲房子,公家派下来,都会答应。”接着他又补充了一下,部队当时还在他家里设了一个专门放东西的仓库。
我们聊着聊着,忽然这个老实敦厚的汉子有些动情地提高了嗓音:“这里的人想念他们一家!”
我问起小时候住在一个院子里,他跟顾城在一起玩的时候多不多,他有些羞赧地说:“人家是读书人,有成绩,与俺们不一样。”听了这话,我特意看了一眼他摩托车后座上的安安静静的媳妇,认真地对他说:“其实,顾城可不如你幸福!”他听了我的话,默然。其实我在心里还悄无声息地对摩托车后座上的女人说了一句:“假如谢烨有前后眼,让她与你对换,她也许宁愿像你一样当一个农妇。”是啊,看到他们在摩托车上相依偎的样子,想想顾城谢烨他们魂断激流岛,那么,谁能告诉我,究竟何谓幸福?
顾城和谢烨,1986年在成都,摄影:肖全
王校长又领我去看顾城一家住过的第三个地方,村西头一处闲房的原址。而我记得顾城回忆火道村时,清楚地说他家先是住在村西,后搬至村东,为何现在却变成了先住村东,后来搬到村西?究竟谁的记忆有误呢,还是大家记忆其实都没有错误,只是村庄重新规划导致相对方位发生了改变?
王校长领着我快走到这第三处房子原址时,特别告诉我,这个原址本来在村西头的路北,而后来对村庄进行了重新规划,使得道路发生变化,这个曾经的路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的路南了。
我老老实实地告诉王校长,应该是从今天早晨一进村起,我就掉向了。我感觉里的方向跟别人告诉我的方向都是完全反着来的。
从小到大,我的方位感一直特别强,并引以为荣。而人到中年之后,竟像是发生了基因突变,一旦来到一个陌生地方,无论这个地方的布局多么简单明了,我都很有可能会掉向。如今的解决办法是随时随地请教他人:“请问,哪边是北?”“请问,哪边是东?”,或者干脆开启智能手机里的指南针功能,总之要对自己的方向错觉从理性上进行强行校正。
顾家一家四口在这个村西头的第三处住处住得时间最久。村西头路北有一家闲置房,他们当时就住在那里,现在原址已拆掉了,在上面重新盖了房子,房子看上去也显旧了,院里杨树在此地已经算得上粗大,但也是后来才种上的。
村子里如今只剩下了唯一的一幢当年的老房子,就在顾城一家曾住过的房屋原址的对面,也就是南面,两院紧挨。这个遗留下来的院落看上去像是半个四合院的模样,房子是传统的瓦房,院里的槐树枝子高过屋顶,房子像是后来被粉刷成了白灰相间的两色,朝向村子的一面有两座房屋的山墙和屋脊,还有两屋之间搭建的平顶屋的木棂玻璃窗,而朝向村外马路的那一面,成了门头房,是一家办理中国移动业务的小店,门上横挂着一个天蓝色大牌子,上写“田园通信 办卡缴费 名牌手机”。
当年顾城每天走出自己的家门,首先看见的就是对面这处院落。
顾城,摄于1957年8月
在那里四处观望时,遇上了一个据称跟王校长年纪相仿的人,家就住在这第三处的原址附近。王校长叫住他,我们一起聊了聊。我问他:“你见过顾城吗?”他说:“当然见过了,天天住对门!”接下来他提及,顾城见了人不爱说话,他不上学,就在家里玩,一家四口有一辆自行车,那时有自行车的人家很少,他们一家四口常常在土路上骑行,前面骑着后面带着,很让当忙于劳作的贫穷的村里人羡慕。接下来他又补充道,他们与村民来往不多,一家人常常自己去赶集买菜。
在北京时就不怎么上学,来了山东也不上学,为什么顾城不上学呢?这个在我脑子里盘桓不去的问题,也是很多人共同想问的一个问题。你问我,我问他,他又来问我,到底问谁去?这个问题,既是一个问题,同时也不是一个问题。反正,那个任性的孩子,那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就是不上学,不想上,不愿上,那就不上呗。在来山东渤海边的村庄之前,顾城早就在大脑里构想出一个颇具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布林”的形象,布林既是他臆想中的朋友同时也是顾城他自己,布林逃学,不想上学,在家一直忙着自己喜欢的事业:金属冶炼和加工食品饲料喂养小动物。布林这个形象存在了很久,偶尔被忘记,终又被记起,并一直持续到新西兰激流岛上。顾城后来以布林为主人公把一首寓言长诗断断续续地写了十年以上,颇具自传性质。布林懂得“没有目的”的重要性,布林活在这个世上,只追求有意思和有趣。
那个不上学的少年,跟着爸爸一起养猪,每天煮拌猪食,由于饲料缺乏,猪都饿得瘦骨嶙峋,于是只好把猪赶到盐碱地和河滩上去,让它们自己找草吃。当爸爸在河里游泳时,少年拿着棍棒在距离大海不远的河滩上写诗,而猪们则早已跑得不知去向。
03
从诗歌角度讲,顾城何其幸运
接下来,我跟王校长道别,从火道村继续往北去。北行大约五公里,到达了海边。当年顾城他们一家,经常到这海边来。
接近下营镇的码头时,沿路可见做水产的店铺公司,途中摆放着一些腌蟹子做虾酱的大缸。码头是一个岸堤直立的小海湾,停靠着一些较大的渔船,也有几艘属于渔政上的大客轮。
继续往北走,就看见了大片大片的海滩和辽远的大海。潍坊的海岸线,主要分布在从昌邑到寿光一带,这里的地形为平原,天然礁石很少,滩涂基本上均为泥质,面积称得上广大。看见了一艘艘的渔船,彼此相隔不远,要么在滩涂上停靠着,要么在青蓝色海面上漂浮着不动弹,那个少年诗人当年曾经写到这里的大批木船:“它们像是疲乏了,/ 露出宽厚的脊背,/ 晒着太阳。”他还有些动情地表达志向:“在文学的大海边畅饮。”
成群结队的白色鸥鸟栖落在滩涂上,聚在某一处避风避浪,扎堆晒太阳,远望过去就是一些密密麻麻的小白点,几乎静止不动,也许是在开大会吧,还有一些则三三两两地在浅海里游弋着。我头一次知道,海鸥不仅会飞翔和行走,还会游泳。
在海边滩涂上,在附近的野地里,常常会看到一簇簇的发红的野菜,紧贴地皮生长着,在生长得多的地方,望过去,会连成一大片。不知它们本来就是这么红呢,还是由于季节原因,由绿变成了红。当地人告诉我,这叫黄细菜,这里的盐碱地上生长着很多,人可以吃,猪也喜欢吃。看来当年顾城放猪时,应该是专找这种生长着黄细菜的地方吧。
“把我的幻影和梦 / 放在狭长的贝壳里 / 柳枝编成的船篷 / 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 / 拉紧桅绳 / 风吹起晨雾的帆 / 我开航了//没有目的/ 在蓝天中荡漾/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天微明/海洋挤满阴云的冰山……我到那里去呵/ 宇宙是这样的无边……”
我在心里一遍遍默诵着这些熟悉的诗句,忽然意识到,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生命幻想曲》是完全凭借一个少年人的想象力而写成,这个认识是不对的!此诗中的想象固然极其飞扬,非一般人可比,但毕竟“诗是经验”,只有到了这火道村附近的海边,才真正意识到,1971年夏天写下的这首诗的内容和节奏,以及这首诗中的辽远和旷漠之感,恰恰来自那个十四岁少年的个人经验,来自这潍河尽头的海滨。
他们从京城到外省乡间暂居,虽无亲无故,好在所遇民风淳朴。既不属于部队人员也不属于村民,这种特殊的位置和身份,使得他们在那个剑拔驽张的时代反而能够保持着疏离的神情,拥有了一种从集体分离出来的相对个体化的生存形式,在不自由中获得了自由。既最大程度上远离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既刺耳又高亢的喧响,同时又不太有当地村民的物质之困,物理和心理的双重距离使得审美得以产生,再加上那种与大自然互动中的格式塔心理学效应,于是,一个少年的禀赋在无意识之中被发觉,在没有目的的状态下被开发,《生命幻想曲》从观察、直觉和天启之中产生出来了。
不早也不晚,恰恰就在青春期的最敏感阶段,在审美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上天安排一个天才少年从中心城市来到偏远乡间,让大自然做他的老师,教导他人的生命与万物的生命是共通的,与此同时,又使他得以巧妙地躲避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滚滚洪流。而当他在外省乡间完成了自我天赋的启动,时代的表情忽然变得温和与松驰起来,少年正在变成青年,又得以返回京城,带着他在海边村庄写下的诗篇,带着他取来的灵感之火,进入了一个文学可以催眠、诗歌可以让人中蛊的时代,于是他成为了新诗潮的代表人物。从诗歌角度来讲,顾城何其幸运,他比很多人都幸运,命运给顾城送过一个叫做“火道村”的大礼包。
顾城在火道村及其附近,留下了那么多黑白照片,无论在田野里还是在庭院中茅屋前,无论与猪合影还是与羊合影,都是有笑容的,神情舒展。那上面的那个少年,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走到哪里都戴着一顶半截裤腿般的高帽子,那上面的少年,长得好看,眼睛里有星辰大海。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不远不近地,从半空中传来了很大的炸裂的响声。站在后来为防潮水和为养殖而修建起来的海中长坝上,望向海的另一侧,那里有一道部队专修专用的海中坝,上面有一丛一堆的东西,专为打靶之用,射击朝着警示区域之内的无人的外海。刚才的炸裂声来自正在海上练习打靶的部队,据说济南军区也常常有过来打靶的。这不由得令人想起这昌邑北部一带在战国时期曾经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军事家孙膑的采邑,这里的民间一直就有专供孙膑的庙宇。
那个天才少年从火道村走出去之后,只活了二十年。他辗转国内各地及世界各地,生命终止于新西兰激流岛。他在那南半球的荒凉的岛上时,想必也常忆及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山东渤海边的小村庄吧,对于一个社会化极弱的人来说,二者确乎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那个少年一直拒绝进入成人世界,自始至终都不肯被社会化,他最大限度地排斥着外界社会,而那种由诗歌文本终至人格内核的极端“纯粹”之中已经悄悄地包含了一种可怕的成分。好像尼采说过,人在孤独之中,一切都可以获得——除了精神正常。
这个天才诗人离开世界的方式是惨烈的,先是将爱人打伤至死,又用一根绳子将自己挂在了树上。关于此事的各类评论已经太多,以致于我不想再发任何议论了。我只想说,他最后的行为,让像我这样如此喜欢他的诗歌同时也喜欢他的人的后来者们,情何以堪?如之奈何?
中国的火道村与新西兰的激流岛相距何其遥远,而那里的海与这里的海毕竟是相通的。诗人的墓床,根据他在晚期诗中的想象应当是在海边,在松林之中。他认为自己死后,“人时已尽,人世很长 /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此句似乎呼应着他少年时代在渤海边的村庄里所写下的那个著名的句子:“睡吧!合上双眼,/ 世界就与我无关”。
本文节选自
《未了之青》
作者:路也
出版社:中国旅游出版社
出版年:2021-10-1
编辑 | 仿生斯派克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