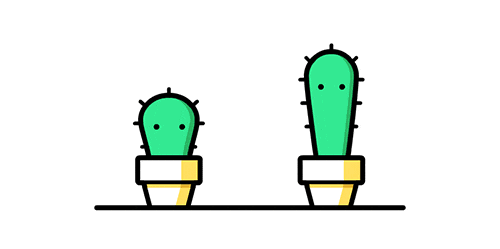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我读过社会这本无字之书
被高中开除之后,章开沅跟着船老板做起了打杂的船工,念起了所谓的“长江大学”。然而实际的生活没有他想象中潇洒,周开沅在船上帮不上什么忙,只有做账的时候才能显显身手。
而且对他而言,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无书可读”,所以他转而读起了“无字之书”,也即身边的船夫和沿途的风光。
章开沅(1926.7.8-2021.5.28),历史学家、教育家,曾著《辛亥革命史》《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等
本文选自《章开沅口述自传》,彭剑整理。
01
“长江大学”入学记
再次被开除,我觉得对不起大哥,不好意思再到他那里去了。这个时候,真觉得自己就像鲁迅笔下的狼,受伤之后,只有忍住疼痛,独自跑进森林,舔干净身上的血痕。不过,实际上,我还没有那么孤独。被开除之后,我得到九中和计政班很多同学的帮助,很多温馨的场景,终生难忘。
在九中和我同年级的周承超,在1943年底高中毕业,但大学的招生考试在暑假,因此,有半年时间,只能在家里复习备考。他和他叔父的一个儿子住在重庆郊外的一座房子里复习功课,房子是他叔父的。他叔父不住那里,住在城里,但给他们留有米、面,还有一些买菜的零花钱。周承超得知我又被开除,毫不犹豫地收留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和周家兄弟住在一起。
九中略影
计政班的同学得知我被开除,对我深表同情。他们曾经在同学中间发起捐款,然后托人交到我手上。虽然杯水车薪,大多都是一毛一分的小票子,但确实温暖我心。
在周承超兄弟俩考取了大学之后,我不好意思再在那里住下去。此时,“吃蚕豆不吐蚕豆皮”的马肇新同学向我伸出了援手。他的父亲是一位教授,认识一个船老板。他向船老板介绍了我的情况,居然把那位船老板说动了,愿意收容我。
船老板是湖北人,拥有两条船,专门跑运粮业务。战前国家向农民征收田赋,是收钱的。到了战时,为了保证前方和后方的粮食供应,改为“征实”。“征实”就是征收实物,由国家统一支配。国统区的粮食,都运到重庆的粮食部仓库集中,然后又从重庆运到各地。这样一来,就需要有一批人来专门从事运输工作。这位船老板,就是其中一员。他人很好,见了我之后,一个劲地安慰我:“你现在的困境只是暂时的,以后还是会有前途的,千万不要想不开。”又说:“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
船老板如此热心,我就登上了他的运粮船,做起了打杂的船工。前些年与池田大作对话的时候,我开玩笑说,我曾经是“长江大学”的学生。时隔多年之后回过头去看当年发生的事情,心情当然很轻松。在登上运粮船的时候,可没有这么洒脱,认为自己从此成了“长江大学”的学生!
不过,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很灰暗。毕竟,在无法继续在周家蹭饭的情况下,又有了新的糊口之处,怎么说都值得庆幸。何况,这次好歹不是完全蹭饭,而是打工,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饭吃,虽然船老板未必看好我的劳动力。那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奇异的想法,觉得自己从此走上了高尔基之路了。高尔基曾经在伏尔加河流浪,我则在长江上流浪,这不是太相似了么?因此,我还有过一点幻想,想着自己将来可以做高尔基式的作家。我似乎离自己的作家梦近了一步。
02
学习如何当船工
我在“长江大学”的基本“功课”,是学习如何当船工。当船逆水而行的时候,我参与拉纤。顺水的时候,我就帮忙烧火做饭。说起来好像每天都有事情要做,其实我所起的作用有限,最多就是一个打杂的角色。
不过,我也有起关键作用的时候。作为运粮的船家,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必须处理好与相关人员的关系,比如说验收斗工,比如说当地仓库主任。斗工很厉害,在我眼中,简直就是神通广大。粮食出仓进仓的时候,都靠斗工。斗工在用斗量粮食的时候,一个动作,可以叫大米都站起来,换一个动作,可以叫大米都躺下去。与斗工关系处理好了,他可以直接让运粮食的人增加收入。如何与斗工处理好关系,这不是我的强项。
但我可以帮助船老板处理好与仓库主任的关系。仓库主任也是决定船老板收入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严一点,船老板的收入就少一点;他松一点,船老板的收入就多一点。船老板知道我学过会计,当粮食运到泸县入仓的时候,他就故意向仓库主任透漏这一消息。仓库主任很高兴,说:“请这个小朋友来帮我做一天账吧。”
原来,仓库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会计,他们的报表往往不大规范,因而常受责难。他说有好多张数据表,准备让我帮他做一天。我正儿八经学过会计,他的数据又是现成,因此做起来很轻松。三下五除二,个把小时就做完了,清清楚楚,中规中矩。至于数字是否准确,那我管不了。仓库主任一看,赞不绝口,请我吃饭,亲自作陪,加了好几个好菜,还备了泸州大曲。这是我在流浪生涯中,享受的一次难忘的高规格待遇。船老板也很高兴。当然,收获最大的肯定是他。
船上的伙食很不错。由于是运送粮食的,每餐都可以敞开肚皮吃白米饭。过险滩的时候,还有加餐,一天吃五顿,供应大块大块的粉蒸肉。吃饭的时候,几坛泸州大曲就摆在旁边,里面插几根芦苇秆,想喝的,对着芦苇秆一吸就行了,根本用不上酒杯。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居然有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好日子,我有时甚至怀疑是否身在天堂。我不能大口喝酒,但能大碗吃饭,大块吃肉。由于前面一段时间老吃“八宝饭”,现在突然有了好吃的,结果一下就吃坏了,胃呆。不过很快又恢复了,继续大碗吃饭,大块吃肉。
船上生活最不方便的是无书可读。有一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看到有两张报纸,几乎是完整的,不知是谁捡来,准备当引火材料。我立即眼睛一亮,决定“以权谋私”,把它们“贪污”了。那种感觉,真的像突然发了一笔横财。有一段时间,一有空闲,我就坐下来看那两张报纸。从头到尾地看,反反复复地看。到后来,连中缝的广告和启事都能够倒背如流了。
但在那之后,我没有得到过第二笔“横财”,无书可读的境况并无改变。不过,有有字之书,有无字之书。无有字之书可读,我转而读无字之书。我身边的船夫、沿途风光、社会百态,都是我的无字之书。
03
最危险的地方叫"寡妇漕"
除了无书可读,我的另一苦恼是没有换洗衣服。由于未带行李,我在船上只有身上穿的一件破汗衫和一条短裤。无衣服可换,只好在晚上搓一搓,第二天再穿。
一般水手都没有我这种苦恼。他们一般只有一件破大褂,顶多外加一条破裤子。拉纤的时候,一丝不挂。为什么会这样?倒不是没有钱买衣服。他们的收入其实还可以,但大都吃喝嫖赌,抽鸦片,胡乱花掉了。之所以会这样,是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川江险恶,随时都可能翻船。
我们所走的从重庆到泸县那一段水路中,最危险的地方叫作“寡妇漕”。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凄清的名字,是因为此处长江被巨石劈为两半,突然急转,水急浪高,异常险恶,船经此处,必须非常小心,经常有船在此出事。水手落水身亡,家中只剩下孤苦的妻子,“寡妇漕”的名字即由此而来。在这样的江段上航行,水手们安全没有保障,早上开船,晚上能否活着到岸都是问题,因此有钱之后,大都及时行乐,醉生梦死,不顾将来。
但也不是人人都如此。比如说我们的舵工,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四十多岁,身材魁梧,爱喝点酒,但不抽大烟,更无其他不良嗜好。开船的时候,往舵桥上一站,威风凛凛,目光如炬,举重若轻,像大将军一样,所有水手都听他的号令。他不依靠任何仪器,根据水花与河流的情况,就可以对河床险阻做出准确判断。我对他佩服极了,作为“长江大学”的学生,他就是我的导师。
舵工和我一样,有点洁癖。水手们晚上都睡在船舱里面,他一个人睡在舵桥上。我才上船时,也被安排睡在船舱里。但船舱里睡二三十人,鼾声很大,此起彼伏。有些人卫生习惯又不好,空气中总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我突然明白老驾长为什么不睡船舱了。于是抱起那块作为垫絮的破毯子,也睡到外面去。老驾长睡舵桥上,我睡舵桥下。这才发现,清风明月,取之不尽,川江之夜,如此美好。
慢慢地,与老驾长混熟了。在月明星稀的夜晚,他敞开心扉,对我讲自己的故事。原来,他曾经有过非常美好的生活。有一个寡妇,即船老板,看上他了,他们结了婚。不幸的是,有一次出船,狂风暴雨,船撞碎了,太太被急流冲走,只有他自己幸免于难。他很怀念他的太太,终生未再娶妻。
他告诫我,不要学那些醉生梦死的水手,糟蹋自己。他还对我说,他瞧不上我们船上那个领唱,太娘娘腔。他说他见过好的领唱,天气好的时候,一嗓子出来,声音就像渗透到了江水中,悠悠扬扬,上下二十里都听得到。我无缘见到他所说的好领唱,只观察过我们船上的领唱,人长得瘦弱,歌声确实不那么雄浑,有点柔弱。
但领唱和舵手都是船上的要角。舵手的工资是普通船工的四倍,领唱的工资是普通船工的两倍。舵手掌握全局,领唱则唱着号子指挥大伙摇橹、拉纤,组织劳动。他们的配合,非常重要。好在老驾长虽然不太瞧得起领唱,但在关键时刻,配合得还不错。记得我们有一次过“寡妇漕”,正好碰到大风雨,桅杆折了,船一下子就被打横了。那真是全靠他们两人配合指挥!
那个时候,号子就不是一般的美妙歌声了,大家呼天抢地,撕心裂肺。真没想到,那些平常让人觉得醉生梦死的水手,在那个时候居然有那么大力气,那么齐心协力。我也跟着大伙尽力地喊着号子,投入到那场生死搏斗之中。最终,我们化险为夷,通过了“寡妇漕”,没有葬身鱼腹。
04
我这个膀子,被人一掰就断了
我们走的那一段川江,除了“寡妇漕”,还有“三抛河”。这一段川江呈“之”字形,水深流急,涡旋甚多,绝对距离虽然不长,但必须反复绕道穿行,很费时间。船在早上进入这一江段,不论怎么努力,等到绕出去,肯定已经日暮黄昏。也许正是这一缘故,在“三抛河”的两头,都有小小的码头。
那一天,暮色渐浓的时候,我们走完了“三抛河”。吃完晚饭,水手们穿上“百衲衣”,上岸去及时行乐,我也跟着去参观。船老板叮嘱我们:“晚上早点回来,老老实实睡觉,不管外面有什么动静,都不要打开舱门,不要理睬。”
那一晚没有月亮,山风吹得树木沙沙响。爬了好多青石台阶,看到了一个建筑。近前一看,是一座破庙。破庙的前面,有一个破戏台。破戏台上,几个穿着破旧戏装的人在沙哑地唱。唱戏的也好,看戏的也好,一个一个都黄皮寡瘦,在昏暗的光线下,似人非人,似鬼非鬼。我无心看戏,转到大殿闲逛。佛前一盏桐油灯,在风中摇曳欲灭。地上铺着些破席,上面东倒西歪地躺着些人,就着烟灯抽鸦片。在大殿的另一角,一盏较明亮的煤油灯前围着一些人,在那里赌钱。我的很多同伴,立即奔向那儿。
原本想着可以欣赏一些美景的,没想到竟是如此悲惨情境。好不容易等到那些同伴过了赌瘾,大家结伴回到船上。老驾长已经在舵桥上躺下休息,我轻轻地在舵桥下铺上破毯,望着深邃的天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以前我觉得小煤窑的工人已经是天底下最悲惨的了,没有想到还有比他们更惨的。煤工的惨,是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造成,船工的惨,则是自我堕落、自我摧残、自我麻醉造成。
想着想着,我闭上了眼睛,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还是被老驾长叫起来的。
“你这个小鬼,睡得真好!昨晚出大事了,你知道不?”老驾长问我。
“什么大事?”我一脸茫然。
原来,昨天半夜,来了一群土匪,把停泊在这里的船只抢劫一空,唯独我们这两条船好好的连一粒大米都没有丢。被抢的船老板,一早遣散了水手,弃船而走,各奔东西。
“为什么我们的船没有被抢?”我问老驾长。
老驾长告诉我:“船老板的帮手老王以前当过土匪,虽然后来洗手不干,但和那些人交情仍在。土匪行动前,他得到了消息,就告诉了船老板,船老板请他向土匪说情,并送了一些钱财,这才免受一劫。”
老王中等身材,但是非常精壮。初次见面,他就瞧不起我的细胳膊细腿,大声说:“你这个膀子,我一折就两断了。”我真有点怕他,不大敢与他攀谈。其实他对我挺好,对我的遭遇表示同情,只是觉得我太瘦弱,做船工实在没有前途。
05
告别川江漂流生活
我当船工的时间不长,大概前后就两个月,但自己觉得收获很多,学到很多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我很乐意在川江继续漂泊,多积累一些船工生活体验,但竟然未能如愿。
川江流浪期间与家人团聚
原来,在计政班读书的时候,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到大哥那里聚一聚。被计政班开除之后,我不好意思告诉大哥,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去他那里,害得他心急如焚,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还是找到马肇新,才知道我在一条运粮船上打工。他约了也在药专就读的三哥开诚,在我那条船必须停泊的码头守候。结果,我一上岸就被他们拦住,并且一同向船老板致谢告辞。临别时,好心的船老板还悄悄塞给我一些零花钱。
相遇之后,哥哥们没有责怪我,只提出来一条:以后不要再乱跑了。为了加强警示效果,他们还请来稍大一些的小叔祖,对我进行训诫。所谓训诫,其实也很客气。他几乎是用恳求的口气对我讲:“你以后就不要去干那种危险的事情了吧。你看,我们从安徽漂泊到这里,多么不容易。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我们怎样向祖父与你父母交代呢?”确实很受感动,自己也觉得有愧于家人,因此决定暂时搁下川江漂泊的浪荡生涯,安分守己,自食其力。
本文节选自
《章开沅口述自传》
作者: 章开沅(口述) / 彭剑(整理)
出品方: 谭徐锋工作室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5-11
页数: 417
编辑 | 白羊
主编 | 魏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