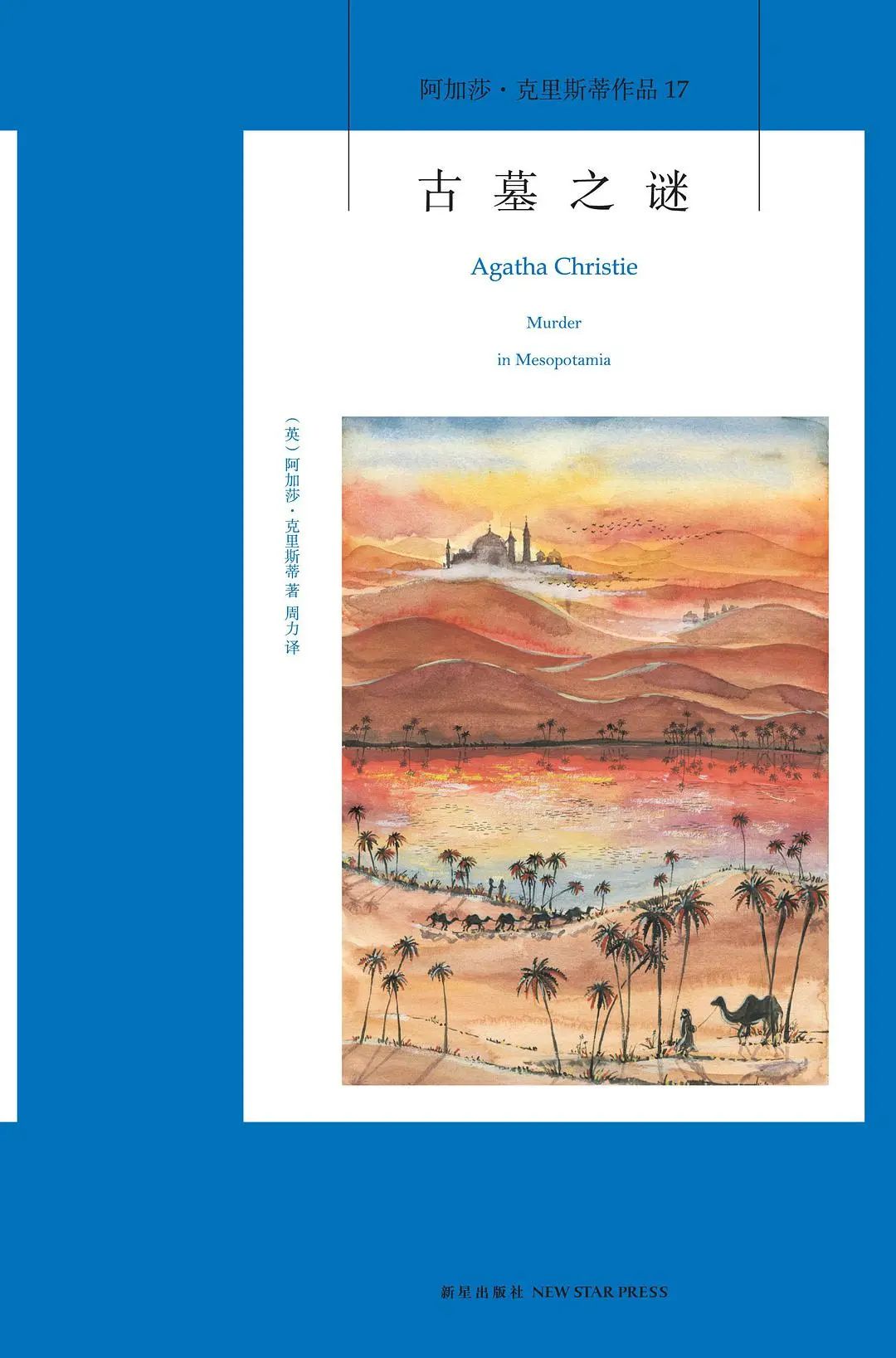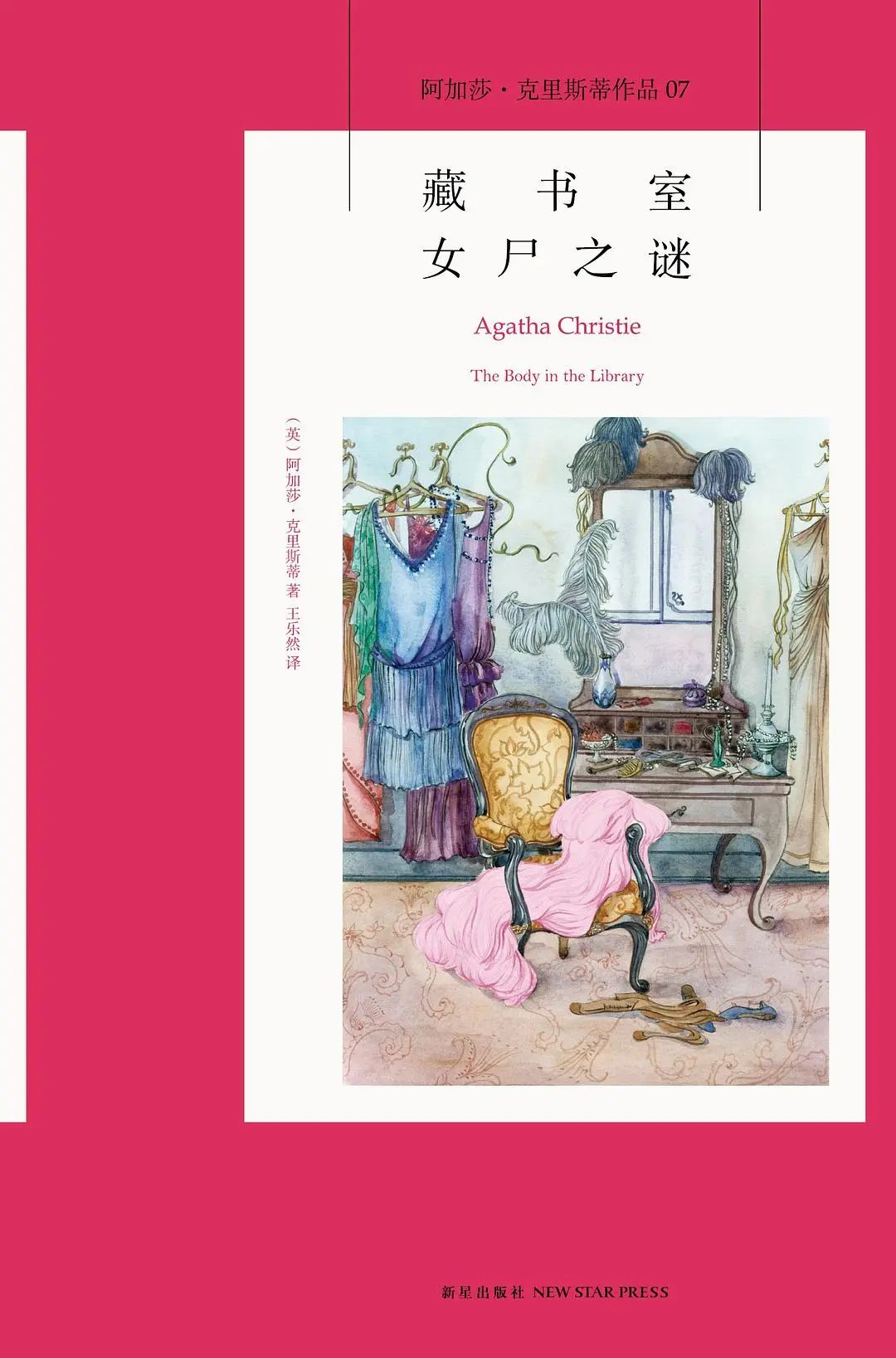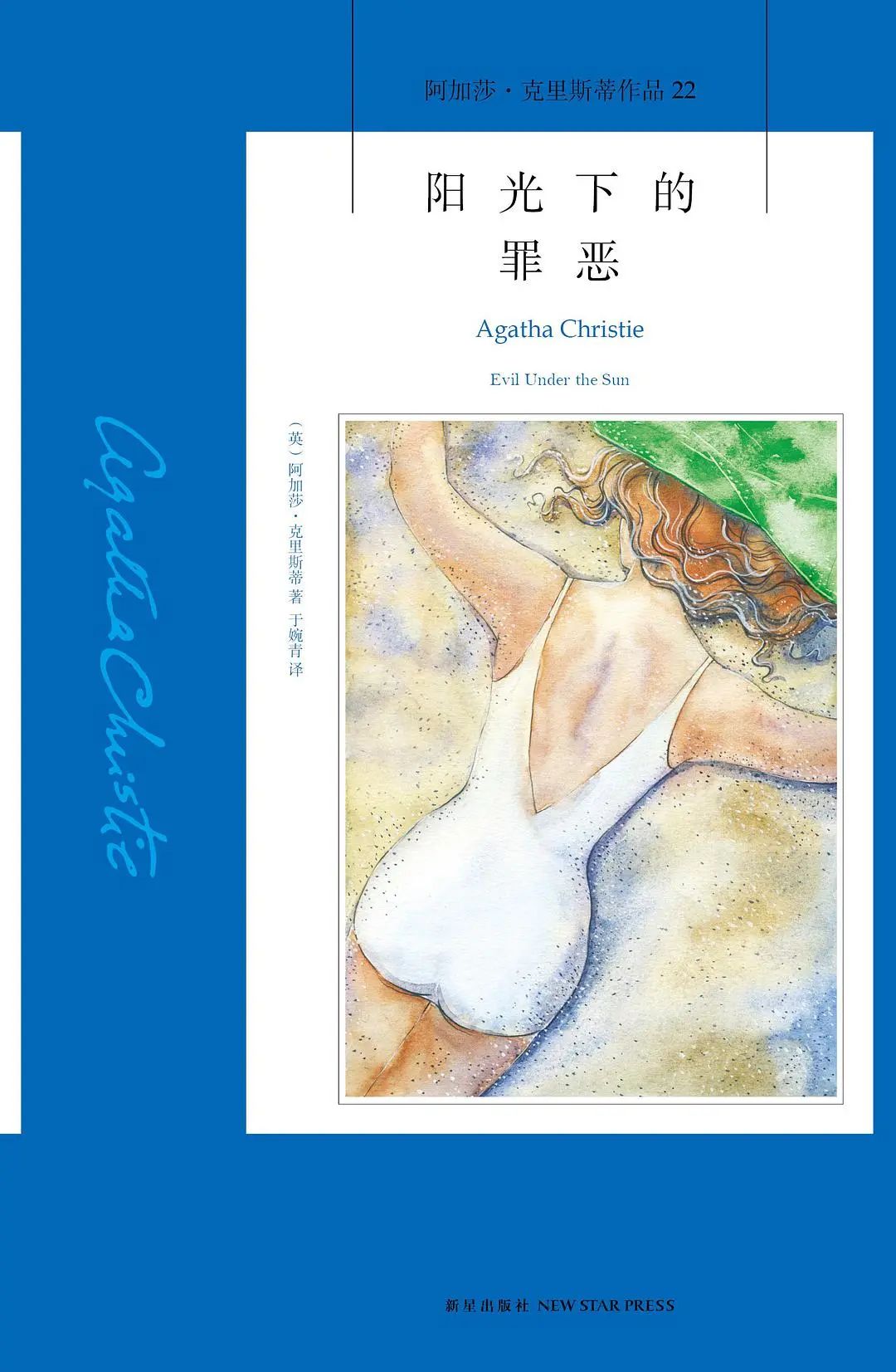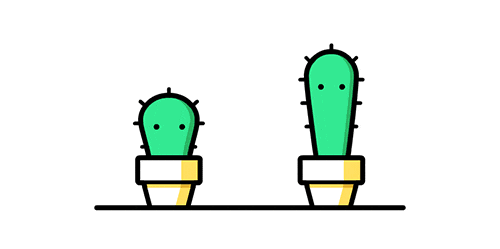王安忆:读阿加莎单纯就是享受
《华丽家族》
一、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读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感受相当单纯,那就是“享受”。
你可以放弃意义的追寻,径直进入故事。她不会让你失望,一定会有神秘的死亡发生,然后,悬疑一定有答案。好比波洛在他的事务所里等待案件,而终会有案件找上门来。
你不必去推敲,难道真的会有如此多的谋杀案件?因为这是与现实无关的,你早已经卸下现实批判的武器,身心轻松,只等着听故事。可是,事后要细究起来,却发现故事中的人,分明又是生活中的面目,情节也是根据日常的情理,是你我他全能了解的。
反倒是那企图超出共识的现实,比如少数几部间谍故事,震惊的效果比较减弱。所以说,这些令人着迷的故事,其实是囿于现实,在生活的范围内索取材料。
也所以,要是检点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你又会发现,故事的要素很简单,不外是争夺遗产、欺瞒历史、谋骗钱财、恩仇相报。然后再派生出敲诈,灭口,掩藏。人物呢,又总是一个家族、一间寄宿舍、一艘游轮,或者一列客车,甚至只是一个晚会和一餐宴席。
这多少也能看出女性写作者较为狭小的社会以及居家的性格。就是这些简要的因素,却组织出这许多故事。这又使我想到女性的另一项技能,就是编织的技能——竹针,毛线球,编织法,竟可以生发出无穷无尽的花样。
那乡下老太婆马普尔小姐,从不离手的毛线活儿,大约也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手里的活儿。这还像一种小孩子的挑绷的游戏,将一根棉线对头打个结,双手撑开,挑出一个花样,再由对方挑过去,形成第二个花样,两个人挑过去,挑过来。
倘若是聪明的小孩,可挑出无数种图案,而要是笨小孩,没几个回合就挑成一团乱麻。阿加莎·克里斯蒂就是那个顶聪明的挑绷能手。她用有数的条件,结构出大量的谋杀,线索错综复杂,就像编织活儿和挑绷上美妙的经纬组织。
这些线条和结构,都是以日常生活作材料,这种材料的具体性,覆盖了抽象的结构图案,给予了可以理解并且引起同情的现实面貌;同时,内里结构的抽象性,又将它们从现实中划分出来,独立为另一种生活。
《古墓之谜》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很像是一种成人的童话,我想,孩子们所以能被童话吸引,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那些精灵是真实存在的。而成人在阅历中储备起的知识和认识,占去想象的空间,排除了信赖的条件,于是,精灵退出成人世界。可是,就像一种进化不完全的后遗症,成人依然保留有对不寻常事件的好奇心。
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认可的人和事,讲述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故事——没有比一桩杀人案更令人兴奋的了。离奇故事里的每一个细节,她都负责给予让我们信服的解释,就像《古墓之谜》里,波洛所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阿加莎·克里斯蒂就能够将一切事情解释得清清楚楚。
而且,她不是求精辟,而是务实际,就像方才说过的,倘若阿加莎·克里斯蒂要讲述一个超出常理的故事,比如间谍类的,《暗藏杀机》《犯罪团伙》《桑苏西来客》等,无论是罪行也好,侦破也好,所根据的理由就都悬了,显见得不是她的强项。
我觉得,马普尔小姐的案件最体现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性质,那就是她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中说的:“一年到头住在乡下,人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人性”。阿加莎·克里斯蒂编织故事的线索,究其底就是“各种各样的人性”,而且就是“一年到头住在乡下”所能看到的人性。因为,马普尔小姐坚信一条:“人性都是相通的”。
以此可见,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犯罪,都是出于通常的人性,绝不会有现代犯罪的畸形心理。比如像英国当代推理小说女作家,露丝·蓝黛儿所写《看不见的恶魔》(台北新雨出版社),那个老罪犯,专门在黑暗的狭长的街道上,袭击金发碧眼的年轻女郎,当他在公寓地下室发现一具同类形象的模特儿之后,便将袭击冲动转向这个橡皮人,因地下室亦有着黑暗、狭长的空间,能够让他在渐渐逼近对象时,积蓄起兴奋感。不幸的是,这具橡皮模特儿被小孩子在游戏中烧毁,于是,地面上就又开始发生一连串的谋杀案。
在此,谋杀便成为一种奇异的癖好,说是谋杀犯,其实倒更像是一个病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谋杀则有着常规的理由,悬念的设置和解答都不超出普遍人性的范围,而且一定解答透彻,也就是“解释得清清楚楚”。在《藏书室女尸之谜》中,马普尔小姐说过一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比较懂得人性”,那是老派人的人性观念,是经验主义的,可是很管用。
比如《命案目睹记》,马普尔小姐说:“我的一大优势是了解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埃尔斯佩思·麦克利卡迪太太不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所以,她说她看见了一桩谋杀案,那可能真的是发生了谋杀案。
比如,《藏书室女尸之谜》,班特里上校古色古香的书房里,躺着一具打扮花哨的女尸,形成一幅“不真实”的画面,而马普尔小姐看着女尸良久,轻声说:“她很年轻”,她注意的是那种个人性质的因素;在《寓所迷案》里,她世故地指出:“现实生活中,明显的就是真实的”;《迟来的报复》里,她又一次说:“犯罪的总是最明显的人”;而在《悬崖山庄奇案》里,尼克·巴克利小姐一次一次遭暗算,又一次一次化险为夷,最后却是她的表妹马吉·巴克利小姐被谋杀,大侦探波洛动用了好些“灰色细胞”,才总算明白这一个简朴的真理:“我看到实际上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马吉·巴克利被杀害了”!所以,不要小瞧了马普尔小姐的认识论,看起来,老是老了些,可并没有减弱说服力。
《藏书室女尸之谜》新星出版社
如果说,马普尔小姐包含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个别人事的理解,那么波洛则表现出阿加莎·克里斯蒂对事物的整体概念,他标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智力水平。
波洛不像马普尔小姐,是从具体性入手,而是从抽象着眼。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着相对于内部性质的外部形式,外部的变形,往往可能意味着内容的转化。中篇小说《死者的镜子》里,引他注意的是,自杀人的姿势多么“不舒服”,那么就是说,死者可能应和着另一种性质的死亡。
波洛特别讲究事物的排序,排序完成,真相就显现了。《尼罗河上的惨案》里,他说:“我们知道的很多,可是逻辑上没有连贯”,这就是说,排序出不来。在此,阿加莎·克里斯蒂体现出逻辑性极强的头脑,就像原始人陶罐上的雷电纹、鱼形纹,意味着有能力将具体的印象归纳概括成抽象的形态,思维发生了本质性的进步。
所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生动的人性情节底下,其实网络着一个图案形式,这个图案有序的变化,将具体的人性材料演变成种种形式。波洛喜欢将自己的推理形容为“拼图游戏”,在《阳光下的罪恶》里面,他向正玩着拼图游戏的加德纳夫人描绘他的劳动:“您得把所有的碎片拼接在一起。最后的成品像镶嵌画一样包含有多种颜色和图案,每一块奇形怪状的碎片都必须被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
有时候,会发生假象,就是说,有一块“按颜色本该属于毛毯的一部分,结果却被用来构成一只黑猫的尾巴”。事情常常是这样,波洛手里握着一块碎片,看起来似乎和整个事件并不相干,可就是这块碎片,“放入它自己的位置上”,真相就显现了。
比如,《清洁女工之死》里边,首先引起波洛注意的是,从来不写信的老妇人麦金蒂太太去买了一瓶墨水;《牌中牌》里,桥牌局中,罗伯茨医生莫名其妙地叫了“大满贯”;《哑证人》则是,小狗鲍勃一夜在外,它的玩具球却在楼梯上……
这块碎片,从事实上脱落,最终又回进事实,“终于各就各位”,复原了事实的全貌,依然是具象的生活。就好比一个关于拼图的小故事,小男孩拼一幅世界地图的拼图,他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拼成,却原来,他是反过来拼的,反面是父亲的照片。我想用这个故事证明的是,在逻辑形式的外部,还是表情活跃的人性面目。
在马普尔小姐主持的案件中,其实也隐匿着一个形式,不过她的形式更具有生活的状态,比如说“歌谣”——《黑麦传奇》中,马普尔小姐意识到这桩案子中藏着一个模式,就是那支歌谣:“唱个歌儿叫六便士,一口袋黑麦,二十四只黑画眉烘在一个馅饼里,馅饼一切开,鸟儿便歌唱,多美丽的一道佳肴献给国王尝!国王在账房数金币,王后在客厅吃面包涂蜂蜜,女仆在花园里晾衣,一只小鸟飞来,叼走了她的鼻。”这就是马普尔小姐所破译的犯罪模式,比较波洛的更有人的性格。
《赫尔克里的丰功伟绩》是一部故事集,共有十二个故事,可明显看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形式感。赫尔克里·波洛和万灵学院院士伯顿博士聊天,聊到名字的话题,伯顿博士的意思是给小孩子起名要当心,因为常常事与愿违,他认识一个以女神戴安娜名字命名的孩子,小小年纪体重已经达到二百四十磅。
波洛的名字“赫尔克里”与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同名,大力神是主神宙斯的孩子,以十二项丰功伟绩闻名。波洛要纠正伯顿博士的成见,为自己正名,决定挑选十二桩精品案件,每一桩都必须对应大力神的丰功伟绩。于是,就有了《涅墨亚狮子》《勒尔那九头蛇》《阿卡狄亚牝鹿》《厄律曼托斯野猪》等一共十二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有着相应的模式。
比如《赫思珀里得斯的金苹果》,在希腊神话中,是关于赫尔克里与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的一场斗争。赫尔克里接过阿特拉斯背上的苍天,让阿特拉斯去偷金苹果,阿特拉斯偷来金苹果后,却不愿再接回沉重的苍天,赫尔克里便施计让阿特拉斯重新负上苍天,自己拾起了金苹果。阿加莎·克里斯蒂将金苹果换成了金杯,这金杯除去有显赫的历史而外,本身也十分精致,上面雕了一棵苹果树,挂了绿宝石的苹果,在它从一名侯爵手中转向金融巨子的当口,被国际盗窃团伙掳走,最终,它当然被波洛找到了。
《阳光下的罪恶》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探案小说,在严格的抽象形式和生动的具体情景之上,又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神秘的别墅》里,新婚的格温达·里德要为他们的小家觅一处住宅,当她看见那一幢维多利亚式小别墅的时候,忽就认准这是她所要的房子,一切都令她熟悉和亲切,甚至是她可以想象的,这一点很快被可怕地证实了。她想象卧室里有一个壁橱,果然就有一个;她想象壁橱里应该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果真就是小罂粟花和矢车菊的糊墙纸……
再有,《命运之门》,托马斯·贝雷斯福特太太整理新居,在旧房主留下的藏书上发现有蓄意划下的字母,拼起来是一个完整的句子:“玛丽·乔丹并非自然死亡。凶手是我们中的一个,我想我知道是谁。”——这几乎有一些《呼啸山庄》的意思了。
还比如,《斯塔福特疑案》,玩灵桌游戏,召来名叫“艾达”的精灵,带来口信,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事实果然是,特里维廉上校被谋杀。这里透露出一股来自哥特小说的惊悚空气,决不会演变成《呼啸山庄》那样痛楚伤人的悲剧,而是正好到激起兴奋为限,表现出女性仁慈的性情。阿加莎·克里斯蒂也有着大多数女性都有的喜好,就是对神秘事物心向往之。
这大约来自于一种女性祖先的遗传,在足不出户的生活里,生出对世界又好奇又恐惧的幻想。那鬼魂与精灵大多活动在封闭的室内,带着家族的徽印和训诫,试图对种种现象作出道德说教。
《死亡之犬》中的十二个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马普尔小姐探案》这一本短篇集里,也有两篇灵异故事,其中一篇名叫《裁缝的洋娃娃》,不仅是神奇,而且非常动人。那一个洋娃娃,谁也不记得它是几时,又是如何来到了伦敦艾丽西亚·库姆小姐的裁缝铺子里,她躺在天鹅绒的椅子上,和房间里的家具摆设格调匹配,加上它那副懒散的态度,“看上去好像她才是这儿的主人”,裁缝铺子里的女人们感到了不自在。又是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它坐在了试衣间的书桌前,好像在写信。女人们都被它乱了心思,记性变得很差,总是找不到东西,也集中不了精神工作,清洁女工不愿意来打扫卫生,因为感到气氛古怪不祥。最后,它终于惹火了艾丽西亚·库姆小姐,她将它从窗口扔出去,扔到了马路上,被一个小姑娘拾走,小姑娘抱住洋娃娃说:“我告诉你们,我爱她,而这是它想要得到的,她想被人爱。”
这一个灵异故事里的惊悚意味被处理得相当微妙,顺便说一句,洋娃娃也是灵异小说里的重要道具之一,在此,它却一反以往,从邪恶中脱身,走入一个抒情的结局。
《马普尔小姐探案》中的另一篇灵异故事《神秘的镜子》,气氛要阴森一些,惊悚的效果更强烈,情节亦要复杂。它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我”宿在朋友家的客房,从镜子里窥见身后墙上洞开一扇门,门里正上演恐怖的一幕——朋友的美丽的妹妹西尔维亚,被一个男人扼住喉咙,男人左脸上有一道疤痕,使他看起来十分凶恶。“我”将这一幻象告诉了西尔维亚,于是,西尔维亚解除了婚约,因为她的未婚夫和镜子里的男人一样,左脸上有一道疤痕。后来,西尔维亚和“我”结了婚,可“我”其实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有一次,嫉妒心大发作,扼住了西尔维亚的脖子,就在这时,“我”从镜子里看见了多年前那个幻象,那个左脸有伤疤的男人正是“我”,因镜子反射的缘故,左脸上的伤疤实是在右脸,而“我”在战争中右脸被子弹划伤了。
这个恐怖故事的结局是,“我”震惊地松开手,认识到心中的“恶魔”,从此与妻子相谐相伴,永不相疑。神秘的预言最终成为道德的警示,及时挽回事态,使善心得到发扬。这大约也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教养,对邪恶有天然的忌讳,不忍看人难堪,尤其是体面的人,于是,尖锐的冲突便在她们的慈悲心肠下化险为夷。
《马普尔小姐探案全集》新星出版社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在经历了残酷的谋杀和慎思严行的侦破之后,总是将结局引向大团圆,用马普尔小姐在《平静小镇里的罪恶》里说的话,就是——“一切都以最好的方式有了结局”。凶手多半是天性卑鄙,犯罪是他们必然所为,受罚则天经地义,比如《古墓之谜》里,阴险的利德勒博士;《ABC谋杀案》里的富兰克林·克拉克先生;《云中奇案》的牙医诺曼·盖尔。或者就是微贱的人物,有他们没他们,世界都不会受影响,比如《H庄园里的一次午餐》里的罪犯霍普金斯护士;《葬礼之后》的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牌中牌》里的安妮·梅雷迪思小姐——她虽然不是本起谋杀案的罪犯,但却是个隐蔽的累犯,波洛曾经略施小计,对她进行测试,这个测试很有些安徒生《豌豆公主》的意思,就是让她帮助在高级丝袜里挑选几品送人,等她挑定,桌上的丝袜便少了两双——这合乎她的女伴出身,当然还有个人品行的缘故,所以就可以放心地让她犯罪了。
“女伴”,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生活的时代里,真是属于一个较低的阶层,《葬礼之后》里,女伴吉尔克里斯特小姐,为实现开一爿小茶馆的夙愿杀了人,人们甚至不惜残酷地寻吉尔克里斯特小姐开心,说她在监狱里已经精神错乱,正兴奋地筹划开茶馆,这一爿茶馆的名字叫“紫丁香丛”。而那些令人扼腕的罪犯,出身于好人家,有好身份,有着可以理解的犯罪原委,特别是女性,这样的故事往往是哀婉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总是让他们服用药物自杀,既可免于受审的羞辱,又怀有着一种自赎的姿态。例如《空幻之屋》里温良的妻子格尔达,爱她丈夫爱到膜拜;例如《哑证人》里,为让她的宝贝孩子过上好日子的母亲,塔尼奥斯夫人;比如,《悬崖山庄奇案》的企图谋取表妹财产以拯救家业的尼克·巴克利小姐;或者像《迟来的报复》,不幸的女明星玛丽娜·格雷格,是被爱她的拉德先生安排无痛苦地进入睡乡,长眠不醒;《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詹姆斯医生写完他的犯罪自述,准备服安眠药了,他最后写道:“安眠药?这是一种富有诗意的公正的处罚”;再有,《古宅迷踪》,弗利亚特太太庇护儿子的谋杀计划,为了夺回失去的纳塞庄园,那儿子从来是个坏料,没什么可说的,母亲却依然是这个光荣的古老家族的女儿,面对前来控罪的波洛,她沉着地说:“谢谢你亲自到这里来把这个情况告诉我。现在你就要离去了吧?有些事情,一个人是不得不独自前去承担的……”虽然没有明示何种惩罚,至少是让弗利亚特太太保持了尊严。
至于那些无辜受惊受磨难的人,阿加莎·克里斯蒂一定要给予补偿,这补偿基本是好婚姻和好出身,比如《云中奇案》中,纯真的格雷小姐,经由波洛撮合,与前途远大的考古学者让·杜邦开始了交往;《怪钟疑案》的希拉小姐,最终证明了她诞生于合法婚姻,父母都是可尊敬的国家政要部门人员,自己也与高层特工科林先生缔结良缘。
这里确有一些偏见,但还有着对人生的现实态度,就像《简·爱》,简·爱最后得了一份小小的遗产,然后再去和罗契斯特相守,即便是两心相倾的爱情,还是需要有尽可能相等的条件,才可保证完美。
显然,那时代的人不喜欢过分的偏离常规,什么都要恰如其分,总之,不能太离谱了。这在《H庄园里的一次午餐》中可以见得,H庄园的老仆人杰勒德的养女玛丽,深得女主人韦尔曼太太的照料,原来她是韦尔曼太太的私生女,波洛揣测道:“毫无疑问,她要适当地关照玛丽·杰勒德,可是不会把所有的家产全留给玛丽。她希望自己的私生女最好还是生活在上流社会圈子之外。”这种保守主义并不负责进行社会批判,但它诚实的表达,使这些故事都有了一种温文尔雅的态度。
阿加莎·克里斯蒂
本文节选自
《王安忆自选集》
作者: 王安忆
出版社: 天地出版社
出版年: 2017-6-1
编辑 | 芬尼根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