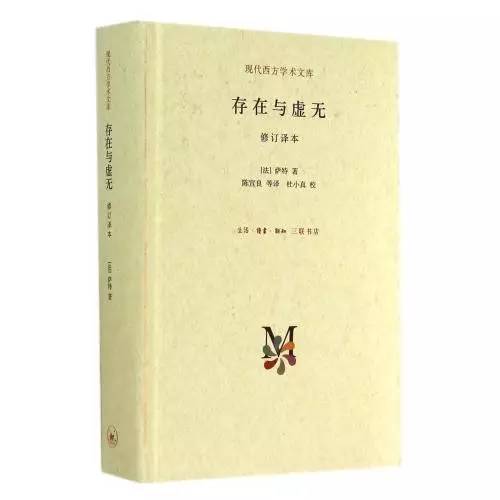人人腋下夹一本萨特的时代过去了|萨特去世40周年


独家抢先看
今天,也就是4月15日,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萨特离世40周年的纪念日。
萨特(Jean-Paul Sartre),法国20世纪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评论家。对中国读者来说,萨特的名字不陌生;相较于雷蒙·阿隆、阿尔贝·加缪等同期的法国哲学家,我们对萨特也更熟悉。但今天的年轻读者,对萨特的认识更多的是来源于他与波伏娃那段长达51年的“爱情契约”,以及拒绝了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但在这些简单的标签之外,对于萨特的哲学思想与理论发展脉络,大多不甚清晰。
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著名法语文学研究者、翻译家袁筱一写萨特的文章。袁筱一笔下的萨特有着一副更复杂、更微妙的面孔。从张爱玲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再到萨特的“他人即地狱”,随着袁筱一教授的思路,我们能够看到70年代到80年代再到当今一代的学人们,都在阅读什么,思考什么,又被什么塑造着。
存在着,仅此而已
文|袁筱一
到了萨特的一百周年,突然间听到了一些关于萨特的声音。感觉像是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又被人挖出来说,瞧,他还没有过时,萨特的世纪仍然没有过去。可是真的没有过去吗?走进书店,发现萨特的身影其实已经变得很淡薄,被淹没在色彩缤纷的图书的春天里。我买到的几本都很旧,一本是他的文论选,另外一套是上下册的《辩证理性批判》。同样哲学社科的书架上,轰轰烈烈地卖着后现代,卖着解构主义和诠释解构的林林总总。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与遗忘抗争,也许大多数人的结果都是如此。他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焦虑,自己的书到了下个世纪是不是还有人理会。他知道生命有限,即便介入过当时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冷战问题,即便介入过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事情终究还是过去了,而且在走进历史的时候,作为事件,几乎不会出现他的存在。那么,他的存在消失了之后,应该用哪种形式、又是铭刻在哪里?他焦急地寻找着答案,在他的有生之年。尽管如今尘土相隔,相信他在彼岸也还焦虑着:焦虑着这一代人的精神状态是否还和他有这千丝万缕的联系。焦虑着,身处彼世,如何在此世体现他的在场。
这一点,我称之为萨特的责任心。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啊,昏迷的时候,还努力地抗争着,生怕离开,这个世界的精神层面会大乱。他一定是在想,他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再给他一段生命,他还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的介入。
萨特与他标志性的烟斗
是最近,在看萨特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跨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并不陌生,但是,我清晰地知道这不是我的世界。这种跨入是有点心悸的:试图捋顺一种明知不属于你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极强的破坏力,以一种别样的光线遮覆你的双眼,于是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只能看到在强烈的光线中有点变形的自己。
就这样,在萨特之镜里,我看到了自己,而且我在问,这个自己,是怎么形成的?再次读了一些萨特的作品之后,我一直在想,倘若撇除我作为一个法国文学追随者和研究者的存在,我,我这一代人,为什么不读萨特,我们读的又是谁?
对于萨特,再次阅读之后,也没有认同,只有艳羡。艳羡他可以这样强烈地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愿望;艳羡他可以产生这样强烈的愿望想要收复这个世界。艳羡他不仅善于思考,而且,他的思考有着明确的目标。这是萨特有别于前人的地方。那么他有别于后人的地方呢?
从我们这一代人读的书说起吧。我们读的是谁?我几乎想不起我在大学里读过萨特。我读的是张爱玲,读的是杜拉斯,读的是昆德拉。这应该是出版界奉献给第一代多识了几个字的小资的读物吧。迥然不同的作家,张爱玲奉献了个人世界,杜拉斯奉献了自虐性的变态世界,昆德拉奉献了——因为是个承受过苦难的男性的缘故——小说的世界,但他们却有致命的相同点:让人绝望,让人只能想到,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要撇清和这个世界的纠缠。那个时候,对于这几个作家的追逐,真的有点像是我的那位哲学老师张一兵教授描写他们那个年代对于萨特的追逐:人人以腋下夹着一本萨特为荣,人人以谈论萨特的一两句“他人即地狱”为荣。
米兰昆德拉代表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以至于到了今天,当像我这样的第一代小资跨过三十岁,迈向四十岁的时候,出版界的市场经济突然意识到可以利用他们的怀旧和他们日渐丰满的口袋,于是重新炒了一遍昆德拉,据说,又将重新炒一遍杜拉斯。至于萨特,他是五十岁人的模糊记忆和少数爱钻牛角尖的人的标语读本,没有市场的价值吧。
处在怎样的时代,为自己贴上什么样的标签,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这重要性不仅仅针对出版而言。想起自己,尽管也许和七十年代末大学生读萨特一样,不是那么了解张爱玲、杜拉斯和昆德拉,甚至没有理由喜欢他们,可是,这个符号贴上去,就不是那么容易揭下来。这个符号几乎成为三个人的三句话,经常出现在我或是我的其他同辈人的笔下:张爱玲说,人生是袭华美的袍,里面爬满了虱子;杜拉斯说:我们爱的是爱情本身;昆德拉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把这三句话和“他人即地狱”并列在一起看,真是有着相映成趣的功效。
我的大学时光,是躲在宿舍里,逃哲学课(而且那时我称哲学课为政治课,后来遭到了哲学老师的严厉批判)和一切自认为无用的课,向往成名、渴望被重视、却害怕崇高和承担因此而来的责任的日子。——这基本上是第一代小资的生活写照,还没有星巴克,还没有村上春树,只有简陋的宿舍和纸质粗糙,印得颠三倒四的书,可是,在张爱玲、杜拉斯和昆德拉的激励下,慵懒而百无聊赖的小资特征正在慢慢形成。然后,大学之后的时光也这么过去了,一不小心就是十多年,无从改变。生活还是没有教会担当,每当面对责任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总是逃跑。
有时看着看着萨特,我就会想,我的上一代人,他们是不是被贴上了萨特的标签?如果用萨特的责任心去看他们,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得到理解。相信他们站在张爱玲、杜拉斯或是昆德拉的立场看我们,我们的无所作为也相应容易理解得多。其实,有很多脑力的游戏,与体制无关,与意识形态无关,仅仅是与这个时代有关。仅仅是和这个时代所贴的知识分子的标签有关。
萨特代表作《存在与虚无》
以前读萨特的时候,一直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能写出《墙》,写出《恶心》、《词语》,写出《脏手》的他要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样连他自己都可能不知所云的东西?且不论对《辩证理性批判》进行怎样的解读(除了译者,几乎没有一个攻读法语语言文学的人能把这本书读下去),有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那就是,在《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上,作为一个调弄文字的高手,他是失败的。
他不是不明白自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因此他退了一步说:“我不喜欢谈论存在主义。研究工作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把研究的名称说出来、确定下来,就是把一个链环的首尾扣上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是一种完成的、已经过时的文化形式,就像肥皂商标那样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一种理念。”——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和文学的差别就在这里。一个是依靠体系的建立关上一扇门,一个是完成文本后开启另一扇门。可是问题在于:既然他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做呢?
奇怪地是,必需解剖了自己,才可以慢慢地感觉到,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问了自己:马克思主义建立以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建立以后,二十世纪还有他的什么事?文学是个备选的答案,但是不甘心啊,不甘心仅有文学,不甘心文学里的那种寂寞。文学可以完成他身后那一代小资的梦想,却不能完成他的。他喜欢的布朗肖说,作品——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存在着。存在,仅此而已。
萨特要的,当然不仅是存在而已。萨特的矛盾有目共睹,他一方面在消弭上帝、消弭对人的规定——即所谓的人性,同时却孜孜不倦、冒着文字的危险想一个问题:他所创立的那个肥皂商标一样的理念是否能够成为先于时代的规定?这是他毫不犹豫地跨进《辩证理性批判》的原因:尽管他不怎么“愿意谈论存在主义”,但是他意识到,如果不承认他为始作俑者的这张标签,一个世纪以后,也许他真的将失去他的在场,永远而彻底。
他应该是在当时左右思想界的两大基本观念里徘徊过的: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主义。但是显然,在他看来,弗洛伊德太个体化。或许,性的问题拿来做个人爱好还马马虎虎。萨特对性不是没有爱好。据说他跑到日本去,见了他喜欢的已故作家谷崎润一郎的夫人,好奇地问她,谷崎是否会将书中的性描写实践于生活之中。可是,爱好归爱好,他想必是认为这样个体化途径太不适用于历史在他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所呈现给他的局面。再说,弗洛伊德在法国有继承人了呀,而且这些继承人,也几乎覆盖了人文的各个领域。
所以他踏入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谈论他的存在主义,怎么着也要将这块补丁缝上去。至少,如果马克思主义延续了一个又一个世纪,那么一个世纪后,就不可能完全将他撇开。这一点,我们在张一兵教授的《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里已经看到:在众多身处现代语境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中,萨特赫然在目。萨特本人在《辩证理性批判》的一开始就定了调子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被超越”。而且,他引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加罗姆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个“坐标系统,只有这个系统才能对从政治经济学到伦理学、从历史学到地理学的任何一个领域中的任一种思想进行定位和定性”。难道我们还能怀疑,这种定位和定性,不是他所企求的东西吗?既然没有办法创立这一个坐标系统,哪怕附着,也是好的。和二十世纪的很多同辈人一样,萨特的责任心造就了他的野心、勇气和担当。
是啊,文学和弗洛伊德的学说一样,尽管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却太容易被消解为个体的体验。后人因而可以说,萨特只有一个,他是个怪物。他的想法不具有任何的普遍性可言。因此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拒绝这个带有太多承认个体天赋色彩的奖项。他想,最大的奖项应该是一个世纪之后,十个世纪之后,他的书还有人看,他的口号还有人引用,或者,能够有人记得他在二十世纪的卓越风采也好——哪怕语言已经变迁,至少,他的灵魂还能不死。所以,文学只是一个辅助的手段,可以帮助他灵魂不死。而他意欲借助《辩证理性批判》所切入的,是人类思考的方法论。
年轻时代的萨特
作为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辩证是一种方法,暂时缓解了二元对立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很多哲人一样,萨特无疑从一开始就野心勃勃地想要消弭二元对立的。因此,他像发现至宝一样扒拉出胡塞尔的现象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因此,他充分挖掘了主体这个概念后,又踏进马克思主义里,野心勃勃地想要实现向客体哲学的转变。可是,痛苦只是得到暂时的延搁而已。仅凭一句“存在先于一切”就万事大吉了吗?仅凭他的所谓自由、责任就能够无视痛苦了吗?我们能够看得见萨特在政治领域的实践,似乎也有模糊截然的二元对立的企图。他想求助于一种绝对的存在。可事实是,存在着,并且仍然二元对立着,因此,仍然感觉身后的痛苦隐隐地威胁着。
回到小资的我们这一代,在萨特的照耀下。我想说的是,绕了这样一个圈子再回头去看我们曾经读过的张爱玲、杜拉斯或是昆德拉,你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从未曾想过要消弭二元对立,并且,他们无限地夸大了这种对立。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不重要,他们承担的,是用文学的方式消解前人种种关于消弭二元对立的努力,将这古老的命题再次夸张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轻与重,水与火,背叛与忠诚,主体与客体,等等等等。在张爱玲的上海人家的炊烟中,在杜拉斯的太平洋堤坝的殖民色彩中,在昆德拉面对所谓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尖锐笑声中,我们喜欢看见自己满含眼泪地站在十字路口,问经过的人:往左走,还是往右走?
当这个世界呈现出纷繁的选择时,你竟然发现,其实所谓的多元,只是由无数个二元组成的多元。多元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带来的只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的痛苦。难怪萨特会说,自由只有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成其为自由。
难怪我们推卸责任,嘲笑崇高,消解悲剧。
难怪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会这样迷恋“悖论”这个词。其实,它只是二元对立的文学形式,文学形式,或者可以说,抒情形式。难怪我也像我青年时代迷恋的这些作家一样,觉得自己只需要提出问题,而不需要解决问题。
二战时期的萨特与波伏瓦
借口很简单,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不需要在萨特的世纪过去之后,代替他接过西西弗斯的石头,壮烈地推到山顶,再看着它轰隆隆地滚下山去。昆德拉跳出来安慰我说,这只是人类臆想和伪装的崇高。
像特雷莎一样,坐着树脂涂覆的草筐顺水漂去,被人在床榻之岸捞起,是怎样一个不着边际的小资的梦想啊。小资的梦想:痛苦,并且美丽。在这个梦想里,终于可以卸下对自己的责任,终于可以把自己的自由交付给命运,听凭历史的处置。
终于可以交出自己的主体性。终于不用理会爱、恨、冷漠这些人类情感的幻觉。因为在这个时代,适时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作家告诉我们,如果爱,如果恨,如果冷漠,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甚至,爱谁,恨谁,冷淡谁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机械地重复着这些行为,仿佛是在华美的生命之袍里捉了一只又一只的虱子;仿佛是托马斯生命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
只是我们依然痛苦。我们从此处逃往彼处,回头去看,却发现彼处已经成为此处,而此处,成了永远的彼处——终究是回不去了。爱是如此,祖国如此,生命如此。我们探讨过的存在问题,莫不如此。这就是辨证的道理啊。它们只有在相互转化的过程中才不再对立。因为辨证要说的是,水与火,轻与重,爱与恨,背叛与忠诚,这些不是两个彼此对立的事物,而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可是,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理想的支撑,束手无策地明白这个道理,又有什么意思呢?
可我们这一代人(我想我们的下一代人也许不会),有时候还是禁不住会想:什么时候丢失了理想的重负呢?当初只知道和其他一切被贴上崇高标签的东西一起甩掉,但是,没有了这重负,尽管生命不再因为悲壮而显得可笑,却真的是无法确定自己的位置。当自己推诿说,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时候,当自己说,人类的命运不在我的身上的时候,自己真的做到像特雷莎那样,在街头倒下去,低得比尘世还低了吗?
如果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出逃?出逃的命运总是如此被动。我们被什么追着而不得不出逃?萨特说,要与人世间的大事件抗争。要通过主体性看清大事件,左右大事件,从而左右历史。但是我们曾经痴迷的这些人都说不是。硝烟中,张爱玲追胡兰成追到温州,瓦解爱情的分明不是“死生契阔”;杜拉斯在渡船上的那个形象,也分明不是殖民造就的悲剧;还有昆德拉,他也分明在说,回不去了,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问题。
无所抗争。如果萨特还在,很想告诉他,无所抗争,无所介入。追着我们,令我们出逃的,或许正是对这份存在的不认可的虚无。
而身在彼世,萨特还能在此世体现在场吗?他的责任心足以让他否认任何先验的存在,否认对于“人性”的种种规定,以直接存在的方式介入今天的存在吗?
或许回答真的是这句话:作品存在着,仅此而已。人也是,存在着,仅此而已。而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也将有自己的标签,他们在他们的青年时代所读的书会带给他们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到了那个时代,萨特的在场仍将通过文字,存在着。不过也只是仅此而已。
他作为标签的责任心,也许可以放下了吧。与今世具体而微的时光脱了干系。至少中国的出版界也许是这么想的。文字可以跨越空间,但是跨越时间的问题,除了以单纯的存在相证明,剩下的,文字无能为力。
《我目光下的你》
作者:袁筱一
版本:黄山书社 2009年版
本文选自《我目光下的你》,作者袁筱一,经作者授权发布。编辑:走走
“特别声明:以上作品内容(包括在内的视频、图片或音频)为凤凰网旗下自媒体平台“大风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videos, pictures and audi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the user of Dafeng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mere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s.”